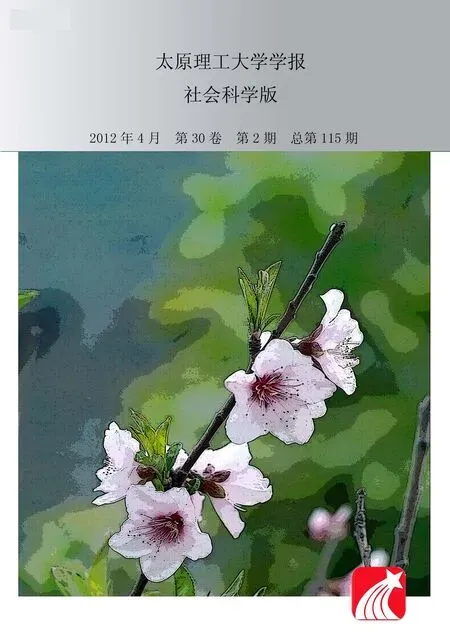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1
柳英英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一、古文运动兴起的原因
唐代科举制度中最受瞩目的是注重文学的进士,这不仅因为个别皇帝对文学的偏爱,更是因为翰林学士政治地位的提高。奏章的撰写、政令的颁布都需要文学修养良好的官员来担当,善于行文的翰林学士往往代行宰相之职。因此每年的进士科考备受关注,及第后有一系列的宴会、拜谒、题名等活动,新科的进士当然是人们眼中最闪亮的明星。
民间对文学的推崇更是到了顶礼膜拜甚至神圣化的地步。有些著名的文人被雕像供奉,有些文学作品的内容也被看做某种预言,能否写出好的文学作品甚至被人看做某种因果报应。种种现象表明人们已经把文学看做某种神圣的东西。文人则是能把文字变为文学,赋予文字以神圣生命力的人,因而文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神圣起来。读书人为了能够获得这种神圣的地位吟诗作句,希望得到在位者或有识之士的欣赏而获得文人的地位,希望通过科举考中进士以证明自己是文人中的佼佼者。对科举进士的崇拜和文学崇拜形成了一种相互激励的机制。在这种神圣崇拜的眼光下,文人们渐渐迷失自我,相互标榜或相互排挤,抄袭、剽窃,为取得功名奔走权门、积极拜谒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科举演变成为一种文学选拔活动,文学也日益虚化浮夸,唐代士风日坏。
当时文人呕心沥血所作的文章辞藻华丽,内容空洞。那些心高气傲、自命不凡的文人大多仅有吟诗作句这一技之长,不通事务,用龚鹏程先生的话说:“他们的世界就是文字所构筑的宇宙,他们的生命则流遁于此一宇宙之中,俯仰歌哭,发引性灵。感性生命之发舒,固然极为淋漓酣畅,理性化的态度却明显地不足。”[1]文人这种不理性到中唐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有些文人看来,文学甚至仅仅是某种形式,与现实无关。文学批判之风逐渐兴起,文人开始对文学本身思考:文学既然是神圣的,那就应该向人们揭示真理,应该发挥其对社会、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利国利民。很自然地“文”与“道”联系起来了,抛开骈体文的华丽、回到古文的朴实之呼声也越来越高。一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呼之欲出,这场运动的两位主将便是韩愈和柳宗元。
二、韩愈的“不平则鸣”
作为一名生活在当时的中下层文人,韩愈也不得不选择通过学文、考科举这条路走上仕途。他一方面对当时吏部的博学宏辞的考试不满,对于文人积极于功利表示批评;一方面也无可奈何被迫写一些应时的文章,并因此而惭愧。进士及第后需经吏部考核才得授官,在众多考核中最受重视的便是博学宏辞。博学宏辞科注重的是文词的华美。韩愈批评所谓的博学宏辞 “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杨雄之徒进于是选,仆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设使与夫今之善进取者竞于蒙昧之中,仆必知其辱焉”[2]。他批评积极求售的文人“求禄利、行道于此世,而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无与操瑟立齐门者比欤”[2]。可是为了养家糊口,韩愈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作一些浮华之文应付博学宏辞的考试,“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2]。
“不平则鸣”是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的观点。“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其于人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之以鸣。夔不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杨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鸣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明其善鸣者也?……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2]
韩愈的“不平则鸣”思想有三点需要讨论。第一,“不平”的含义。有的学者认为不平有两种含义:一种是“鸣国家之盛”[3]和“自鸣其不幸”;另一种是“不平”并非是内心的“不平静”,实际上是一种“愤懑愁苦之情”,在《送孟东野序》中则为后者[4]。“鸣国家之盛”只是其鸣的一个方面,夔之鸣,周公、伊尹之鸣,李斯之鸣,皆是此类。但是当时的唐朝并非兴盛,藩镇格局、边境危机、宦官当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韩愈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如他在《答崔立之书》中提到:“方今天下风俗尚有未及于古者,边境尚有被甲执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为忧。”[2]而像孔子、屈原等人之鸣则鸣国家之衰,鸣自己为国之志不得行,而非只是为个人情绪的发泄。比较重视自我情感的魏晋之文风则受到韩愈的批评,指出:“就其善鸣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从以上的分析中可见韩愈并非只为个人的愤懑愁苦而鸣,更为看重的是国家的兴衰,鸣国家之兴,鸣国家之衰,体现了儒家勇于担当的精神。
第二,所鸣之器为文章。在这里韩愈提到的有三种“鸣”之器。第一种就是以建立事功为鸣,如:咎陶、禹、李斯;第二种是以创立学说、立言撰文等为鸣,如:孔子、屈原、墨翟、老聃、司马迁、司马相如等;或者是此两种兼有;第三种是比较特殊的,如夔以《韶》乐鸣。历来儒家所强调的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是:立德、立功、立言。韩愈所谓的“鸣”者正是指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而在此篇中他所强调的是立言,也就是为文,著书立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其于人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文章无疑是善鸣之器。他的这种观点在另一篇文章《后汉三贤赞》中也有所表露。《后汉三贤赞》所赞的三贤是王充、王符和仲长统,这三位人物的共同特点是都曾著书立说,前两位更是终身未仕。可见韩愈对为文是颇为重视的,尤其是在那个重文的社会风气中。
第三,所鸣者为古道。以上两点已经分析了“鸣”之音和“鸣”之器,那所“鸣”的内容是什么呢?虽然仅仅从《送孟东野序》一文中难以知晓,但从韩愈的其他文章多次提及自己所崇信的是古道。在《答尉迟生书》中提到,“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2]。在《题(欧阳詹)哀辞后》中提到,“苟爱吾文,必求其义,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2]。在《答李图南秀才书》中提到,“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2]。在《答陈生师锡书》中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2]。在韩愈看来,正是因为古文是古道的载体,自己才欣赏古文、提倡古文,究其根本其最为重视蕴涵于古文中的古道。“古”是相对于今而言的,陈若水曾经指出,“韩愈的‘古’,就是佛、道以前的世界,一个以人伦价值为唯一准绳的秩序”[5],这种看法颇有道理。韩愈在解释“道”的时候,指出自己的“道”既非佛又非道,而是尧、舜、周公、孔子、孟子的行仁义之道。
韩愈所提倡的“不平则鸣”的为文观点,实际上是在呼吁儒学传统的恢复。“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如何才能使文章充实起来,在韩愈看来就是儒家的道的仁义。在他谈到自己为文的过程中,多次强调的是颂尧舜之道,遵六经之旨,读圣人之书。他提出为文不能急功近利,要谨遵圣人之旨,读三代两汉之书,提高个人的道德品行修养,否则为文便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空有虚华的外表。
古文运动并非一场简单的古文复兴运动,而是一场以文为载体的儒学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韩愈冲到了最前方,他提出“不平则鸣”,要求为文者用儒家的眼光,面对社会现实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而非在骈体的华丽辞藻中无病呻吟。石介对韩愈在倡导古文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作了高度评价:“唐之初,承陈、隋剥乱之后,余人薄俗,尚染齐、梁流风,文体卑弱,气质最脞,犹未足以鼓舞万物,声明六合。……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学独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云和》,千数百年希阔泯灭已亡之曲,独唱于万千人间。”[6]韩愈多次提出重古道,重古文,却没有明确提出文与道的关系,明确提出文与道之间关系的则是古文运动的另一位领导者柳宗元。
三、柳宗元的“文以明道”
柳宗元是较早提出“文以明道”的人。柳宗元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提出:“诚有意乎圣人之言。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7]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又曰:“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7]柳宗元认为文的作用就是明道,圣人著书立说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对道的阐释、传播和传承。因此评价一篇文章的优劣,关键不在于其文辞而在于其所传之道。柳宗元对当时虚浮的文风提出严厉的批评:“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7],认为这类只重文辞的做法,根本没有领会到为文的实质,并且造成恶劣的后果,“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7]柳宗元在批评时文的时候也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年轻时也没有明白做文章的真实意义,以“好辞工书”、“务采色”、“夸声音”以为能。
柳宗元在强调以“道”为本的基础上,也肯定了文辞的重要性。没有思想内容的文章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但是空有一番道理,表达拙劣也是令人缺憾的。韩愈倡导写古文,行古道,但其并非不工文辞。苏洵评价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鳖蛟龙,万怪惶惑”[6]。黄子云认为韩愈的文章写得好是因为他“无句不琢”又善于“炼气”[6]。韩愈提出,写好文章要炼气,但并没有详细论述文与道的关系。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提出,在坚持“明道”的基础上,文章的文采也很重要,“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喻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7]。一篇传“道”之文,如果文辞优美,对“道”的传播、对启迪人们的思想影响更大。柳宗元的观点是以“道”为体,以“文”为用,文以明道,文章的文采最终服务于它所承载的道理。
柳宗元所说的“道”的有三个特点。第一,推尊儒家经典,突破汉唐的注疏之学。“理不一断于古书老生,直趣尧、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难有也。”[7]儒家的“道”并非在汉唐诸子的注疏中,因此柳宗元指出欲得儒家之道一定要从儒家经典本身探寻。“本之《书》以求其志,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7]柳宗元所倡之道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儒为本,兼采数家。与韩愈的道不同,柳宗元的“道”突破了儒家的限制。韩愈在《原道》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2]。而柳宗元的“道”并未局限于儒家思想内,在熟知儒家经典和儒家圣贤的理论同时,为文明道还要“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7],并且还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7]。柳宗元认为“道”并非儒学专有,也蕴含于其他学说中,因此对佛、道等都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然而他的这种兼容并包的思想却遭到了后世儒学家的批判。朱熹对韩、柳二人文章的评价说:“韩不用科段,直便说起去至终篇,自然纯粹成篇,无破绽”,“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批评柳宗元“反助释氏之说”,因此他提倡读二人文章要先读韩文,如果先看柳文“便自坏了,如何更看韩文”[8]。柳宗元所倡之“道”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施道于物。柳宗元认为“道”的层次不能仅仅停留在从经典中获得其含义或者通过写文章向其他人阐释其理论的层次上,而是要用于现实生活中,要对个人、对社会发挥实质性的作用。“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7],在柳宗元看来,把从经典之中学来的“道”用于致君尧舜、仁民爱物才是“道”的最终宗旨,也只有如此才能“不负孔子之笔舌”[7]。
开始于八世纪中期的古文运动,并非一场简单的由古代散文取代骈体文的文学复古运动,而是以文人推动的以文学带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变革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韩愈和柳宗元互相支持、互相呼应,为打击浮华的骈体,恢复古体散文的传统作出了努力。韩愈提倡“不平则鸣”,要求写文章要应世而鸣,要言之有物,不能图有虚表;柳宗元则更进一步的提出“文以明道”,要求文章要以“道”为根本宗旨。韩愈强调独尊儒学,以六经为宗;柳宗元则以儒为主,辅以诸子,兼涉佛道。虽然二人在对“道”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但是在打击骈体文,提倡古文,尊崇流经,恢复儒学传统的观点上是一致的。他们二人的思想也影响了宋代文学家和思想家:一方面出入佛老,兼通三教;另一方面,排击佛老,独尊儒术。
参考文献:
[1] 龚鹏程.唐代思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46.
[2] 韩 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687,880,687,982-983,687-688,607-608,1296,725,731,4.
[3] 唐晓敏.重论韩愈的“不平则鸣”——评钱钟书的一个观点[J].绥化师专学报,2003(3):11-13.
[4] 陈智富,卢 欢.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新论[J].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06(3):29-32.
[5] 陈若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1.
[6] 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91-92,117,1152.
[7] 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886,873,886,829-830,578-589,789,873,873,673,886,660.
[8] 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4:12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