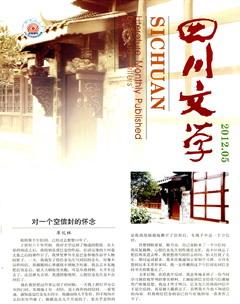芭蕉夜雨
何文君
搬到新居是国庆之后,时维九月,序属三秋。白天,小阳春的太阳暖暖地烤着原本阴冷的盆地,以及盆地里这座高楼大厦起起伏伏的城市。全城的人似乎都在享受着这稍纵即逝的美好时光:府南河——这是那条绕着成都划了大半个圈的河流的俗名,其实,它正式的学名要好听得多,它叫锦江——河畔的露天茶园里,到处挤满了懒洋洋的人群,他们或品茗闲谈,或闭目假寐,金子般的阳光慷慨地洒满大地,他们便像淋浴在海浪中的一尾尾兴奋的鱼。
这样的秋天无疑是美好而深刻的,可惜它太短暂,短暂得每年大概不超过两个星期。仅仅半个月——或者才十天,曾经温暖动人得如同冬天里的大火炉的太阳不见了,即便偶尔在天上露个脸,也是一脸冷寂。更糟糕的是夜晚。天黑得更早了,夏天里八点钟天才擦黑,而现在,六点刚过,大大小小的窗户便亮起了一盏盏橘红色的灯。夜晚,原本阴沉的天空忽然下起了雨。雨裹着风,风挟着雨,让人忍不住打了个长长的寒噤。夜深了,躲进厚厚的被子,刚感觉到了一丝暖意,可是,窗口忽然传来了紧一阵慢一阵的声音,那声音,曾经让千百年来的才子佳人为之断肠,为之销魂,为之相思,为之长吟,也让我披衣独坐,独自陷入深长的回忆。
那声音,便是雨打芭蕉。
搬家那天,我便意外地看见了主卧外面花园里那丛生长得碧绿油亮的芭蕉。之所以说有些意外,是因为现在的所谓高档社区里,绿化大抵都是移栽的有上百年历史的大树。具体说到成都,银杏之类的珍贵树种往往是首选。我住的这个小区,就有不少双臂合抱也围不上的银杏,但就在众多的名木古树中间,偏偏有那么一丛芭蕉,而这丛芭蕉,偏偏就选择了安家在我的窗前。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
在中国,芭蕉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植物,更是背负了无数中国人情感寄托的隐喻之物。打开厚厚的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古典诗词,我们轻易就能发现历代文人墨客对它的关注与寄托:“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这是白居易的芭蕉;“芭蕉为雨移,故向窗前种”——这是杜牧的芭蕉;“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这是李煜的芭蕉;“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这是李清照的芭蕉,“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是蒋捷的芭蕉……如果我愿意,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诗词里的芭蕉继续延伸下去。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诸种植物之中,芭蕉大概是最为文人喜爱的一种。而文人对它的喜爱,竟然是它最能引起人的離愁别绪——在那种万籁俱静的夜晚,难道还有比疏密有致的冷雨,打在宽阔的芭蕉叶上发出的悠长而又清脆的声音更能勾起人类因为季节变幻而联想起自己如同浮萍般的身世,以及心上的人儿在远方,事业和家山也在远方的无边无际的忧郁和感伤吗?
我曾经非常喜欢丰子恺笔下的芭蕉,寥寥数笔,却画出了一种闲散淡定的心境。不过,丰子恺画的不是夜雨,尤其不是秋雨打击之下的芭蕉,因此才有那么一番优雅暗含其中。对芭蕉夜雨引发的无端愁绪与惆怅,描绘得最为到位的,其实是宋朝诗人杨万里,他写道:“芭蕉得雨更欣然,终夜作声清更妍,细声巧学蝇触纸,大声铿若山落泉。三点五点俱可听,万簌不生秋夕静,芭蕉自喜人自愁,不如西风收却雨更休。”从科学上讲,秋雨中的芭蕉之所以容易引发聆听者的愁思,可能和芭蕉的叶子宽大厚实有关,当淅沥的秋雨打在芭蕉叶上,空寂宁静的夜里,声音便显得格外清脆浑厚。而声音的大小,雨量的疏密,则给聆听者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历朝历代,芭蕉和文人雅士们结下了不解的缘分。最为人津津乐道者,可能首推大书法家怀素。怀素是个和尚,因为穷困,无力购买用于习字的纸张,只能另想办法——他想出的办法就是向芭蕉要“纸”:怀素在寺院旁种了浩浩荡荡的万余株芭蕉,没有去过寺院的人,若是没人引路,竟然会在芭蕉的丛林里迷路。芭蕉叶子长大后,怀素便裁下叶片铺于桌上,遍临历代大家书帖。练字入魔,不分昼夜,万余株芭蕉叶片的生长,竟然不及他的书写速度。后来,怀素干脆揣上笔墨,信步走到芭蕉树前,长一片,写一片,不久,芭蕉丛中,竟然废笔成冢。这个故事的真伪虽然没有人去用心的考证过,但怀素曾在他的自述里提及,想必是真实的。少年时,当我偶然从老师那里听来这个故事,似乎一下子触类旁通——就在我家的院子里,也有一丛肥大的芭蕉。于是乎,我也学着想象中的怀素的样子,用一把剪刀将芭蕉叶剪下来,铺在吃饭的八仙桌上,装模作样地在上面写字。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是,芭蕉太绿而水太清,上面的字迹总是若有若无,以至于练习两三次之后,我便大失所望,终止了这个学习古人的游戏。
少年时老家庭院中的那丛芭蕉,每逢秋雨之夜,自然也会淅沥到天明,不过,那时候它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愁绪和忧思——一则,我还不具备后来的阅读所带来的文化准备,因为由雨打芭蕉便想到离别的,必然是那些受过古文学熏陶的读书人,倘在一个文盲那里,即便把他关在一万亩的芭蕉园,天天用秋雨打芭蕉,他也未必会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二则,年少贪睡,脑袋一挨上枕头便睡着了,任它窗外是雨打芭蕉还是风拍茅屋,均一概不知不闻了。
让我对芭蕉真正产生审美或者说精神层面的注意力的,是另一个关于芭蕉的故事:故事和清朝著名文人、堪称生活家的李渔有关。李渔在他的书里讲,他有一个心爱的小妾,名叫秋芙,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诗书画俱工,并兼善解人意,总之是万里挑一的一流人物。两人在典雅的江南园林里,过着琴棋书画的优雅生活。秋芙在窗外的庭院里,种了不少芭蕉。秋夜,雨打芭蕉,快乐如神仙的李渔也勾起了片片愁思。他睡不着,裁剪下一片芭蕉叶,在上面写了两句诗: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第二天,他发现秋芙在他的诗句后面添了两句,道是: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后来,秋芙患上了肺病,这在那个抗生素还没影儿的年头,无疑就是注定走投无路的绝症。果然,秋芙以青春年华夭折,从那以后,每逢听到雨打芭蕉,李渔便难以压抑心中的那份悲怆与伤感。这个有几分小资情调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少年时的我。正如歌德说的那样,谁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在那个可能会为了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微笑而枉抛心力的年代,在那个自以为所有诺言都像金属一样质地坚硬的时代,我对班上的一个女生有着一种朦胧的好感。非常巧合的是,她的让我喊起来就要面热心跳的名字中,也有一个秋字。她让我无法抵抗地联想起了李渔笔下善解人意而又聪明若斯的秋芙。只不过,她比秋芙更健康,常年在运动场上奔跑,她看上去不是那种病兮兮的古典美人,而像一头又年轻又骄傲的小鹿。在这头小鹿的矜持之前,我的相思注定只能是在五步以外,注定只能是“心悦君兮君不知。”而想念她时,我常常伫立在我家院子中的那丛芭蕉树下。那时候,离我用芭蕉叶写字已经过去两年了,我长高了长壮了,芭蕉树也长高了长壮了,把大半个窗户都遮得严严实实。一次,母亲在饭桌上抱怨,说那芭蕉挡住了太多的阳光,又招蚊子,而且没什么用,不如把它砍了。父亲正要响应,我却站起身来极力反对,一向在父母面前温顺的我,为了不让父母砍芭蕉,竟然和父母吵了起来,两个老人都有些莫名奇妙,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激动。不过,他们到底还是没有砍芭蕉,到底还是没有因为他们的不知情而砍伐一个少年心里单相思的信物。
中学校园里也是有芭蕉的,而且远远比我家更多,不是一丛,而是一片小小的芭蕉林。最初,我跟着同学到这芭蕉林里早读。这里空气新鲜,人也少,有时候,芭蕉旁边的那株老槐树上,会有一两只早起的鸟儿在发出宛转动人的鸣叫。夏天,芭蕉也会结出一些果实,看上去像是香蕉——其实,那时候我还没吃过香蕉,香蕉只有云南和两广那边才有,在我就读的那个偏远的小镇,又是二十年前那个交通极其不便,物流极其不发达的年代,这样的小镇是不可能有香蕉的。我是从书上知道有一种热带水果叫香蕉。那时候,不少人以为芭蕉就是香蕉,因此芭蕉树上结出的果实才只有一支钢笔长短时,就被那些越墙而来的村民或是小孩摘走了。为了摘取果实,芭蕉往往很受伤。清晨去早读时,便看见一地狼籍,被折下来的芭蕉叶到处都是。后来,当我恋上了那个叫秋的女孩,我更爱往芭蕉林里钻了。有时是躲在里面读书——那正是朦胧诗席卷全中国的年代,我最喜欢的诗人包括北岛和顾城。顾城那首著名的短诗,我觉得把话说到了我的心尖尖上:
你一会儿看我,
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看云时很近。
除了读书,有时我干脆以几张巨大的芭蕉叶铺地,懒懒地躺在上面,望着头顶的天空发呆。这样的发呆是天马行空的:柏拉图式的恋爱,晦暗不明的前途,对远方的渴望与恐惧……这些突然之间就会袭上心间的莫名感受,它们构成了我青春成长的一大背景。在这背景的映衬下,我一天天地长大,一天天地成熟,同时也不可救药地,一天天地实用和功利。或许,这就是每一代人都要周而复始重复的成长主题吧?
当校园里飘满了栀子花的香味时,我们就要毕业了。那时候大学尚未扩招,招生名额少得可怜,像我们那种农村中学,能够迈进大学门槛的幸运儿,其比例可能不到百分之五。秋的成绩很好,用老师的话说,她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校门。而我的成绩则很不平衡,语文和历史这样的文科很好,数学和英语却很差劲,老师虽然也鼓励我说有机会,但我以为自己更像玻璃瓶中的苍蝇——前途光明,出路不大。眼看毕业分手的日子就要到来,有好多次,我站在距她的座位只有几米远的暗处,鼓足勇气想请她出来走一走,顺便也把压抑了一年多的心里话说给她听。然而,最终我还是选择了默默地走开。我惟有站在密不透风的芭蕉林里,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些。青春的沉重注定無法用幻想来承担。
毕业晚会那个晚上,原本一直晴朗的夏天,却突然下起了小雨。夏天里难得一见的温柔小雨。秋穿着一袭白色长裙,清唱了一首歌:《当我们毕业的时候》。许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自己的伤感和心酸。她的歌声还没结束,我已经飞快地跑出了教室,我跑到了那片生意盎然的芭蕉林,手扶一株芭蕉,像扶着走失多年终于再次聚首的亲人。无声的小雨里,我放声大哭,眼泪和着雨水滑进嘴里,咸咸的,如同那个时代的青春与初恋的滋味。我知道,从那时起,我已真正长大成人。
二十年后,当高中同学组织第一次毕业后的同学会时,好些同学已经被无情的岁月修改得面目全非。原来的电线杆长成了大胖子,原来的长头发变成了秃顶。时间真的就是一把杀猪刀。秋没有来,听和她一直有联系的女同学说,早在五年前,秋就远涉重洋去了美国。原来,毕业后,她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当了一段时间老师,是在一个边远的小城。她不甘那种一日重复一日,一天抄袭一天的枯燥生活,从学校辞了职到北京去打拼。最艰难时一天只吃三个馒头,睡觉的地方是一间只有五个平方米的小小屋,这小屋深处地下三米,墙上全是水迹。她也曾经成功过,最发达时手里有两家公司和一两百号员工。然而,最终她还是在经历了两次不幸的婚姻后,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并被这个美国人带回了远在大西洋畔的老家。如今,哪怕是和这个最要好的女同学,秋也没有再联系过。没有人知道她的近况,甚至也没有人知道她是否还活在世上。就像一滴水跌进了大海,你再也难以找到它的影踪:或许每一滴水都是它,或许每一滴水都不是它。但它就在眼前的这片海里。就像舞动在我的青春岁月里的芭蕉,它可能是这一株,也可能是那一株。但无论哪一株,都那样固执而坚忍。从它的叶片上滴落的雨水,一直,滴了二十多年,从我的少年时代滴到了中年时代。
前几年,当我读到好友聂作平的一首叫做《大地呈现花园和种子》的诗时,无端地,我想起了我生命中的芭蕉,和那些雨打芭蕉,彻夜难眠的岁月。虽然他并没有在诗里写到芭蕉,但他所写出的那种成长的伤痛,我也曾经拥有过。如今,它已成为我生命中至关重大的一笔财富。我知道,这样的财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尽管它曾经以酸涩的方式到来,但最终,却是一种无以言说的幸福。每当秋雨淋漓,每当芭蕉夜雨,这笔财富就会再一次增值:
大地呈现出一些花园和种子。在午后
一只蜜蜂扇动弱小的微风
这举世无双的采花大盗,它让花园
从东南奔跑到西北,它让种子
从春天奔跑到冬季
大地必须呈现:从无到有,从一到万
种子必须发芽。花园必须一次又一次
开满欲望的花朵,如同我们在人间的岁月
常常欲仙欲死。大地呈现:就象久违的爱情
因为伤害,从而景然有序。大地呀
你的花园是你的伤口,你的种子
是你无法延伸的衰亡和爱情
尘埃落定:大地呈现出花园和种子
种子萌芽。花园长出翅膀。大地是圣洁的
它有着无辜的泪水,和忧伤的美丽
责任编辑 聂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