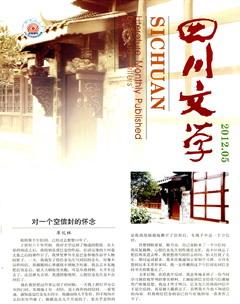伤疤
闫文盛
商野在《都市新报》干不下去的时候,就狠狠心,把工作给辞掉了。那时他已经三十六岁,在媒体界,这个年龄早已不占优势。商野的妻子是本地人,在一家很小的公司里做会计,因为收入低,所以就把钱看得越来越重了。商野辞职,却完全是他一个人的意思,他知道即便和妻子商量,也是通不过的。辞职后,他也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等到该往家里拿钱的时候没有拿回来,妻子才发现丈夫已经失业了。
商野本来很讨厌“失业”这个说法,可妻子偏偏喜欢用这样的词语来刺激他的神经;当他觉得无法制止她的时候,他就采取了一种策略:从妻子的身边走掉。发现丈夫失踪之后,这个叫林心雨的女人有些绝望了。她没有找他,而是坐在屋子里,一遍遍地回忆起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场景。她呆呆地坐到了凌晨两点时,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丈夫的一位朋友打来的,这个人叫卫显义。林心雨见过这个叫卫显义的男人,但对他印象不佳。卫显义似乎也知道这些,所以长话短说,连招呼都没打就说:“老商喝酒了。喝过头了。现在你们家隔壁的区中心医院输液。你带点钱过来吧。”林心雨愣了一下,脑子里似乎有些缺氧。她坐了很久的身子也有些滞重,她挣扎了一下站起来时有些头晕目眩的感觉。她还嘀咕了一声:“老商,我头有些晕。”可是老商没有听到她的话,他现在躺在隔壁医院的病床上,人事不省。
林心雨带了钱赶到时,气不打一处来,可是一腔怒火无处发泄,她觉得自己心里郁积的不快越来越深。她没有看卫显义,可是又总想同他说句话,问问老商到底是怎么喝醉的?卫显义呢,也有些生气,因为一起吃饭的朋友走的走,散的散,谁也没有主动帮一下忙。他把老商送到这里来,也是因为知道这里离老商的家近,有点儿急着推脱责任的意思。可这个女人来倒是来了,话也不说一句,满脸的不快全冲着他,好像自己是这件事情的主谋,卫显义的愤恨就很深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说的话就有些重:“我说,老商喝酒,可能是在家里受气了。男人有条软肋你是不能轻易捏的。你捏他重了,他就自暴自弃了。如果听我句话,就不能这么着做事。”这话里,也有提示的意思,本意呢,是好的,可林心雨情急之下听不进去,反而觉得他多管闲事:“多谢了。老商都多少年没喝酒了。今天,也是拜你们所赐吧。”话不投机半句多,卫显义骂了句“他娘的”,转身就走了。
商野和林心雨的战争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爆发的。他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女人,先是有点儿愧疚,可是眨眼之间,就被满心的不快占据了。因为林心雨非但没有安慰他,而是一味地责骂他:“老商,你真是个混蛋。”“你要不喝死算了。你有种就死在酒桌上,到这里显什么宝。”这话在老商听来,太刺耳了,就是刚刚进来的医生都觉得不妥:“他刚刚醒酒,让他多休息一会儿,有什么事回家再说。”这还是客气的一位,有一位护士看不下去,就呵斥她:“这是在医院,嚷什么嚷?”林心雨被噎了一下,愣了半晌,缓不过气来,她死死地盯着老商看了几眼。老商呢,早闭上了眼睛,他觉得自己的心被刚才妻子的几句话撕碎了。等到医生离开了病房,林心雨就狠狠地拧了老商一下:“你这个死鬼。”
从这一天开始,商野觉得自己心里的愧疚渐渐淡薄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仇恨。因为在报社里磨蹭得年龄大了,商野觉得自己的心态也已经老去了,可看看周围的朋友们,一个个牛气烘烘的样子,他又觉得不甘心。去几个还算熟悉的报社找工作碰了几次壁后,商野完全对眼前的情形失去了判断。有一天,商野在街头闲逛时,一辆白色宝马车“嘎吱”一声停到了他的身边。车里的人钻出头来同自己打招呼时,商野疑惑了大半天。这是一位十年前同在《都市新报》就职的旧同事。听他话里的意思,现在势头正猛的《新早报》就是他在投资运作。商野觉得他坐在车里同自己说话是一种嘲讽,又觉得他之所以在这里耽搁半天,其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显示今天他所取得的新成就。
“这真是可喜可贺啊,”商野言不由衷地说,“不过,我早都看出来了。你小子,就是有能耐。”
旧同事说:“我们分别,也有十年了吧。”
商野现在既希望同他多说几句话,又迫切想结束这种无聊的谈话。他看看周围郁郁葱葱的树木,看看头顶明晃晃的太阳,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站在这里做什么?毫无疑问,他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屈辱。他想也没想就冲口而出:“伙计,今天是不是没什么正事可做?”
坐在宝马车里的人愣了一下。他显然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尴尬。不过,他还是递了一张名片给这个乱讲话的人:“我听说你上周去过《新早报》了,可是为什么又不找我呢?”
商野灰溜溜地转到天黑才回家去。林心雨早已做好了饭,正坐在饭桌旁生闷气:“煤气费、电话费,还有物业费都得交了,你这一整天死哪里去了?找到工作了吗?”商野没有接腔。可是,看着女人那张因为生计被折磨得蜡黄的脸,商野鬼使神差地就把名片拿出来了。
直到这会儿,他才仔细看了一下这张做工考究的名片,上面写着:
李秋生新远传媒集团董事长
妻子将饭盛了,隔着桌子递过来,商野的手有点儿抖,不小心就把碗磕了一下,饭菜都撒出来了。妻子“啪”一声将自己正在端着的碗往桌子上一放:“你要死啊,怎么回事?”商野仿佛受惊似的,站起身来,就要往外面走。妻子在后面大声喊:“你出去了就别再回来了,这个家,越来越不像个家了。养个没有用的男人。”商野像被這句话刺了一下,心里有些悲伤,他忽然噗嗤一笑,说:“我觉得也不像个家了。”
妻子没有看到商野正在扭曲的脸色,还在一个劲地唠叨。商野觉得忍无可忍,就扭转身来,走到饭桌边,直愣愣地看着她。林心雨被他这种前所未有的神色吓怕了。
商野一字一顿地说:“我明天就去上班,我就去找找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李秋生在办公室里忙碌。看见商野进门时,他微微笑了一下,然后就三步并做两步走过来:“我说嘛,你肯定会来找我的!来,坐下。”商野冲他笑了笑,就在真皮沙发上坐下了。
未等商野讲明来意,李秋生就把手下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招来:“这是薛秘书,让她带你去见郑总。听说你已经见了一次郑总?”商野说:“是见过一次,可当时郑总觉得我年龄大了,不合适。”说完这句话,商野就觉得自己的脸部有些发烫。
李秋生沉吟了一下,然后就拨电话:“我来给郑总说,他不会驳我的面子。”电话拨通了,那边却似乎还在反对。李秋生似乎有点儿生气:“老郑,我这是第一次向你推荐人。他的业务能力我清楚……好吧,就算我落你个人情。”电话挂掉后,李秋生叹了口气,才把目光转向商野:“怎么回事?老郑对你的印象不太好,你们第一次见面就起冲突了吗?”商野不好说“是”也不好说“不是”,他正被自己的愚蠢弄得喘不过气来,有一个声音在激烈地反对他继续逗留在这里,可另外一个声音却鼓动他留下来。
他想起那个个头不超过一米六的老头,想起他鹰一般的眼光以及半秃的脑壳,又无来由地泛上来满腹的沮丧。李秋生盯着他看了半晌,说:“老商呀,要我说你什么好?我记得我长你两个月吧,我以老哥的身份说句话吧:别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情。老郑不坏,不,应该说是挺好的一个人。你不要为以后的事发愁。”
这一次,商野没有看李秋生的目光,他觉得自己太过窝囊了。他有些憎恨这个自以为是的前同事。
第二天,商野就到《新早报》上班了。
妻子开始恢复了一些对他的柔情。有好几天,她都没有再责骂他,也没有再提及那些令他不开心的日常琐事。她甚至在他正式上班的第三天,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陪他喝掉了半斤白酒。没出息的商野在喝完这顿酒后又醉了一次。半夜里,他还摸索着爬到妻子的身上,想行使丈夫的权利,却被林心雨一个翻身给弄了下来。
商野在醒酒后失眠到天明,他睡在妻子身边,却觉得离她十万八千里。
林心雨借着熹微的月光看到他泪流满面,她突然觉得他令自己讨厌。这个哭鼻子的男人令自己万分讨厌。她背转了身子,以僵硬的睡姿坚持到天明。
白天里,面对同事们猜疑的目光,商野再也没有像在《都市新报》那样,能够将那种闲云野鹤的心态保留下来。混迹于一帮年龄都没有超过三十岁的编辑中间,听他们谈论着名车、别墅,谈论着泡妞、情人、出国、炒股等等话题,商野觉得自己真是老了。他心里的负荷越来越重,以至于来到《新早报》不到一个月,他的名声就传遍全报社了。许多人都觉得他有心理疾患,似乎不适应于目前报社蒸蒸日上的形势。甚至有几个比商野还年轻的编委当面和郑总提及这件事情,提议应该把他从编辑队伍里“踢出去”,“我们都认为,无论他是靠谁的关系进来的,都应该被清除。”
关键的时候,郑总并没有像商野所担心的那样,去听信人言,甚至,他不用听信人言,只依据自己旧日的感觉判断,将他从编辑队伍里“踢出去”。倒是有一天,商野用心制作的一个关于“民间文化”的专题获得了他的赞赏,他在全社职工大会上表扬了这个“原来他根本不赏识的人”。在他发表这番陈辞的时候,商野留意到坐在他旁边的李秋生。
这个人正目光炯炯地环视全场,一副志得意满运筹帷幄的大将模样。
商野突然想起十年前和李秋生为同事的年月。他那时似乎并不出色,业务能力较之商野,差了一大截。有一次,为了申报职称,他甚至求商野帮忙修改过一篇论文,为此商野和他在单位里熬过一个通宵。在此之后不久,他就从商野的视线里消失了。
这以后他是怎么发迹的,直到今天,商野完全不知情。相比之下,李秋生对他的一切,反倒了如指掌。所以,他才会以过来人的口气劝说他“别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情”。
想到这句话,商野非但没有感激,反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这种奇怪的心理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反正看着这个不可一世的旧同事,他觉得自己心底那些恶毒的念头就不可遏止。尤其是来到《新早报》以后,目睹了这个人今天的一切,商野心里的怨怼就越来越深。
令商野愤愤不平的是,自己这些年里一直在像老黄牛一样辛勤耕作,每年都囊括省里颁发的大大小小的新闻奖,即便就在他辞职离开的时候,总编都以一种痛失英才的口吻对他说:“小商啊,你一走,这里可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像你这样了。十几年了,你怎么就可以舍弃这个平台呀?这差不多是你的家啊?你在哪里还待过这么久?”可是《都市新报》历时一年多的欠薪事件几乎成了省城媒体界的一个笑料。他商野即使再不舍,为了生计,也没法再在这里干下去了。
李秋生看商野时,目光总是温和的。但是,商野就是忍受不了这种温和的目光。他总想做出一种样子来给自己看,证明他就是那高高在上的,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人。狗屁!商野想,明明自己帮过他,他却要做出这副样子来,他何曾对自己表达过这一层谢意?
有几次,李秋生叫商野到他的办公室,问起商野最近的情形。但他又首先声明:自己对他的情况是了解的,知道他做得不错!但是为了确证,他需要来自商野本人的反馈,“我总不能亏待了你嘛!”说完这句话的李秋生,总是喜欢拍打一下商野的肩,就像一个长辈爱抚晚辈似的。
在这种时候,商野总会生出一种抵触情绪来。他希望放在自己肩膀上的这只手是十年前的李秋生的,那样,自己才会坦然受之。甚至,商野还想过将自己的手放到李秋生的肩膀上,来证明他们的亲昵关系,“如果非要证明什么的话。”
有一回,他几乎就要这样做了,却惊奇地发现郑总在自己的身后站着,他只好告辞出来了。
郑总是来找李秋生商量事情的,可商野觉得他像个幽灵一般,“也许是因为他长得瘦小吧?”商野在喃喃自语的时候被同事小柳听到了。小柳是个喜欢打听别人隐私的女孩子。她说:“商野老师,您在说谁长得瘦小?”
商野看看这个不谙世事长相灵秀的女孩子,几乎就要把心里的那些想法都对她倾倒而出了。忍了忍,才终于没说。小柳不解地看着他:“商野老师,您不舒服吗?”商野点点头,说:“我胃疼。”小柳知冷知热地帮他倒了一杯水:“刚烧开的水,要吃药吗?”商野摇摇头,说:“不用了。”想了想,又说:“谢谢。”
小柳仔細地盯着他看了半天,说:“商野老师,您真逗。同事们都觉得您挺怪的。”
商野心里一动,说:“连你也这么认为吗?”小刘说:“当然。可是,现在好像不了。”
商野拍拍她的头,说:“小柳,你挺可爱的。我老商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非常意外,一向沉默寡言的商野同小柳的话多起来。小柳四处传播她从商野那里探听到的新消息。商野本来都是和她说着玩的,或者,潜意识中,把他当做自己的妹妹甚至女儿;这些年里,他仿佛积累了太多的话需要倾吐,而小柳以她的好奇心激发了他的倾诉欲——结果却是,他们私下里说的这些事情被小柳分毫不差地散布出去了。
开始的时候,商野总是会在事后责问她,因为小柳全不否认,而他自己又似乎有点儿疼惜她,久而久之,他也就认同了她这个传声筒的角色。
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双方的关系就变得无比亲近了。
商野压根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的危险性。他正淹没在前所未有的自豪感觉中难以自拔。当他和小柳交流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骨子里好为人师的一面。如果小柳有一天没来或者出差去了,因为找不到说话的对象,商野就会在工作的间隙茫然四顾,到处寻找小柳的身影。如果小柳某一次因为心情不佳而对他的讲述略表不屑,他就会变得异常难过,仿佛死了亲娘似的。
说什么呢?后来商野在回想自己这一段走失的生活时,总会陷入到这个过时的问题中呆呆地出神。他完全找不到昔日滔滔话语的头绪,每逢这时,在下意识中,商野就会想到:必须求救于小柳。
在他们说话最多的那几个月里,小柳姑娘把商野从里到外地了解得透透彻彻。小柳有一天对商野断言:她比作为妻子的林心雨对他的了解都要多。
或者正是这句话触动了商野的神经,他开始想象小柳对他的这种了解预示着什么。他忽然觉得自己对这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讲的话太多了。他对她肆无忌惮的传播欲也过于放纵了。听听同事中间都在怎么讲述商野吧?
“一个迂夫子。他怎么就敢和李秋生比?”
“一个狂妄的家伙。不识时务。他怎么就不知道郑总一直是在帮他?”
“一个抑郁症患者。他怎么就从来不和别人沟通?”
“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人。他怎么就只对小柳说话?莫非他也在贪恋小柳的美色?”
最后这个说法,居然是通过小柳之口反馈到商野的耳朵里来的。小柳露出一种天真无辜的神色:“商野老师,他们的说话可是当真?可不要说是我在诱惑你?如果你太太来找我的麻烦,那我这辈子岂不毁在你的手里了?”
商野大失所望,他觉得自己所遇非人。他怎么就觉得眼前这个小姑娘是可以倾听他心声的人呢?听听她所说的话吧:“我可没有看上你。你要钱没钱,长得也不好看。我要喜欢你这个年龄的,也可能只李总一个。他才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呢!”
商野知道她口中的李总就是李秋生。又是李秋生!他知道这个小女子口无遮拦,可他已经阻止不了她,他从来就阻止不了她!
在他们之间无话不谈的那几个月里,商野正走向他人生中最大的两个极端。一方面,他所编辑的版面、所制作的专题都独领《新早报》风骚,以至于老郑后来对他的印象已经大为改观,不仅不再说他“不赏识这个人”之类的话,而且,就是有人在他面前提及商野的不足之处,他也全部都顶回去了,商野成了郑总眼中的红人,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其二,商野在《新早报》名声败坏,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顶峰。除了郑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诋毁商野。他们说,这是一个不应该被包容的家伙,即使他的才具比现在多上十倍,都不足以抵消他对他们的污蔑。商野对《新早报》批评最狠的一句话流播最广,几乎成了“狗咬吕洞宾”的代名词,因为这句话的锋芒指向了李秋生。
商野说:《新早报》,一份用人民币印刷垃圾的典型报纸,李秋生在重蹈《都市新报》的覆辙。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商野在《都市新报》时所感觉到的盲目扩张的恶果,在他来到《新早报》半年之后开始上演。《新早报》走厚报路线,报纸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200个版。由于过于追求报纸版数的冲击力,致使报纸质量每况愈下。知情人说,这个决策完全是李秋生的主张。商野也知道这个信息,可是骨子里头对李秋生的一丝不屑,使他无所顾忌这句话所带来的负效应。
据说,郑总竭力反对李秋生的思路,甚至不惜以辞职相要挟,但对于郑总一向礼让的李秋生拍了桌子,让他闭嘴,“我意已决,诸君勿再多言”的意味传递得极其鲜明。
也许,商野只出于一种简单的义愤,也许,更多的还是对李秋生的嫉妒,在不知不觉中,一种不良的情绪已经把商野给淹没了。但在众多的人都开始指责自己的时候,商野却表现得如同无事人儿一般。
李秋生显然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有一次,他在电梯里遇到正急匆匆上楼的商野,还像往常那样招呼了他一下:“老商,最近怎么样?”商野迎着他的目光说:“还好。”
李秋生将目光平视楼梯口,没有和他继续说下去。商野看了看他的脸色,发现一切如常。
可是,刚出楼梯,李秋生就把他叫住了:“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吧。”商野还犹豫了一下,想: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可是,等到他们相随着进了门,李秋生就开始接一个长长的电话。听口气,好像是一个妻子之外的女人打来的。李秋生丝毫没有避讳商野的意思,他冲着电话里说:“没什么,没什么,这里只有我的一位兄弟。”
商野百无聊赖地等着这个长长的电话结束。
在这个过程中,李秋生始终没有看商野一眼,也没有对这件事情表示歉意。商野想,他对自己视若无睹。即使后来,商野已经等得不耐烦,起身去了一次里面的卫生间,甚至直到他从卫生间出来,李秋生的电话仍然没有打完。
商野把手中一沓子《南方都市报》抖动得哗哗作响。起初他还担心自己的举动招致李秋生的不快,后来却又似乎巴不得如此。
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甚至四十分钟,等到商野再度站起身来,推开门准备先行离开的时候,李秋生才结束了他漫长的通话。他喊了一声:“商野,最近外面好多人在说你的闲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商野不得不回了一下头。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而是说:“你相信这些话吗?”
李秋生站起身来,到饮水机上接了一杯水:“你说呢?”
商野已经对这场谈话丧失了兴趣:“你如果相信他们的话,那就是我说的。如果不相信,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你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了,老李。你怎么想,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我还有点事,先告辞。”
李秋生目送他出门后,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经过这次谈话,商野一直在酝酿着辞职的事。他不想等着辞退的通知张贴出来后,自己才被动地离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自己就太不识趣了。
可是,一想到林心雨,商野就有些泄气。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林心雨的情绪总是时有起落,但家里的经济危机好歹算是过去了。林心雨再也没有拿那些最琐屑的家庭经济账来烦他。因为有了在《新早报》这份不菲的收入,商野的腰杆也明显地比以往硬了很多。现在林心雨再来数落他,也没有动辄就使用“窝囊”这样的词,反倒因为他到了《新快报》以后收入的上漲,使她觉得自己的底气也足了。她甚至开始改变他们不要孩子的初衷,完全放弃了避孕,已经准备当一个母亲了。
但是她仍然会时不时地提起一些自以为可以激励他上进的话题,譬如偶尔谈论一下她所在公司的老总。看起来,这个刚满三十岁的男人仍然叫他佩服得不得了:“老商,人家比你可是小了一大截呢!可你看看,现在你还缺少的房子、车子,人家都有了。再过几年,人家是什么前景?你呢,总是这熊样,要不得赶紧上进呢?”商野听了总是苦笑。他觉得自己的形象在这个女人的心目中,早已不知道坍塌了多少回了呢?也难为她已经守了他整整十年了!
他有了辞职的念头以后,顺带就考虑起他们的婚姻来了。想来想去,他不知道现在两个人被拴在一起,到底意欲何为?可是假如自己的生活里没有了林心雨,又将何去何从呢?
一想到这个问题,商野就头痛欲裂。有一次,他终于没有忍住,将这个令他困惑的难题对小柳讲了。当时小柳的表情很夸张,她说:“你是想引起我对你婚姻不幸的同情吗?老商,同志,别再做你的千秋大梦了。”这个反应很让商野吃惊。他摇了摇头,像要把心中的不屑驱除出去。
接下来,他试图谈话的愿望渐渐地淡下去。可是小柳却好奇心十足地追问他一些细节,甚至问他:“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分居了?”商野看着她微笑了。他觉得她真是太好玩、太稚嫩了!这以后她说什么话了,他都没有听进去。小柳仔细地看了他半天,觉得他现在越来越让自己琢磨不透了。
当天夜里,吃过了晚饭后,商野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呆呆地出神,林心雨呢,就偎在他的旁边织毛衣,对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温馨时刻。可商野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的脑子里纠结着一些事,怎么理也理不清楚。好几次,林心雨转过头来看他,都被他忽略了。等到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他站起身来的片刻,林心雨就发作了。“不许接”,她说,“不许接手机”。商野被她的声音吓了一跳。他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
“你已经好久不同我说话了,老商,”她大声喊,“照这样下去,我不知道自己怀上你的孩子到底是对是错?”急切间,商野听得分明,她是说她已经怀孕了。这大出他的意外!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他俯低身子去看她,这个小他四岁的女人!她仍然是娇小的,这会儿,显出罕见的无助和恐慌。
他显然被这崭新的事实所击倒了,整整十年了,因为她的坚持,他们从来没有把要一个孩子当做人生中的必要程序,也正因为如此,他几乎从来没有当一个父亲的必要的心理准备。他觉得自己在这种简单的生活里所泯灭多时的责任感,似乎再也找不回来了。可是,这个意思,他没有能力表达出来。
最近一段时期,商野发现自己心里矛盾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手机铃声停顿了十多分钟后,再一次发出刺耳的尖叫。这一次,商野没有动。后来是林心雨听得不耐,命令他:“你去看看,到底是谁这么讨厌?已经十点多钟了吧?”
商野看来电显示,是小柳打来的。她迫不及待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却没有说她为什么这么晚了还找他。商野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说自己正在搞创作呢,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说完就把手机挂上,关掉了。
林心雨说:“你撒谎了。你为什么要撒谎?”
商野抱了她一下,说:“单位里的小同事,问版面上的事情。”
林心雨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她冲他大嚷:“我不相信,商野。你的言行举止都出卖了你。老实告诉我,是一个女人打来的吧?”
商野无奈,只好解释:“确实是单位里的一个女同事。我没骗你,小雨。”
这一晚,商野和林心雨都在辗转反侧中睡去。第二天天亮以后,商野刚到单位,就发现同事们都拿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小柳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她大大咧咧地站在他的办公台前,敲着他的桌子说:“老商同志,昨晚怎么不接电话?”看看周围无人,又低下身子,以一种耳语般的声音说道:“是不是太太在疑心你?”看商野不接腔,又说:“出大事了。都在议论,你知道吗?”
商野抬起头来,疑惑地看着她:“什么事情,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
小柳的表情无比沉痛,“唉,没想到你真说对了。听说李秋生欠了一屁股债务,《新早报》经营不善,就要完蛋了。还听说郑总就要辞职了。”
商野料到这是早晚的事。却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小柳看着同事们熙熙攘攘地涌进来,言犹未尽地说道:“老郑待你不错,你跟他走就行了。据传《晨报》早就在请他了。他对人家说,还要在这里最后一搏。你早点去找找他,都说晨报人才匮乏,你去了或许能受到重用呢。”商野没有听下去,因为他看到李秋生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进来了。
同事们很快都各就各位了,在李秋生的环视下,都浑若无事一般。
商野突然觉得小柳的话如同虚言,他埋下头去,继续把昨天没有完成的那个专题策划写完。
李秋生在他的桌前站住了,他没有抬头,直到有一只手伸过来,向他递烟:“老商。”他接住了,却没有抽:“李总,这里不允许抽烟。”李秋生呵呵干笑了几声:“他娘的。”
一周以后,《新早报》就开始大幅缩版。先是减成了100个版,即便如此,仍然是商野所反感的厚报路线。紧接着,不到半个月,又减少到了64个版。这一次大缩水,使《新早报》在广告客户和广告订户中引起了巨大震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份原本朝气蓬勃的报纸,就元气大伤。
继郑总辞职不干,先后有二十余名编辑记者毫不犹豫地离去。小柳也辞职走了,说是要去投奔上海的表姐。表姐也做媒体,在一家规模不大的周报当执行主编。小柳走的那天还劝说了商野一回,要他及早去找郑总,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郑总去《晨报》后,在最近一段时期中肯定要重新洗牌。你去得晚了,估计就不会有你的好位置了。老商同志,当断则断啊。”
在这方面,年纪轻轻的小柳总显得比商野棋高一着。
與此同时,李秋生找他谈话。要他稳住阵脚,千万不要在这时候动走的念头。因为商野所在的文化编辑部,目前已经人丁萧索,堪当大用的也没有几个了。
商野觉得一向意气风发的李秋生有些疲惫。有一天,商野刚到报社,看到他从宝马车上下来。那辆车似乎好几天没有洗过了,车上的几缕灰尘,在此刻的商野看来,格外扎眼。
紧随在李秋生身后的,是一个商野从未见过的女人。非常意外地,李秋生在商野面前停留了一下,向他介绍说:“这是我刚刚从京城请来的常总编,是咱们的同龄人啊。”商野愣了一下,他看到这个姓常的女人眼中滑过一丝疑惑。
李秋声尴尬地笑笑:“我的朋友。咱们这里的主力文化编辑商野。”
林心雨显然开始察觉到了商野心里的动静。关于《新早报》的变故,她早已听说了十之八九。为此,她又和他大吵了一次。起因是她埋怨他为什么不早些言明,“早知如此,我们就不能要这个孩子。”她的想法直截明了,“现在我们仍然自顾不暇,孩子生出来,岂不要跟着我们遭罪?”听了这句话,商野心中苦不堪言。
自从郑总走后,商野所编辑的版面和采写的稿件都无人赏识,他报上去的专题经常会被卡下来。有一次,他甚至已经制作好了一个大通版,又因为某个编委的一句反对意见被临时撤换下来,改做其他内容了。商野一气之下去找总编理论。他进门的时候李秋生恰好也在。
常总编听他说了情况,没有发表意见,而是把询问的目光转向李秋生。
李秋生回避了,说:“这种编务上的事情,你做主就行了。”
商野说:“这种情况,郑总在的时候很少发生,这是对编辑劳动的不尊重。而且这个策划完全是自采的,中间费了多少周折,您应该清楚啊,常总。”商野说话的时候无所顾忌,说完了才觉得自己提了不应该提到的人与事。
“别在这里提什么郑总,你是一个编辑,就应该服从总编的意思。记住,你现在是在与常总说话。”李秋生毫不客气地说这番话,在商野听来,分外刺耳。
商野在愤恨之下,第二天就去找了郑总。郑总似乎对被拿下来的这个专题非常感兴趣。他说:“你把它拿来让我看看,如果合适,我这里也可以用。”商野觉得不妥,又禁不住郑总一番劝说。三天之后,这个专题就在《晨报》刊登了。
看到这个既成事实,常总和李秋生似乎非常生气。
研究如何处罚商野的时候,李秋生非常恼怒地拍了桌子,骂“郑玄成这只老王八”,又骂商野不识好歹。这句话很快就从编委会传出来,商野听说李秋生竟然如此风度全失,竟然可以对刚刚离开的郑总指名道姓了,就知道自己再待下去必然无益。
带着这个道听途说的消息,商野再度来到郑总这里。意外的是,被人骂成“老王八”的郑总居然丝毫都不生气,而是笑嘻嘻地说:“果然不出我所料,李秋生这只小王八,还有商野你这只小王八,都不是什么正经东西。你说,到我这里,你准备做什么呢?”
郑总如此反应,显然大出商野意外。他支吾了半天,也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表述明白。郑总看他这副熊样,越发瞧不起他。但他还是泄露了一个秘密给他:
“我和李秋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年轻人,你怎么就这么不成熟呢?我跟你透个底吧,李往《晨报》投入了3000万元,是这里的大股东……说实话,李秋生这个人并不坏。你不应该为这种事计较啊。”
商野有些头晕目眩的感觉。步行下楼梯时,他不小心与一个急匆匆跑上来的人撞了一下。那个人手里提着一个热水瓶,瓶里的水洒了一地,滚烫的开水把两个人的双脚都烫伤了。
过了好久,商野的烫伤才好。问清了事情的经过,林心雨心疼地把他大骂了一通了事。
可是从此以后,商野的双脚都留下了一片疤痕。每逢刮风下雨的日子,他的脚就有些疼。林心雨不以为然地说:“这倒是件新鲜事儿。你又不是风湿病,学人家凑什么热闹?”说完了,就过来帮商野揉脚。她像揉面一样揉脚,商野就像杀猪似的喊起来,弄得街坊四邻都听到了。
责任编辑聂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