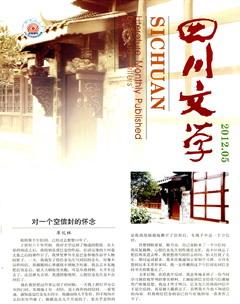泣忆山伯
在“著名诗人杨山诗歌研讨暨朗诵会”上,只觉得有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眉之上,心之下,丝丝缕缕都是愁。
2010年11月23日凌晨杨山先生不幸逝世,距今已逾周年。这期间,有不少朋友问我,山伯待你如弟子如儿子,他老人家溘然长逝,怎么未见你有悼念山伯的只言片语?对此,我其实也时时扪心自问。今日今午,此时此刻,我可以作答了。今生今世,山伯是我恩师,他教我如何作诗,几十年如一日;今世今生,山伯如我父执,他教我怎么做人,几十年如一日。山伯走了,这世上最牵挂我的那个人和这世上我最牵挂的那个人,走了。我心悲戚,我已悲到极处;我心伤痛,我已痛到极致。悲到极处,何以有言?痛到极致,何以有诗?
虽无诗,虽无言,我心深处,对山伯的印象,却难以磨灭,且日渐日新时渐时新。
臧克家《有的人》有言:“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山伯就是我心中一直“活着”的那一个人。
范仲淹在《严(光)先生祠堂记》诗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山伯当属范夫子崇高评价的那一个人。
杨山是山,与平地无关,和平庸也无关。我还油然记起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岘首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今天,高朋满座,嘉宾云集,我们重新登临杨山,再度感悟杨山。
重庆文学界年纪稍长者都知道,重庆村30号老文联大院原有三伯。一是杨甦,著名评论家,《红岩》杂志副主编,称甦伯,也是我的恩师;二是杨山,著名诗人,《红岩》杂志副主编,称山伯,也是我的恩师。两伯之外,还有一伯,那就是当时市文联的党组书记王觉。王觉级别较高,为让高级干部与高级知识分子有所区分,于是,睿智而幽默的作家诗人便效仿军队里中将肩章比少将肩章多一颗星的故事,在觉伯称谓之后添了一伯,称王觉为“觉伯伯”。
显而然之,称觉伯伯,感觉要公事一些严肃一些;称甦伯称山伯,感觉要家常一些亲切一些。
山伯,我如此呼了唤了几十年,我也在他屋里进了出了几十年。山伯待我如弟子,待我如儿子。山伯并没远走走远,他依旧在我身边在我心间。
印象之一 可敬的山伯
山伯,1940年以年仅16岁于《华西文艺》发表第一首诗作《塔》,开始步入诗坛。但是他真正成为一个诗人,真正将自己的生命融入诗歌,还是在他结识了抗战当年在重庆的诗坛健将编辑大家荒芜、力扬、聂绀弩之后,正是这几位慧眼识珠的前辈惊异地发现了他,精心地培育了他,让他在诗歌的道路上边走边唱。这一走唱,竟然便历经71度花落花开,25500多个漫漫时日。哪一个日子他老人家不是孜孜矻矻躬耕于诗垦地哟,哪一个日子他老人家不是躬耕到太阳落坡了,月亮又上山。
巴尔扎克说:作家是什么?作家就是时代的秘书。山伯作为一位时代的秘书,自是毋庸置疑,而且,山伯作为一位战士诗人,更是名至实归。山伯是诗人,也是战士。上世纪四十年代,正值山伯走向社会走向生活的青年时代。那时节,风雨如磐暗故园,万户萧疏鬼唱歌。山伯追求进步,向往光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不遗余力而不计荣辱进退。山伯在中学求学时,以写《悼萧红》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被所在中学通知:“下期勿庸来校。”山伯在国立歌剧学校求学时,又因撰写红色诗歌编辑进步刊物揭示人世之不平,而被歌剧学校再一次除名。
抗战时期,山伯写出了为他的诗歌人生带来巨大声誉的长诗《睡熟的兵》。这首诗,前面发言的诸多诗家都纷纷提及,说明这首诗已经深入人心。此诗描写了一位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蒂而壮烈牺牲的中国士兵横尸于冰凉而污浊的土地上的悲情壮景,对我们民族英雄予以了热烈的礼赞,对衣冠禽兽般的侵略者施以了无情的鞭挞。除此之外,对于这首《睡熟的兵》,我还有更为深邃的感觉——我以为,山伯正是借这个熟睡的兵,借这个长睡不醒的战士,宣泄了他对当时黑暗社会睚眦皆裂般的极大愤怒。于此有诗为证:“让他在太阳光下睡得熟吧,/请你不要叫他。/啊,我亲爱的人,/假如他醒来,/他将疯狂地痛哭,/他将会被赶到不知名的地方,/他将无处栖息,/他将没有一碗饭,/他将失掉甚至一秒钟畅快呼吸的自由……”士兵如果醒来,他将没有吃一碗饭的希望;士兵如果醒来,他甚至断无呼吸一秒钟的权利。在一个黎民百姓的生存权都荡然无存的那个暗无天日的社会里,生不如死,死强于生。如此批判,真是鞭辟入里;如此刻画,真是入木三分。
半个世纪之后,《睡熟的兵》也理所当然地选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抗战文学名作百篇》。
山伯的可敬,在于在每一个时代的交接处,他作为诗人都没有失语;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他的诗歌都没有缺席。山伯真是言必信,行必果:“我生活在这世界上,我有所感,故我歌。我写诗像写日记一样;我将感觉、印象记下来。然后反复修改。我的《雅歌》《雨天》《睡熟的兵》《自画像》《答赠贝者》《夜饮》《桥》《雨天的信》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就如前面的朋友们提到的他的诗作《黎明期抒情》、《给一个普通的人》,都是他在伟大祖国大地回春之后发出的深情的歌吟。特别是他在八十年代于《诗刊》发表的名作《雨天的信》,更是以上世纪四十年代为背景,闪回了当年国统区人民反压迫、反内战的磅礴画卷,也再现了当年国统区人民争自由、争民主的壮阔气象。在《雨天的信》中,山伯款款诗云:“听雨在巴山的楼头/ 雨点儿敲开了记忆的门扉/我想起我们在那小小的屋里/雨点儿和油墨香把两颗心沁醉// 我们不时地望着窗外/一朵乌云在江上低低地飞/而我们不给秋天一声叹息/心中装有个偌大的花园盛开玫瑰//我们刻着蜡纸刻着愤怒的惊叹号/要给予贫困者重重的一锤/我们轻轻哼着小曲儿,哼着/曲子里闪耀着大阳的光辉//几十年过去了,雨点儿将青鬓染白/你可曾斜倚楼头将昔日情景回味/雨天,我多想你打着伞前来并肩倾吐/倾吐寻梦者风中雨中寻梦的故事……//然后,相互微微的一笑/久久看窗外两只布谷鸟在春雨中飞……”当年,那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多么值得悠悠回味,那血火凝结的战斗情谊多么值得好好珍惜。好好珍惜昨天只为开拓更加有声有色的明天,悠悠回味昨天旨在走向更加有滋有味的明天。山伯的这一首《雨天的信》与郭小川那一首《甘蔗林-青纱帐》,理该当作如是观。
由是,桃李有言,也依旧下自成蹊了。1985年,《中国文学》(英文版)与《中国日报》以及1992年《中國文学》(法文版)均分别介绍了山伯其人其诗。1992年,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宣布山伯为1991/1992年度世界名人,其生平成就也载入其传记辞典。
山伯作为一个诗人,他自未及弱冠之年始,笔耕不辍到他耄耋之年直至他生命最后一息,其创作生涯之绵长,在当今诗坛,无人能出其右。山伯作为一个诗歌编辑,也从他未及弱冠之年始,编诗辑文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其编辑生涯之绵长,在当今诗坛,无人能出其右。山伯作为一个诗歌活动家,自1986年同方敬、林彦、凌文远发起组建且入主重庆新诗学会,办会办事,日理万机,活跃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其诗歌活动生涯之绵长,在当今诗坛,依旧无人能出其右。在重庆诗坛,山伯是山。在中国诗坛,山伯是山。在世界诗坛,山伯又何尝不是一座山。仰之弥高,望之愈坚,何其巍峨,何其伟岸!
山伯的可敬,在于关乎诗歌的每一方领域,都有山伯始终不渝的坚守,都有山伯呕心沥血的操持。由是,诗坛重光,再显辉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山伯的可敬还在于,对诗歌,他不仅投入了自己大量精力,而且还投入了自己不菲的的财力。他算不得富裕,严格说来,他还比较拮据。他退休之后,主持重庆新诗协会,创办银河系诗刊,开展诗歌活动,常常为之埋单,已是家常便饭。山伯以每月3000元退休金,既要聊以维持一家的生计,又要支付保姆的月薪,还要承担络绎不绝来他家的众多诗友的伙食费、茶水费、香烟费的花销。有客人来,山伯自抽老塔山老龙凤抽得津津有味。朋友送他的中华烟、天子烟,他全部用来款待了客人,款待得他备觉心欢体畅。作为育才学校曾经的执教人,他实实在在地践行践为着他的老校长陶行知的光辉遗训:“揣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认识山伯的朋友们都知道,山伯屋里的家具是何等的破旧,山伯的穿着是何等的陈旧,山伯的生活方式是何等的老旧。然而,认识山伯的朋友们也都知道,山伯的诗歌作品,却日见日新;山伯的诗歌理念,却日闻日新。如若太阳,每天都让人耳目一新。值此人心不古的当下,值此诗风日下的今日,山伯为诗歌之发扬蹈厉为诗歌之革故鼎新,将身外的一切身内的一切奉献得干干净净,确实难能可贵难能可贵。
说到山伯的可敬,我自然想到了他身后那位伟大的女性,那就是让我对之常常肃然起敬的师母咏梅。
《银河系》,是山伯一个人的杂志但又不是山伯一个人的杂志。主编山伯之身后,还有一个默默无闻却兢兢业业的“不管部部长”的咏梅师母。多少年来,她承担了主编以外的编辑部主任、创联部主任、接待办主任、伙食团团长等等多重兼职。虽然每一个职务,她都分文不取。然而每一个职务,她却都做得尽职尽责。每一项庶务,她都料理得清清楚楚;每一份事体,她都处理得头头是道。于老作协在中山三路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咏梅师母从重庆村30号,脚步蹒跚地来到作协大楼,为山伯发信,也收信;如果遇到有山伯的汇款单,她还要脚步蹒跚地到上清寺邮局去领款。新诗学会热热闹闹有饭局,她总是飘然而去。诗人们欢天喜地要合影,她总是避易远退。在山伯家里,我不时听见山伯问一声“笔吶?”咏梅师母便将那支老派克迅捷地递到了山伯的指掌之间;我还不时听见山伯问一声“烟吶?”咏梅师母便将那半盒老龙凤即刻搁放在山伯的书桌上 。有客来访,咏梅师母立即奉上一杯清香馥郁的铁观音。临近饭点,咏梅师母会悄悄安排保姆为客人加添两款家常菜。有诗人夜访山宅,同山伯一不留神聊至子夜,咏梅师母都会铺床置被,盛情邀请来客留宿。名声响遏行云如贺敬之、李季、方敬、曾卓、高缨、木斧、陈犀、严辰、叶文福、晓雪、朱先树、刘扬烈、赵丽宏、孙静轩、沈重、顾城与女友谢烨以及不少名不见经传的打工诗人,都曾于山宅酣然入眠至东方之既白。顾城与谢烨夜宿山宅之时,他俩尚未婚配,上床前显得局促不安,山伯宽厚地笑笑,对他俩说:“你们已经住在一起了,就住在一起吧,我是绝不会向你老头顾工告密的”,一側的咏梅师母也连连随声附和。
咏梅师母,活脱脱就是山伯的脚,就是山伯的手,就是山伯的心。
每天晚饭之后,我都会看到山伯和咏梅师母走出重庆村30号,顺着那道狭狭的斜坡往下漫步前行,两位老人十指相扣,相依相偎,相偎成黄昏时分好一道令来往行人眼热心跳的风景。每每目击此景,便令我感触万端。古人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以为,两情若是久长时,为何又不可在朝朝暮暮 ?!谓予不信,请读读这一对诗坛伉俪,请看看这一对诗坛伉俪。他们配合之默契,配合之亲密,配合之永恒,在中国诗坛,着着实实也没有任何伉俪能够出其右!
印象之二可爱的山伯
山伯也有闲情,山伯也有逸志,山伯也不时如若东坡聊发少年狂。山伯业余唯一爱好,就是仿效沫若、老舍、梁实秋打打小麻将。很多时候,他都仅仅邀约到林彦公刘(扬烈)教授。于是,山伯就会发挥他的权威,一个电话打到了那边厢:“四娃子,我们这里三缺一,你赶快来救场,救场如救火哟!”
四娃子者,著名诗人范明也。可爱的山伯有所不知,每一次救场的范明每每接到山伯的电话总会面临一连串的“不得不”因之总会于心深处暗暗叫苦:第一,山伯的麻将价码是一炮两角钱,这与范明的麻将价格尚有不小的差距,所以,范明不得不推;但是面对山伯的“发号施令”,作为山伯弟子与世侄的范明又不得不来;(山伯与范明之令尊甦伯即杨甦乃多年世交)上场之后,懂事明理的范明为让老爷子高兴,又不得不输;输了之后,范明还不得不承受山伯善意的奚落。赢了七八毛钱的山伯一脸写满了欢喜与得意,有板有眼地训戒说:“四娃子,莫要搞忘了,生姜还是老的辣也!”此时的范明还不得不强颜为欢,频频点头只称是。
山伯的可爱,还在于他记性无比的好,同时忘性却也非常之大。这好像是一种悖论,然而,奇怪的是,这悖论居然就于山伯一生并行不悖。所谓山伯之记性无比的好,是指他创作、编辑诗歌几十年来,他的诗稿与作者的诗稿他从来没有弄丢过一首半首。就在他那杂乱无章的以客厅充作的多功能厅里,无论是哪个作者走到屋里来问起诗稿,他都能够很快找出来访作者的诗稿。他不仅能很快找出来访作者的诗稿,而且,他还能就这位作者的诗稿说出其利弊得失一二三。然而,说到三伯忘性大呢,那就跟生活中丢三落四的陈景润好有一比啰。长于此,必然短于彼,伟人大约都如是。每遇刮风下雨,山伯出门参加文坛聚会,每一次回家他都必然丢一样东西,必然丢失的东西就是那一把伞。从这一特殊的层面上看,山伯也为重庆文坛贡献了不知道有多少把伞哦。落了一把又一把,落了一把又一把,丢丢落落,落落丢丢,无穷匮也。山伯得诗,首首出新。山伯丢伞,了无新意。所以,每一次兴邦把外出参会的山伯送回家,讨好卖乖地对咏梅师母说:“师母,我把山伯完璧归赵了哦。”师母都会抢着诘问:“山伯回不回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把伞回来没有?”结果,每到这个时候,山伯就会像个做错了事的三岁顽童一样,面露愧色地唯唯诺诺道:“哎哟哎哟,啷个的嘛?又搞忘了又搞忘了! ”然后迅即地转身,疾言厉色地斥责: “兴邦!我跟你说记到记到,你啷个又没有记到嘛?!”
山伯斥责得煞有介事。那光景,好像丢伞的责任全在兴邦,他山伯自己,断无丝毫责任。
山伯哟山伯,说到此,我突然萌生了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打算将一把精致的伞送到您的墓前。您不出門,这把伞就为您遮风祛寒;您若出门,这把伞就为您挡雨驱雪。
山伯,说到底,我多么渴望成为陪您伴您千秋万代的那一把伞!
印象之三 可亲的山伯
山伯待我乃弟子,待我如嗣子。仔细想想,我于他老人家门下执弟子礼于他老人家家中执儿子礼,已逾四十个春夏秋冬的周而复始也。
初识山伯是在白纸黑字之间。那是在大中国万马齐喑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的文艺百花园,虽正值高天滚滚寒流急,却也时有大地微微暖气吹。作为文学青年的我,在刚刚复刊的《四川文学》及《重庆日报》刚刚恢复的副刊之上,偶尔读到了山伯的几首小诗。诗的内容,已记不得了。记得的是,诗显得极精粹,极精美,每行诗的音步也极少,多则两三步,少则一步甚至只有一个字。由是,我记住了一个诗人的名字:杨山。
自此,我同山伯的交往一发而不可止,这着实让我始料未及。
经诗友的引荐,我很快结识了山伯,而且也很快成了山伯家中的常客。于是,在我于重庆石棉厂做学徒工的时候,每逢周末,我都会揣着我的诗稿去拜访山伯,听他对我的诗稿横挑鼻子竖挑眼。稍后,在我于西南民族学院读中文系汉语言文学的时候,每逢寒假暑假返渝探亲,我都会揣着我的诗稿去拜访山伯,听他一如既往地对我的诗稿横挑鼻子竖挑眼。再后来,我大学毕业进了《红岩》文学杂志社,成了编辑也成了山伯的同事,继续聆听山伯对我的诗稿横挑鼻子竖挑眼。虽然我同山伯相交渐深渐笃,虽然我自山伯的弟子嗣子转而又有幸成为了山伯的同事,然而山伯对我严之又严的要求,从来就没有打过毫厘的折扣。因之,我的诗稿可以走遍大江南北可以刊发于国内诸多报刊,却就是很难刊发于他老人家先前主持的《红岩》诗歌版以及他老人家后来主持的《银河系 》诗刊。山伯评诗一般很简约,简约如他的诗,好与不好都是一句话。如果诗不好,那他就会说一句:“张华,你这个诗单薄了也。”那一个“也”字,悠长悠长,余音袅袅。一听那余音袅袅的“单薄了也”,我就会紧张,我晓得,我的的诗作已被枪毙了;如果山伯说:“张华,你这几首诗就要得噻”,那一个“噻”字,依旧悠长悠长,余音袅袅。一听那余音袅袅的“就要得噻”,我就会窃喜,我知道,我的诗稿一定是进入了他老人家的法眼了。果不其然,我那几首山伯所谓的“要得噻”的诗,转眼之间,便刊发于那一期的《红岩》杂志上。
记得有一次,在山伯家里,他问我:“张华啊,你看到最近范明发的那组诗没有?”我回答:“看到了。”他就接着又问:“你觉得哪一首最好?”我回答:“《跋涉者》”。山伯一边点头称是,一边居然就抑扬顿挫且朗朗上口地背诵起来:“旅行袋破旧了,/岁月在脚下遗失。//昨天,我寻找友谊,/得到告密的状纸。/我寻找财富,/得到镀金的假币。/我寻找真理,/得到假冒的圣经。/我寻找光荣,/得到耻辱的印记。//旅行袋破旧了,/也许,该寻找客栈休息?//不!/我寻找心,寻找爱,/寻找邂逅的热泪。/我寻找矿藏、寻找火,/寻找钻杆的旋律。/我寻找灯、寻找剑,/寻找传教士法衣后的秘密。/我寻找诗、寻找歌,/寻找信仰山岳的阶梯。//旅行袋破旧了,/我的追求不会在失败中死去。”诵毕,山伯一声感慨:“范明这诗就要得噻,要得就要得在一个真字!”
山伯一语,点醒我这个梦中人。
山伯提醒我,山伯教诲我,作诗,须以真为上,须以真为先。诗人,要敢于说真话,要敢于吐真情。如此这般,诗作,才具生命活力才可永垂不朽。
这一刻,严竣的山伯山伯的严竣,悄然走进我心深处……
那般清静,那般亲近。
责任编辑肖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