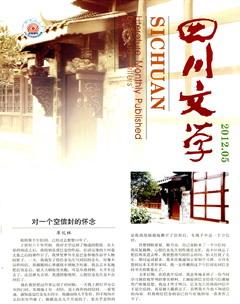草原往事
徐岩
1
从来没有去过海拉尔,那个被称为草原的地方。
可三哥总是跟我念叨它,说那座城市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安静。我的脑海里就时不时地浮现出小学语文课本里学过的一些美好的诗句,比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是我哪有时间去游山玩水呢,就把这个去走一走的念头在心里边搁着,姑且当成打算,寻找机会去。可是事情有时候往往会朝你思路的反方向发展,越是不想理会的东西却越是找上门来。这不,这个周五的早上,小胖就打来电话说三哥突发脑溢血住院了,念叨你和老五俩。小胖是三哥的司机,跟三哥在海拉尔包工程有几年了,跟亲侄似的。我说你给你五叔打电话了吗?小胖说没有,你们联系吧。
我忙给在区税务局当副局长的老五打电话,说了三哥住院的事,我特意强调人是昏迷状态。老五嗓子沙哑地说,咋搞的,肯定是酒闹的,喝起来不管不顾的,老是玩命。我心里想你小子也是他妈一路货色,不喝酒却吸烟赌博,大清早的嗓子便跟鸭子似的。人那,总是老鸹落在猪身上,看见别人看不见自己。老五在电话那头接着说,九点钟在公路大桥集合,我开车去,总比火车要快一些,去早了说不定能赶上三哥立遗嘱。我说小王八羔子,少来你那乌鸦嘴。老五临撂电话时跟我说,把小七叫上吧,三哥最得意她了。
九点一刻,我们四个人乘老五的黑色本田离开市区,走松北镇经大庆直奔海拉尔。车上除了小七申玲外还有另外一个年轻女人,披肩发、圆脸,很俊气,是我從没见过的。我以为是老五的老铁或朋友之类的,也没多问,只是跟坐在身后的申玲说三哥的事。申玲是我们几个大学同学中最小的一个,在有线广播电台做播音主持,活泼、开朗,至今仍是独身主义者。有一回哥几个喝酒,都追问小七啥时候嫁人,举着啤酒杯子猛灌的申玲哈哈笑着说,她要嫁也得嫁一个像三哥那样的男人,小七的话说得语惊四座。
车过带岭之后进入了山区,柏油路也变成了沙石路,而且明显窄了些。老五一边开车一边接听频繁打进来的电话,竟把车子开得晃起来。坐在他后座的那个梳披肩发的女人把手搭在了他肩上,轻拍了一下。老五便靠边把车停了下来,随后,司机就换了人。女人神情专注,把车子驾得很稳,就连转弯时我们都感受不到颠簸了。我想这女人还真有两下子,把偌大一部进口轿车驾驭得得心应手。
借抽烟点火的机会我侧着脸看了她一眼,竟很文质彬彬一个人,她也侧着脸回了我一个妩媚的笑。我忽然间心里窜出一个想法,她会是老五的情人吗?老五虽算不上什么俊男,但这两年仕途上却正是春风得意,税务局可是交人的单位,上上下下都被他捋顺得极其得体。我闭上眼睛沉思一会儿,想努力从记忆里搜索出三哥孟庆余的模样,图像却总是模糊的,影影绰绰的,一点都不亲切。可以说,作为我来讲,自己是欠三哥人情的,在大学当老师评职称时是三哥帮着找的人,要不然你永远都得往后排,即便是你工作干得多么多么出色,或者论资排辈排到了,也不一定是你。但是,三哥这几年盖大楼当包工头钱是赚足了,可人也见面少了,拿老五的话说,整天花天酒地,商场战场的哪还顾得上咱们哥们。
2
三哥跟三嫂离婚那天,三嫂请我和老五、老六、小七吃了顿饭。是城南那家饺子馆,她点了我爱吃的红烧肉、老五爱吃的五香干豆腐和老六、小七喜欢的女式菜锅包肉。还点了三哥平时得意的下酒菜芹菜炝花生米。三嫂端着酒杯说我跟你们三哥是好离好散,不存在别的问题,现在他钱挣大发了,我也真不想跟着他操心了,但你们日后还是我的好兄妹。
那是两年前的事,三哥跟三嫂离婚,把哥几个都喝多了,下雨天啊从饺子馆出来谁都没坐车,就那么扯着胳膊在大街上走,差点被警察当成醉鬼。那之后,三嫂带孩子回了老家桦南县的丁家堡子,老六谢小丹也去了上海,在一家广告公司做业务员。
之后就是三哥二婚,从海拉尔用大卡车拉回来十只羊一头牛和三头猪,雇人统统宰掉在城郊的农庄办酒席。就跟乡村的婚宴一样,露天地里摆了三十张桌子,大盘的盛肉,大碗的斟酒,那排场简直吓唬人。可婚礼只有老五一个人帮着张罗,老六和小七都没有到场,她们是生三哥抛弃三嫂的气。我因为出差去河南没有赶回来,就给小七打电话,求她帮我补礼,可小七说人家孟庆余可是腰缠万贯,会在乎你那点钱吗?我说他的钱是他的,我的是我的,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不是重吗。小七说她不管,她连去都不去,咋帮人随礼呀。没办法我只好又求老五,总算是尽了一份兄弟之情。
后来老五给我打电话惊呼,说三哥二房娶了个瘸腿女人,还拄着一只木拐呢。我说别他妈瞎掰,就你在场,开不得玩笑的。老五在电话里赌咒发誓地说他如果有半句谎话,开车翻沟里。我说你就乌鸦嘴,不亲眼见到谁会信你个臭收税的。没想到老五说的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三哥真就娶了个瘸腿女人,他在婚礼上曾经动情地说,这辈子他孟庆余不会再爱任何一个女人。
三哥回海拉尔后,我出差回来给他挂了个电话,说挺遗憾没能去帮他端盘子敬大家伙喜烟。三哥说你小嫂许诺了,有朝一日你们去海拉尔的时候,她会亲自下厨房给你们做红烧肉吃。我说她也知道我爱吃红烧肉?三哥笑着说,我念叨的,她看过你们几个的照片。
三哥结婚半年后的一天,我跟老五、小七一块吃饭,小七说他妈的农村土包子一个,有多少钱能咋,就是天天吃海参,说话也免不了大碴子味。我们仨分析三哥和小嫂缘何能走到一起,小七说那女人虽然瘸但人长得却漂亮,说不定是个小妖精呢,两人勾搭到一块后她才碰上什么事把自己弄瘸了。老五说有可能,小七这说法不排除是正确答案之一。我说等有机会三哥会跟咱们说清楚的,他虽说是从农村考上的大学,智商却不低,要不做买卖怎么能挣到钱呢。
3
车到加格达奇境内时,老五提议找家小饭馆填饱肚子,说再往前走就是莽莽林海了,怕找不到地方吃饭。梳披肩发的女人把车停在道边的一家小饭馆旁说就这家吧,有面可吃。小七说姐姐怎么知道有面可吃?披肩发女人拿嘴朝小饭馆的墙上一努说,有字写着呢。果然泥抹的墙皮上有杀猪菜和手擀面几个白漆的大字,里倒歪斜的写得很清楚。
老五说就吃手擀面了,吃完了早点赶路,看来今晚得在乌鲁布铁住一晚了。
小七说住乌鲁布铁好,那个小镇子太干净了,晚上可以听松涛的回响,简直太美了。
我说你住过那儿?
小七说当然,好几年前了,也是跟三哥开车回海拉尔,还有二哥。老五一边掏烟卷吸一边插话,你那时正和老二谈朋友吧。小七没言语,脸上却罩上一层黯然的阴云。老二叫夏雨,是我们拜把子的大学同学里面长得最漂亮的一个,学习成绩也好,不知怎么大学毕业却选择了当兵,叫大学生转现役。谁的劝说也不听,毅然决然地背行李去了内蒙古边境,当了名中尉军官。小七当时正在追他,两个人也很要好,但老二的选择却无形中在两人之间矗起了一座大山,相互间隔开了。你想想两个省份,相隔万里,又是省城和边境之分,因此,便疏远了。老二最终在满洲里附近找了个女医生,在边防扎了根,而小七至今未嫁。
乌鲁布铁的确是个美丽的林区小镇,在黄昏的光照下十分可爱和生动。我们按小七的意思住进了山脚处的空中木屋,正好是两人一间房,两男两女分开住。等行装安顿下来之后,老五便开着车拉上那个披肩发女人去河边洗车了。小七跟我说,这大山里还有河吗?河边的景色一定很美。我说要不你也跟着去看看吧,据分析有山必有河,而且河流都是顺着山势走。小七嘟哝着说,瞧老五那德性,咋会带上我,生怕坏了他的好事。
我说申玲你不要任性,那女人说不定跟老五没什么关系。小七瞪大了眼珠子显出一分少有的惊讶来说,不会吧,老五的人品你还不知道吗,残花败柳都不会放过的。我说过去的事少提,人都是在进步的,他现在不是改很多了吗。小七一边穿外套一边说,狗改不了吃屎。
在她的提议下,我陪她去镇上走走。
黄昏的初始美已经过去,太阳只剩了一个小火球径直往山的坳处落去,夜色即将来临。这个小镇其实只是个林业作业组,有个二三十户人家,都住著简易的木刻楞房。或者是原木垒的,或者是板夹泥的,规整简约,富有生活气息。
走出镇子一头是一条沙石路,路旁是变了颜色的艾草,有红黄和暗绿三种,哪一种都呈现着颓废。夜色深一些时,小七和我的身子挨近了,继而又拉住我的手说,三哥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我说就是生病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能挺过来的。再说了人都有生老病死,有啥可怕呢?
小七的手细腻温软却冰冷,抓在手心里像攥住了一小团积雪,拉着她感觉到她整个身体都在抖颤。
我在小七的房里呆到九点多,老五和那个女人才开车回来。老五随我回到房间时跟我说,三哥和小胖的电话始终都打不通。
我说大山里信号就是不好。
4
这个晚上我失眠了,就是因为三哥。
在大学那几年里,我们情同手足,也同甘共苦,七个人像亲兄弟。除了老大读研究生出国之外,其他几个人都保持着很好的联系。将近二十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三哥凭借着自己的打拼成了暴发户。可是有钱人也不好当啊,钱多了也是烦恼,拿三嫂的话说,富贵踅摸淫事,你三哥他有俩臭钱便不是他了。那句话应该是“富贵思淫欲”,他却把思字改成了踅摸,你别说还真挺通俗易懂的。
记得有一次我跟三哥在城里的一家酒馆喝酒,他感慨着说,他就是吃农村粮食的命,要是有一天看不到绿油油的庄稼棵子或者瞧不见松软无际的泥土,他的心会觉得空落落的。我说三哥你是酒话,我不相信。他说为啥呀?我说那三嫂怎么说,三嫂也是实打实的纯朴呢,你咋还说甩就甩呢?三哥的脸上多了层红晕,他把杯中的剩酒喝进去后说,那是一言难尽。
那一次他跟我透露了和三嫂之间发生的一件事。两人结婚后生了个女孩,三哥为满足老娘的愿望一直想再要个男娃,给他们老孟家留个后。可三嫂却在怀孕期间知道了三哥在外面除她之外还有女人,于是就偷偷跑到医院去做掉了。等三哥知道事情真相后气得摔杯子砸碗的,竟一气之下不回家了,也就导致了后来两人的分开。
那一回三哥喝酒时是这样跟我说的,可老五对这件事情也有见解,老五的说法更是令人费解。他说三嫂之所以要坚决地做掉那个孩子,原因很简单,那孩子不是三哥的种。我说你别瞎掰啊,小心风大苫了舌头。老五却告诉我孩子的父亲是万传海,三嫂开的五金商店雇的司机。万司机我见过两回,比三嫂年龄小上几岁,黑黝黝的脸孔,说话之前先笑一笑,给人憨厚的印象。家也是乡下的,来城里打工,因为跟三哥建筑队里的一个项目经理熟,就被介绍到商店里开车,跑销售和进货。我说三嫂凭啥告诉你这个呀,三哥知道吗?老五说不知道,三嫂找他问三哥外面有女人的情况,还亲口说出来两个女人的姓名和基本情况,看来她都掌握了,是准备要跟三哥摊底牌的。我说那三嫂干嘛要把她跟别人生娃的事告诉你呢?老五说就是为了让咱把口风透给三哥呗。这个愚蠢的女人,不怪她是乡下人,一点脑子都没有。我晓得老五看不上泼辣朴实又头脑简单的三嫂,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对其有成见,表现很明显,那就是每回三哥在家里招待饭,他都会借故把饭局推掉,轻易不登三哥家的门不吃三嫂烧的菜。
我曾经劝过老五,毕竟要看三哥的面子,三哥对咱们哥几个都不薄。比如说你老五从税务所调往分局的时候,人家三哥还不是掏了腰包的,要不你拿啥送礼,又怎么能提升呢?老五说事都在心里,可那女人竟拿屎盆子往自家人身上扣。
我说你一个国家干部咋就总跟一个家庭妇女计较呢?
5
有一回小七申玲请我和老五吃饭。她说认识个男人,是个警察,离过异,正追求她呢。之所以请我们饭,就是她拿不定主意了,让我们两个哥哥给她把舵。小七边说还边从兜子里掏出张照片来把那男人指给我们看。是个比她大好几岁的矮胖男人,眉眼倒是有些棱角,就是面相老了些。
老五当时皱着眉头说,妹妹你是找哥啊还是找爹呀,一个黄花大闺女找啥样的没有,这不是犯贱吗。我拦着老五没让他再说更多难听的话,问小七他们相识的经历。小七滔滔不绝地如实说来,竟吓了我们两人一大跳。
那男人是个刑警,一月前在破获城西系列抢劫案时救了小七一回。算不上英雄救美,但也有嚼头。小七说当时她随台里的摄像师跟着警队去抓捕一个犯罪嫌疑人,进行所谓的现场报道,爬楼梯时小七因为紧张崴了脚,并摔一跟头。带队的人就让那男人把小七先背回楼下的警车里。为此那个男人很生小七的气,嘴里唠叨着说你们女人就是麻烦,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把小七背到车里后竟锁了车门跑回去参加行动去了,落得小七一人孤零零地叫唤。
可还不到两分钟那男人又跑了回来,发动火驾车把她送到了附近医院里,男人依旧是满嘴的牢骚。把她从车上扶下来,再背到三楼的处置室,把她交到医生手里才走。小七说最让她感动的是这个警察男人还替她在楼下的挂号处交了三百块钱押金。
我问小七后来怎么着了?小七说后来她找那个警察还钱时知道那个犯罪嫌疑人抓到了,因为手里有枪,抓他时有两个警察负了伤,但却立了功。那个背她的警察跟她开玩笑说就怨小七,如果小七不生事他不也成功臣了?小七说那警察男人说话还挺幽默,人也憨直得可以。
我说你们认识得倒有些戏剧性,警察的职业也挺稳定,我看倒可以考虑,你不妨跟他相处一段时间,若满意就把自己嫁掉算了。
后来就再没有听小七说起过,其实也不用问结果,两人自然是没成,要不小七到现在咋还是单身族呢。昨晚小七跟我说起了那个警察,说他也在海拉尔,是半年前去那里任职的。我说是基层挂职锻炼呢还是提职呀?小七说不知道,只听人说他下去挂职了,兴许是提了。
我说你们俩说不定真就有缘分,抽空见他一面,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小七笑着说,那老哥回不了省城就惨了,那就得跟着他扎根边疆干革命了。
6
下午三点钟,车驶进海拉尔市区,我们把草原的影子甩到了身后。海拉尔这座新兴的草原边城到处都是正在建筑的楼房。有成型的,也有正盖一半的,到处都是堆积的砖瓦水泥,怪不得三哥也把建筑的摊子铺到了这座城市呢。
三哥的司机小胖在城门口接住了我们,他一见面就掉眼泪了。老五扯着喉咙跟小胖说,别挤猫尿,咋回事快说。小胖扶着车门子拿衣袖擦眼睛,然后说三哥就剩一口气了,正在市医院抢救呢。我坐进小胖的汽车,在前边带路,两辆车一前一后驶进了市区,直奔城西南角的医院而去。在车上小胖简单跟我说了三哥住院的经过,三哥没什么病,只是因为拖欠民工的工钱而逼得那些民工造反,其中有两个领头的爬上了工地旁的一幢大烟筒,害得三哥动了气,他正好喝酒回工地,便在喊闹事工人不听的情况下,亲自爬上了烟筒,想把那两个人拉下来,却没抓稳,从半截腰掉了下来,摔成了重伤。
我说三哥咋这么傻呀,欠人家钱给就是了,跟着爬什么烟筒呀,都四十好几的人了。
小七在一旁边掉眼泪边说不值呀不值。小胖说关键是三叔手里没有现金,几百万元的工程款也压着拨不下来,都急死人了。
我们哥几个赶到抢救室后,三哥刚下手术台,脸色极其惨白地望着我们几个。从绷带中露出来的两只眼睛浑浊无光,只是不错眼珠地看着天花板。医生告诉我们他绝对不能多说话,至于能不能保命还在观察中。
我们进病房没多久,三哥后娶的那个瘸腿女人从外面进来,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记满了密麻麻的数字,她坐下来抹着额头上的汗水念给三哥听。好半天我们才弄明白那是往来亏欠的账目,一笔一笔写得十分地清楚。念过一遍之后,瘸腿女人问三哥说是这样吗?三哥想了会儿才点了头。之后他接过瘸腿女人递给他的一支笔在那几页纸上签了字,方艰难地跟我们几个一句句说话。三哥说他不是别人想象中的坏人,在他手下干过活的绝大多数农民工都解决了生活困难,只是今年这几幢楼盖得艰辛,楼起来了资金却迟迟不到位,压得手下的那些民工也不耐烦继而酒后闹事了。
三哥的脸色很不好看,他趁瘸腿女人出去时跟老五说,有点钱他存在了城里的一家农村信用社,不用折子,只要写对名字和密码就可以取,就给你三嫂吧,这事你去办,然后他跟老五说了密码。
小七拉著三哥的手哭个不停,她说三哥你别那么伤感,没有事的,养段时间就会好起来的。
三哥还想说什么,却被进来的医生劝住了,那个戴眼镜的医生把我们推了出来,说病人刚做完手术,需要的就是休息,身子太虚了。
我们几个人就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等,我和老五一根一根的抽烟,小七到院子里面去了。医院的走廊里暗淡无光,赶上日头偏西,白天的嘈杂也跟着静下来。
我跟老五说,看情形三哥没事,话说得有条有理。老五说,不见得,病人总是有回光返照一说。我在心里想,要是真的这样,那对三哥也太残酷了些。从一个乡下孩子念完大学,再舍弃工作搞个体建筑,钱有了腰背也弯了,本该再奋斗个三年两载的,就能歇手享享清福了,却赶上这无端的祸事。三嫂倒是行了,经历了婚姻的破裂,能承受得住。可那个刚刚跟他步入生活的瘸腿女人咋办?
天更暗些时,瘸腿女人从病房里出来,跟小胖说,三哥让你带几位叔叔去水晶宫吃饭。顺便把那里的陈账清了。瘸腿女人说着就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小胖,之后她冲我们几个笑笑说,抱歉呀她得陪着三哥,就不能招待你们哥几个吃饭了。
我们出医院大门,没有随小胖去水晶宫吃饭,尽管那里是海拉尔最高档的酒店,但谁也没心情。老五拽上我和那个梳披肩发的女人开车去了城南甘河边上的一家削面馆,每人一碗刀削面,吃得沉默不语。
一碗面吃完时,小七打来电话问我们在哪儿?问完之后要赶过来。我说你这疯丫头,究竟跑那去了,只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你人影了。小七说别啰嗦了,见面再说,她有急事要跟哥几个说。
十几分钟的光景,小七推门进了削面馆,她身后还跟着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男人。两个人坐下来后小七把那男人介绍给我们竟是追求她的那个警察老范,目前正在海拉尔代职锻炼,任市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7
老五一边吃面一边埋怨小七,都啥时候了还有闲情逸致出去转悠。我们都知道老五的话里所指,可小七却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三哥犯有行贿罪,他一旦病好,公安机关就会收网抓他。
之后,警察老范跟我们讲了三哥涉及的几件事,听得我们真是目瞪口呆。为了几幢大楼盘的夺标,三哥竟不惜代价送礼几十万元;为索要工程款,花重金从南方雇请漂亮女孩投其所好;就连瘸腿女人的舅舅也因为收受三哥的贿赂而被政府免了职,三哥是因为内心的愧疚才娶了瘸腿女人。
老五问那个警察,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警察说他看过立案的材料,判个十年二十年不成问题。老五说那现在怎么办?警察说,鉴于他的病情,公安机关目前还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但已派人对其进行监视。小七插话说三哥一定还不知道公安机关介入的事。我说三哥没那么简单,他肯定全都知道,你没看见他把一些事情都交待好了吗。
几个人都开始沉默不语。
最后是老五说了话,老五说问问三哥要不要把他的家人接来见面。
小七说这件事她去问。老五还提出来跟办案的警察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把三哥接回省城去治疗,医疗设备好医护力量强是一方面,他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如果一旦三哥医好了,警方便也可以办案了,这是个一举两得的法子。
可最终老五的提议没有被警方批准,三哥只好继续留在海拉尔治疗下去。
8
由于工作原因,我和老五先开车回省城,留下小七和那个梳披肩发的女人帮着看护三哥。
路上老五问我那个梳披肩发的女人咋样?我说挺好一个女人,温顺又不多言多语,看来是个贤妻良母。老五笑了,他边把着方向盘边点燃了一根烟,美美地吸两口后对我说,就是就是,一个不错的女人。我不无嘲讽地笑笑说,真拿你们这些腐败分子没办法,吃着锅里的惦念着盆里的。
老五摇开车窗,将吸剩的烟头扔出去看着路的前方说,你兄弟哪有那份闲心呀,告诉你吧,是三哥的相好。我惊愕得差点没咬了舌头,说这可能吗?老五随后把真相告诉了我。梳披肩发的女人叫王小丽,是个幼儿教师,跟三哥已经好了五六个年头了。她之所以能够爱上貌不出众的建筑老板,就一个原因,她说三哥这人心好。三哥义务扶养了两个孤儿,都寄养在王小丽工作的幼儿园里。三哥在城里盖房子时每周都去一次幼儿园看那两个孩子,而王小丽就是那俩孩子的辅导员老师。一来二去的三哥接孩子回家或出去下饭馆,有几回把王老师也带上了。
我插老五的话说,那女人出于感动而爱上了财大气粗的建筑商,这倒是一个很值得小七她们电视台宣传的新闻素材。
老五说你别把人家女人想那么坏,她跟三哥好上之后,竟没跟三哥要过一分钱,你说这怎么解释?我说女人家里也是富裕的呗,人家不缺钱。老五说笑话,我跟三哥去过那女人的娘家,在郊县的一个小镇子,她母亲家务,她父亲是个邮电局职工,至今还住着两间平房。
我说那她图什么呀,这世上怪人还真不少。老五说她是可怜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三哥养的那两个孩子起先是住校的,后来就跟着女人回家里住了,当然生活费是三哥出的。我说这不过分,那她就这么不讲名分吗?老五说是,她有男人,在监狱里服刑,她说她男人是酒后误伤了人才进去的,她得等他出来。
我说三哥他累不累呀,就这么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的。老五说能不累吗,啥事都得摆布好,这不都累到医院去了吗。
我接着问老五说,王小丽的身世三嫂和瘸腿女人就不知道吗?
老五说不知道,她们都被蒙在鼓里。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快晌午了,找地方吃饭,这时间怎么过得咋这么快。
老五说是啊,人的一生啊就是他妈的弹指一挥间,转瞬即逝。
9
四天后,我跟老五又开车去了海拉尔。这次我们走得没有那么急,因为小七来电话已经哭着告诉我们三哥的死讯。三哥手术后在病房里躺了整整五天半时间,离开了他为之拼搏奋斗了三十九年的人世。三哥临死前说的一句话是,他想念人世间所有的亲人。
我的眼睛湿了,为我的同学加兄弟,他的少年时代和中学时代一直在黑龙江一个叫拜泉的小镇里度过,然后是省城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就在那个时期相识相知,可以说他吃了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两年多的饭票。后来做建筑商在城里或者周边的城镇盖大楼十五年,挣了几百万的钱(真正多少无从考证)却没见到他怎么花,最终以悬挂飞翔的方式告别了尘世。
在三哥的遗体告别式上,我见到了那两个被他收养着的孩子,都六七岁的样子,他们穿着整洁而干净的衣服,面色红润,眼泪像珍珠般滚滚落下。他们的手被那个叫王小丽的梳披肩发的女人拉着,认真地向躺在棺杶上的三哥的遗体鞠躬。
还有特意赶过来的三嫂和一些亲友,悲哀的神色洇在他们的脸上,使人不忍卒读。
最后面还有一大群农民工模样的人,他们也都默默地低着头,不吭气。
丧事后我们帮瘸腿女人送走了捞忙的人,也告辞回省城,路上小七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她哽咽着跟我们几个说,是三哥留给我们的钱,瘸腿女人交给她的,哥几个每人两万,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老五说他不要,那可是三哥的血汗钱。我也表态说不要,钱有多少是多呢,多了多花,少了少花,人咋都是一辈子。小七说她给在上海的老六也挂了电话,她的意见和你们哥俩一样,既然大家都不要,咱就想个办法把这笔钱派个用场吧。我说三哥他义务扶养的那两个孩子有份吗?小七说三哥给王小丽留钱了,特意交代了有那俩孩子的费用,这就不用咱们操心了。
好半天,开着车的老五说卡里有多少钱?
小七说十万块。
老五说可惜三哥的父母都不健在了,要不给他们正好,名正言顺。
老五又问小七说,他还欠农民工的钱吗?
小七说不欠,她特意问了三哥工地上的总监工老刘和小胖,三哥住院后,建设单位的老板慌了手脚,马上给结了积压大半年的工程款,早早就把拖欠工人们的工钱结算清了。
老五说,那就把这笔钱存起来,等日后找个适当时机给三哥修个墓。
我说这主意不错,想必三嫂和瘸腿女人有这想法,也不一定张罗得起来。
小七也点头表示赞同,这个计划就定下来了。
我们开车出海拉尔城区时,老五摇开车窗玻璃说,路边上的那两幢楼都是三哥盖起来的,你们瞧瞧,有多气派。
我和小七顺车窗朝外面望去,见路边上果真有几幢刚刚竣工的高楼矗立着,醒目而伟岸。那拔地而起的楼面上有大幅的“龙江银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字样。
我们的心禁不住忽然间就有了无限的酸楚。
我想,那楼兴许就是三哥单薄又羸弱的骨骼吧?
责任编辑聂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