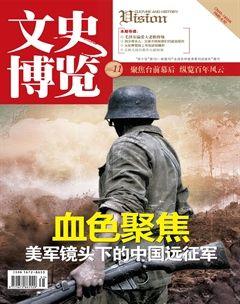那一年,我从造反派手中捡了一条命
1949年9月,我进入长沙的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政保科工作。1963年2月,长沙市公安局党委决定在望城县坪塘镇利用“大跃进”大炼钢留下的厂房,组建强制劳动(简称“强劳)单位——长沙市红砖厂。我请缨前往,加入了针对强劳的教育改造队伍。
1966年6月,“文革”开始。社会思想意识逐渐出现混乱,活跃于各个舞台的造反派主张“无产阶级”登台,仇视一切“资产阶级”事物,“公检法”(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被其列入资产阶级队伍,喊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全国各地出现多个组织,进行打击“公检法”活动。我所在的强劳单位,许多强劳人员也开始骚动,想方设法与狱外造反派进行联系,脱逃事件屡屡发生,管制工作难度愈来愈大,干警与强劳人员之间矛盾丛生。
由强劳单位所掌控的犯罪证据材料对于逃脱的强劳人员来说至关重要,这关系着他们的历史清白问题。于是我向上级反映,建议将单位的重要文件和强劳人员的档案深夜转移,并参与了档案的转移工作。可是,这也招致了强劳人员的强烈恨意。此时,传来消息,说兄弟单位有三位同志被造反派强劳人员抓获,不久即遭乱棒活活打死,惨不忍睹。为避免锋芒和伤害,组织决定让单位人员都暂时回家规避。
回到株洲老家后,我对单位和工作总是牵肠挂肚。一天,终于忍不住闲着,带着我爱人和舅舅一起来到株洲市里了解形势,不料却大祸临头。三名流窜到株洲的强劳人员认出并盯上了我,伺机将我抓获,并立马进行严控,追逼档案去向。造反派强劳人员致电长沙“头头”,说逮住一条“鲨鱼”——教育股血糊袋子(档案)的掌管者,要求派车来,将我接到长沙审讯。恰逢当时长沙方面没有车,公交又中断,于是我一直被监控在株洲。在被監控的那些日子里,我完全失去了自由,甚至大小便也有人跟着,晚上睡觉四人同房,还关门落锁,毫无空隙向外透露消息。
而当时没有被认出来而侥幸逃过的我爱人与舅舅则心急如焚。他们深夜找到株洲市军管会,哭诉情况,要求营救。军管会当即派遣两位同志连夜找到造反派驻地,询问情况,讲述政策,希望他们能够迷途知返。可是效果并不明显,造反派强劳人员仍然对强劳单位干警十分仇视。军管会同志只得暂时放弃劝说,离开时,他们想要带我一起走,可是未能成功。当时军管会并没有绝对权威,我深知即便能够跟他们离开,造反派也不会善罢甘休,第二次被抓的话情况会更糟,只有自己慢慢伺机逃脱比较保险。
一天,株洲市数万人游行示威,大街小巷人头拥挤,混乱不堪。造反派强劳人员要到某地去取枪支弹药。为保险起见,便将我交给驻地值班人员。我在值班室佯装犯困,倒在值班室内的长椅上睡下,不久便“鼾声大作”,一副睡得很熟的样子。值班人员见此情形,便放心地走出办公室去上厕所。我感觉时机到了,趁机狂奔出值班室,窜进人群之中,一口气狂奔七八里,跑到舅舅家里,得以安全脱险。
我的逃脱实属奇迹。后来,一位知情者见到我还战斗在政法部门,不由感慨万千:“你还活着,万幸万幸,你在株洲被抓,长沙那伙歹徒挂出了‘刘文焰必死无疑的大横幅,只要你被抓到长沙,肯定见马克思去了!”回想起过去种种,我也无限感慨。我深知干革命哪会不担风险,只希望好人一生平安。
(责任编辑/木夕)
(电子邮箱:dyy101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