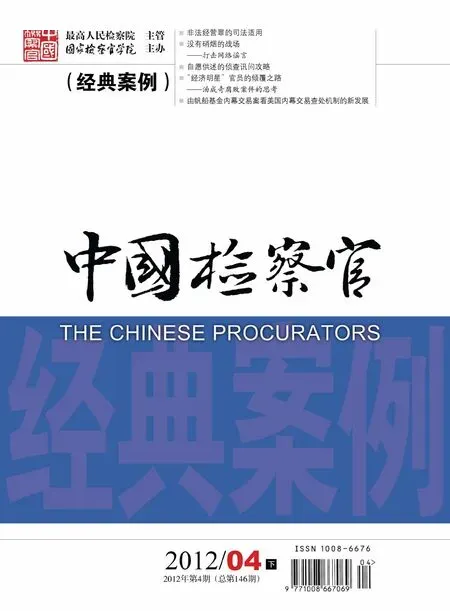上游犯罪数额未达起刑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否成立
文◎王珊珊
上游犯罪数额未达起刑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否成立
文◎王珊珊*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付某,男,年龄46岁,小学文化程度,收废品个体户。犯罪嫌疑人李某于2011年5月11日,在北京市西城区菜市口地铁西南出口中国移动大厦门前盗窃被害人倪某电动三轮车电瓶2个(8块),经鉴定价值人民币672元;2011年5月17日,犯罪嫌疑人李某在北京市西城区菜市口同仁堂药店门前盗窃被害人郭某捷马牌电动自行车电瓶1个,价值人民币96元;2011年6月13日,犯罪嫌疑人李某在北京市西城区菜市口地铁西南出口中国移动大厦门前盗窃被害人王某都市风牌电动自行车电瓶1个(4块),价值人民币144元;2011年6月16日,犯罪嫌疑人李某在北京市西城区椿树馆街14号院门前盗窃被害人赵某新日牌电动自行车电瓶1个(4块),价值人民币240元后被民警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付某承认于2011年6月9日及6月13日共三次收购李某盗窃所得电瓶的犯罪事实。其中付某前两次收购李某盗窃所得电瓶,经查证分别是被害人倪某丢失的电动车上的电瓶和被害人郭某丢失的电动车上的电瓶,经鉴定共计价值768元,而付某第三次永收购李某盗窃所得电瓶现没有找到被害人,无法完成价格鉴定。本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以被告人李某涉嫌盗窃罪,被告人付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1年9月向地方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2011年12月20日地方检察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之规定,提起公诉。2012年1月5日付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地方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二、分歧意见
上游犯罪数额未达到该类犯罪的起刑点,作为下游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否成立?
第一种意见认为,付某收购他人盗窃而来的财物,可以确定价值的两次盗窃的数额未达到盗窃罪数额较大的起点[1],即前盗窃行为尚不构成犯罪,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刑法》第312条已经明确了,本罪的犯罪对象是“犯罪”所得或是其收益,因而本罪的本犯应当首先构成犯罪,在此前提下才可以认定本罪的成立,否则就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所以犯罪嫌疑人付某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嫌疑人盗窃后可以向多人销赃,尽管某一收购赃物的嫌疑人所收购的赃物价值尚未达到盗窃罪的起刑点,但不影响其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行为,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犯罪构成。同时,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没有数额限制,故应当认定犯罪嫌疑人付某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三、评析意见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从犯罪构成要件上分析,付某的行为完全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全部构成要件
首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并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构成本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付某为年龄46岁的正常人,显然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体特征。其次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他人的犯罪所得或是犯罪所得收益,而有意掩饰、隐瞒。这种“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推定其应当知道。具体到本罪,行为人在主观方面的“明知”可以理解为,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行为对象具有“涉赃性”,但仍然掩饰、隐瞒。其中“应当知道”,应立足于主客观统一的判断标准加以认定,即对于正常的普通人而言,在行为时能够认识到行为“涉赃性”的话,正常的行为人也应当具有此认识。本案中上游犯罪人多次将新旧不同、型号不同的电动车电瓶卖与付某,显然不属于正常的处理废旧物品的行为,本案的嫌疑人付某显然应当认识到其收购电瓶的“涉赃性”,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观故意。最后,第312条客观方面表现为,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从条文上看,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没有数额限制,即只要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与该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一致,不论其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数额是多少,都应当构成本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付某采用了典型的“收购”方式,在犯罪的客观方面也完全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犯罪构成。因此说付某的行为完全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应当以该罪论。
(二)本罪的上游犯罪的确在本罪犯罪构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成立本罪并不要求上游犯罪也成立犯罪,只要上游犯罪的行为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即可,而不要求具备有责性与可罚性[2]
我们这一观点是立足于大陆法系的有关理论,上游犯罪与隐瞒、掩饰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案发状态、查处方式及审判进程不同,只要有证据证明发生了上游犯罪,行为人明知系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仍然实施窝藏、转移、收购、销售等掩饰、隐瞒行为的,就应认定隐瞒、掩饰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成立,上游犯罪是否定罪对其并不具有影响。这是因为行为人只可能明知上游犯罪的行为事实,不可能明知上游犯罪的法律性质。如果将“明知”理解为必须了解原生行为已经达到犯罪程度或者符合犯罪成立条件,实在强人所难[3]。实践中有观点进一步主张,在分析上游犯罪与下游犯罪关系的过程中,应当从普通意义上将上游犯罪理解为事实,而不是从规范角度将上游犯罪理解为法律意义上的有罪[4]。基于此,在程序上严格要求上游犯罪业已定罪的才能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在规范解释上似乎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并不能以上游犯罪数额构成犯罪为基础,也即犯罪嫌疑人付某的行为,不能因为其收购的“赃物”数额不足盗窃罪的起刑点而逃避法律的制裁。
(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性质,决定了犯罪嫌疑人付某的应受处罚性
我国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二节中规定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将其明确定位为妨害司法罪的一个独立罪名。“赃物犯罪妨害了司法机关顺利追缴赃物与从事刑事侦查、起诉、审判的正常活动秩序。财产犯罪、经济犯罪等发生以后,司法机关一方面要追缴赃物,将其中的一部分没收、一部分退还被害人;另一方面要利用赃物证明犯罪人的犯罪事实,从而顺利进行侦查、起诉与审判。赃物犯罪妨害了司法机关在这两个方面的正常活动秩序。”[5]这表明了我国刑法是将正常的司法秩序作为该罪侵害的客体。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一般情况下被统称为“赃物”,“赃物”是追查涉及赃物犯罪的重要证据,是否追缴到很多时候是能否认定犯罪的关键,因此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必然会给司法机关在发现其上游犯罪、寻找证据的过程中带来重大障碍,即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所侵害的法益也是国家正常的司法秩序,而非公民的财产权利,这就决定了不应以涉案赃物金额作为定罪标准,而应当综合各项犯罪情节,如“犯罪所得”中“犯罪”属于何种性质,以及从窝藏、转移、收购或销售时行为人动机和造成的后果等要素进行认定。所从本质上说,只要行为人使用窝藏、转移、收购、销售等方法掩饰、隐瞒的是“赃物”,不论“赃物”的价值是多少,都破坏了国家正常的司法秩序,都应以本罪论处。
综上所述即便是坚持“罪刑法定”的原则,也应全面、客观地理解本罪。尤其是本罪所规定的“犯罪所得”的含义,这里“犯罪所得”不是要求上游犯罪成立犯罪而获得的非法利益,而是由实质的违法性的犯罪行为所获得的非法利益。这样在办案过程中就可以避免上游犯罪的行为不成立犯罪,而导致本罪也不成立,使得本罪的行为人逃避法律追究的情况发生。因此本案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被害人的刑事责任。
注释:
[1]注:2012年3月1日以后,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司法局联合印发的 《关于盗窃等六种侵犯财产犯罪处罚标准的若干规定》,盗窃罪数额较大的起点由之前的1000元改为2000元。
[2]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0页。
[3]吴占英:《妨害司法罪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4]肖晚祥、苏敏华:《上游犯罪行为人尚未定罪,如何认定洗钱罪》,《人民司法·案例》2008年第2期。
[5]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32页。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10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