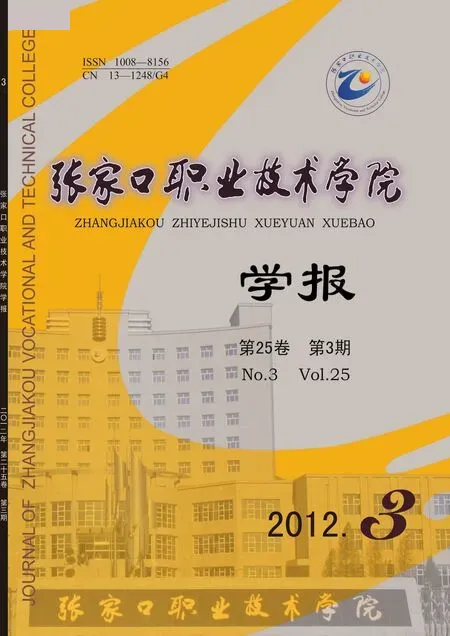粤港澳产业转移背景下贺州工业园区发展策略研究
江维国
(广西师范大学贺州学院,广西贺州542800)
引言
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地区称之为产业转移。欧美学者较早对产业转移的经济动因展开了研究,日本学者后来追上。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1984)从劳动力成本角度分析了产业转移。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1990)认为发展中国家因发展压力而被迫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是产业转移发生的根源。日本学者小岛清(1987)则借鉴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产业转移对投资国和投资对象国是一种双赢选择的观点。此外,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则从微观角度对产业转移进行了解释。这些理论对解释国际产业转移现象有一定的说服力。改革开放后,国内也开始了对区际产业转移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邓小平提出的利用外资办厂、设立深圳经济特区等理论和实践,从本质上讲,与产业转移的精髓一脉相承。国内对产业转移理论的创新最早主要集中在以夏禹龙为代表的“梯度转移理论”和郭凡生为首的“反梯度转移理论”间的探讨。本世纪初开始,国内区际产业转移理论的研究得以较快发展。张可云(2001)认为区际产业转移是区际产品和要素流动之外的另一种区际经济联系的重要方式。陈丹虹(2008)则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研究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园区、产业集群、劳动力等的转移对策[1]。寿思华、蒙良在《广西工业发展报告》(2006)和方乃纯在《广西工业发展报告》(2008)中,结合广西实情,分析了广西在产业承接中的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并提出了相关发展对策。李达球、蒋满元等在分析了广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取得的成效、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后,提出促进广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产业承接策略。
工业园区是二战后一些发达国家为发展经济、改善城市布局结构,所采取的一种重要的企业地理集中的规划区。国内外有许多成功的工业园区,如美国硅谷、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等。优质工业园区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区域竞争力。20世纪80—90年代,我国一批学术团队,先后从新技术革命、政策科学等视角对工业园区问题进行了探索。顾朝林、赵令勋(1997)提出中国发展园区的模式应该建立内生型园区为主导,初期则以建立各类扩散性的经济技术工业园区为重点的观点。范晓屏(2005)通过对浙江省特色工业园区的实证研究,探讨工业园区的持续发展特性、工业园区与专业市场以及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关系[2]。华金科(2009)在分析广东产业转移园产生背景后,将其划分为混合型、专业型和单一型三种类型,提出第二种和第三种产业转移园区值得大力提倡的观点。华金科、华金秋(2010)对福和产业转移工业园区调查研究后,提出湖南承接产业转移的对策[3]。高歌(2007)在《促进跨国公司参与广西产业集群发展研究》一书中,结合广西实情,对产业集群与工业园区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蒋团标则在《基于工业园区产业集群主导下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以广西贺州市为例》(2006)一文中,对贺州工业园区的产业集群布局进行概述后,运用SWOT分析法对贺州市工业园区发展产业集群进行分析,并提出基于工业园区产业集群主导下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对策。
一、粤港澳地区产业转移的新特征、新趋势
产业转移是资本、技术、智力等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变动。产业由优势地区向弱势区域转移是大势所趋,但产业转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不同阶段的产业转移会表现出不同特征和趋势。
(一)“腾笼换鸟”态势日渐深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快,粤港澳地区迫切需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外包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以及信息产业等,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4]。另外,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过多地被传统产业占用,也不利于其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早在2008年5月,广东就出台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旨在调整结构、升级产业。“腾笼换鸟”——把其比较优势日益丧失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挪出空间引进和发展高技术和高管理水平产业成为粤港澳地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产业调整的主旋律。
(二)承接要求高且日益提高
粤港澳地区最初向内地进行产业转移,主要是受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土地、厂房等生产要素成本所吸引,转移表现为局部和尝试性的。同时,在以往的承接与转移中,政府参与的成分也比较多,市场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以上两个因素导致转移企业在当地“水土不服”现象层出不穷。当前,转移主体为了后续健康发展,不得不全面审视承接地区各项条件。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决定因素往往取决于综合要素成本或成本收益比,企业在进行产业转移时,更多地考虑承接地的软硬环境、产业互补性等综合性因素[5]。这显然对承接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单个企业转移向产业链转移过渡
粤港澳地区最初的产业转移基本上是以单个企业为主。一些受成本制约较为明显、对开发中西部市场有较大愿景的企业率先将部分车间或工厂转移到内地。这种转移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的联动性和互补性显然不强。随着产业转移逐渐成为政府和企业界的共识,粤港澳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方式日益多元化,产业链整体搬迁和制造业抱团转移正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比如,2008年年初以来,号称“世界鞋都”的东莞出现了大量企业倒闭或外迁,不少鞋厂正向成都、重庆等中西部城市、东南亚地区转移。业内专家预计,纺织服装业、制鞋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把整个产业链西迁,形成中西部区域产业集群[6]。
二、贺州工业园区承接粤港澳产业转移要素分析
在粤港澳地区产业转移呈现新特征和新趋势前提下,客观分析贺州工业园区承接粤港澳产业转移的要素禀赋,有利于提高承接的质量和效率。
(一)有利因素
第一,区位独特。区位是一种不可复制的优势资源,也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贺州市位于广西的东部,与广东省清远市、肇庆市毗邻,至广东广州市仅215公里,至港澳430公里。目前在建的广(州)贺(州)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贺州到广州仅需2个半小时,将进入“粤港澳两小时经济圈”。贺州是大西南东进粤港澳的重要通道,也是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优惠之地。贺州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战略结合点。这些区位优势都是贺州承接粤港澳产业转移发展园区工业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
第二,承接条件不断完善。2006-2010年,贺州全市累计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项目2533个,投资总额779.45亿元。2011年1-11月,贺州引进外来投资项目359个,投资总额212.12亿元,同比增长11.39%。在“十一五”期间,贺州以工业园区为平台,已经承接不少粤港澳地区转移项目,对当前粤港澳地区的产业转移较为熟悉。贺州目前正在着力建设1个国家级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2个自治区级工业区、3个自治区级A类工业集中区、2个自治区级B类工业集中区,以促进工业项目向园区集聚,实现园区经济跨越发展。这些经验和平台,使得贺州工业园区承接粤港澳产业转移的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厚。
第三,资源优势显著。贺州市雨量充沛,水系发达,水力资源极为丰富,全市水能蕴藏量达72万千瓦,可开发量达50万千瓦,工业生产电力成本低。贺州全市有林面积61.38万公顷,森林蓄积量达2500多万立方米,木材资源极为充足。贺州是矿产资源宝库,境内已探明黑色金属、稀有金属、大理石、花岗岩等矿藏60多种,其中大理石储量约26亿立方米。贺州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拥有较多可供开发的土地资源。成本和资源优势的耦合,有利于集聚生产要素,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能够为其工业园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良好支撑条件。
(二)不利因素
首先,市场观念有待加强、市场机制尚须健全。贺州改革相对滞后,市场竞争机制不健全,存在一定的地区封锁和条块分割现象。贺州工业园区也是由政府主导,园区经济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园区本土企业经营能力、管理水平以及市场意识等较粤港澳地区企业有较大差距。贺州园区本土企业经营者普遍缺少对企业长远发展及潜在危机的忧患意识,对产业承接总处于观望、等待状态,产业承接中出现了“政府热、企业冷”的尴尬局面。政府可以也应该在产业承接的政策制定、硬软件设施提供以及信息传递等方面起主导作用,但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必须通过企业间的合作互动、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才能真正实现。
其次,园区规划起点不高、区内产业配套能力不强。贺州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园区规划起点不高。贺州当前虽然高度重视园区经济,也有意将园区作为承接粤港澳产业转移的平台,但因规划者视野以及特定条件的制约,园区的规划、建设与粤港澳的园区差距相当明显。贺州工业园区配套能力不强,园区内企业间互补性较差,未能形成高效的产业链。如旺高工业园区,截止2010年共引进项目48个,总投资额近30亿元,项目却涉及服装、制药、食品加工、塑料包装、稀土开采加工、建材、电子等行业,企业间联运性显然不强。另外,因贺州物流业起步相对较晚,无系统管理的大型物流中心,道路运输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这些因素制约了其工业园区的发展。
最后,承接产业与本土资源结合度较差、人才瓶颈明显。在西部大开发的十年里,特别是“十一五”期间,贺州通过其几大园区承接了粤港澳地区不少转移企业,但因其所承接的项目与本地优势资源的结合度较差,并没有打造出特色工业园区。本地要素禀赋是其工业园区建设和发展的保障,也是其特色园区形成的基础。贺州工业园区在做大总量、提升规模的同时,更应注重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和导向性。贺州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众多,但大多缺乏基本操作技能,技术工人相对短缺。贺州成熟企业不多,高层次技术、管理人才也较为欠缺。人才瓶颈也是贺州工业园区承接粤港澳地区产业转移的障碍之一。
三、粤港澳产业转移背景下贺州工业园区发展策略
贺州在承接粤港澳产业转移、推进园区工业发展时,应根据本地产业特色及要素禀赋,遵循市场规律,选准产业承接点,注重承接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灵活性。
(一)更新观念、长远规划
一提产业转移,就有人认为是能耗高、污染重、技术落后的产业,认为承接产业转移就是承接低端产业,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事实上,粤港澳地区转移的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产业转移也在不断演进,粤港澳地区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面临转移。其次,要更新贺州工业园区本土企业经营者的观念,让其深刻认识到产业承接是本土企业做大做强的历史机遇,要鼓励、引导园区企业经营者积极、主动参与到产业承接的大潮之中。只有政府和企业共同树立起“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市场运作”的产业承接观念,才有可能利用粤港澳地区产业转移的契机做大、做强贺州的园区工业。
贺州已有工业园区的改造和发展、新工业园区的规划和建设既要面向现代化、专业化、特色化的方向,也要定位于自身要素禀赋充分释放与粤港澳产业承接的科学对接。贺州应该借鉴新加坡苏州工业园“适度超前、梯度推进”的规划原则,大力加强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特别是现代物流体系的建设,提升贺州工业园区品位。客观地讲,目前贺州几大工业园区虽然发展较快,但其规划的起点却可以追溯到若干年前。贺州可以以政府、园区或协会行为,组织园区管理规划者、园区企业经营者到粤港澳地区成熟工业园区考查学习,实地了解产业转移及园区管理,更新经营观念、提升规划水平。
(二)强化招商引资、加强人才培育
贺州在抢抓粤港澳产业转移机遇的同时,更应提高招商实效,着力引进行业龙头企业,促进园区招商引资由粗放低效型向集约高效型转变。招商引资时,主导者应根据现有工业园区或规划工业园区的定位方向,结合粤港澳地区产业转移新特征和新趋势,确定招商引资的重点和原则。即:重点引进与本土特色产业和资源优势结合度较强的产业、重点引进产业集群;遵循从注重招商数量向注重招商质量转变原则、遵循从以招企业为主向招产业为主转变原则、遵循从招项目到招产业园的转变原则、遵循由全面招商向重点招商转变原则。如贺州西湾(平桂)石材粉体产业园主导产业为石材粉体加工业,其招商的重点就应该是与该产业相关的高新技术型新材料项目。
人才是最活跃的先进生产力。未来区域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资本、技术、投资环境或者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贺州应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大科技研发经费的投入,提升园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并将这类措施政策化,以此吸引人才储备较充足的迁移企业。贺州各大园区也可以与本地高校建立对口机制,培育和储备专业人才。园区及园区内企业应完善用人机制,建立人才激励制度,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参与到贺州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中来。
(三)打造特色园区、完善善后机制
贺州几大园区虽然有不同的定位,但因园内企业经营项目繁杂,园区工业没有形成鲜明特色。电力、林产、矿业、电子、新材料是贺州五大支柱和特色产业,但实地考查各个园区,发现其并不能体现这五大支柱和特色产业。贺州应该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通过政府有目的的规划引导、政策扶持和推进机制,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工业园区,引导同类企业及要素资源向园区有序转移,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克服无序承接。如利用贺州丰富的林业资源,创建纸浆木材加工专业性工业园区;利用马蹄、脐橙、茶叶等特色农业,打造具有贺州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深加工工业园区,在此基础上,有针对地承接粤港澳相关行业龙头企业甚至产业集群,实现特色园区的打造与粤港澳地区产业承接的紧密结合。
在善后机制上,贺州应该从财税、金融、投资、土地、环保、治安等方面出台支持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详细政策,为园区建设发展创设、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尽最大努力提高和拓展外迁企业的适应性和后续发展空间,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确保企业“引得进、留得住、站得稳、做得大”。
总结
贺州作为一个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要改变其工业园区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应该立足自身的要素禀赋,结合粤港澳产业转移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从观念更新、园区规划,招商引资、人才培育,特色园区的打造、善后机制的完善等方面着手,实现产业承接与园区建设发展的和谐共振。
[1]陈丹红.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研究[D].暨南大学,2008:30-39.
[2]范晓屏.特色工业园区与区域经济发展[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5.182 -217.
[3]华金科,华金秋.产业转移园区理论与实证研究——兼论湖南的对策[J].特区经济,2010,(04):203-204.
[4][5]江洪.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与对策[J].中国经贸导刊,2009,(18):07.
[6]张永贵.促进我国产业集群转移与承接的健康发展[J].中国投资,2010,(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