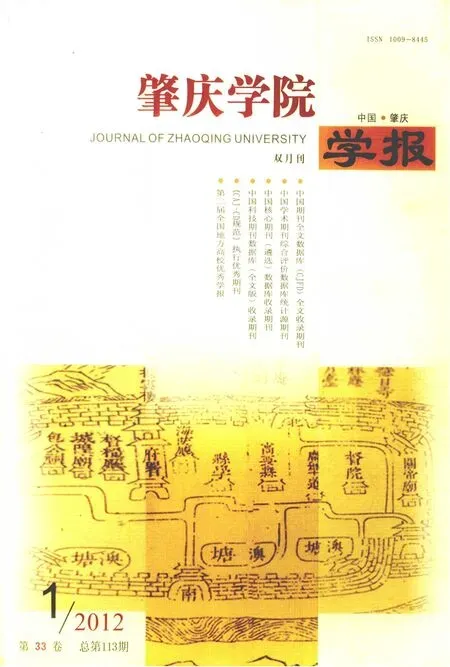家族小说的别样书写——钟道宇长篇小说《紫云》简评
黎保荣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中国现代文学的家族题材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和《憩园》,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雷雨》《原野》《北京人》,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等,都书写了家族中人的命运曲折、家族衰落的历史过程以及家国同构的文化特质。而在当代文学中,涌现了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家族小说,虽说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但这些风格不同的叙事作品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人物性格的类型、情节故事的原型、结构形式的设置、叙述方式的创造均表现出较多的模式化倾向。这既是不同作家对同一母题原型创造性的误读,也是作家难以摆脱的艺术局限,自然也昭示出作家原创性的匮乏”[1]。例如,“十七年”时期的家族叙事呈现的是不同家族之间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而新时期以来的家族叙事则表现出不同家族之间作为不同利益共同体的对垒,都体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结构模式[1]。无论是现代家族文学还是当代家族小说,似乎很少致力于民间情怀、凡人琐事,也鲜见以某物为线索的家族小说创作,而钟道宇的端砚题材小说《紫云》在此方面则似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小说《紫云》的题目可谓以少总多、含蕴精粹,所谓“紫云”者,其意有三:一是主人公紫云,二是端砚的别称“紫云”,三是如紫云(云彩)一样聚散无定、变幻莫测的(家族)历史与人生。小说就是以器物紫云(端砚)为线索,以人物紫云为内容,以史的紫云为意蕴,营构出一部端砚文化史诗和端砚家族传奇。《紫云》里着墨最多的程家,不是大家族,而是靠采砚、刻砚、卖砚而勤劳致富的中小家族,这家族中有名有姓地提及的就有程世昌、程家良(程紫云之兄)、程学谦、程端正、程天赐、程柳旺(第八代传人)、程志存(程柳旺孙)。大家族是以往家族小说的主要写作对象,而《紫云》恰恰相反,注重中小家族的民间情怀、凡人琐事,以一种小历史、小传统与以往的大历史、大传统形成对比,也因此具有了自己的特色。
但是,小说《紫云》并不是因为小家族、小人物、小历史、小传统的“小”而显得“狭隘”,而是化“小”为“精简”。除了精简的人物(紫云)、精简的线索(端砚)之外,小说更营造出精简的故事内核,就是“夺爱”,并以“夺爱”来连接整个家族的历史。
首先是夺爱砚。端砚别称紫云,在中国所产的四大名砚中,尤以端砚最为称著。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惊叹:“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小说中程世昌家祖传的10块老坑砚石极其珍贵,程世昌及其爷爷皆爱砚成痴,程世昌为了守砚宁愿困顿,他为了让砚保持嫩滑而让妻子、女儿、儿媳夜夜抱砚而眠。由此可见端砚之可爱,以及程家尤其程世昌对祖传端砚之痴爱。但是,县令出身的黄莘田欲买程世昌的端砚不成,便利用他儿子程家良的嗜赌恶习,让程家良欠下一身赌债,必须用10块老坑端砚才可勉强抵债。程世昌闻此噩耗,大病不起,不久命丧黄泉,亦可见其被横刀夺爱砚的打击之重与痛苦之深。
其次是夺爱人。夺爱人的一条线索是程紫云与三个男人的故事,表现出一种三男爱一女的故事框架。顾公望与紫云既有同门之情又有爱恋之意,但是后来顾公望应召入宫制砚,无辜落得被净身的悲惨下场。后来顾公望到端州做钦差,对紫云的变心不作望夫女而恼羞成怒,既然自己的爱根(男根)被阉割,既然自己得不到紫云,那么就让无意夺其爱的紫云丈夫也不能与紫云长相厮守,于是阴谋害死了紫云丈夫马二驹,并谋划杀害了知晓此阴谋的紫云曾经的爱人郭木桥。顾公望爱人被夺,他却夺人性命,这条夺爱人的线索充满了血腥,圆润的端砚、圆熟的技术、圆美的计谋反衬出其残缺的心灵。
夺爱人的另一条线索是程紫云的儿子马青阳与她的哥哥程家良的儿子程学谦的爱情争夺战。如果说顾公望他们是非亲戚之间的夺爱,那么这里就是亲戚之间的夺爱。程学谦和马青阳既是表兄弟又是师兄弟,但是他们都爱慕郭月季,当程学谦无意中偷窥到马青阳与郭月季卿卿我我的情景时,妒恨交加,因此趁朝廷查办偷卖贡砚之机诬陷马青阳,让即使拜顾公望为干爹的马青阳也得不到特别关照,被迫出走四会。马青阳到四会黄晋江的玉石行谋生,后来得到赏识,娶黄晋江的大女儿橙花为妻,并设法得到黄家小女儿桔花的价值不菲的翡翠玉镯,重回端州开砚行,与继承程家良、银盏产业并娶郭月季为妻的程学谦斗法,最后买通别人偷走程学谦受朝廷督办的百鸟归巢砚,使得程学谦被迫偷换太太公的极品老坑砚石墓碑而精神恍惚变得疯狂。这样的夺爱,虽不见刀光剑影,但同样阴森可怕。两种夺爱,虽然人物身份、关系和性格不同,但那种破坏性的恨意却是一样的。
小家族、小人物、小历史、小传统、小故事之外,小说似乎颇为关注小民心态。例如顾公望在被无辜阉割,爱人又另嫁他人的情况下,如果换一个作者,可能会将其变态心理勾画到底,但是作者却以顾公望出身下层为背景,表现了其杀人之后的适可而止与惠爱于民的相对简单的内心。马青阳的心理从爱到恨到悔,之后大做善事,更是简明扼要,脉络清楚。但是对于小民心态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是如下三方面:一是紫云的心态,例如黄莘田弄得她家破人亡,自己还要卖身黄家为奴,她反而很快融入黄家,并做了巨鹿夫人的义女;顾公望害死她的丈夫和情人,她却主动恳求顾公望放过她的儿子。这两件事情本来都是令人怒不可遏且充满仇恨的,但是小说更多表现的却是紫云作为一个民间弱女子的逆来顺受、惊惧忧伤、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看似不可思议,但也不能不说这传达了某种民间的真实心态——“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弱女子怎么和人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活着就好。二是嫁给老实男人的民间婚姻观念,例如紫云喜欢朴实、善良的“本分山民”马二驹;桔花被马青阳诱惑怀孕,发觉马青阳不过是逢场作戏之后,倾心于让人“感到放心”的“穷是穷了点,但还算老实勤快”的黎家男人,觉得“这个没有心计的男人真好”。三是民间信仰。如马二驹迎亲时对苦楝树落子于伞的忌讳与不良预兆,蔡老板的远亲偷程学谦的百鸟归巢砚时害怕遭天谴的心理,紫云对兄长程家良说断路话之后的不祥之感与赶做兄长寿衣时的凄然(哥哥的寿衣,一定要亲妹妹来做),程家良的撞鬼遇见已死的好友、妹夫马二驹,程学谦偷太太公墓碑后撞邪总是被斥为败家子,最后疯狂。
小家族、小人物、小历史、小传统、小故事、小民心态,小说对此虽然勾勒不算深刻丰富,但却如此真实如此精简,似乎也可以说真实与精简是另一种深刻与丰富。小说以地域文化为题材,但是意蕴超越地域文化,直指家族历史、人生与人性:谁能料爱砚如痴的父辈会有嗜赌如命的不孝子?谁曾想规规矩矩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会遭遇不测之变而心性迥异?谁能知马青阳和程学谦较量一辈子,他们苦心经营的砚行牌匾会在他们各自去世后的同一天同付一炬?这一切不知是“命运的暗合还是巧合”,人生变幻竟如此离奇。正因如此,指出小说《紫云》作为一部有特色的家族小说,似非夸张之言。
[1] 曹书文.当代家族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J].探索与争鸣,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