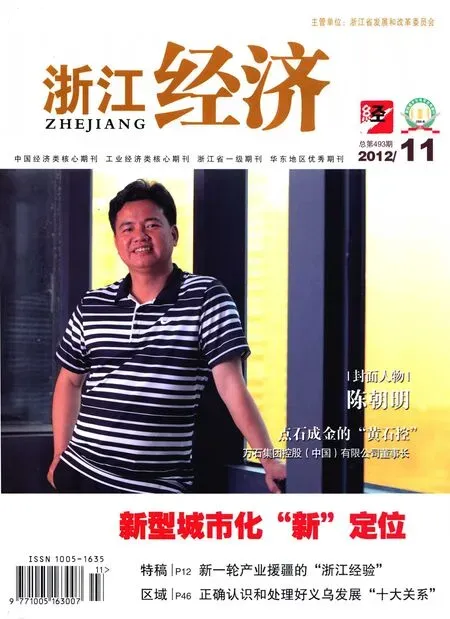“乡村里的都市生活”:一个新的切入点
□ 文/柯敏
“乡村里的都市生活”:一个新的切入点
□ 文/柯敏
当前,浙江已迈入城市化发展提速期。随着农业产业结构比重的逐渐走低,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如玉环、义乌、龙港等地已先后着手实施推进“全域城市化”理念。实际上,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是一种全域影响过程,是在中心和主城区增长极的培育、成熟的基础上,在全域城市化空间进一步形成科学合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功能完善、城乡对接与协调发展的城镇网络体系。据《南方周末》报道,在丽江、洱海等边陲小镇近来涌入了一批批来自上海、北京的“金领移民”,这些人为了享受乡村小镇安逸的生活而放弃原有城市生活。如何正视这种“暗流”涌动,借力大都市中心扩张效应,优化城乡全域统筹的空间模式,已成为当下科学推进新型城市化必需面对的问题。
从本质上看,这种人口异地转移方式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高级阶段,大城市吐故纳新、缓解集聚压力的一种内在需要——相对于农民被迫涌向城市寻找生存机会,“由城入村”现象是出于个体生活观念差异、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一次主动选择。与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 0年代大规模“逆城市化”现象相比,尽管这种趋势尚未成为主流,总体规模较小,且主要人群为依赖信息技术仍可保留其经济功能的自由职业者,以及收入来源完全不由居住地决定的退休老人等。其空间模式也不同于郊区化的渐进式圈层扩张方式,而是呈现出一种跳跃性、候鸟式特点,较多依赖于本地服务机构,独立展开城市功能,因此可以称之为“乡村里的都市生活”。
从外部效应分析,这种城乡人口的自由对流,成为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跨越延伸的跳板和捷径,为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分享城市化能量、吸纳现代文明创造了平等的机遇,大大激活了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效应。根据发达国家发展经验,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规模化转变,传统农村聚落将逐渐减少,并转型成为生产据点或者休闲度假区,乃至最终形成由都市中心——郊区中心——小城镇——农村据点的多中心、节点式、网络化的全域城市化结构。农村据点作为全域城市化梯次演进的末端,须以社会服务设施配套和城市福利制度的全面覆盖为基础,并在据点内部,形成小型分散化、就地循环式的现代化生态型基础设施支撑体系,比如建造适用于1 0 0 0户人家的小型污水、垃圾处理厂、掘地式取水井、太阳能分布式能源等,避免大规模、高投入的城市管网设施建设模式。
结合浙江发展实际,在城市化发展成熟阶段,为适应城市化发展新需求,有必要开展“乡村都市”建设据点的前瞻性研究:一方面,结合实施海岛保护开发战略和山区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一批生态环境优美、历史积淀深厚、基础设施有保障的海岛村和山区度假村,开展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村生态基础设施改造以及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试点工作;另一方面,根据需求人群特点,进一步挖掘养生养老、郊区一体化办公等经济业态的发展潜力,谋划全域城市化的新型发展模式。
城乡人口的自由对流,已成为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跨越延伸的跳板和捷径,为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分享城市化能量、吸纳现代文明创造了平等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