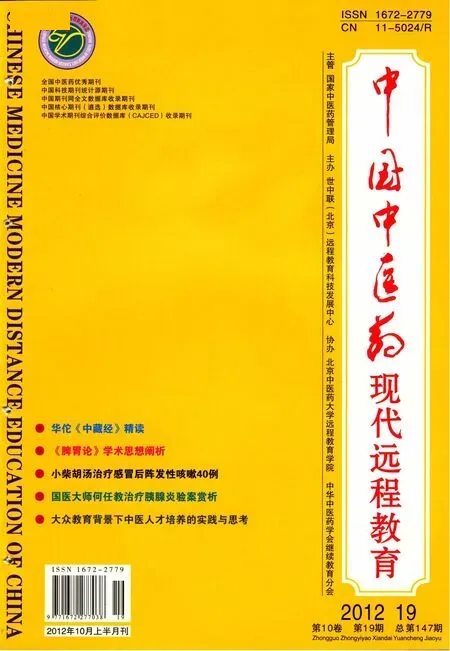阿尔茨海默病与炎症
杨同章 沈 伟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烟台264199)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神经变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进行性认知功能障碍和精神异常。其病理特征为:神经元外的淀粉样蛋白(Aβ)聚集形成老年斑(senile plaques,SP),神经元内tau蛋白异常聚集形成神经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 tangles,NFTs),脑皮质、海马胆碱能神经元及其突触大量丢失,皮层动脉和小动脉出现血管淀粉样变性。AD的病因至今尚未明了,其发病机制目前有多种学说,其中以淀粉样蛋白学说,tau蛋白过度磷酸化学说和像APP、PS-1、PS-2、ApoE等各种基因突变学说为主。但这些均不能完整地解释AD的发生。随着近年对AD发病机制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脑内慢性炎症反应可能是其重要病理特征之一,AD可能是一种慢性的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反应,包括局灶性的脑损伤和高度难溶的淀粉样蛋白(bettaarnyloid,Aβ),从而提出了AD的炎症学说。本文主要介绍一下阿尔茨海默病与炎症的关系。
1 AD与炎症反应
炎症反应在AD发生中的作用近来受到普遍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资科表明,AD患者脑内持续存在着慢性炎症反应,并可能是其他病理特征形成和发展的诱发因素。
1.1 流行病学依据 在需要长期使用NSAIDs治疗的疾病人群(如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患AD的危险性明显低于同年龄对照组。氨苯磋(dapsone)是一种具有抗炎特性的治疗麻风病的药物,现也用于变态反应性疾病和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有学者发现,长期接受氨苯磋治疗麻风病的患者AD患病率低于未接受治疗的患者,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些麻风病患者脑内的淀粉样斑块较同年龄的对照组明显减少[1]。
1.2 病理学依据 早期的病理研究已经证实,在SP和含NFTs(尤其是当NFTs被挤出细胞外时)的变性神经元附近存在明显的胶质反应,某些胶质细胞突起紧紧包围着SP并插至斑块的核心与Aβ直接接触。因此有人认为,小胶质细胞的激活与Aβ沉积形成有关。头部受伤是散发性AD 的危险因子之一,在试验性局部性脑损伤动物模型中,即使在受伤后很长时间仍然可找到包括持续单核巨噬细胞浸润等慢性炎症存在的客观依据[2]。
1.3 免疫学依据 AD病灶内存在大量的补体,而血液循环中的补体并不能通过血脑屏障,提示AD病灶中的补体来自于脑内。试验表明星型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是脑内补体的主要来源,给AD模型动物注射Aβ相关肽可诱导小胶质细胞产生C3。AD的胶质细胞可产生多种炎性细胞因子,其中包括IL-1、IL-6、IL一3、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一氧化氮(NO)等,这些因子的过度表达和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对神经元有损害作用,同时又可以反过来刺激胶质增生反应,进一步加剧神经元的退行性病变。在AD患者外周血中也观察到IL一1、II-6、α1-抗糜蛋白酶等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明显升高[3],但在正常衰老过程中并不存在这种现象。CD一40是一种可在脑内产生的天然蛋白配体,当其与神经胶质细胞上的受体结合时,后者即可被激活,从而诱发附近神经元的炎症损伤。Aβ可增加小胶质细胞上受体数目,当用特异性抗体阻断这些受体时,小胶质细胞即不能被激活,即使小鼠脑内存在大量的Aβ沉积,其神经元的损害也将大大减轻。
1.4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依据 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AD病理演变过程可能起始于Aβ的沉积,随后才有胶质细胞的激活并最终引起神经细胞的变性死亡,而Aβ前体蛋白(APP)mRNA的过度表达则又是Aβ沉积的关键。有报道指出,炎症因子IL一1能够上调APPmRNA 的表达,PGE1也有类似作用并且能够被免疫抑制剂所抑制。氧化酶一2(COX-2)是神经元的结构酶并在风湿性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时以及AD大脑病变区域的基因表达上调,NSAID正是通过抑制COX-2的基因表达而发挥其消炎镇痛作用的[4]。
2 AD的炎症机制
2.1 Aβ沉积在AD炎性反应中的作用 Aβ在脑内的沉积是AD脑中主要的病理变化,它在AD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Master等在1985年从AD脑内的淀粉样肽纤丝中分离到一种分子量为39000和43000的多肽,并命名Aβ,由其淀粉样前体蛋白(βAPP)在β分泌酶、r分泌酶作用下裂解产生。而在βAPP代谢中除有Aβ途径外,还包括sAPP途径。全长的βAPP可在Aβ16残基处被α分泌酶水解,产生可溶性片段sAPP及C末端片段。sAPP被认为具有神经元保护和促生长作用,而Aβ具有神经毒性作用,脑内Aβ代谢途径及sAPP代谢途径哪个占优势,对AD的病理及疾病进展起决定作用[5]。
Aβ激活胶质细胞内大量的信号反应途径,包括酪氨酸激酶依赖的级联反应、Ca2+依赖的Pyk2或PKC信号活化途径、p38和ERK2MAPK激酶信号途径等,驱动了一系列的炎症反应进程。这些研究都证明了Aβ形成过程与慢性炎症反应有关。
2.2 脑内胶质细胞介导AD炎症
2.2.1 星形胶质细胞 星型胶质细胞通过与炎症介质相关的多向性方式而被激活,这种活化的星型胶质细胞表现为细胞肿胀、肥大、突起增多以及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表达增强。星型胶质细胞可分泌TNF—α、IL-6、载脂蛋白E(ApoE)、α1一抗凝乳蛋白酶 (α1—ACT)、α2 -巨球蛋白 (α2 一 MAC)、C 一反应蛋白(CRP)以及s-100β蛋白等胞外酶,对NP和NFT的形成发挥重大的作用。s-100β蛋白在AD脑中活性过度增强,参与构成NP和NFT的形成。过量的s一100β蛋白引起大量的Ca2+内流导致神经元死亡,同时还可诱发星型胶质细胞活化,导致脑循环增殖反应[6]。Gitter等发现培养的人星型胶质细胞(U-373MG星型胶质细胞)暴露在IL-1β 24 h后,α1一ACT 及神经保护性的αAPP水平增加,而用Aβ39-43处理后,αl—ACT 分泌明显增加,且IL-8水平增加了2~3倍,αAPP分泌明显降低,表明Aβ可通过降低αAPP水平而致AD相关的神经病理改变。
2.2.2 小胶质细胞 许多研究表明,AD实验模型中活化的小胶质细胞数量明显增多,以海马部位最明显,海马及前脑区域IL-1、TNF-α、APP-mRNA表达增强,而且大鼠的记忆能力下降以及行为改变,均证实了活化的小胶质细胞对神经元的慢性损害作用。作为脑内主要的炎症反应细胞,小胶质细胞在淀粉样斑块周围大量分布,Aβ激活小胶质细胞后能引起许多细胞毒性的炎症递质产生。Dandrea等通过三重免疫组化实验来标记AD患者脑内海马和皮层区域内活化的小胶质细胞和反应性的星型胶质细胞以及淀粉样斑块的关系,证实了活化的小胶质细胞和星型胶质细胞与NP的空间相关性[7]。
然而,小胶质细胞在NP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未完全清楚。许多学者认为可能和Aβ与小胶质细胞的相互作用有关。体外研究证实,在培养的小胶质细胞中,凡是能刺激蛋白质磷酸化的制剂均能促进Aβ形成,使Aβ在细胞溶酶体内异常聚集,导致细胞损伤。Giulian等将人工合成的Aβ的不同片段进行有关的实验发现,Aβ的N端是结合小胶质细胞所必不可少的结构,而Aβ的C端则是激活小胶质细胞所必需的结构。
3 AD与抗炎治疗
迄今为止,AD尚无特效治疗方法和药物。目前治疗AD的主要药物包括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脑细胞代谢激活剂、脑血循环促进剂、神经营养药、雌激素以及抗氧化剂等。抗炎治疗源于AD的炎症假说。由于甾体类抗炎药副作用较大且对患者的记忆力有损害。多项流行病学调查也显示,在长期使用甾体类抗炎药的人群中AD的患病率并没有显著降低。因此抗炎药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甾体抗炎药(NSAID)。
Trepanier等在对28例AD病人进行为期6个月的吲哚美辛或安慰剂治疗后发现:AD病人的认知操作分在安慰剂组明显下降(下降幅度8.4%),而在吲哚美辛组则略为升高(上升幅度1.3%)。对210例AD病人进行的回顾性研究发现:服NSAIDs组的平均病期较未服NSAIDs组明显延长(P<0.003);服NSAIDs组在MMSE、BNT等上的评分也较未服NSAID组为高。
另外,NSAIDs还可以通过对自由基的清除作用而减轻AD脑内的炎症反应。由于AD炎症假说尚未最终确实,目前的临床试验多为回颐性资料,而前瞻性研究的样本均较小且观察期限短,同时NSAIDs本身尚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因此,将NSAIDs全面推广于AD的临床治疗为时尚早。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双盲的NSAIDs临床干预试验有助于进一步明确AD炎症机制,以及抗炎治疗的临床价值,同时还可以确定NSAIDs的最适剂量。
4 展望
AD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明确,多数学者认为AD应是一个由多种病因,并可能通过多种途径所致的慢性的复杂的病理过程。AD的炎症(免疫)机制假说起源于流行病学的统计资料,有关AD大脑内的补体系统、神经胶质细胞、(炎性)细胞因子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成果为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从上述各方面资料可以得出AD炎症机制的基本理论框架:Aβ的沉积可能是正常老化过程中的产物(因为在大多数非痴呆老年大脑中均能够观察到与AD大脑类似的病理现象,而且只有量的不同,并无质的差异,也可能是机制尚不明确的病理产物)。取得共识的是,Aβ沉积是AD病理过程的最初事件,但Aβ本身可能并无神经毒性,也不会引发明显的神经症状,但却可以诱发包括神经胶质细胞增生、炎症细胞和细胞因子激活在内的一系列炎症反应,促使神经细胞产生NFTs并导致神经细胞的死亡或加速死亡,从而引起一系列的临床征象,而神经细胞的死亡又可以成为新的炎症反应的刺激因素,并使AD大脑内的炎症反应得以不断延续和增强,病灶得以不断的扩展。
目前,Aβ对神经元的毒性作用是直接的还是通过神经胶质细胞,尤其是通过小胶质细胞间接起作用还在争论之中。总之,炎症(免疫)机制在AD病理演变过程中可能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NSAIDs可能为AD的防治开辟新的途径。
[1]McGeer PL, McGeer EG. NSAIDs and Alzheimer disease:epidemiological, animal model and clinical studies[J]. Neurobiology of Aging,2007,28(5):639-647.
[2]Gate D, Rezai-Zadeh K, Jodry D, et al. Macrophages in Alzheimer’s disease: the blood-borne identity[J]. Journal of Neural Transmissi on,2010,117(8):961-970.
[3]Lcastro F,Pedrinl S,Caputo L,et al.Increased plasma Levels of interleukin -l,interleukin-6,and alpha-antichymotrypsin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 disease:peripheral inflammation or signals from the brain?[J].J Neuroimmunol,2000,103:97.
[4]Rezai-Zadeh K, Gate D, Town T. CNS infiltration of peripheral immune cells: D-Day for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J].Journal of Neuroimmune Pharmacology,2009,4(4):462-475.
[5]Lane RF, Shineman DW, Fillit HM.Beyond amyloid: a diverse portfolio of novel drug discovery programs for Alzheimer’s disease and related dementias[J].Alzheimers Res Ther,2011,3(6):36.
[6]Hoozemans JJ, Rozemuller AJ, van Haastert ES, et al.Neuroinflammation in Alzheimer's disease wanes with age[J].J Neuroinflammation,2011,08:171.
[7]Dandrea MR,Reiser PA,Gumula NA,et al.Application of triple irmnunohistochemistry to characterize amyloid plaque-associated inflamnmation in brain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J].Biotech Histochem,200l,76(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