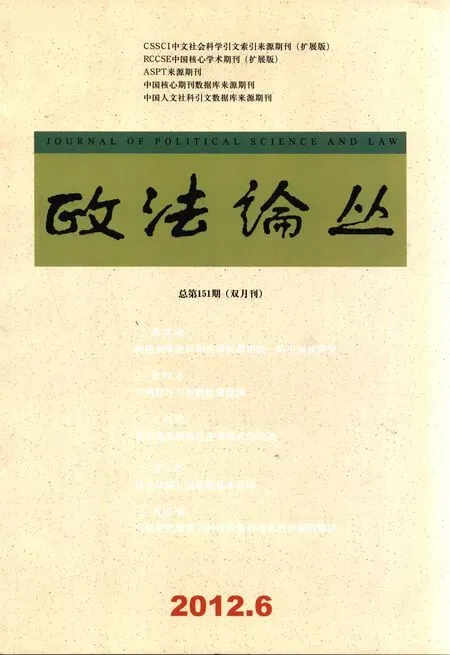论测谎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可采性*
潘志玉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论测谎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可采性*
潘志玉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事实认定对于司法裁判具有关键作用,民事诉讼中事实的认定是靠证据来支撑的。测谎技术本身是科学的,关键在于怎么科学地去用它。测谎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可以归于鉴定结论之列。测谎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不仅具有良好的实践基础,而且也不存在理论障碍,测谎证据的应用能为解决陷入事实认定僵局的疑难案件打开一扇希望之门。对待测谎证据,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民事诉讼中严格规范测谎证据的适用条件、范围和程序, 并适时推动测谎证据立法化。
测谎结论 证据 法律真实 客观真实 可采性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法律所确立的司法裁判的一项基本原则。可以说,是事实而不是法律决定了案件的裁判结果,法律只不过是给裁判结果所套的一件合适的外衣而已。然而,在民事诉讼中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并尽可能使该事实与实际发生的客观真相保持一致并非易事。这是因为,摆在法官面前的存在争议的案件事实都是已发生的过往事实,由于事物具有不可逆转性,已发生的事实不可能自动地重现于法官面前, 当双方当事人自说自话,各执一词,加之受当事人举证能力以及法官认知水平所限,事实认定出现僵局的情况在司法实务中屡见不鲜。在2007年“南京彭宇撞人案”中,原告坚称是被告撞倒了她,而被告则坚称自己是见义勇为,主动帮扶。撞或没撞被归为该案最大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根据其所谓“日常生活经验”并运用“逻辑推理”,认定“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判令被告赔偿45876元,判决一出,舆论哗然。被告上诉后,民众将关注转向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等来的却是双方和解撤诉,于是“撞与没撞”至今成为一大谜局。无独有偶,天津许云鹤案件①又一次让法院陷入事实认定的无限纠结之中。
然而,民事诉讼中事实的认定是靠证据来支撑的,在当事人没有用尽所有证据方法以及法官无法给出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推定之前,法官是万不能盲目地急于下判的。因为法官不只是简单的纠纷裁决者,还是社会的工程师,其“在处理具体争议时,除了考虑法律规则以外,还要考虑具体案件的事实、法律原则、案件的社会影响、道德、伦理、政策等因素,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作出最后的决定”。[1]应当说,在“彭宇案”中,撞还是没撞只有 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双方必有一方是说了谎的,测谎证据的应用或许能为此类疑难案件的解决打开一扇希望之门。
应当说,在“彭宇案”中,撞还是没撞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双方必有一方是说了谎的,测谎证据的应用或许能为此类疑难案件的解决打开一扇希望之门。
一、测谎研究与应用缘起及测谎机理
(一)测谎研究与应用缘起
测谎研究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到了20 世纪测谎技术逐渐发展成型,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已日臻完备。民事诉讼中测谎问题在证据法上的提出,是在美国以一系列著名的判例作为开端的。在美国,测谎技术很早就作为刑事侦查的辅助手段,但作为法庭证据的运用却有一个从否定向有条件的肯定逐步演进的过程。1962年美国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在审理“State v.Valdez”一案中裁定:“尽管测谎仪作为一种审查陈述可靠性的方法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但我们认为该技术的发展已达到足以获得可采性的程度,当然需要有诉讼双方认可的测谎协议。”之后美国联邦和越来越多的州法院开始在诉讼中采纳测谎结论作为法庭证据。在我国,测谎仪的专业称谓是多参量心理测试仪,或叫CPS多道心理测试仪(Computerized Polygraph System)。1990年,公安部科技局与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合作,成立心理测试仪课题组;一年后,我国第一台自制心理测试仪研制成功。2001年1月4日,公安部科技鉴定委员会对国产PG-7型多参量心理测试仪进行鉴定认为:公安部科技信息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的PG型多参量心理测试仪,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具有创新性,整体上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
(二)测谎机理探析
说谎的人什么样?童话故事中的匹诺曹,一说谎鼻子就要长一寸。童话毕竟是童话。现代科学证实,人在说谎时生理上的确发生着一些变化,有一些肉眼可以观察到,如出现抓耳挠腮、腿脚抖动等一系列不自然的人体动作。还有一些生理变化是不易察觉的,如:呼吸速率和血容量异常,出现呼吸抑制和屏息;脉搏加快,血压升高,血输出量增加及成分变化,导致面部、颈部皮肤明显苍白或发红;皮下汗腺分泌增加,导致皮肤出汗,双眼之间或上嘴唇首先出汗,手指和手掌出汗尤其明显;眼睛瞳孔放大;胃收缩,消化液分泌异常,导致嘴、舌、唇干燥;肌肉紧张、颤抖,导致说话结巴。这些生理参量由于受植物神经系统支配,所以一般不受人的意识控制,而是自主的运动,在外界刺激下会出现一系列条件反射现象。据测谎专家介绍:测谎一般是从三个方面测定一个人的生理变化,即脉搏、呼吸和皮肤电阻(简称皮电)。其中,皮电最敏感,是测谎的主要根据。可以说,现代测谎过程,不仅是简单的测谎仪器的操作过程,而是综合各种不同的科学领域(包括:心理学、生理学、心理生理、交流学等)的知识进行分析、判断的复杂过程。
关于测谎技术,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不同理解,做过不同的概括。如有学者指出,测谎就是使用测谎仪的“技术人员按照一定的程序步骤,运用它记录被测试人在回答问题时的心跳、血压、呼吸频率和深度、脑电波、声音、瞳孔、体温、皮肤电阻等方面的参数变化,然后予以分析判断,做出被测对象是否说谎的结论”。[2]也有学者认为测谎技术就是“专业的测谎人员运用测谎仪器记录测谎对象在回答所设置问题的过程中某些生理参数的变化和规律,经过分析得出被测谎对象在回答有关问题时是否说谎的判断活动;所做的判断结果——被测验者说了真话还是谎话——就是测谎结论”。[3]但他们表达的实质是一致的:即“测谎”不是测试“谎言”本身,而是测验心理经受刺激引起的生理参量的变化,或者说是在测试受验者真实的心理痕迹。总之,“测谎”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二、测谎技术应用蕴含的理念冲突与风险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在享受技术带来的舒适便捷生活的同时也感觉到了很多实践或理论上的困惑,技术的双重性作用逐渐显现出来。测谎作为科学技术的产物亦是如此,它一方面可以运用于司法实务帮助法官认定争议事实,另一方面却也给诉讼法理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一)引发理念冲突
首先,测谎技术的应用会引发人们对追求实体公正抑或程序公正的抉择,容易陷入捉襟见肘难两全的困境。因为测谎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实体公正,但测谎作为手段或工具,因属于新的技术应用,如果没有法定的、科学的程序规则予以规制,测谎会很容易越过法律的底限。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使程序正义受损,而且使实体正义的目的也不能达到。因为,根据公正的涵义,公正不但必须做到,为了令人信服,它还必须被人看到,即正义必须曝光于阳光之下,毒树之果不值得留存。正如马丁·路德金的警世名言:“手段代表了正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正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不可能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4]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证据制度可以促进案件事实的发现,但还有限制发现案件真实之手段的重要功能。发现真实并不是诉讼的唯一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牺牲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和秩序性,实在是一种“饮鸽止渴”的方法。于是我们的确需要进一步思考,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在解决纠纷上存在着怎样的价值观,我们又如何在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两难中做出抉择。
其次,测谎技术的应用引发人们对测谎技术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的争论。英国著名科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5]就是说,科学的结论、理论是可以通过实证方法证明是错误的,从而得到修正。科学不能解释所有问题,甚至有时科学的结论是错的,而伪科学可能是正确的。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心脏是思维的器官,因为当人失血过多,则思维变得模糊。而柏拉图认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为脑袋位于人体最高处,离上天最近。显然,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推论错了,因为心脏是血液循环器官,柏拉图的推论不如亚里士多德科学,但是答案居然正确。虽然科学有时会出错,虽然伪科学有时会蒙对,但是更常见的是,伪科学的误导多于启迪。事实上,作为一项新型的实用技术,在1980年以前,我国对测谎技术还普遍持有一种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一度把它当作是唯心主义的伪科学。1980年,公安部一个刑事侦查技术考察团在日本考察时,发现这项技术早已在国外被广泛应用,并且具有一定的科学原理,这才首次将这项技术带回了国内。直到现在,测谎技术仍然处在人们对其科学与伪科学的争吵漩涡之中。
(二)引致或增加伦理与道德风险
“反技术派”和伦理、司法界的一些人士对测谎仪深恶痛绝。他们认为:测谎仪带着一副科学的面具却无法遮蔽它的本质——测谎是对人精神的“刑讯逼供”。测谎仪是利用“一般不受人的意识控制的植物神经系统”,体现的是测试者与被测者之间的精神较量。根据测谎仪的工作原理,当人接受测试时,担心自己的违法事实被揭露,产生恐惧,形成“波形”。但这一“波形”难以区分“慌”与“谎”的差别,即被测试人担心个人隐私被揭露时,表现出的波形与当事人害怕案件事实被揭露产生的波形可能相同,这就为冤假错案埋下伏笔。另一方面,测谎仪对每个公民合法的隐私权带来极大的威胁。隐私权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使用测谎仪时,必然要向被测试人提出许多问题,范围包括受测人的社会背景、知识层次、心理素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所处环境、工作经历等等几乎所有情况,其中有些部分会涉及个人隐私。美国中央情报局30年代曾对一尖端科研机构的物理学家进行测谎,其中有一项结果令测试人员大为吃惊:约95%的被测试者有手淫的习惯!这个情况后来被泄漏出去,引起人们对中央情报局的强烈谴贵和对测谎技术的愤恨。[6]
(三)架空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与证明责任规则的法律风险
诉讼的功能在于“定分止争”、解决纠纷,而解决纠纷的基础是对事实的认定。事实可以分为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当双方举证后,事实依然不清楚,就可以采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做出对负有证明责任一方不利的判决,即在无法穷尽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民事诉讼通常会根据法律事实做出裁判,即使有悖客观真实。有学者指出,测谎证据的应用问题研究,重新开启了对于客观真实的探求,而过度追求所谓的“真相”,有时本身就可能成为引起纷争的根源。运用测谎结论认定事实,虽然可能促成个案的正确裁判,但从根本上规避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适用,甚至架空了整个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也就是说,采用测谎结论会破坏传统的民事诉讼规则,测谎结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案件的事实问题,但它对于程序正义理念和证据规则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而且会造成更多目前难以克服的新问题。[7]
三、测谎证据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可采性
在测谎结论的使用问题上,英美法系的多数国家秉承开放的风格,在保证被测人基本权利获得的情况下,承认测谎证据具有可采性。但是,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在测谎证据问题上,仍不改其传统的严谨的司法和立法风格,不承认测谎证据在法庭上的地位。我国对测谎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起步较晚, 20世纪80年代后期, 我国开始引进和研究测谎技术, 并首先将测谎技术运用于刑事侦查领域。但是, 对于测谎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 长期以来争论较大。1999年9月10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请示》的批复以测谎结论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为由排除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可采性, 使得刑事诉讼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渐趋淡化。然而,在民事诉讼中可否运用测谎结论作为证据使用,争论依旧存在。
证据的可采性源于英美法系的证据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中的一个特有概念,其主要涉及证据的适格性、关联性、可获得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等问题。其中,证据的适格、关联与可获得在我国证据理论中实际指的就是证据的资格与能力问题。
(一)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探究
尽管民事诉讼法没有将测谎结论明确界定为法定证据形式之一,但从证据理论来分析,测谎结论是完全具备证据的“三特征”属性的,进而可以认为测谎结论是有证据资格与能力的,这是测谎证据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具有可采性的前提和基础。首先,测谎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科学理论依据、科学方法和客观数据之上,对人体反应的各项指标所进行的科学判断、分析,并不是主观臆断而得出的,因此测谎结论具有客观性。现代测谎技术已不是“五听”时代凭人的感官去发现、认定被测试者的生理变化,而是运用了心理学、生理学、医学、语言学、逻辑学、现代电子学、机械学等多学科的原理与技术,不但能发现、收集、记录到人的视觉器官不能发现、收集和记录的被测试人的微小的生理变化,而且还能准确地进行定量分析,加上科技工作者的研究开发和经验总结,使测谎的准确度大幅度提高。其次,测谎技术是依据“刺激——反应”原理来探测受测对象内心对某些事物的“关心”程度而表现在生理上的反应作为判断的根据,因此,测谎结果与案件具有关联性。并且,从测谎的内容看,测谎是以被测试者回答预置问题为内容,这些“问题”是由测谎专业人员所设计,自然与案件的发生、发展等密切相关。再次,证据的合法性要求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证据的取得方法不违法。我们不能认为测谎结论因为难以归入我国法定的七种证据形式而否定其证据能力及其合法性。“测谎仪的运用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是当事人陈述;二是对当事人的生理反应进行科学鉴定。无论是当事人陈述还是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都是证据的法定表现形式,测谎结论的使用只是将它们二者结合起来了”。[8]从方法论上讲,我们在讨论测谎结论是否具有法定证据形式,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应该从应然的角度进行论证,而不能单单从实然的角度即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中去僵化地寻找答案。[9]测谎结论只要不属于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就应当认可其合法性。
那么测谎结论应该归属于哪种法定证据种类呢?当前大部分学者将测谎结论划归鉴定结论的范畴,笔者认为,在法律未能立法界定之前,将其做此等归属,并无不妥。这是因为,鉴定结论是鉴定人关于案件中某些专门问题的意见,属于“意见证据”,因此又称为专家意见。鉴定的目的是解决案件中凭借普通常识无法判明的专门性问题,因此鉴定人不能只报告其在检验或测试中观察到的现象,必须在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可见,鉴定结论不是对案件事实的客观记录或描述,而是鉴定人在观察、检验、分析等科学技术活动的基础上得出的主观性认识结论。测谎结论就是测谎专家根据测谎仪器检测的结果对被测人生理反应征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向司法机关提供的结论意见,完全符合鉴定结论的基本特征。[10]
(二)测谎证据应用于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必要性
近年来,因证据原因导致事实难以认定、判决左右为难的民事案件数量大量增加。一些上升为公共道德事件的个案,在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勉强调解、和解结案,引起社会广泛非议。近期发生的天津许云鹤案件就极为典型。发生于两年前的一个看似简单的交通事故,经过一审判决之后,公众看到的仍是扑朔迷离的真相,是肇事司机撒了谎,还是学雷锋反被诬,公众期待法律能还他们一个真相。该案之所以一直悬而未决,争议四起,原因在于最关键的几个证据要么没有,如监控录像和目击证人;要么即使有,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受交警西站大队委托,由天津天通司法鉴定中心就涉案轿车是否与原告身体接触所出具的《交通事故痕迹鉴定意见书》给出的鉴定结论为:“不能确定HAK206号小客车与人体接触部位。”在庭审当场,当法官询问鉴定意见中“不能确定小客车与人体身体接触部位”的具体含义时,天通司法鉴定中心人员回答,“既不能确定津HAK206号小客车与行人王秀芝身体有接触,也不能排除津HAK206号小客车与行人王秀芝没有接触。”最后,一审法院在证据不清,事实不明的情况下,按照其不能服众的逻辑推理做出判决。这引起公众质疑与舆论哗然就在所难免了。
除此,对于南京“彭宇案”与江苏淮安“豆饼老太捡钱归还反成被告案”,法院同样是在证据不清,事实不明的情况下,最终以促成双方和解的方式结案,殊不知,法院的此种处理方式极大地冷落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任与期待,因为它给公众的感觉是事实真相没有厘清,法院是在“和稀泥”,因为和解意味着本该清晰的边界刻意被模糊掉了,由此带来的“破窗效应”②值得反思。质言之,法院和法律没有发挥其作为社会道德底线维护者的作用,在社会要求其做出明确的是非判断之时,法院没有勇于担当,而是选择了回避。
试想一下,如果在此类上升为公共道德事件的案件处理中引入测谎技术的话,——实际上因为双方当事人都想向公众证明自己,所以会自愿接受测试——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及时澄清事实和明辨是非,都会给社会公众一个接近真相的法律事实。测谎结论用作民事诉讼证据的最大益处是,一些颇为棘手的司法实践案件或因测谎技术的运用而重现曙光。徐州市中院在审理原告王某与被告刘某民间借贷上诉案中,因原告称借据原件丢失、被告坚决否认借贷事实,在被告申请和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法院委托专业测试机构分别对原、被告进行了测试,依据测试结论下判后,一方当事人再也没有露面,更没有申诉、缠诉;苏州市金阊区法院也有类似的先例,在一起股东权纠纷案审理中,法院在证据均衡的情况下使用了测谎技术,原告在得知测试结论后,从坚决不同意调解到很快撤回起诉。[11]类似的案例不一而足。
总之,测谎证据的应用有其不可小觑的积极价值,能够对事实疑难案件的审判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尽管我们的民事程序法现在强调的事实是法律真实,即法院不再将发现客观真实作为其绝对追求,但在还没有穷尽所有的证明手段用以发现客观真实的情况下,法官是不能盲目地放弃对客观真实的发现,并退而求其次地强调其所谓的法律真实。测谎证据的应用,能够使法官认定的事实与客观真实无限接近,这既是对当事人负责,也是对法律和社会负责。
(三)测谎证据应用于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可行性
首先,测谎证据能够应用于我国民事诉讼之中具有良好的现实基础。如前所述,当我们对于民事诉讼中测谎的理论研究仍处于“后知后觉”时,司法实践早已走到了理论和立法的前面。另据《法制日报》报道,从1994年到1999年,沈阳中院已接受全国各地司法机关的委托测谎500多例,有效率和准确率均达到90%以上,其中对经济、民事案件的证人、当事人测试占50%,其测试结果作为支持性证据使用,效果甚佳。
其次,测谎证据的应用引发人们所担忧的“实体公正抑或程序公正”以及“科学抑或伪科学”的理念冲突是完全可以被克服的。事实上,测谎技术是一项集心理学、生物学、医学、电子技术等多学科于一身的实用技术,测谎这个技术本身是科学的,有科学根据的,这一点不能动摇,关键就在于怎么科学地去用它。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法律对心理测试实验规定了一整套严格的操作程序,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只有经过正规测谎学校的学习和训练,获得资格后才有权进行这项技术的操作实验。所以在我国,只要提高测谎专业设备的可靠性与科学性,加大对心理测试研究人员和相关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起相应的从业人员及机构的资格认证制度,完善测谎技术应用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从严规范测谎程序及其适用条件,那么,最终实现实体上的公平和公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同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我们可以赋予当事人对是否启动测谎程序的选择权,此时测谎技术的应用完全体现出程序正义的理念,其所追求的价值依然是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
再次,测谎证据的应用所引致或增加的伦理与道德风险是可以被控制的。那种认为测谎技术是“对人精神的刑讯逼供”的说法值得商榷。测谎仪表现出的是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测的,并不意味着可以控制人的思想。应当说,民事诉讼中的无辜者都是欢迎并乐意接受心理测试的。心理测试技术区分无辜者与真正的说谎人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8%以上。无辜者经过测试,失去的是被冤枉的沉重心理负担,获得的是清白与公正。心理测试能使无辜者早日摆脱诚信嫌疑,免除不必要的精神困扰和心理压力,怎么能说是对其精神的“刑讯逼供”呢?关于测谎技术有可能威胁到被测者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一说,更难成立。我们并不否认测谎技术在应用不当情况下可能会侵害到被测人的某项合法权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控制和解决。并且,现在已经有很多科技成果取得了合法的证据地位,如指纹与DNA鉴定等,应用这些技术的鉴定专家并没有取代法官,因为所有证据材料只有在经过法庭质证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最终依据。测谎证据也仅仅是所有间接证据中的一种而已,不可能左右法官的自由心证。
最后,测谎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不会架空举证责任分配与证明责任规则,相反,它能够与证明责任理论做到良好衔接,可以成为证明责任规则的有益补充。证明责任理论允许法官在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完全甚或不能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做出裁判,这是因为法官在诉讼中有时无法完全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但为了解决纠纷却又不得不对案件做出裁判,针对这一现实中的矛盾,各国的立法者均允许法官依据一定程度的盖然性标准对案件事实做出认定。在民事诉讼中,还会出现当事人争议的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现象,但即便如此,他仍然需要依据证明责任的规则将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判归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可见,证明责任理论是有适用条件的,不能被滥用,这个条件就是因客观原因不能发现客观真实,导致事实真伪不明。如果客观真实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或手段发现,我们是不能放弃对客观真实的发现而随意去认定一个自以为是的法律真实。而测谎证据的应用就是帮助法官认定客观真实的,这与证明责任理论并不冲突,是可以和谐相处的。
四、结语
测谎证据在特定条件下基本符合证据的三个属性特征,可以将其归为鉴定结论的证据种类,在证据理论上属于间接证据范畴。测谎技术作为一种现代高科技的产物, 我们既不能绝对排斥其在民事审判中的应用, 使其游离于民事诉讼程序之外, 也不能将其“神化”, 将其视为冲破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僵局的万能武器。对待测谎证据,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理性地规范运用测谎技术认定事实的具体方法, 在运用证明责任理论不能达到预期社会效果时,辅以测谎证据来认定事实,将测谎证据的应用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理论完好衔接起来。
法官作为一个法律人,既是社会公正的建设者,也是社会灵魂的守护者,他不应仅仅是机械精细地、刻板而冷峻地操作法律,而应同时把伟大的博爱精神、人文的关怀、美学的原则和正义的情感以专业化的理性而又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11]鉴于测谎证据的应用实践先于理论与立法,不妨顺水推舟,鼓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能动司法,在民事审判实务中对于测谎证据的适用条件、范围与程序进行相应地探索和创新尝试,总结经验与得失,适时推动测谎证据立法化。
注释:
① 2009年10月21日11时45分许,被告许云鹤驾驶津HAK206号轿车沿天津市红桥区回棋路由南向北行驶至红星美凯龙家具装饰广场附近时,遇原告王由西向东跨越中心隔离护栏,后原告倒地受伤。原告起诉后,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车辆与行人是否发生物理接触并不影响交通事故的成立,假设双方并未发生碰撞,原告系自己摔倒受伤,但被告在并道后发现原告时距离原告只有四五米,在此短距离内做为行人的原告突然发现被告车辆向其驶去必然会发生惊慌错乱,其倒地定然会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该法院于2011年6月16日做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后被告上诉,本案正在二审程序之中。
② 由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该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猖獗。
[1] 陆而启,王铁玲.事实发现:能动与回应之间[J].政法论丛,2010,4.
[2] 吴丹红.民事诉讼中的测谎——基于证据法角度的分析[J].中外法学,2008,6.
[3] 邹积超. 论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J].中国司法鉴定,2004,3.
[4] 冀祥德.程序优先: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冲突选择[J].诉讼法论丛,2003,9.
[5] 宋远升.测谎原理、冲突与法律思考[J].犯罪研究,2008,4.
[6] 乐荩.“测谎”技术的是是非非[J].科学之友,1998,5.
[7] 汤维建.这样取得的证据是否在非法证据排除之列,人民法院报,2004-02-22(3).
[8] 戴承欢,蔡永彤.测谎结论的制度之维:交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9,3.
[9] 何家弘.测谎结论与证据的“有限采用规则”.中国法学,2002,2.
[10] 杨银行. 民事诉讼证据不应排除测谎结论[EB/OL]. http://www.jcrb.com/jcpd/jcll/201012/t20101211_477879.html ,2010-12-10.
[11] 江国华.常识与理性(二):法官角色再审思[J].政法论丛,2011,3.
TheAdmissibilityofLie-DetectingEvidenceinCivilLawsuit
PanZhi-yu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nan Shandong 250014)
The determination of facts is very critical to the judicial judgement, and it is based on evidences in the civil lawsuit. The lie-detecting technology itself is scientific, and the key problem is how to use it scientifically. The lie-detecting evidence has the competency of evidence which belongs to expert conclusion. It is provided with goo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lie-detecting evidence to be used in the civil lawsuit, and there are also no theoretical obstacles in using it. The applying of the lie-detecting evidence may a door of hope for solving case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facts. It is correct for us to standardize the applying condition, scope and procedure of lie-detecting evidence strictly, and to push forward legislation of the lie-detecting evidence in proper time.
lie-detecting conclusion; evidence; legal truth; objective truth; admissibility
1002—6274(2012)06—109—06
DF721.3
A
山东政法学院2011年度科研规划课题:测谎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研究(2011F12B)的中期成果;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民商事法律与民生研究中心成果。
潘志玉(1980-),男,山东德州人,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责任编辑:张保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