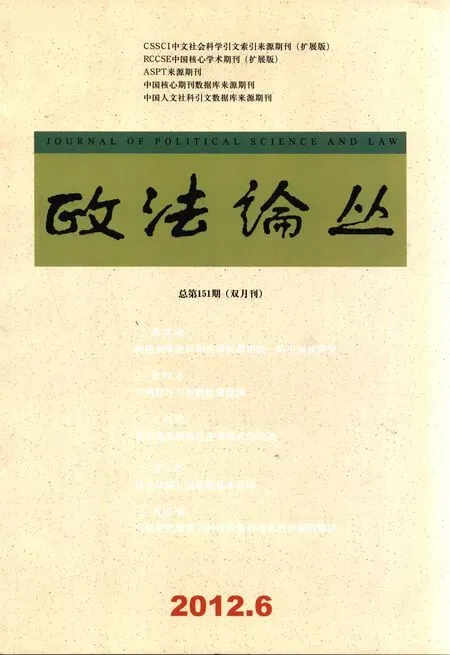再谈监禁刑执行变更范式的转换
王利荣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031)
再谈监禁刑执行变更范式的转换
王利荣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031)
刑法修正案(八)在限制减刑的同时,犯罪化、刑罚化的取向明显,监禁人口增加和场所周转率下降将陷监禁刑的执行于极度的被动;鉴于当下现制依重于减刑已不适应行刑需要,废除减刑代之以假释又不能解燃眉之急,应对之策是:一方面在节制减刑基础上,清晰适用对象和条件;另一方面为加大假释力度,设置过渡场所和尝试电子监控技术,或能走出监禁刑执行的困境。
监禁率 减刑 假释
一、讨论的缘起
剥夺人身自由的技术原理是把判决对象送入人工建筑物,隔离于社会。在这样的单性社会中,服刑人与常态社会的关联不只是被物理切断,他们被迫改变自主行为方式和思维观念,受制于一套系统、细致到琐碎程度的日常行为规则,衣食需要处于低度维系状态,性需要受到长期压抑,都令其痛苦由肉体深及内心。用反个人社会存在的形式惩罚犯罪人即使以报应为由,也不应回避这一现实:“监狱作为犯罪的控制将这些人一生中宝贵活跃的时光由此转变为没有价值的人生。”[1]因此,一方面随着分类监禁和服刑人再犯罪危险评估制度的细化,针对性行为引导、心理辅导、包括谋生技能、人际交往技巧在内的教育等非制裁性因素,渗入监禁刑执行之中;另一方面,为适应服刑人再社会化需要,附条件缩短刑期和改变隔离方式成为常制。
与教育因素渗入监禁刑执行过程相比,近年对于我国大陆地区监狱重减刑、轻假释现象的理论批评不绝于耳,减刑假释的规范结构、范式转换虽是老话题,相关研究却大多重复于规范或政策诠释,一些溯及转换前提的有价值的研究并未引发理论上的深度讨论,另一些在比较国内外自由刑变更执行制度基础上根据性质疑减刑存在的观点,亦未引起学界重视,近年在法律类核心期刊上针对监禁刑变更执行的有份量的文章甚至寥寥无几,这种理论寂寥状态本身就是问题,它既蒙当今社会重近期治理所赐,又暴露了桌面理论的短处。但笔者执意展开这一话题与其说基于理论担当,不如说是基于对整个行刑制度走向的深层忧虑。
第一,本世纪初推进社区矫正的活动虽然表征了国家决策层整体有效抑制犯罪的战略眼光,即通过落实对假释人员的管理扩大假释适用整体带动监禁刑执行向非监禁刑的转化,细化包括执行逆转在内的行刑管理制度同时保障社会的基本安全。现实却是,目前除衍生出一个规模不小的政府部门、一套中看不中用的管理规则,社区矫正的推行没能让当今社会看到松动监禁刑执行的明显实效。
第二,2010年5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两个选择:限制减刑的范围和扩大不得假释的对象。它们或者是为配合限制死刑适用适度延长生刑,或者是适应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需要,并非为剥夺自由刑变更执行定调。但“限制”与“不得”的程度差别、法律要求相关部门在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对社区的影响,却都在传导这样的信息:慎用变更执行尤其慎用假释。
第三,将于2013年1月1日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执行程序的修改集中在对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机关、适用对象及条件、监外刑期计算以及收监程序的规定上,对严重违法假释人员的收监程序却至今模糊。这至少在客观上不利于监狱后门的开放。何况据我国刑事法运行机制的惯性,试图依赖程序法强化对行刑的过程控制,结果往往是令整个行刑处于保守状态。
第四,2012年7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扩大了限制减刑的对象。这表明立法上对死缓人员的限制减刑产生了整体限制减刑的司法效应。然而,司法部门在放缓减刑节奏的同时并未在司法解释层面扩大假释,进一步将监禁刑执行部门推到极其被动的位置,因为监禁周期的普遍拉长会明显增加监狱人口,监狱人满为患,个案矫正方案必然耽于空谈。司法解释大篇幅用于规制减刑还会固化甚至放大减刑在整个变更执行中的作用,如此运作的最终结果无外是:因监狱紧闭后门,社会一次次被拖入受再犯罪侵害的风险之中。
二、现制依重减刑根由与弊端
一直以来,剥夺自由刑的执行依重于减刑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监狱日常管理主要围绕减刑考核展开。每年提请法院减刑案件约三至五个批次,这远远高于其他变更方式的运用,由于对服刑人行为的考核标准细化到超乎一般人想象的地步,监狱刑期管理的基本节奏是量化评估个人行为,根据分数和比例提请减刑。第二,减刑规范化程度高,过程控制特点明显。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解释确定了减刑起始期、频率和力度,减刑内容的详尽程度明显大于假释要求,司法行政部门与之相应,也将规范服刑人行为考核和提请减刑程序作为规范行刑活动的重要步骤。第三,长期以来,减刑率明显高于假释率现象从未改变。据司法部统计,2001年监狱系统被减刑的人数37万余人,占在押服刑人总数的25.39%,假释人数不到1%。[2]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2004年法院系统裁定的减刑案件43万余件,减刑人数占在押服刑人总数的比例是26.6%,假释率不到2%。[3]依其比率,绝大多数刑期在五年以上的服刑人都得到过减刑的奖励。另据2008年全国人大立法调研结论,近年监狱减刑率超过27%,假释率维持在2%。社区矫正推行以后,一些省市假释率有所提升,但适用比率一般不超过10%。
1.现制长期依重减刑的原因
剥夺自由刑执行依重于减刑具有内在原因。第一,减刑适用面宽且可多次适用,被判处不同刑期、刑种的服刑人有可能通过约束自己的行为争取减轻处罚,这种接近自由的机会是均等的,行为要求是统一的,因而可以帮助服刑人系统了解和接受主流规范;可以持续规导服刑人与法律合作,令其形成社会认同的行为定势。第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奖励,减刑能够及时回报服刑人不断接近自由的努力,持续吸引其注意力和予以有效的闲暇管理,进而有效维护场所管理秩序,有效组织服刑人劳动。第三,与公众、司法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在抽象层面视服刑人为社会另类人员不同,行刑部门与管理人员每天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个体,他们深感单调监禁生活对服刑人的影响,而且无时无处不感受到服刑人对自由的渴望,服刑人待在监狱的时间越长,他们因监禁反而强烈的本能渴求就越具有触动人心的能量,在真正了解他们人性需求的一面以及犯罪的社会致因之后,管理者不可能不为所动。在这个层面上看,监狱其实比法院更愿意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用足减刑的空间。
剥夺自由刑执行依重于减刑具有以下外在原因:第一,减刑的适用不会即时改变服刑人被监禁的状态,加上公众视线被高墙电网遮挡,封闭场所内服刑人的状况包括刑罚变更通常不为舆论所关注,监狱、法院承担的部门和个人责任风险不大,迄今为止,互联网相关负面言论和舆论相关负面报道概率较低的现象可予印证。第二,监狱选择变更执行方式的余地不大。适用假释对社会环境和社会管理能力的综合要求较高,对于临近出狱的服刑人放不出、管不住的问题,监狱是难有作为的,因而,行刑部门不得不依重于减刑。第三,因现有量刑步骤不清晰和程序控制不力,加上直接受被害人情绪影响或者身处公众舆论的压力,法院往往选择重惩犯罪人,因此,监狱在行刑阶段减轻处罚在客观上具有弥补宣告刑过剩的效果。第四,为了提高罚金执行率,法院将减刑捆绑罚金的执行加剧了自身对监狱部门的依赖,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淡化司法监督的作用,法院节制减刑的意识和效果都不明显。
2.过度减刑的弊端
近年,理论界与实务界都看到了过度减刑的弊端。
第一,过度减刑导致罪刑因果律的中断和紊乱,伤害了公众报应犯罪的正当情感。根据刑法规定,法院在有罪认定基础上裁量刑罚必须本着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这意味着为保持刑法评价的连贯性和一致性,除非判决有误,不宜一再频繁更动原判刑罚。这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将假释作为刑罚变更方式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大陆地区,尽管基于人权与社会安全双重保护的辩证解读,罪刑均衡只是抽象性判断,加之以责任为刑罚上限的基本立场,都为行刑阶段动态的单向调低罚度提供了依据,限定不同刑种的实际执行期限同时表明社会宽恕是有限度的。而且依其本意,所谓在法律框架下的“适度”减刑,一定是指有关部门在综合权衡服刑人犯罪性质、人身危险性程度以及再社会化可能的具体判断,并非简单指不超出法定最低刑期,或经简单考核和批次裁量。
第二,频繁减刑会削弱刑法的行为引导功能。理论上看,既然刑罚被用于谴责支配犯罪行为的意志,随其蔑视和漠视法律态度的改变,处罚程度在量刑阶段被削减与在行刑阶段被有限削减的理论依据是相同的,而且都不悖于由主观责任主义向量刑责任主义伸展的制度原理。何况,以服刑人接受社会共同生活基本规则为条件减轻原判刑罚,能够在降低其再犯可能性换取社会安全的同时,降低因监禁刑执行带给社会的沉重负担,缓解个人与社会的尖锐冲突。但是,如果减刑适用成了人皆有份的事情,服刑人必然视其为福利或者权利,这不仅不能引导服刑人接受维系正常社会生活的基本行为规则,它还可能加剧服刑人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行为倾轧,影响场所内正常人际关系的形成和维系。事实上,过细和过于简单的行为要求和考核虽有利于维系场所秩序,却不利于服刑人公民意识的养成,长期处于考核中的服刑人要么形成双面人格,要么不再适应自由社会的生活。
第三,单向度的减刑对犯有重罪的服刑人更有利,轻其所重的选择缺乏理性。在1997年司法解释中,为减缓长期犯的自由饥渴感,被判处10年以上徒刑的服刑人一次减刑可达2年,其他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服刑人一次减刑仅1年,鉴于如此倒置轻重缺乏根据,更新后的司法规范取消了相关规定。但是由于服刑人行为考核是有周期的,考虑到刑期越短再犯率越高,监狱对3年以下徒刑的减刑是非常慎重的。据有人统计,经过一次或多次减刑,原判5年以下徒刑的服刑人的平均服刑刑期约是原判刑期的5/6;原判10年至20年长期徒刑的服刑人平均服刑刑期是原判刑期的4/5。[4]据笔者调查,一般来说,不满五年徒刑的服刑人在扣除羁押期和入监初期集训期后,一般能获得约6至10个月的减刑;以月均奖分1.6分计算,服刑人在正常情况下一年得奖19.2分,外加风险抵押分、行政奖励折合分、其他专项奖分,一年得分30分左右,由于得80分才能减刑,服刑人服刑2年8个月可减刑1次,这样一来,3年以下服刑人如果先行羁押期较长的话一般是没有减刑机会的。
第四,法院公开宣告重刑表明自己站在被害人和公众一边,此后隐性的分批次的削减刑罚以顺应监狱部门的要求,会因司法立场的摇摆不定而失去公信度。如果减刑不加节制的话,法院自身角色转换的讨巧的意味更浓。同样重要的是,减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服刑人欲求,却无法真正满足他们向社会生活过渡的基本需求。
三、因限制减刑带来的监禁压力
正是看到以上行刑制度的缺陷和司法对策的偏差,刑法修正案(八)阐明了整体限制减刑的立场。立法定调限制减刑的策略,叠加立法犯罪圈的扩大,一些具体犯罪法定刑等级的增加,以及刑事诉讼法对监狱收容范围的扩大,结果必定是监狱系统收容的周转率下降,人口空前膨胀。近年监狱人口已呈增长的态势,2007年在押服刑人约140万,2012年增至167万人,[4]只是受益于国家斥巨资改善监禁环境,监狱系统才能应对如常。但继续层层加码的话,场所收容很快超负荷,整个监狱机制再度低水平运行的状态。
1.“生刑延长”导致监禁压力
具体地说,普遍拉长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人员的实际服刑刑期,导致收容场所周转率下降。①通过分类监禁维系场所安全也是决策者和执行者不能不接续解决的问题。
据修正案(八)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原规定是20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对此新近生效的司法解释要求,不属限制减刑对象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5年,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这类服刑人最低服刑刑期升至17年,明显高出了过去一段时期同类服刑人的人均实际服刑刑期,在2008年12月30日之前,死缓人员的平均服刑刑期是16年零4个月。
法案还规定,被判处死刑缓刑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而由于近年最高人民法院加大控制力度,死刑集中适用于结果极其严重或者手段极其残忍的暴力性犯罪,因而不难推断限制减刑对象占死缓人员总数的比例至少达至80%。据司法解释,这些人员的减刑起始期、间隔期以及减刑幅度,必须从严掌握,可见,他们待在监狱的时间会更加漫长。
2.重罪刑期普遍拉长,导致监禁压力
据法案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服刑人经减刑后实际执行刑期不得少于13年,比原规定延长了3年。而过去一段时期,无期徒刑执行的平均刑期才14年。而且为配合立法变化,司法解释提高了变更这类服刑人刑期的起始标准。据解释,初次变更被判处无期徒刑人员的刑期是2年,且一般减为20~22年(原规定是18~20年);重大立功减15~20年(原规定是13~18年)。
与此同时,法案扩大累犯范围和加重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尽管涉及面不大,但就监狱收容压力而言,它们具有层层加码的作用。
与之相应,刚刚生效的司法解释明显缩减了对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服刑人的一次性减刑幅度,过去一次性减刑幅度不超过2年,现在缩减到不超过1年,这显然直接降低了监禁场所的周转率;司法解释对加重了对狱内重新犯罪的减刑限制,这些都在不断加大监禁压力。
限制减刑带来的压力不仅仅是场所收容能力不足,在押服刑人普遍情绪波动,可能引发场所管理中诸多难以预测的冲突现象,进而加大监狱管理的难度。
3.常见犯罪门槛降低或刑量增加,导致监禁压力
刑法修正案(八)明显扩大传统且常见犯罪的犯罪圈。比如,增设盗窃罪的行为犯类型,即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即构成犯罪,其中因扒窃入狱的概率虽不高,入户盗窃人入狱的概率却会增加,盗窃历来就是有罪率和判罚率最高的罪名,目前在主要收押有期徒刑10年以下服刑人的监狱中,盗窃类型占犯罪类型比例已经超过了20%,随着法案的实施,这一比例将有所增高。又如,法案规定多次敲诈勒索行为构成犯罪,且敲诈勒索情节严重的法定刑等级增至10年至15年,监禁率有所增高;再如,法案增设了强迫交易罪的三种行为类型,增设了寻衅滋事罪的加重法定刑幅度,对这些危害行为的判罚率增高,监禁率也会随之增高。
4.轻罪涌入,加大监禁压力
新近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经先行羁押余刑3个月以上的服刑人须移送监狱执行刑罚,这不仅对分类监禁提出了新的要求,监狱人口还在增加。
这里,本文没有批评以上立法选择的意思,只是想说明限制减刑及其他方面的立法变化必然致使监狱拥塞,因而接续的要求是增设监狱类型,在扩容规模的同时,逐步打开监狱的出口。
四、调整执行变更范式的争点
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都看到了减刑过滥的弊端,转换执行变更范式即扩大假释也早已是人所共识,只是,在如何具体改变现制问题上,学界存在不同看法。
过去一段时期,基于对态度刑法的警惕,早些时候就有学者提出废除减刑、完善假释的主张。[5]近期,个别学者在比较分析发达国家行刑变更模式基础上提出与之相似的方案:“一方面对判处管制、拘役的罪犯保留适用减刑的制度;另一方面,在减刑制度与假释制度重合适用的领域,即在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范围内废除减刑。并且应当在累进处遇制的基础上完善假释制度。”[6]与之相似的观点是除非服刑人有重大立功表现予以减刑,其他情形应当适用假释,两类观点在理论立场上较前者温和,但它们的实践效果几乎等同于彻底废除减刑,因为现制中对拘役、管制的减刑比率极小,在服刑中因重大立功表现被减刑的情形也不多见。笔者主张走温和路线。具体方案是:第一,限制减刑的适用对象或范围,第二,先在现有减刑空间划出假释范围,逐步过渡到普遍适用假释。以上持不同方案的学者都看到了现制弊端,而且对变更执行原理的解读是相通的,分歧在于减刑是存还是废。
假释的正功能是显而易见的:②第一,假释不实质否定刑罚的性质,适度适用假释不会动摇责任刑法的根基。第二,无论刑满释放、减刑后的刑满释放,还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出狱人的再犯罪风险始终存在。但与第一种释放相比,减刑后的释放提前了出狱人再犯罪的风险,与第三种释放相比,前两种释放方式即时解除了罪犯的身份,因而社会对其再犯罪风险的防御相对被动。适度适用假释则既能合理降低刑罚的力度,又能从个人顺利回归社会和社会有效防卫两个侧面,应对再犯罪风险。第三,在临近出狱阶段,服刑人经自身努力直接获得自由要比得到自由的许诺更具吸引力,它的行为引导作用不亚于减刑;更重要的是,假释在服刑人监禁生活与社会生活间形成了过渡期,这明显符合人性需要和行刑规律,一方面,相关部门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扶助和行为指导,有益于假释人平稳渡过出狱之初谋生最困难的阶段;另一方面,被假释的人员因珍惜自由而尽力约束自己的行为,令其更可能学会呼吸自由的空气而不靠犯罪生活。第四,在致力落实假释人员处遇的过程中,社区与民众防范再犯罪风险的意识和能力,社区自治能力都可能有所增强。
历数假释好处告知人们,用假释替代减刑是不存在理论障碍的,监狱在考核基础上预告假释期甚至不致打破其管理节奏。[7]至为关键的问题是预告的假释能否兑现。毕竟这些年来没有谁反对扩大假释,而曾经大张旗鼓推进社区矫正的制度尝试至今仍未有效落实假释人员的行为督导,进而仍未促使监狱真正打开出口,表明扩大假释绝非经转变行刑观念即可实现。坦率地说,目前且不论用假释替代减刑,能将假释率提高到出狱人总数的5%就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种状况虽然不能成为放弃探索扩大假释路径和方法的理由,却能够成为否定当即废除减刑的主张的现实根据。
全面启用假释替代减刑对法院量刑适度的要求很高。在德日等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法官往往低于往年平均值适用刑罚,既然处罚的轻缓化表明行刑阶段不宜再做减法,应服刑人大多重返社会的需要必然普遍适用假释。在我国大陆地区,量刑与行刑有着独特的制度联结,这种形式逻辑上难以圆说的关联既是政策短视、审判和执行机制摩擦的产物,又渗入众多难以言说的具有相对合理性的人文因素,此时,用假释全面替代减刑很有可能令监狱刚刚启开的一条缝隙再度被封合,相对保留减刑的作用空间和扩大假释,则更有可能扭转行刑的取向。
应当看到,造成重减刑、轻假释现状的原因不仅仅是监狱不愿打开出口或者是法院态度过于保守。影响假释适用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服刑人的家庭成员愿否接纳他, 被害人反应是否强烈,个人有无谋生技能或者生活有无着落等等,直接决定他们能否顺利跨进社会,而这些因素非服刑人或者监狱可予左右。何况长期服刑人重返社会通常存在一个从心理到行为再度转换的过程,具体地说,他们在服刑前期对监禁生活的适应到服刑后期会成为回归自由生活的障碍,他们被迫接受监狱规则角色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形成监禁烙印效应和自我认同降格的心理,自身适应社会的能力随之减弱,此时,即使监狱愿意打开出口,他们未必都能顺利跨出第一步。第二,在社区矫正及基层政府组织接手特殊生活扶助、就业指导和行为规制的意识和能力均显不足时,陡然普遍适用假释,极易导致假释人脱管,假释人再犯罪率的骤增招致舆论批评、招致被害人的情绪反弹,都极有可能断送扩大假释的方案。第三,对于假释人行踪能否有效监测,监狱、法院很难做到心中有数。毕竟在中大城市,假释人隐入人流难觅行踪,农村空穴现象严重且易受害人群集中,一些假释人返乡难以谋生,如果不切实应对放归何处的难题,假释替代减刑的方案就只能是理论清谈。
笔者以为,合理适用两类变更措施的具体做法应是:(1)针对被判处10年以上徒刑和无期徒刑的服刑人,更宜采取小幅度、多频次减刑,令其看到走向自由生活的希望,同时应紧缩原有减刑空间改用假释,假释时机宜选择在服刑人临近出狱的半年或3个月内,同时将原减刑余下的空间作为假释的考察期。这样做不仅能够整体有效控制行刑的力度,将经减刑后的余刑作为假释考察期还将社区矫正控制在合理的时间范围。(2)对被判处10年以下服刑人、未成年人、老年人更大力度的放缓减刑频次和幅度,代之于假释。(3)对被判处3年以下的服刑人不予减刑而是直接适用假释。
当然,如此扩大假释仍须解决在押服刑人“放得出”、“管得住”的问题,这意味着决策者和实施者必须在财力投向和制度运作中采取更为切实的措施步骤,以顺从服刑人再社会化之基本需求,有效维系在押服刑人的良性生存状态和实现社会自卫。这里,所谓决策者和实施者不只是指国家司法行政部门和监狱系统,更多时候是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规划中明确给予一个空间,制订、部署和调整行刑方案更可能收到实效。对此成功事例虽不多见,反面例证却不少。自本世纪初以来,监狱管理和非监禁刑执行统归司法行政部门管辖,按理说,行刑一体化或多或少能够促使监狱打开出口,事实却是监狱硬件设施和管理条件虽有所改善,整个行刑管理的封闭程度越来越高,各省市出监教育基地或中心徒有虚名。这些现象至少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监狱出口得从外面打开,出口的钥匙在地方政府的手中。③
五、服刑人何以“放得出”
目前,扩大假释的现实步骤是在宏观决策层面明确将假释人员管理作为落实社区矫正的重点目标,省市一级政府在国家宏观刑事政策的支持下硬性提升适用假释的比例,同时增设中间监禁场所,解决服刑人“放得出”的问题。
首先,近年推行社区矫正的过程表明,假释能否扩大适用取决于省市一级政府的决心。(1)这一级地方政府拥有调配财力、人力资源的优势,它能够通过改变对行刑活动的财力投向,实质性改善扩大假释适用的基础条件。(2)在保一方平安的同时,地方政府直接承受了维系监狱运行的日愈沉重的财政压力,因而具有松动监禁刑执行的动力。目前,江苏、上海等省市所以能够提高假释率就已初显政府统筹部署的成效。(3)更有可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城市规模和年均临近服刑人的情况,策划假释进程,客观评估试行效果,调整假释方案。(4)更重要的是,这一级政府真正关注和持续支持刑罚结构改革的方向,才可能起到为执行和审判部门松绑的作用。因为随着假释率的提升,假释人再犯罪的概率必然有所提高,由此追究审判、监狱及社区矫正部门的责任,将原本应由社会共担的风险不由分说地转嫁到某一部门或某些个人的头上,通过行刑社会化降低成本和提高预防再犯罪效果就只能是理论的自说自话。
其次,具体做法是增设中间监禁场所。2009年笔者调查重庆市社区矫正活动时发现,假释人员仅占“五类人”总数的1%,而且经重庆市监狱系统假释的人员全部是在当地有户籍、住所的人。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近年上海等地假释率虽有提升,却仍然集中适用于当地有户籍、或有居所的服刑人,如此扩大假释虽出于有效监控的考虑,但它却瓦解了假释实质的条件,背离了适用假释的初衷,而且明显有失公平。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随着修正案(八)的实施,这一现象还会加剧,因为法案要求假释服刑人应当考虑其对居住社区的影响。
目前,通过紧密不同省市社区矫正部门移交和接收假释人员的程序,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服刑人“放得出”的问题。但仅此不够,在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原属农村籍的服刑人可能已经失去了土地和居所,城市拆迁可能会加剧服刑人无家可归的状况,因此在大中城市根据年均临近出狱人的比例设置过渡场所,为居无定所、衣食无依、暂无谋生条件的假释人提供1至3个月栖息之所,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打开监狱的出口。
设置中间监禁场所的理论意义显而易见,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疏通监狱的出口,帮助“三无”假释人、刑释人员平稳渡过出狱后最难熬的阶段;随着社区矫正的推进,理顺刑法相关规定,这一场所还可以担负对轻度违法或违规的管制、缓刑、假释人员的禁戒性处分。现实却是,无论是国家司法行政部门还是地方政府对此都未形成清晰的概念。近些年来,国家司法行政部门和各省市政府在改善监狱设施,扩大监狱关押规模方面,花费了数以百亿的资金,为维系整个监狱系统运行已经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这个负担随着监狱人口迅速增加将越来越重。此时再不考虑转向投入尝试运行中间监禁场所,花钱未必买得到平安。况且增设这样的场所,并非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只是改变财政的投向,因为假释适用越多监狱收容服刑人的周期就越短,减少监禁费用转而支持这一场所的运转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况且,设置和管理此类场所已有域外经验,且受社区矫正转制和立法滞后的牵制不大。
只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原子化的社会,有效运行这一场所会遭遇诸多难以周全预计的困难。在筹划期间,这类场所发生重新犯罪的现象很难避免,场所内滋生有组织犯罪的极大风险,接续生活扶助、就业指导等永无休止的麻烦,都会摆到有关部门的面前,如果没有政策自上而下强力推动,恐怕没有谁自找麻烦。相对而言,在一些发达国家社区具有一定的自治能力,宗教组织及其他民间慈善组织自愿承担对这类弱势加另类群体的扶助,这就明显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以致政府的投入有一定回报率。而在我国大陆地区,主要靠社会力量建设或运行这类场所并不现实,一来有此意愿的企业及热心人士不多,场所管理很难保证资金支持的持续性和活动的稳定性;二来,这类管理行为毕竟不同于单纯的慈善事业,在当下社区控制能力薄弱的情形下,落实相关法律事务,有效避免场所管理的弱化甚至性质的灰化,令地方政府不愿越雷池一步。现实之举是政府主导场所管理。
中间监禁场所的性质更像是过渡场所,这类场所明显不同于目前监狱系统所设的出监教育基地,被收容人日出夜宿,行为自由度类似于近年出现的北京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上海“新航驿站”、江苏赣榆“过渡驿站”。当然,这些由政府设置的场所运行中极易出现两大问题:一是场所试行重声势,一遇阻碍极易夭折,目前,如何科学估算在狱临近出狱人以及其中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人员的比例,在中小企业集中地区或交通便利的城区如何选择场址,谋划收容规模,如何明确经费来源、收容期限、管理人员配比以及管理模式,都是需要理论与实务共谋策略的重要方面。二是场所管理极易滑向准监禁模式,因而有必要根据行刑个别化要求,不断积累管理经验,制订和调整不同于监禁模式的“观护”方案。
六、假释人何以“管得住”
我国《刑法》第86条规定,被假释的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服从监督;按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须报经批准。而在一个幅员辽阔且人口流动量极大的国家,要真正掌握假释人员的行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近年这种情况有所改观。继南京、重庆等市社区矫正部门运用手机定位技术后,越来越多的省市司法行政部门启用这项技术根据刑法规定落实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行为监测和具体管理。目前,一方面由于该技术适用触及被监控人隐私权的敏感问题,相关技术运用处于磨合期,监控实效有待评估,它的作用没有引起外界重视;另一方面,由于跟踪技术较为成熟,花费成本较低,该技术运用受到了管理部门尤其管理人员的普遍欢迎。
采用电子跟踪监控技术并非国家及地方司法行政部门的独创。启用电子监控技术的好处很多:第一,形成对象行踪轨迹,及时向特殊对象发出短期警告和越界警示;第二,减少直接监管带给假释人的心理压力,匿名状况中生活更有利于其再社会化,同时在减少监控者与被监控者冲突的同时,降低监控强度和保证效果。我国大陆地区采取手机定位技术与台湾针对犯罪人适用电子脚镣的做法还不尽相同,后者的监测效果更明显,手机的功能则更具综合性。手机本身是提供就业及职业培训信息的平台,同时是假释人人际交流的工具。当然,这并不说明假释人员对此领情,毕竟行为受监控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假释人对配发和必须使用指定手机的做法所以存在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一般是担心自己的行踪以及人际交往的信息由此被泄露,罪犯标签更加明显,自己的生活可能受到过多打扰,家人及朋友行踪一并受到监测。
笔者以为,就假释人员行为监控而言,手机定位技术值得尝试。第一,借此可以打破多年行刑机制运行的沉寂,毕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假释人“管得住”的问题就是在同等概率上解决“放得出”的问题。第二,所谓附条件的释放本身含有对适用对象行为的要求,相关管理部门适度观察他们的行踪是正当的。第三,处于手机监测下的被假释人所受到的行为管束力度明显低于监禁阶段,该技术运用令更多符合条件的服刑人得以适时重返社会,能够整体降低行刑的力度;与人为面对面管理,该技术运用稳妥处理了观测与干预的关系,除非越轨,假释人的生活不被打扰,他们的行为不受干预。而且由于监测屏幕上呈现的行为人活动轨迹只是一条移动的曲线,他所在的位置只是一个圆点,被监测人仍有相应的隐私权。
当然,以上提及的手机定位技术的正效应是以适度运用为前提的,因而该技术运用须予系统规制。规制的要点是:避免假释人利用技术空白逃避监测;同时,对被监测者活动轨迹须予以严格保密。假释人使用手机形成的通话及信息记录保管应当与普通公民通讯信息管理基本一致,他的通话和信息内容均不允许被监听。
七、余语
从文章结构上看,本文紧接列举众多问题再度分析现制弊端和立法变化带来的压力,略显絮叨,如此大篇幅强调当下行刑的被动局面和系统预测行刑机制积弊,却是希望为真正有效调整执行变更格局而在理论上有所造势。毕竟行刑社会化事关社会的长治久安,再难也应做。此外,近年笔者多次撰文讨论行刑格局的调整并都提到了新场所的设置和新技术的运用,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毕竟文章说服这个社会改变隔离犯罪人的直觉反应已是颇费口舌的事情,说服政府及公众在促使服刑人再社会化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更是不易。
注释:
① 法案实施以后,部分死缓人员长久隔离社会或绝望或反社会情绪极端化,均会加重监狱防自杀、自残和暴狱的压力。建立重警戒型监狱迫在眉睫。患精神病的服刑人和老年服刑人的医疗须有政府提供基本经费。此外,服刑人的老龄化还对社会救助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形成了两难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加大对监狱的投入,监狱管理状况将恶化;如果一再为服刑人、出狱人埋单,政府和社会将不堪重负。
② 详见张波:《假释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一个实证的考察》,《法律适用》2005年第11期;姜树政、刘建军:《假释的功能作用及有效发挥之路径》,载高憬宏主编:《减刑、假释的法律适用与司法实践——中国·欧盟法律和司法合作项目成果》,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作者在《行刑法律机能研究》中也已系统归纳过假释的功能。
③ 应当看到,因地方政府中职位应选举周期发生变动,党政一把手倾向于在执政期间有所建树,问题是落实再犯罪预防是一项很难量化评价的活动,它不可能将实施者带到政治舞台的中心,相关制度推进中还会不断招致舆论质疑,这往往是搁置行刑改革方案的重要原因。
[1] 许华孚.监狱与社会排除——一个批判性分析[J].犯罪与刑事司法研究,2005,5.
[2] 李豫黔.改革和完善我国假释制度的理性思考[J].中国监狱学刊,2001,2.
[3] 姜兴长.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A].刑事审判参考(总46集)[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 彭辉.监狱减刑失衡与减刑制度改革[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7,2.
[5] 侯国云.论废除减刑完善假释[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5,1.
[6] 王志祥.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路径前瞻[J].法商研究,2009,6.
[7] 李云峰.限制减刑、扩大假释——对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的立法思考[J].中国监狱学刊,2006,6.
ReconsiderationoftheConversionofChangeTypeofImprisonmentEnforcement
WangLi-rong
(Law Schoo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230031)
Criminal Law Amendment (8) limits the commut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causes apparent orientation of criminalization and penalty. Both the increase of prison population and the decrease of place turnover rate will make the imprisonment enforcement in an extremely passive state. In view of the both facts that the current mechanism that replies on commutation has no longer met the execution needs, and that the way of abolishing commutation replaced by conditional release can not meet the urgent need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 i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On the one hand, based on the commutation control, it shall be made the applicable objects and conditions of commutation clear.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ditional release force shall be increased by setting up transitional spaces and trying electron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this way, the imprisonment enforcement can walk out of predicament.
imprisonment rate; commutation; conditional release
1002—6274(2012)06—040—08
DF613
A
王利荣(1957-),女,湖南衡阳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刑法理论、刑事执行法学。
(责任编辑:张保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