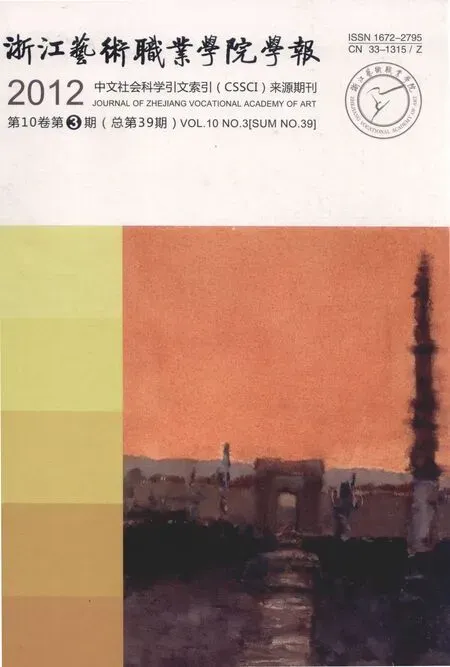文化想象与身份认同: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民族电影
王 青 刘小玲
民族电影也被称为少数民族电影。电影研究者王志敏曾指出:“判断一部影片是否少数民族电影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保证依据,应当是主创人员,即导演与编剧必须具备少数民族身份。而且,这种身份不光是血统上的少数民族身份,而更是指少数民族文化的身份。”[1]本文用民族电影指称“少数民族电影”。
今年4月23 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特别推出“北京民族电影展”,旨在“展示多元文化,映像多彩中华,和谐多样文明”。由一个国家集中展示众多民族的母语电影,这在世界各大电影节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举措着实让人兴奋不已,也引发人们对当下中国民族电影的现状进行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电影纳入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出现了像《五朵金花》《阿诗玛》《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这样的经典影片,在带给观众审美愉悦的同时,有力地配合了建国之后歌颂民族大团结,宣传社会主义祖国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转型,我国民族电影却发展缓慢,困境突显,尽管有一些导演、主创人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创作出不少优秀的电影,一些电影走出了国门,在国外电影节上频频获奖,但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电影的影响力与传播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民族电影在文化想象与身份认同的矛盾处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影视产业发展迅速,市场化水平逐年增高。但是,与快速增加的国产影片相比,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相对滞后。目前,我国每年摄制的少数民族影片不到当年影片创作总数的5%。[2]尽管数量不多,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民族电影中看到电影人的努力与执著,看到我国民族电影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进步。相比“十七年”民族电影在主题、情节设置、影像叙事等方面的表现,新时期以来的民族电影已经在多方面取得突破,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影片。
民族电影通过书写本民族人民的生活故事,表现我国多元的民族文化。由宁才导演的《季风中的马》(2005),通过沙化的诺日西里草原牧民乌日根为了孩子能够重返校园做出的一系列努力,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的体认。万玛才旦导演的《静静的嘛呢石》(2006),描写小喇嘛的生活。生活在寺院的小喇嘛在回家过年时,迷上了看电视,电视是小喇嘛做生意的哥哥买回的,还买了VCD 机和《西游记》光盘,小喇嘛被电视片《西游记》深深吸引,提出要带回寺院给老喇嘛和僧人们看,在回寺院的途中,答应给小喇嘛在嘛呢石上刻六字真言的刻石老人已不幸去世,小喇嘛带去的《西游记》光盘吸引了僧人们,连小活佛也高兴得不得了。小喇嘛就在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现代文明与古老传说之间穿梭,充满好奇和疑惑。西尔扎提·牙合甫导演的《买买提的2008》(2008)是一出鼓舞人心的电影。影片描写到沙尾村顶岗的县文体干部买买提组建少年足球队,并向村民承诺:“谁家的孩子如果参加足球队并夺得冠军,就可以在2008年去北京看奥运会。”美好的目标使村民一致拍手赞成,村长明知这是个骗局,但却想借此把散了心的沙尾村村民重新聚在一起,实现打井种树的愿望。影片描写买买提带着这支“梦想队”,经历了许多困难,最终夺得了胜利,商人亚森开出了“梦想队”往返北京的费用,卡德尔村长也如愿以偿,和村民一起打出十口机井,种下三千棵防沙树。海涛导演的《锡林郭勒·汶川》(2009)则以汶川地震为背景,写出蒙、汉两族人民的团结与友谊。此外,一些优秀的民族电影已经产生了国际影响,如谢飞的《黑骏马》(1995)、陆川的《可可西里》(2004)等。在影片中,蒙古族、藏族、苗族、维吾尔族等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场景得到了充分展现,使观众走进他们的生活。
我们发现,在民族电影中,在表现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时,也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一种文化想象与身份认同的焦虑。具体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对峙,现代与传统的对峙。它确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言:“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3]我们经常在民族电影中看到蓝天、白云、青山、碧水的大自然景观,以及少数民族人们纯朴善良的心灵,与现代都市喧嚣的形成对比。民族地区人们自由自在的生活,让城里人羡慕,但是,城市的生活又着实吸引着身居大山深处和远在天边牧场的人们。《静静的嘛呢石》中的小喇嘛和活佛对于电视以及《西游记》的痴迷;《美丽家园》中的哈萨克青年阿曼泰在走出草原经历了一番闯荡之后,发现故乡、草原在自己心中的位置是那么重要;《青槟榔之味》中的立春最终在喜庆的祝福声中,离开了自己暗恋的姐夫,钻进出租车与同学一起踏上深圳的寻梦之旅。这种城乡对峙的情形,深刻反映出一种现代性的焦虑,也是一种认同的焦虑,源自于对于某种先进文明、文化的羡慕、向往而引发的焦虑,一种危机感的集中表现。正如吉登斯所言:“焦虑实质上就是恐惧,它通过无意识所形成的情感紧张而丧失其对象,这种紧张表现的是‘内在的危险’而不是内化的威胁。”[4]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观念、区域性发展无疑都受到了挑战。民族电影在文化想象的镜像传达中,也表现出这种焦虑感。
二
在看到民族题材电影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民族电影面临的困境。每当我们提到“十七年时期”的民族电影,如《五朵金花》《阿诗玛》《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伴侣》时,无不为其中的故事情节、电影插曲、浓郁的民族特色所吸引。时隔几十年,即使现在再看,观众仍为演员真挚、淳朴的表演而折服。
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入新世纪后,其影响力与传播效果却在缩小。究其原因,在消费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电影的生存压力加大了。电子媒介的发展,大众文化的冲击,受众选择的多元化,使得民族电影不再像“十七年时期”“一枝独秀”。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对于民族题材电影也相应有了更高的审美期待。而民族题材电影受制于资金投入、演员、故事题材、市场发行等诸多原因,都远远没有满足观众的审美要求。目前,民族电影投资少、回报率较低,因此,大多依靠政府资助。由于得不到大的投资,和那些大投资、大制作、明星阵容的“大片”相比,民族电影通常在制作等各方面都显得局促,在国际国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的同时,面对的却是市场的冷淡和叫好不叫座的现实。比如在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可可西里》获得最佳故事片奖、《静静的嘛呢石》获得导演处女作奖,《花腰新娘》获得最佳女主角奖提名,但是这些电影很难进入主流院线。《可可西里》在国际上已屡获大奖,但全国票房仅500多万。
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民族电影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艺术上都存在着手法单一,情节模式化的缺点。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通过影像再现生活场景,建构文化空间,表达文化想象。就民族电影而言,书写本民族生活时,视角的选择,叙事手段的运用直接关系到影片的质量高低。
对待少数民族地域的感知,民族文化的认识,民族电影应该如何面对受众的期待视野,决定了影像叙事的手段。即如何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关系。不应该把民族电影变成消费社会的文化符码,迎合其他民族猎奇的眼光。如果是这样的视角,就会使一些民族题材电影刻意对民风、民俗的展现,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文化,而这种表现往往流于平面化、表层化,不能深刻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意蕴。例如一些民族电影,或直指或波及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比如《婼玛的十七岁》里哈尼族风情特征的梯田、民居、纺车、服饰、开秧门仪式、民歌、打泥巴与选情人等民俗的表现,《滚拉拉的枪》中,通过和奶奶生活的滚拉拉为了得到父亲赠送的猎枪而寻父的过程,展现了苗族部落男孩成人礼的仪式,苗人出生时的种树,在其死后砍树作为棺木,下葬时朋友为他唱指路歌等风俗,《尔玛的婚礼》中羌族婚礼的习俗等。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区之间交流增多。人们也喜欢在节假日到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观光。人们在欣赏少数民族地区的旖旎风光时,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出于各个民族地区充满着热切的表达欲望,一些民族题材电影对特色地区的持续书写,使这些曾经是封闭的地区,开始以一个特殊的文化代码得以表达,成为一种奇观化。无论是《婼玛的十七岁》,还是《花腰新娘》《别姬印象》都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但是,正如一些论者所说:一些人“在进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时,编导们往往热衷于展示少数民族的愚昧、落后和本能,许多影片缺失了真正属于少数民族自身本质特点的文化内涵,许多导演宣扬了汉主体的文化乃至西方文化”[5],这样做的结果,只是把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作为展示的符号,并不能让人们真正了解我国多民族的文化风貌,表现在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
西方学者萨义德在阐述“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时所言:“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对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6]作为多元文化的表现,民族题材电影不仅要给本民族的观众看,还要满足其他民族的审美期待,更应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关键在于要挖掘本民族的异质文化,同时还要表现人类共通的情感诉求。所以,民族电影不应仅仅停留在迎合“他者”的目光与欣赏趣味,应当以民族性的内核、民俗性的色调,通过具体可感的文化样态,完成本民族的形象建构。
三
少数民族地区有着自己深厚的文化积淀,有着本民族的族群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国家民族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的民族电影纷纷走出国门,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这是喜人的现象,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许多民族电影展示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矛盾心理。例如:《成吉思汗的水站》中,看护戈壁滩上成吉思汗的水站就是守护一段历史,一段民族的记忆,但是,在牧区的现代化进程中,戈壁上开了矿,通了火车和公路,水站的作用渐渐减弱甚至失去。《我们的桑嘎》中,黄月娇为传承侗族文化放弃了在上海的工作,她弟弟黄正宇则喜爱流行歌曲,最后,黄正宇在自己喜爱的侗族女孩逼迫下学习侗歌,而且从心里接受了这一古老的文化,而他们的父亲为了去广州打工却学起了粤语。这种矛盾心理也表现出电影创作者的思考,如何正确表现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关键在于矛盾张力的表现,越是有张力地表现这种矛盾,越是能够引发人们的深层思考。正如有论者指出:“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最深厚的根基并不在于那些诸如歌舞、手工艺等‘形于外’的东西,而是在于价值观这种‘神于内’的内容。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价值取向的部分形成了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上的‘根脉’。”[7]
分析民族电影走出国门,走上国际影坛的现象,要思考我们的民族电影靠什么满足西方观众的审美期待问题。有人认为,这些民族题材的电影很大程度上是自觉靠拢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语境,满足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和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尤其是对中国少数民族 (地区)的想象与认知。因此,“这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展现各自的民族风情之外,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先进∕外来文化与落后∕本土文化的冲突、碰撞、融合与反抗,呈现出民族文化对先进∕外来文化的妥协、接受、向往与融合”[8]。这种表现形式,无疑是把少数民族地区看做落后的、未开发的区域。这样的表现手段会使人物塑造僵化,情节设计模式化,它实际上影响了人们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真正理解和感知,进而也影响了对我们国家形象的认识。所以,民族电影表现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塑造自己民族性格的过程,它是自我身份的认同,也是文化身份的塑造。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指出:“身份绝非根植于对过去的纯粹‘恢复’,过去仍等待着发现,而当发现时,就将永久地固定了我们的自我感;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己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3]211所以民族电影应当是既有可观可感的文化样态,还应有无形的集体无意识般的心理积淀,既表现这个民族的过去,也表现这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些民族电影创作者正在努力,他们在电影中力图有机地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结合。如《婼玛的十七岁》就较为鲜明地体现了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撞和融合。影片中属于哈尼族“梯田文化”系列的有民居、纺车、服饰、开秧门仪式、民歌、“选情人”、打泥巴仗等符号,而属于现代都市“电梯文化”系列的则有时装、高跟鞋、高楼、摩托车、随身听、口红、巧克力、照相赚钱等符号,这组符号之间紧张的关系,既表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也展现了以婼玛为代表的年轻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
四
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多彩的文化、悠久的历史、说不尽的故事。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国力增强,各民族人民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作为中国电影一部分的民族电影,曾经有着辉煌的过去,也曾经创作出在走出国门的影片,如何能让民族电影获得更大的发展,重建辉煌,是所有电影人,乃至整个民族的责任和使命。
首先,应加大力度努力挖掘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着力表现各民族人民的新面貌与新生活。让传统与现代对话,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对话。这需要我们的民族电影立足本土,既要有本土意识又要具备开放的眼光。要把该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表现出来。在电影剧本的创作上,真正能够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处,表现该民族的喜怒哀乐,生死爱欲,能够洞察到该民族灵魂深处的东西并把它们表现出来。在这方面,一些导演如塞夫、麦丽丝、万玛才旦等人已经做出了努力,力图从少数民族的角度,抓住和再现民族精神实质,完成对民族电影的去奇观化,真正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内涵。正如塞夫、麦丽丝夫妇所说:“从新的角度深下去,从内容上是民族的,还应该把心态摆平和,不要太功利了,沉下心来,做一些能把中国民族化的东西深下去,能贴近老百姓的东西。”[9]
在艺术表现手段上,民族电影应当不断尝试多样化的创作技术。少数民族地区独异的自然风貌、地理环境、民风民俗,都具有巨大的表现空间,应当用多样化的镜头语言将其完美地传达出来,而避免单一的纪录片式的表现方法。因为,多样化的视听语言是一部电影成功的基础。在演员的选择上,应当以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相结合的方式以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演员与汉族明星演员相结合的方式来增强电影的艺术性,达到民族性与艺术性的和谐。
其次,国家应当加大对民族电影的扶植力度。与国内一些大制作的电影背后有雄厚的财力保证、投资商的支持相比,我国民族电影基本上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扶植,在投资少、规模小的情况下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举步维艰,这也制约了电影制作规模、手段和技术的运用。在新形势下,国家对于民族电影应当加大投资力度,扶植、培育民族电影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国家还应该出台良好、宽松的政策,从宏观上加以调控,保护民族题材电影的生存与发展,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作为电影制作方也可以借鉴一些电影商业化成功的经验,争取到投资方,有充裕的资金保证让电影人拍出更优质的电影。同时,也应探索我国民族电影的传播途径,走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力求让更多的观众欣赏到民族电影。
再次,民族电影制作者要不断充实内涵,加大走出去的意识。借鉴西方电影成功的经验,强化类型片特点。彻底改变目前民族电影观众少,小众化的现状。类型片电影有自身的特色和风格,梭罗门就曾指出:“各个国家的主要电影公司通常努力生产一定样式的影片。如果某部影片受到欢迎,电影公司通常努力生产一定样式的影片。如果某部影片受到欢迎,电影公司就希望把这部成功的影片尽快变成一种样式,以保持公众的兴趣。”[10]美国的格杜德尔等人曾给类型电影下定义为:“类型是由于不同的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或形式。”[11]民族题材电影也可以有自己的模式和类型,确立文化战略发展方向,创作出优秀的民族电影,以开放的眼光,实现我国民族题材电影与世界各国民族电影的平等对话,为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而作出贡献。
最后,我们也呼吁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民族电影,有更多更好的民族电影产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民族电影。在研究中应当借助电影学、文艺学、传播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对民族电影及时展开研讨、批评,通过对民族电影的批评学研究,扩大其影响力,培育观众,提高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制作手段,让民族电影重铸辉煌。
[1]中国电影家协会.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G]∥第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探讨会文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100-101.
[2]饶曙光,陈清洋.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究[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 (2).
[3]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49.
[5]谢德明.期待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再度辉煌[J].民族艺术研究,2008 (6).
[6]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426-427.
[7]赵学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文化政策[N].中国民族报,2010-01-22.
[8]周根红.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电影的民族文化境遇[J].民族艺术,2009 (1).
[9]赛夫,麦丽丝.沉下心往深处走[J].电影艺术,2002(2).
[10]梭罗门.电影的观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215.
[11]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