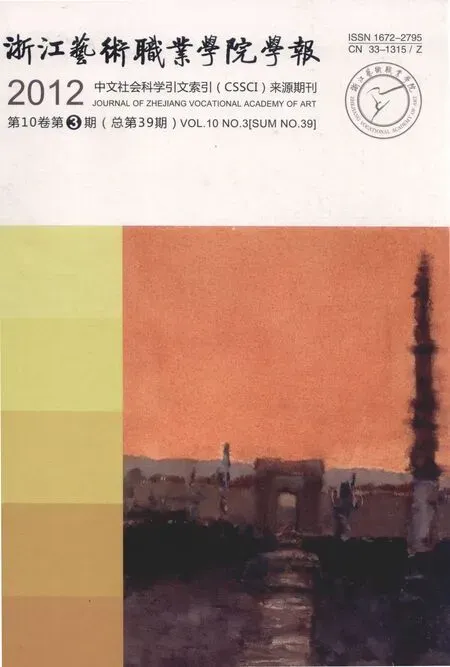从昆剧《班昭》到越剧《班昭》
中山文 伊藤茂
序
“假设有三张票,分别是昆剧、话剧和越剧,三场演出质量上没有差别,你会选择看哪部戏?”这是第一次见面时,杉山太郎先生曾向伊藤提出的问题。自称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迷俱乐部代表的杉山的回答是,“毫不犹豫选择越剧。”而作为日本古典戏剧研究者的伊藤则回答选择昆剧。选择“昆剧和越剧”的问题,其根本上其实是选择哪种戏剧指向的问题。
昆剧与越剧的审美是完全不同的。昆剧属抑制的美,而越剧属煽情的美。现在,有一位导演只通过一部作品就表现出了这两种极端的美感。敢将自己在最高的演员和创作人员下编排出的完美昆剧《班昭》重新演绎,这一点,我由衷地想为杨小青导演的勇气拍手称赞。
一、昆剧《班昭》
2005年6月,我们邀请杨小青导演访问日本。当时,谈到重排《班昭》,她说还肩负了要将其选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重大使命。她说,“是应该发挥昆剧本来的特征,做成流芳后世的昆剧作品;还是沿之前路线做出符合现代人感觉的作品,我也很为此困惑。”摆在她面前的,是“继承与创新”这一中国戏剧现在面临的根本性大命题。
我们并没有可以帮她解决烦恼的力量,只能就近代以前诞生的戏剧,在与诞生时期完全不同的现在如何生存这一问题上,将日本曾遇到的类似的困难与尝试,为杨导做些介绍。
在日本,能乐歌舞伎等古典艺能也曾面临“传统戏剧改革”这一课题。尤其是明治维新(1868)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 (1945)后。为防止观众流失,古典艺能方面倾注热情、满怀真诚的做了许多工作,这种尝试,2 次差不多都用了25年才结束。但就结果来说,却没做任何改变。正确的说法是——“认识到没有必要做任何改变。”这并非讽刺,而是日本的古典艺能有了这样的认识——在新的时代存活,古典化也是一条路——长期的挣扎,因这一认识而稳定下来。日本的古典艺能并非简单地从古传来的古典,而是自己选择了古典化这一道路,以古典的名号作为今天的存在。
但是,中国的古典戏剧与日本的古典戏剧道路并不相同。中国戏曲为成为现代戏剧,比日本古典戏剧进行了无数、重复性的尝试,探索新的道路,也展现了一定成果。
我们也知道上海昆剧团以戏剧现代化为目标成立以来,也一直在进行各种努力。“文革”后,上海昆剧团在复演传统剧目的同时,很早就尝试改编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血手记》)、《上灵山》这样的话题之作,也有梁谷音的独角戏《婉容》和郭小男导演的《夕鹤》等作品。
听到上海昆剧团邀请杨小青导演排演新编《班昭》的消息,在觉得意外的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一种新的可能性。除了对排惯越剧的杨导编排昆剧的意外,我们也很有兴趣知道,昆剧在杨导的执导下会有怎样的变化。
我们曾在2001年、2003年 (排练)、2005年观看过三次昆剧《班昭》。2005年9月观看时的深刻感动令我们难以忘怀,这部戏也于当年11月入选精品工程。可以说,这是至今为止我们在中国看过的最优秀的戏剧作品,称之为“完美”也不为过。登场人物只有6 人,每个人的造型都极具说服力;故事展开 (包括台词),都水到渠成,人物与命运的刻画也充满戏剧性。较之催泪的感动,更让人体会到的是一种深刻的理解,这的确是罕有的观剧体验。
杨小青导演用庄重的节奏和压抑的情感展现了“昆剧”原有的风骨,没有杨派越剧的痕迹,更包罗了极大的优点。正如她自己所说的,这是对“与传统相融合”为目标的新编戏曲的结论。
同时,在昆剧这一古典样式中,描写“女性与事业”这一现代性题目,也让人惊讶。杨小青导演把班昭的人生作为自己的问题思考,并将这一思考传递给观众:对于女性来说能够接受的人生与令人满足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班昭是否得到了这些?而作为观众的你呢?
班昭继承哥哥班固的志愿,穷其一生完成《汉书》。为承继班家事业,怀着作为学者的使命感,她牺牲了很多。也正因为如此,在她的人生中最重大的事业——所做的学问达成之时,她与一直尊敬、支持她的马续与傻姐之间也有着强烈的羁绊。两人对班昭深深的理解与爱;班昭对两人深切的感激。三人之间,构筑起的深刻理解与羁绊,并不是孩子或是一起生活的关系。这也让人思考,到底完满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
杨小青导演通过这部作品追求的是现代女性的生存方式。可以说,昆剧《班昭》就是直指向这一思想性与主题性。
杨小青导演在2005年曾说过:“我作为昆剧的导演,还没能完全理解它的典雅。”班昭表现的严肃之美,确实与昆剧相符。张静娴扮演的班昭,也将近代的自我与古典之美相结合。班昭这一人物,并不作为个性而是被塑造成古典美的典型。这种塑造,直接证明了昆剧带有的“古典样式之美”的存在意义。
确实,昆剧也许在现在是少数派的戏剧,但是,它并不是“无意义”的。昆剧是有其发挥价值的,《班昭》证明,即使在现代,昆剧也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它重新唤起了作为昆剧演员对其存在意义的思考,也揭示了上海昆剧应该保留和前进的道路。
二、越剧《班昭》
要讲越剧《班昭》,就必须要讲导演杨小青执导越剧的道路。这是因为,这部作品是典型的杨派越剧,对越剧这一剧种来说,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
1.“父系越剧”到“母系越剧”
杉山太郎先生曾就越剧这一剧种的特征说过:“是年轻男女以爱情为武器与封建思想战斗的姿态。”女性在与社会封建体制斗争的时候,必须要有与其携手战斗的男性伙伴。但在现实的父系社会中并不存在这样的男性,所以由女性扮演“男角”就成了必要。……在越剧舞台上登场的“才子”,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与女性共同斗争的伙伴,是只在舞台上存在的梦的结晶。这种特征与该剧种在解放前的形成有关,是直接受到共产党的指导的影响。这种思想性,使越剧作为女性戏剧得到成长。
杉山把受共产党指导这一时期的越剧称为“父系越剧”,其中描写的是共产党想展示给当时女性看的登场人物与男女关系。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变化,在女性导演杨小青手中诞生了新的作品,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恋爱成功的女性观众,在这里看到了与自己重合的主人公形象。这拉开了“母系越剧”的时代序幕。
2.茅威涛的小生
杨派越剧获得高度评价是与中国女性文学的繁荣和男女平等主义的渗透发生在同时期的,这并非偶然。其反应是,1993年《西厢记》北京公演时,上百名女大学生为求一票围在剧场前这一小插曲。她们是读着于20 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的女性作家的作品长大的,也是在社会变化中要求与男性平等并为自己争取幸福的知识女性。
在市场繁荣的改革开放、女性选择权更为广泛的时代,作为社会精英的女大学生们追求工作、恋爱、经济等地位时,茅威涛演出的“烦恼的小生”不是正与她们自身重合吗?
在父系社会中,女性要成为社会主体,必须要遵守父系社会的动作样式和规则,将自己装扮成男性。换言之,活跃在社会上的女性,多少在精神上有男性的武装。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化妆成男人”的女小生绝不只是舞台上的人物,而是她们自身。
《陆游与唐琬》中描述的家族关系、职场上的人际关系、事业与爱情的冲突,都是时代女性无可避免的问题。人生要选择什么,舍弃什么,社会中的自己该如何生存……在这个时代,无论是陆游人生的压抑与牵绊或是张生的痛苦都不仅仅是男性的问题,忍受孤独与寂寥也不只是男性特有的,也是女性应该获得的。
茅威涛所具有现代的美感,是超男女社会人应该具备的“双性”美。对她们来说,茅威涛不再是理想的“男性像”,而是理想的自己。舞台上的茅威涛为女性增添了勇气,她们甚至会说:“茅威涛就是我自己。”
3.地方越剧团与旦角
2000年后,杨小青导演将重心放在浙江省内的越剧团和新工作上。以温州市越剧团的新编南戏展演(《荆钗记》《拜月亭》《洗马桥》《白兔记》)和《晋公子重耳》为首,杨小青还执导了诸暨市越剧团的《西施断缆》《天道正义》,浙江越剧团的《红色浪漫》《日落日出》等作品。在2006年的中国越剧艺术节上,她参与了超过10部地方剧团的作品。
这一时期,各地方剧团也涌现了诸多获得高评价的新星,如汤丽芳、陈雪萍、郑曼莉、周柳萍、楼明迪、陈芸等,很多女演员在参与过杨导的执导作品后,都完成了自身的蜕变,迈向新的高度。
同时,也诞生了许多以女性(旦)为主人公的杰作。由女小生向旦角这一主人公的转变,是不是象征了现代的中国女性自立在社会上已经脱离了精神男装化?这点值得回味。
另外,这一时期的作品也不局限于男女爱情,而是描写了多种感情与复杂的人际关系。杨小青导演回首自己人生时也说过:“我想,现在的我有众多人的支持,人生并不仅有男女之情而已。”这应该也是现代社会中女性的感悟。
可以作为代表的例子是,2006年获得中国越剧艺术节金奖的《天道正义》(浙江诸暨市越剧团)。这部戏是根据传统经典《铡美案》改编的,不再是糟糠妻被飞黄腾达的丈夫抛弃的凄惨,而是作为秦香莲在现代的成长故事。
这部戏评剧也曾翻排过,但越剧《天道正义》中的秦香莲 (楼明迪扮演),与评剧中依赖于权力者的秦香莲是完全不同的人物。被信任的丈夫抛弃,秦香莲在认清事实后,舍下对丈夫的迷恋,靠自己的力量带着孩子开始了新的人生。被这种高洁打动心底的,不仅我一个,演出结束后剧场中所有观众起立,暴风般的掌声长时不息。
对于女性来说幸福是什么?女性为此应该如何生存?越剧《天道正义》直面这一难题取材,带着杨小青导演的明确意图,创造出了新版的秦香莲。其结果是,塑造出了即使回到宋朝也能被当时女性观众认同的现代的新女性形象。
现在的越剧界,也有以因追求大型舞台装置与形式美而受到追捧的剧团。但这部作品却正好相反,简单的舞台设计,有效的照明,实力派演员都成了其取胜关键,并得到会演前十名的佳绩。杨小青导演的执导,成为地方演技精湛的女演员演艺生涯的推动力。同时,不再是茅威涛那样的大明星,而是女性观众了解到“我”作为人生主人公的存在。
4.越剧《班昭》
我于2010年初观看了越剧《班昭》。越剧中将台词与唱段增倍。抽签决定结婚对象时的惊讶,对曹寿的失望愤怒,与马续离别的悲伤等,班昭各个时期的感情起伏都直接传递给观众。陈晓红饰演的班昭并没有张静娴班昭的神圣感,随着陈晓红的唱段,观众流泪感受到戏中的感情。陈晓红饰演的班昭身上,充分展示了一般人带有的朴素感、感情上的动摇与热情。
观众对于昆剧与越剧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越剧里不需要昆剧般压抑的“古典之美”,反而是一种人性的解放,即通过越剧展现出人间恢复,或称之为文艺复兴。张静娴的班昭是按昆剧规范塑造的,但陈晓红的班昭则是能展现越剧女演员个性的作品,或者也具有成为《梁祝》这样越剧古典作品的可能性。
另外,陈雪萍扮演的曹寿也符合越剧人物的形象。昆剧中何澍演出的是为发迹不择手段、自私卑鄙的男性的悲剧。陈雪萍扮演的曹寿虽然性格复杂,但到最后都是范派小生的样子,给人感到阳刚之美。
舞台美术上,越剧版最大的变化是舞台正上方悬挂的镜子。让人感觉从始至终是从天上看着舞台上的人物。从正面看戏,观众会将感情投入到眼前主演的悲壮命运中;再看到舞台上方,隐约的班昭影子之外,会更注意到其他人物也是与班昭同样的存在。这给了观众不可思议的感觉。也会从中领悟到,现实社会并非某个典型人物,而是受不到光照的每一个人都在竭尽全力经营自己人生的这一信息,连班昭也不例外。这样看来,抛开突出登场人物这一视点,导演的意图难道不是要平等地对待支持过班昭却未能青史留名者吗?
描绘班昭去世的终场,我们感到,昆剧是终成大业,融入历史中的幸福感;而越剧则是一种解放感——是从历史大事中解放出,作为一名普通女性终结的满足感。环视周围,其实在现实中,不是也有很多女性无可奈何必须要走自己并不想走的人生道路吗?班昭也是儒教束缚中,认真劳作的妻子与母亲的同类。但越剧中的班昭则由衷认为那是种幸福。像班昭一般生存的女性,也从自身中看到这样的精髓并获得幸福感。
三、结 尾
“到做不出新作品时就退休。”
杨小青导演在2005年曾这样说过,这是杨导作为艺术家的真心。她也曾断言,作为艺术家自我模仿是可耻的。我们为能有这样一位女性艺术家用心为我们不间断地创作作品感到喜悦,而且,再没有能比与她生在同一时代,在旁观看她的作品更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们衷心地希望,能有更多一日,更多一部,有她的作品陪伴在旁。
[1]伊藤茂,杉山太郎,中山文.雾里观花——中国戏剧的可能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2]伊藤茂,杉山太郎,中山文.中国戏剧的可能性——三都纲上剧谈[J].中国戏剧,522 号,2000,11.
[3]伊藤茂.我看梅花奖[M]//中国戏剧梅花奖20 周年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4]中山文.梅花奖与茅威涛[M]//中国戏剧梅花奖20 周年文集,中国戏剧家协会,2004.
[5]中山文.试论姚水娟和樊迪民的越剧改良运动[J].戏文,2006 (12),中国话剧研究,2008,3 (11).
[6]中山文.试论越剧《天道正义》中的近代女性形象——以2006年中国越剧艺术节作品为中心[M]//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