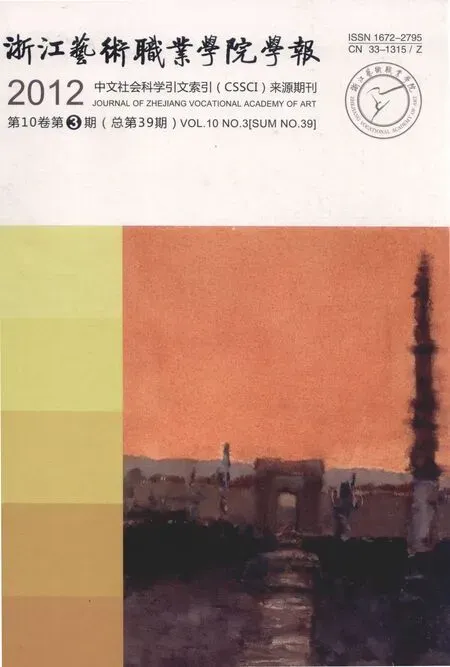重新认识 倍感亲切——杨小青导演散论
沈祖安
一
我认识杨导,已经超过五十年了,她当年的形象已有点模糊。但是我最近找出一张老照片,是从田汉和梅兰芳等戏剧界前辈在1959年从东海前线回到杭州,和文艺界人士座谈的集体合影,看到了一个梳着两根比较粗的长辫子的小女孩,盘腿坐在前排左侧的地下,那股灵气和那份天真,使人感到:那么一个清纯的小女孩,要到我们戏剧团体来,能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吗?凡是有聪明小女孩的人家,都会想到那么娇小的孩子到戏曲舞台上去磨砺,都会有那份心疼和担忧:他们能熬过三个黄梅四个夏、风霜雨雪十几年吗?
我要说的这个小女孩,就是今天誉满大江南北、名传海峡两岸的中国戏剧界的著名导演杨小青。
岁月不饶人,当年我还是一个刚到而立之年的戏剧工作者,但在天真活泼的杨小青面前,却有点老气横秋,因为我们都是老师一辈。韶光易逝,今天已人称“杨妈妈”的杨大导演,对年长者虽仍然尊敬,但说客套话未必是她的擅长。我记得她说过几次同样的话:“这些年来,我虽排了不少戏,也有比较喜欢的,但是还没有一个自己很满意的。还不能在前辈面前毫无愧色地说一句:‘这是我的代表作!’”但是她也会加上一句:“希望你们都能健康长寿,一定能看到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她这番话,是多年前中国剧协在宁波市为她召开的研讨会上说的。她说得很平淡,但说得包括主持李默然主席在内的与会者动容,寥寥几句话,使我们的心头突然涌起一股热流。
都说杨小青导演排的戏,很能煽情,但是讲话的口才一般。但是她的话很实在,在一定的时空间,和听众的心灵通上电,照样能教你动情。所以她人缘很好,关心她的人多,也都愿意看她排的新戏。因为每在她新排的戏中能够看到“戏”的新的变化,以至杨小青自己的变化。
二
杨小青进浙江越剧团是20 世纪50年代中前期。没有几年,她就开始兼学化妆和舞台后勤工作。开始都觉得惋惜,以她的灵气和勤奋,难道还不能成为一个观众喜爱的好演员吗?那时候,我们没有可能和杨小青交换各自的看法,但是凡在后台的化妆间和排练场上,杨小青那股质朴而开朗的性格,使人感到她热爱戏曲,不管是前台和后台,是演戏还是搞化妆,那一股充满着无限热情的开朗的笑容,说明她是一个快乐的阳光女孩,是一个很有主见也有自信的力求上进的姑娘。所以,早年处境不顺,但很早就使人相信:这个小姑娘不会被命运所屈服,而且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长话短说,在十年“文革”以后,我在浙江越剧团的排练场看到她,虽然还是那么娇小,那么灵巧,但她已经是一个很有主见、也懂得如何表达自己正确意愿的助理导演。
还是长话短说。曾几何时,杨小青在张骏声、胡汝慧、方海如和阮敏等导演的提携和支持下,已经把排练场上的学习心得,记满了好些小本子。据我了解,有更多无形的小本子,都深藏在她的心里,留在她的脑海里。终于檐滴石穿、水到渠成,杨小青以一个执行导演的身份,出现在她的前辈和同辈的师友之间,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也得到了领导和前辈们的期许。从20 世纪80年代中前期开始,杨小青终于在新组建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开始了她的导演生涯。而后,她更以一个抱着从头学起的年轻导演的心情,和比她年轻得多的演员们,尤其是作为她的晚辈——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原生代演员们以及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新生代演员们,进行了亲密的合作,经历了同舟共济、甘苦与共的艺术人生。
三
我有一个癖好,就是习惯在不同场合观察我所关心的人在不同的时空中的神情,尤其喜欢窥察他们的眼神。对杨小青当然更是如此。虽然这种机会并不多,但从来不放过,因为这是我感知她在面对艰辛中如何战胜困难中找到新的感觉,以此找到自信和找回自己的细微而生动的那个瞬间。我也曾发现:小青也曾经在眼神中出现恍惚,有过犹豫,尤其在临场改戏和遇到突然的难题,排演场上七嘴八舌时有过迷惘。当有人问道:“导演,怎么办?”她轻轻摇手:“……不要吵,让我想想……”小青的一句“让我想想”,声音很轻,但是被人们听见了,全场从哗然到寂然,但是她往往在全场所有人质疑和询问的眼神中找到答案。她站起身来,甚至举步维艰地难以走动,但是心潮迸涌。借用评弹演员表书的“咕白”:“此刻脑子里像电风扇调了快挡:呃而而而转个不停。”可能戏暂时停顿,但是她脑海里的浪涛翻滚,也往往在这时候,使她从山重水复中走向柳暗花明。有时,一个不重要的角色一句不经意的提问,触动了她。她的眼神也始终是稍纵即逝的那个瞬间,这就是她的聪明,这也是她与生俱来的那种灵动的天赋。为什么那么小巧的杨小青竟然胸中有千军万马可以调动?为什么小巧的杨小青会排出那么多波澜壮阔的铁马金戈的历史大戏?在她成功之后,人们由钦佩到仰慕而生发出来的溢美词:“杨妈妈厉害呀!她一肚子都是学问,把好多书都化作她的知识和经验!”当然,也是有点溢美的词句。
其实,杨小青读书并不多,因为她从小就没有机会读书,后来也不可能有闭门读书的机会。但是,她的特点就是看到一本书和一篇文章,总会自然地成为她思考和反思的动力,尤其是看别人的戏,看年轻导演和大名家排的戏,都会成为她可以调动和学习的契机。再遇到突如其来的“拦路虎”,杨小青的脑子急转弯的应变能力,是她的“特异功能”。有时候的急中生智,暂时应付了急难,但是后来有了更成熟的点子,又把它改了。所以,她的改戏,也和提高和比较中的对决,是相通的。所以,人们习惯于杨导演以新的感悟来否定自己,超越昨日的自己。事无大小,情有深浅,导演有时的反复,正是戏的升华。有时我们也看到她的妙着,往往是从原先的臭棋中衍化后的异变。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从20 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不到30年的艺术历程中,由于现实的需要、时代的机遇和历史的夤缘,终于成为浙江戏曲界乃至中国越剧界一支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生力军,并且以锲而不舍的特别能打硬仗和能争取一切机会打胜仗的快速部队,同时也终于搭建起江南戏曲界一个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特殊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杨小青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创人员,很自然地以她自己的艺术劳动,通过一个个新剧目的实践,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演员;同时也靠自己的勤奋劳动、艰苦奋斗,完成了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这个平台上,共同成就了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和舞台新秀,同时从中也形成了自己。人们为她高兴,不仅是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而是哺化不久刚开声的小青蝉,在三次蜕变后,化为高处长鸣的大知了。也在这个平台上,杨小青接受了各种挑战,交出了优秀的答卷。戏剧界的“杨妈妈”——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优秀导演杨小青在我们中国越剧艺术的美妙舞台上闪亮登场了。二十多年来,她终于在这个平台上放飞了自己,一个华丽转身,杨小青逐渐成为戏曲界倍受欢迎的大牌导演。
有相当一批老戏曲工作者,大家都经过从关心到担心以至开心的不同阶段,分享到了杨小青艺术历程中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的那份喜悦和欣慰。老同事们对她的关注,最初可能是俯视的,因为她太小,小得那么可爱。后来,开始平视了,因为她那么勇敢,在长期艰苦奋斗中又始终那么神清气爽地向前跑,渐渐地跑到我们的前面了。直到本世纪开始,我们开始觉得,有时会在不经意之间,偶尔用仰视的眼光去捕捉那一份成功者的悠然的笑容。这种笑容很自信,但并不诡谲,因为她没有“大牌”的感觉。但是她一直自信,自信自己能在不断转换的环境中坚持争取兼收并蓄,争取学习新事物的一切主动权。当她感觉到兴奋和快活的时候,正是从被动转为主动时,被大家认可的时候。所以,年近花甲,她也不见老,因为她认为自己尚无倚老卖老的权利,惟身心保持年轻化,才能破旧立新和除旧迎新。因此,她逐渐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杨小青,一个在不断战胜自己中犹如春笋解箨为冲天翠竹后如释重负的超然的杨小青。这个杨小青,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她并不陌生,又觉得格外亲切。
四
说实话,我看过杨小青排的戏,可能已远不止十个,但能让我记住的,却不到十个,而能使我难忘的,只有三个。现在我想说的,就是其中的两个。
第一个是20 世纪90年代末到21 世纪初,杨小青为杭州越剧院排演的新编传奇剧《流花溪》。首先要说的,这个戏的作者是我多年的忘年交包朝赞,他是以编民间故事见长,特点和特长是贴近现实生活。三十年来,他一口气编出了二十多个能被文化市场普遍接受的舞台新剧目。按理说,《流花溪》原先并非包朝赞最精心的力作,但是后来和杭州越剧院合作后,在杨小青导演的合作担纲下,戏日趋完美,成为她导演的代表作。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是描写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在时空变换中经受的并不相同的遭遇和各不相同的结局,但在受迫害和受歧视的程度上,由于本人不同的抗争,其结果和产生的影响是并不相同的。
在杨小青导演的构思中,从中国古代到20 世纪中前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农村妇女中,受封建礼教的专制迫害,手段是残酷的,其规律是相同的。因此,她让舞台上出现三个不同时期中同样存在的,类似世俗轮回的封建桎梏,让观众直接感受到受迫害者内心的感悟:如何用不同的方法来冲破这个轮回,但是其结果是大同小异。不同遭遇和结局,比较生动地揭示了中国农村古老家族在不同时空的不同遭遇间,从发生的些微的变化,发展到惊人的裂变。虽然未能推倒顽固的深宅大院,但是动摇了它原有的秩序——承重的大墙坍塌了。这三个人物——冬花、秋花和春花,她们面临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的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征兆和异端,她们背靠的是几千年形成的以男权社会压迫妇女、主宰弱小者命运的那股强权势力;从封建的男权势力中异化出来的一批助纣为虐的妇女,在同样受迫害中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作为——譬如同样作为妇女的三太婆,那股为大男子压迫妇女为虎作伥的心理变异,正是为了说明妇女与命运抗争中也需要同自己的落后和愚昧进行抗争。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看不见的世俗轮回有多么可怕!
这个戏的主题激动了杨小青,由于她的感悟和渲染,又深深地打动了观众。尽管剧本还不完全成熟——包括妇女自设女祠堂这段戏,有了些微既得利益的老年妇女三太婆,竟然要野蛮地镇压为了争取生存权利的青年妇女春花的悲惨结局。这段戏的情节有悖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深受苦难的妇女不可能动用男权社会法器来迫害妇女自己——开女祠堂的情节,是缺乏社会典型性的。但是,导演的努力以及导演和各方面的合作,在舞台上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耐人寻味和发人深省的问号:处在20 世纪初年的1911年前后,封建制度已在风雨中逐渐坍塌的前夜,我们台下的观众感受如何?最后由秋花和女儿春花对唱的这段浪漫主义手法的展示,是导演让观众对这个存在于观众心里的中国妇女被封锁的世俗轮回的命运,必需要将它粉碎。——至少,在观众心目中,它被粉碎了。杨小青导演帮助编剧包朝赞弥补了这个不足。(这个矛盾最后如何解决,关系到这出戏能否成为精品的关键。当然,目前总体来说,这是一出尚可深入探索的不失为好看的戏。)
我想,应该说这是杨小青的导演生涯中的一次大手笔。她强化了受压迫的妇女与旧的封建制度不可调和的因果关系。
我很欣赏剧情中那个细节——“一串钥匙联系了三代人的命运”。特别是秋花在不同的时空间,从冬花手里接过了那一串管理全部财产的钥匙,从现象上看,它象征了胜利者的喜悦和没落者的悲哀。但是,从实际效果中感到:它是一种嘲弄。因为台下的观众对此所表达的疑虑和嘲笑,是对封建统治的一种揶揄。尽管这本戏没有很高深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观念的形象概述,但是观众形象地感受到这是一本几千年来中国封建制度吃人的历史和历代被压迫妇女受苦受难的悲惨经历。尤其由于导演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封建大家族的气势和仆役成群,争风斗势和声嘶力竭、外强中干,用大幅度的舞台调度以及舞台场景的造型和舞台情景的气氛,以及小人物之间的钩心斗角和插科打诨,都是为了衬托局中人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感情宣泄。每一场落幕,尽管悄然无声,但使观众感觉到那已不是柔软的丝绒幕布,而是一排排厚厚的石墙,重重地压在观众的心头。如果要我说一句赞美的话,我最想说的是:杨小青所以成功,正因为她善用小细节,增强小高潮,托起人物性格变异和骤变的剧情高潮,这正是她所擅长的:以少胜多和小中见大,藉些微而见恢弘的风格,也是她慧眼独具的地方。
五
我同时也喜欢杨小青在新世纪开始的十年之初,她为上海昆剧团认真排练了新编传奇剧《班昭》。同时也在十年的后期,为杭州越剧团重排了新移植的越剧本《班昭》。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杨小青前后为上昆开排和为杭越复排,虽然磨的好像是老调重弹,但绝非依样画葫芦的同一把剑,也不是双刃剑,而是双股剑,各有自己的格局,也都有自己的锋芒。
班昭和她的师兄妹为了续修《汉书》所经历的那段班固父子和师生的故事,我不重复了。我特别想说的是,在杨小青的心目中所感知的和所体会的东汉历史学家班昭——曹大家的传奇故事,当然,都是历代有心人塑造的比较真实的形象。
没看过戏的听说曹大家,必然会吃惊。但逸史所述的(包括野史中的演义)曹大家,已非史籍中的班昭,现在也不必再出现。但是新传奇中的曹大家,还是有自己的特色。这部戏的前面三分之二内容,是写班固和班昭以及两个学生为续《汉书》所经历的不幸。故事的动人之处,主要是是非颠倒的朝廷,在禁《汉书》和重续《汉书》的过程中,使人扼腕,也使人跌足,但都是这本戏的幕后背景,有戏,也是交代过程的过场戏。而后三分之一的戏里,主要的转折点,就是把满腹忧愁、无限悲愤又无所适从的班昭,在经历了巨大的感情折磨几乎被击倒之后,终于自己挺立起来,并在权衡之后,以她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周旋于汉室朝野的特权阶层。她的不拘小节和涉足浮名虚利,以致趋奉官场,不避声色,对于一个知书达理、心高气傲的名门淑女而言,实在是极不情愿也不甘心的牺牲小我(声誉)以全大我(修史)的一种权宜之计。一切都为了实现父亲的未竟之志,达到重续《汉书》的目的,她不惜和昔日所鄙视和蔑视的王公巨卿沆瀣一气。她在最后第二场所出现的,是那个醉酒归来,在心爱人面前所表露的使人不敢相认的放诞无忌的曹大家,她心里的痛苦和悲凉,愤怒以至仇恨,那种自高处跌落、反差极大的心理的和形神的淋漓尽致的表述方法,在瞬间逐一展现。虽然都是稍纵即逝的刹那之间,但是导演的高明和演员的努力,使台下观众的一双眼睛也精明起来。可以说,多么细心的观众,就可以看到班昭多么深沉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为此,我在上海和杭州,两次细看这场曹大家薄醉归来的倾情诉说,因此,我对原来就赞赏的张静娴的表演艺术,更加折服!这场戏的出现,是全局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高潮。起初观众都会感到突然和震惊。观众希望得到解答,但是导演没有解答,因为局中人自己当时也无法解答。直到最后一场,班昭的师兄已经先她而去,而她自己也到了山穷水尽、心力俱竭的地步。这个时候,朝廷传来了大家等待已久的那句话:“《汉书》完成了,褒奖曹大家。”从舞台处理上说,这是简单的幕后交代,但是这时候观众激动了:不啻一声春雷,台下的观众和班昭抱着同样的心情:多年大旱,终于盼来了这场春雨,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要有这么多人牺牲,这个沉重的代价,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与之对立的爱国知识分子所坚持的为理想和信念——守志不渝和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的胜利。张静娴成功地塑造的班昭,在戏剧界赢得很大的反响,2011年,我有幸在向她颁发昆曲终身成就奖时,真诚地说了一句:“谢谢您!”我在另文《艺术·生活·气质》中已有阐述。对于杨导演的艺术探索,我想在看了越剧演出后,又有了新的理解。剧本的成就、导演的构思和演员的创造,三者缺一不可,又首在导演的运筹帷幄,激发了演员,丰富了剧本。
几年以后,杨小青为杭州越剧院重新排演了越剧移植本《班昭》。果然,这是杨导演在原有的基础上跨上了新的台阶。
如果说,昆曲本《班昭》,让观众生动地看到了班昭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那么,越剧移植本《班昭》,更使我们有机会感知到班昭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当然,重头戏还在后面的两场戏:曹大家薄醉归来乍见到大师兄后的性格发展,以致《汉书》续成后,师兄溘逝,直到班昭恢复了自己以后,她在泫然和俨然中的悄然归去!她是殉情,也是殉道——一个一代女中豪杰为自己的理想而献出了自己的毕生,这是功成于道的凤凰涅槃。
杨小青在越剧本中有所取舍,但没有大动干戈,而是在每一场、每一段甚至每一句念白中,进行了精心的斟酌;对于每个细节的生发和衔接,调和鼎鼐,匀称了针线。因此,她把张静娴老师请来,为越剧本塑造班昭的陈晓红进行辅导。终于,陈晓红在舞台上有了扬长避短和发挥自己优势的机会。这也是戏曲舞台上长跑的接力赛。
导演的努力,使即将告别人世的班昭,有机会向观众报以灿烂的微笑。这个微笑使满场的观众得到相应的满足。因为人的理想观念可能受到时代的约束,但是人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必然穿透历史、超越时空。
杨小青作为一个优秀的导演和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她在艺术实践中贯穿了自己的信念,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人所具备的几千年生生不息的骨气和志气。
我认为:昆曲本《班昭》的成功,不仅为戏曲舞台增添了一个闪光的艺术典型,而越剧本的成功,首先是承袭了昆曲舞台艺术的凝重、洗练和精到的传统;尤其在表演艺术上的蕴藉与含蓄,而越剧本的优势,在同一位导演的苦心经营中,又注重越剧的写意与工细兼备的表现空间,更加灵活生动。
陈晓红的成功,有张静娴的心血,而张静娴重演《班昭》,必然会汲取越剧有益的营养。归根结底,是杨导演的慧心和慧眼,用同一双巧手,以不同针线,绣出了两株不同的玉兰花:一株是皎洁的白玉兰,清沁宜人,一株是略带紫色的广玉兰,暗香动人。
我相信,再过几年再看昆曲本和越剧本,我们再开研讨会,在张静娴和陈晓红的曹大家出来谢幕时,会更加容光焕发。因为《班昭》不朽,杨妈妈也还未老。因为舞台艺术永远是常演常新常青的。因为杨小青导演的眼神,始终是年轻的。
我要说的杨小青导演的精神,就两句话:作为一个今天始终在为事业不断作贡献的文化人,她可以通过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创造以及不断地改善条件、改变环境,从而不断地挑战自己和战胜自己,最后在戏曲发展史上留下最真实的自己。我想,三十年前的杨大姐可能没有想到能达到今天的高度,但是她今天的杨妈妈所得到的,足使不够勤奋的同行们有所感奋和感悟。因为艺海无涯,不进则退,有理想的人绝不会被眼前的进退所困惑,更不会被鲜花和掌声所迷惑,绝不会被浮名和虚衔所陶醉。
聪明的杨导演所以被那么多同行和戏迷眷爱,因为她始终清醒地审视着自己。我有八个字,为本文作结:檐滴石穿,分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