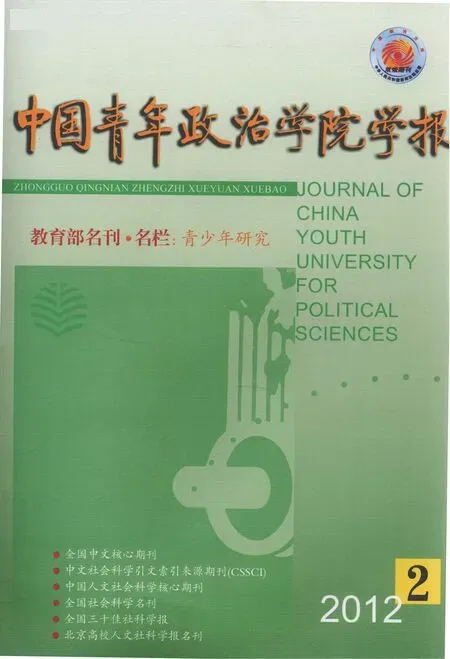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绩效评估报告——基于皖北农村与胶东城市的实证考察
李 亮 汪全胜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一、问题背景:后立法时代的法律绩效评估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2011年刚刚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而据有关学者统计,自1979年到2007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颁布了409部法律,其中修改了147部,占通过法律的35.94%。而在历年的立法中,修改过2次的有11部,3次的有4部,4次的有3部[1]。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立法已经进入了“后立法时代”[2]。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2010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中提出要加强立法调研和论证,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技术规范研究和应用工作,不断提高法案审议的质量。结合常委会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法律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选择一到两件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开展立法后评估试点工作,探索建立立法后评估工作机制,并且启动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立法后评估试点工作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执法检查工作,这可以视为立法后评估,也就是法律绩效评估从理论到实践、从制度设计到实践操作的具体检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出“后立法时代”的来临是有理论与实践依据的。一般认为,法律绩效评估是政府及有关主体对法律执行的情况加以说明、检验、批评、量度与分析,其作用在于确定法律政策是否合法、正确,推断法律之利弊,为将来法律的完善提供参考。
相对于法律绩效评估这个新鲜事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07年4月24日公布,2008年5月1日起正式生效,其实施已有近三年了。毫无疑问,条例的出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董铭诉上海徐汇区房管局”案,到“任俊杰诉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和城建档案馆”案等,都颇受各界关注,引发激烈讨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绩效的问题随之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与思考,但对于该问题的探讨却主要集中在理论上,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实证研究则关注的比较少。一部法律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实践的社会效果,这似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更令人遗憾的是,仅有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绩效的实证研究也大多聚焦在城市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实施状况、公众评价等实证研究上,关注农村地区政府信息公开立法运行实施状况的研究微乎其微,尤其缺乏对比研究。该领域的研究长期得不到重视,基于此,笔者以实证调查为基础,借助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着眼于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在城乡地区的运行现状、原因、完善思路等方面的探索,较为客观地呈现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绩效评估的结论及启示,以期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实证考察方面,选取皖北农村地区和胶东城市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农村方面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阜阳市和亳州市的部分地区①该地区位于淮河平原,在古代被誉为“吴头楚尾”之地,地处安徽省北部,过去以传统农业为主,社会构成比较复杂,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历来被视为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天然宝库,选取该地区作为调查地,具有典型代表意义。作为调查地,具体包括颍上县、利辛县、涡阳县、蒙城县、界首市等。胶东城市地区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青烟威地区,具体包括青岛的市南区、市北区、崂山区、阳城区、平度市;烟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山区、芝罘区、招远市;威海的环翠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荣成市、乳山市、文登市等地区。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座谈会、文献分析等方法,对调查结果运用SPSS数据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确保调研数据的真实、可靠。同时,需要交代的是文章分析的依据以本次调研为基础,故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运行现状的评估
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运行现状的评估主要由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知评估与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绩效的了解、态度与评价两部分构成,具体阐释如下。
(一)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知评估
第一,在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知上,市民的信息意识要普遍高于村民。在农村地区的调研显示,农民普遍缺乏信息意识。“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政治要求;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需要;是转变执政方式,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制度性保障。”[3]同时,我国各级政府掌握着全社会绝大多数的有用信息[4],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满足公民自身生产、生活的需求。然而,通过走访却发现农民普遍缺乏信息意识,甚至对于什么是政府信息也了解不多。调查统计的数据显示,在“您是否了解什么是政府信息?”一项的调查中,有57%的村民表示不了解,有29%的村民表示了解不多,两项合计高达86%。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回应度较低。有超过一半的人对该条例完全不了解,有30.06%的人了解一点,基本了解的有12.88%,非常了解的仅有2人”[5]。相对于农村地区,城市地区的调研统计数据则显示63%的市民比较了解,17%的市民十分了解,两项合计比例为80%。这说明了市民的信息意识要普遍高于村民。对村民与市民的走访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第二,村民和市民都需要政府信息公开。虽然农民的信息意识普遍缺乏,但农民也渴望政府信息公开,在调查中发现,农民无论对国家关于农村的大政方针政策、财政收支状况、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宅基地使用的审核情况,还是计划生育政策及罚款等情况都希望能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由此,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明村民的参政议政愿望还是有的,问卷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您认为是否应当公开政府信息?”一项调查中,高达93%的受访者表示应该公开。对比村民,市民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更高,在同类的调查中,认同需要公开政府信息的受访者的比例高达98%。
(二)政府公开信息的传播途径与立法绩效评价
第一,在政府公开信息的传播途径上,城乡地区也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通过调查了解到,村民获取政府信息的途径仍以传统媒介为主,统计数据显示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介获取政府信息的人群比例高达89%。段尧清等人的调查显示,当前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途径主要为广播(62%)、报刊(54%)等传统媒体,其他途径如新闻发布会、电话、信息公告热线等仅占10%左右。因此,当前政府信息公开应以传统媒体为主,方便广大公众[6]。
第二,对政府信息的关注面城乡也有差异。向佐群在湖南、山东等地的调研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即“农民较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政府信息”[7]。而城市地区的调研则显示,市民关注政府信息的目的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该项调查统计显示,基于参政议政、保障知情权而关注政府信息公开的比例分别占23%和16%,相对于农村地区的统计数据,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第三,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绩效的评价普遍偏低。在农村地区的调查发现,村民对政府信息公开绩效的总体评价较低。《条例》第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然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在实践中几乎被倒置,演变成了“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能不公开就不公开,免得招惹麻烦事”。在一项“您对目前政府信息公开实施状况的总体评价怎样?”的调查中,统计数据显示,仅有1.5%的受访者表示满意,高达98.5%的受访者对政府信息公开实施状况的总体评价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绩效在农村地区的实施不容乐观。而在城市地区的调研也显示,市民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绩效的总体评价不高。在同类的调查中,统计数据显示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绩效评价不高的比例也达到87%。总体看来,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在城乡地区的评价不高,情况并不乐观。
三、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现存问题及成因的评估
政府作为信息公开的主体,尤其是基层政府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地方及基层政府信息既是公众的关注主体,也是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的薄弱环节。“在众多问题中,比较集中的观点有两个:一是政府信息公开在地方贯彻执行不到位;二是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不强”[8]。上文具体阐述了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在城乡地区的运行现状评估。现就现状所呈现的问题及成因作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评估。
(一)城乡地区的信息效能的差异
城乡地区的信息效能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在信息的获取能力、识别能力、整合能力、利用能力等方面。以上文中提及的皖北的G县为例,在G县2008年、2009年、2010年度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中没有出现一起提起行政复议的案件,同样也不存在行政诉讼的案件。当真是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较好地满足了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从而没有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形吗?答案是否定的。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起步较早、信息公开配套制度相对比较完善的上海市为例,2008年度因申请信息公开而提起行政复议的683件,行政诉讼258件[9]。相比较而言,市民在信息获取能力、识别能力、整合能力与利用能力等方面的情况都普遍好于村民。一方面,市民的信息意识普遍较高,比较关注政府信息公开;另一方面,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健全,能够为市民在获取政府信息乃至于主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方面提供极大的便利。
(二)政府公开的信息价值不高
目前,就农村而言,政府公开的有价值的信息较少,大量信息与村民的具体关联度不高,信息内容不适应生产、生活的需求,而大量与生产、生活有关的、有价值的政府信息应该公开却没有公开。这是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绩效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皖北的利辛县为例,该县2008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累计630条,便民服务类信息仅占5.5%,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类信息占2.2%,而政府工作动态类信息却高达35.4%,在笔者对当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访谈中,工作人员也坦言,“信息公开一旦出了问题,那就麻烦了,所以还是能不公开就不公开的好”,在对当地村民的访谈中,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公开的政府信息与自身关系不大,关注政府信息公开没有意思”。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李学的实证研究中被解释出来。他发现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未取得公众的认同,民众并不认同政府现有的公开行为。
(三)政府信息公开传播存在障碍
政府信息公开在传播方式上存在障碍,这种障碍在农村地区表现得较为明显。在上述调查中,我们得出了村民获取政府信息的途径以传统媒介为主的调查结果,在向佐群等人的调研中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调查发现,大部分的政府信息都是通过政府网站等现代传媒手段公布的,只有少部分信息通过传统媒介公布,这样就会造成信息传播与信息接收的错位,从而导致信息公开的渠道不畅通。莫于川教授在苏、闽、川、滇等省的调查中也发现,“公共图书馆作为条例中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场所遭遇了‘冷场’尴尬。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共图书馆的上述优势,只在少数大城市存在。对于广大一般性地区而言,非但上述优势荡然无存,反过来,图书馆公众认知度低、软硬件条件匮乏等劣势恰恰使其难以承担公开条例赋予的新职能”[10]。
(四)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配套机制的缺失
政府信息公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在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尤其是缺乏监督与问责等配套制度。《条例》第35条规定,“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可以发现,关于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的责任规定是粗线条的,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对于“情节严重”,什么情况才能“构成犯罪”,以及给予“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标准,均未明确。
四、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评估启示与完善思路
(一)宏观层面:制度有力保障
第一,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调研发现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绩效不乐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效力不高,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没有纳入到公开的范围,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只能约束各级政府,对人大、检察院、法院及党的工作机关都无约束力[11]。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使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上升到法律层面,提高法律效力,从而在立法上和制度上保证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入推进。
第二,突出立法的针对性,重视城乡差异。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主要是基于城市地区的制度框架考量的,表面上虽然保持了体系的一致性,但到头来还是免不了“麻烦事”,在调查中发现的种种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对此的一种佐证。上海市立法研究所和上海市社科院法学所联合起草的针对世博立法的评估报告中指出,追求体系结构完整,弱化了法规的针对性、操作性和专业性,看似周全却难以有效实施,只能用各种方式来不停地“打补丁”。因此,在此后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及其完善的过程中,应该认真审视这一情况,立法的针对性并不会破坏体系的完整性,反而会有效地提高立法的效益,最大限度地实现立法目的。
(二)中观层面:机制配套完善
第一,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考核方面,有必要将公众参与度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成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进行监督检查的重要对象[12]。以此敦促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切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同时也有助于形成信息公开稳健运行所需的社会环境。
第二,引入独立第三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绩效评估机制。有学者认为,独立第三方评估主体是指由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以外的人员进行的正式评估,包括受行政机构委托的研究机构、专业评估组织(包括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中介组织、舆论界、社会组织和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等多种评估主体[13]。目前,我国已经开展的立法绩效评估的实践中,主要是立法者自身绝对主导开展的“内部性”评估,虽然“有效把雇员与整个评估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自我管理、自我调控”[14],这种评估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在未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绩效评估中,应逐步引入独立第三方的绩效评估机制。
(三)微观层面: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平衡
第一,政府信息公开立法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条例》中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服务的宗旨和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调查中发现政府的信息公开并没有严格遵循该宗旨与原则,而更多的是以政府自我为中心。
第二,构建多元化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通过调研发现,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和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之间存在着错位问题,向佐群等多位学者的调查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因此,在未来的政府信息公开中要构建多元化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形成政府信息公开传播网络,充分重视传播渠道不畅所产生的裂痕,把握好信息传播渠道的有机结合与转换,尤其要做好基层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充分重视传统媒介(如电视等)在农村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同时加强现代传播媒介在城市地区信息传播中的建设。
[1]杨 斐:《法律修改研究:原则·技术·模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1页。
[2]汪全胜:《立法后评估概念阐释》,载《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3]陈福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几个问题(上)》,载《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1期。
[4][10][12]莫于川林鸿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准备调研报告——以苏闽川滇数省作为考察重点》,载《法学》,2008年第6期。
[5]龚来良:《武汉市政府信息公开现状实证调查与思考》,载《经济师》,2009年第3期。
[6]段尧清:《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响应情况调查报告》,载《图书情报工作》,2008年第4期。
[7]向佐群:《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页。
[8]贺 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实施现状及其启示——以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网上数据为分析范本》,载《电子政务》,2009年第11期。
[9]周汉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问题与对策探讨》,载《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7期。
[11]石雨霞:《浅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贯彻落实》,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7期。
[13]程祥国李 志:《刍议第三方政策评估对我国的启示》,载《行政与法》,2006年第3期。
[14]Laird W.Mealier& Gary P.Latham:“Skills for Management Success:Theory Experience and Practice”,Richard D.Irwin,A Times Mirror Education Group Inc.Company,1996,p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