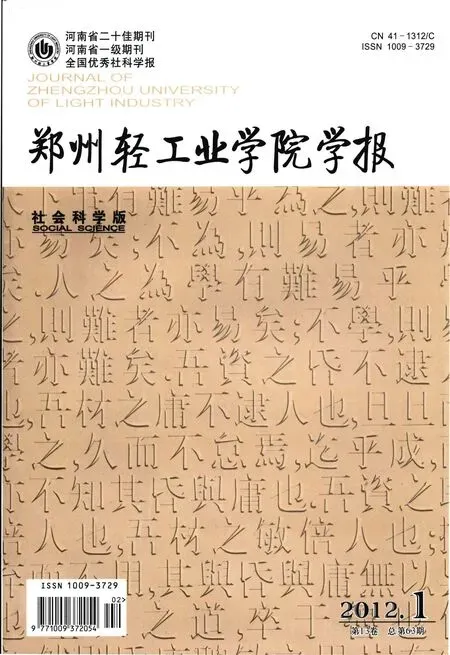从间性思维看林语堂的翻译策略
陈奕曼
(广东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广东揭阳522000)
间性强调个体内部诸系统以及不同个体间的独立与共存,是一切事物之根本。全球范围的文化交流使间性理论成为文学、美学、哲学等学科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间性的凸现”已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共识[1],为当下的学术研究拓展出新的视野。然而,间性虽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传统的学术研究或是受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或是宣扬文化全球化,抹煞了文化的多元性。不同文化间的冲突随着全球经济交流的频繁而日益显现,给跨文化交流带来障碍。
译者作为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文化输出和输入过程中,不仅要保证目的语读者能正确理解译文,还要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特征。本文拟以跨文化翻译的成功典型——林语堂先生的翻译作品——为例,研究间性思维在跨文化翻译中的具体运用。
一、间性理论与间性思维
间性理论主要包括主体间性、文本间性、文化间性、文学间性、话语间性等,其中又以主体间性为其理论基础。主体间性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并非主体对客体的支配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共在关系,并强调主体间的平等沟通与融合。文化间性是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内的具体表现,体现了不同文化文本之间的平等对话,强调文化的共存及融合。
间性理论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哲学渊源,其生成涵括了差异哲学、他者理论、视域融合及交往理论的相互借鉴、融合与发展。差异哲学坚持二元对立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强调主动的、发展的、具有创造力的“延异”,认为“存在的基本原则不是统一而是差异,归根到底,存在不是统一,而是繁多”,“事物不同于它自身,存在就是差异”。[2]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是间性理论的渊源之一。从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角度来看,文化之间的沟通既是当前视域与过去视域历时融合的过程,也是自我视域与他者视域共时融合的过程。[3]同时,间性的生成又来源于巴赫金的“他者理论”。“他者理论”彻底否定中心主义,认为“存在即共存”,是有差异的共存。不同文化间必须允许“他者”的存在才能实现沟通对话,否则,交流就无从谈起。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和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以上诸多理论观点皆为间性理论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人总是在某种‘间隙’的意义上求得生存的价值”[4]。所以,间性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本质,无“间”不立,对它的把握与运用,在翻译领域自然是至关重要的。
间性思维是一种通过多元对话而达致的二元互补、多元互动互化的居间思维,正是它可以担纲文学对话的思维基础。[5]它不承认主体对客体的宰割性和霸权性,所有的人、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是间性地联系在一起的。[6]间性翻译思维就是译者须始终保持在原文与译作、原作者与译文读者、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不偏不倚,扮演好“中间人”的角色。语言、文化、思想都是二者之间的存在物,既不属于彼又不归于此,一切都处于“间”的状态。这与梁实秋先生倡导的“中庸”翻译可谓异曲同工。“中庸”翻译也体现了“间”的思想:译者必须立于原作者与其自身二者之间,采取适宜的翻译策略,将作者作品的内在精神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中庸”的完整含义,在最大程度上调和直译与意译之间、归化与异化之间的矛盾。
在翻译活动中,间性思维与间性理论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具体的翻译实践。一方面,哲学上讲“意识指导实践”,在翻译过程中亦是如此,只有具备间性思维,对中西方文化有清晰的认识,才能在翻译中运用间性理论,正确处理不同文化差异导致的问题;相反,任何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都会阻碍跨文化翻译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意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反映意识”,间性思维来源于对间性理论的认识与接收,只有从内心认可与接收了某一理论或主张,才有可能将其付诸具体的实践;而对间性理论的运用反映了译者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间性态度。因此,在翻译中,间性理论与间性思维缺一不可。
二、间性思维与跨文化翻译
翻译理论界历来就存在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之争,这种争论本质上没有脱离“译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等中心主义的桎梏,而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使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总处于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中,把翻译本质问题遮蔽在混沌之中。[7]因此,译者应该跳出这个“中心”的枷锁,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用更科学的理论解决翻译中出现的问题。间性理论和间性思维应运而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和方法。
翻译本身就是一种间性活动。这是因为,翻译涉及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源语言与目的语、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扮演着“中介”的角色,是两种文化沟通的桥梁。关于翻译的这种间性特征,最早的论述可追溯至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所作的《会饮篇》(Symposium),他在转述其师苏格拉底关于“爱”的思想时说:
他们(精灵)来往于天地之间,传递和解释消息,把我们的崇拜和祈祷送上天,把天上的应答和诫命传下地。由于居于两界之间,因此他们沟通天地,把整个乾坤联成一体。他们成了预言、祭仪、入会、咒语、占卜、算命的媒介,因为神祗不会直接与凡人相混杂,只有通过精灵的传递,凡人才能与诸神相沟通……精灵的种类也很多,爱就是其中之一。[8]
这里“爱”(“爱若斯”,Eros)扮演人与“神”之间的“中介”,使他们之间实现沟通,在各种事务中担任必要的媒介。简而言之,这里所说的“爱”的作用也就是间性的作用,这种作用使万物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各自发挥着本身的优势。苏格拉底所说的“爱”是以“翻译”的形式形成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媒介,使人与神的沟通成为可能。[9]钱钟书曾直接点明翻译的居间作用,认为翻译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姻缘”,缔结了国与国之间惟一的较少反目、吵嘴、分手挥拳等的危险的“姻缘”。[10]总之,翻译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沟通来达到共融。越来越多的译者也逐渐意识到单纯的归化或异化、译者中心或读者中心皆无法有效解决跨文化翻译中的问题,近年来对翻译间性作用的关注成为热点。
翻译致力于两种语言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在跨文化活动中发挥间性的作用。因此将间性理论引入跨文化翻译,以间性为指导,立足作者与读者、原文与译文、源语言与目的语之间,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力求实现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融合,这对于解决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冲突、文化对峙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林语堂的间性翻译思维及其在翻译中的表现
林语堂是成功进行跨文化翻译的典型代表,他具有致力于两种文化平等对话的间性思维,并将其应用于大量的汉英作品翻译,其中占较大比例并较有影响力的是他的Chuangtse(《庄子》)和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浮生六记》)。此外林语堂还英译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如《兰亭集序》(The Orchid Pavilion)及《归去来辞》(Ah,Homeward Bound I Go)等,这些作品都有他间性思维的体现。
翻译是语言文字的操作过程,但绝不仅限于此。译者面临着跨时空、跨语言和跨文化的巨大障碍,在译文中如何真实地传达和表现原文的信息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就对译者本身的条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1]译者立于原文与译文、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译者,不可能轻而易举就完成一部作品的理解和翻译任务,他们头脑中总是储备着丰富的知识,本身又深受某种文化背景的影响,有着独特的情感和生活阅历,以自己特有的价值、审美取向、人生观审视和理解文本。林语堂出身于东方文化,对之有成熟的认识和深厚的情感;同时,其基督教牧师家庭的影响和后来30余年旅居海外的生活创作经历也赋予了他西方文化的背景[12],这样双重的文化背景使其有着中西合璧的文化观念,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和翻译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林语堂的哲学思想也呈现出西方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儒佛道哲学的中西结合间性思维。除了林语堂特殊的生活背景和他对东西方文化的熟悉这些客观因素之外,他本人对东西方文化的观点和态度也在他的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林语堂拥有中西合璧的文化观,所以在翻译中更易站在中间的位置,客观地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文化选择的态度上,林语堂以去粗取精、多元整合为特色。在他的翻译中,间性的运用颇为明显。如“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兰亭集序》)译为
In the ninth year of the reign Yungho[A.D.353]in the beginning of late spring we met at the Orchid Pavilion in Shanyin of Kweich'i for the Water Festival,to wash away the evil spirits.
原文“永和”、“癸丑”都是西方读者所不熟悉的时间概念,而详细解释的话又不免显得累赘,所以林语堂在直译之后又加上确切的时间,以方便读者阅读理解。另外,“修禊”是古代的一种祭祀活动,文人墨客聚集一处饮酒赋诗,祈求一切顺利。林语堂取其本意,译为“Water Festival”,并附加简短的解释,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原诗的意思。
翻译策略是译者文化观在其作品中的体现。从其译作可以看出,林语堂很注重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在他的翻译中,归化与异化并未被完全对立,而是平分秋色、并行不悖地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既体现了译者游刃于中西两种文化的自由,也表现了他对两种文化的态度。[13]他一方面考虑到读者阅读需要和接受能力,用简洁明了的、归化的思维方式来传递源语文化,另一方面,又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原汁原味,异化翻译一些专有名词;必要的时候将两种方式相结合,达到双重效果。这种翻译策略充分体现出林语堂的间性思维,即在处理归化与异化关系中立于归化与异化之间,使其各自发挥效用。比如对于汉语中西方读者不熟悉的概念、表达等,林语堂不是一味迎合西方读者而抹煞原文的特色,而是巧妙地利用各自语言的关联性进行贯通,使其互通有无。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东坡诗文选》)译为
But rare is perfect happiness—
The moon does wax,the moon does wane,
And so men meet and say goodbye.
I only pray our life be long,
And our souls together heavenward fly!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是他最著名的词作之一,反映了中国人在月圆之夜普遍的思念和怀人的情绪。虽然在西方文化里月亮与离愁别绪没有关联,但读者通过对全诗的阅读能够自然地体会到原诗所表达的情感。汉语表达讲求对称,经常出现四字格,如“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但英语强调简练,一般不喜重复,林语堂充分了解东西文化的差异,将其译为“The moon does wax,the moon does wane,/And so men meet and say goodbye”,简短又不失其意。另外,“婵娟”一词本指“明媚美好的月色”,如直译恐西方读者不明所以,意译又有失其美感,所以林语堂站在“间”的角度,将其意思升华,译为“our souls together heavenward fly”,符合西方基督教中有关灵魂和天堂的思想,有效传达了原诗的神韵,同时又整合了两种文化,促进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在西方的传播。
在翻译中,常常会出现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不能兼容的现象。所以应该把归化与异化适度结合,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既为目的语读者提供原汁原味的外国作品,又符合读者的口味。比如在下例中林语堂用异化手段翻译了不会给西方读者带来理解困难的修辞语句之后,对典型的中国典故人物“尧舜”用归化的手段进行了概括化的处理。“有笔头千字,腹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东坡诗文选》)译为
With a thousand words from our pens,
And ten thousand volumes in our breasts,
We thought it not difficult to make our,
Emperors the best.
从林语堂的译文可以看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保持源语文化的韵味,同时又要充分尊重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阅读需要,以“间”的态度对待其要翻译的作品。林语堂正是将这种间性思维运用到其翻译实践中,他的作品才在西方读者中广受欢迎,这足以说明其译作的成功。
四、结语
随着全球文化交流速度的加快,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显得日益重要。对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把握也成为跨文化翻译过程中不容小觑的问题。在跨文化翻译中,既不能抹煞源语文化的个性,也不能无视目的语文化的境况,而应当像林语堂那样站在中间的角度,保持不同文化的特点,促进不同文化形态自由平等地对话与交流。
[1] 郑德聘.间性理论与文化间性[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4):73.
[2] [美]加里·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M].辛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412.
[3] 蔡熙.关于文化间性的理论思考[J].大连大学学报,2009(1):80.
[4] 蔡新乐.张柏然,许钧.翻译的本体论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9,89.
[5] 鹿国治.间性思维与比较文学[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42.
[6] 王虹光.论对外传播的间性思维[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363.
[7]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35.
[8]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的《会饮》[M].刘小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74—76.
[9] 蔡新乐.自我翻译:行走在翻译“间性”之上的思想家的苏格拉底简论[J].上海翻译,2008(1):11.
[10]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
[11] 李洁.古典艺术散文译者的先在性[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4):23.
[12] 王少娣.试论林语堂翻译文本的选择倾向[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2):69.
[13] 王少娣.跨文化视觉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