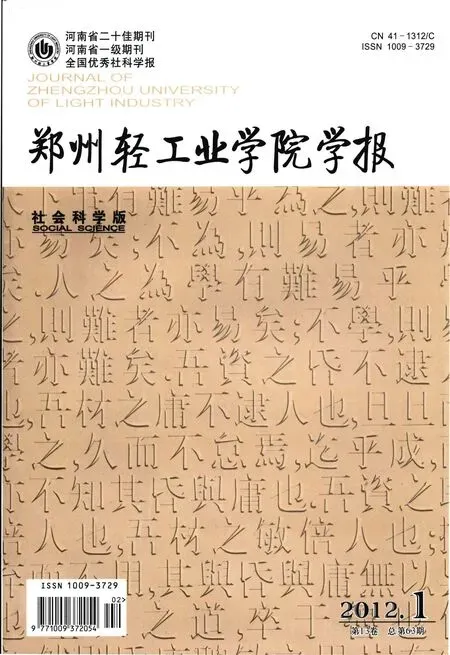先秦儒学的两个路向——浅析孟子与荀子哲学思想之异同
罗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
对于孟子与荀子之间的关系,如仅仅将孟、荀作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来概括,则过于简单化了。冯友兰认为孟子代表了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翼,而荀子则代表了儒家的现实主义的一翼,同时指出孟子有左也有右,左就左在强调个人自由,右就右在重视超道德的价值,因而接近宗教;荀子有右也有左,右就右在强调社会控制,左就左在发挥自然主义,因而直接反对任何宗教观念。[1]笔者认为这个概括是很有见地的,本文拟就这几个方面进行比较,以阐发孟子与荀子哲学思想之间的异同及其对后世儒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天论:准形而上学与自然主义
“天”在先秦时代人们的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功能的角度看,“天”在古代扮演了五种角色,分别是主宰之天、造生之天、载行之天、启示之天、审判之天。这样的“天”一直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并且为人间设立了秩序。但是,随着天子失德,“礼崩乐坏”,对“天”的信仰出现了两大危机:造生与载行之“天”由于不再表现仁爱之德而变为自然之天;启示与审判之“天”由于不再保障正义之德而变为命运之天。这两种观念分别以“天”为具象的自然或以“天”为盲目的命运。这样一来,人们既不能从自然中获取超越的理想,又不能从人间复杂的境遇中发现正义的原则,因而陷入精神危机。
孔子的“志业”在于把人的命运转化提升为使命,再将它上溯于“天”,重新为“天命”下定义,让人人自觉其内在向善的力量,经由择善而走向至善,以符合“天命”的要求。孔子一方面去除了“天”的神学宗教色彩,另一方面将人的道德实践与“天”联系起来,唤起人们内在的自觉性。孟子在这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不过孟子哲学中的“天”较具动态性和威权性,相对地增加了形而上学色彩,“天”成为人类道德法则及其实现的权威性根源的代称或假定。也就是说,孟子假定存在着这样一种超越的权威,即道德规则存立所要求的一种因果存在性,亦即其性善和道德学说的形而上学的根据。孟子云: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2](P345,P354,P348)
在孟子看来,宇宙实质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宇宙的形而上学原则,人性就是这些原则的例证,“天”就是这样一个道德的宇宙。一个人通过充分发展他的禀性,就不仅知“天”,而且同“天”。这种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天”,实际上起着一种象征性作用,它作为义理之基础的权威代表者,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荀子与孟子一样曾经游学于稷下,并且可能是稷下最后一位大思想家。身处这样一个大的学术中心,荀子的思想明显受到其他各家的影响,他在对孔孟和诸子的继承与批评中开辟了先秦儒学的新局面。相比于孟子重视对孔子之学的继承,荀子更注重发展孔子之学,其思想更具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对孟子准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倾向的批评也甚为严厉。荀子曰: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避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讠雚讠雚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3](P84-85)
在天论方面,荀子所言之“天”为自然之天,这大概受到老庄自然主义学说的影响。荀子曰: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3](P325-327)
孟子所言之“天”为义理之天,以人性为“天”之构成的一部分,此为孟子言性善的形而上学根据;而荀子所言之“天”是自然之天,其中并无道德的原理。荀子以为,自然界之现象乃自然按照其规律运行使然,其所以然之原故,圣人不求知也。荀子把人看做在宇宙中与天地同等重要的存在,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利用自然提供的一切来创造自己的文化,履行作为人的职责。所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3](P336)。
荀子将自然的人与自然的天地齐观,大大提高了人的价值,其“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更加接近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能力,为其人性学说提供了依据。
二、人性论:性善与性恶
人性论在孟、荀的哲学思想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对孟、荀人性论的比较研究不仅仅是区别孟、荀哲学的关键,更是进一步研究孟、荀哲学思想的必经之路。
孟子提出人性善,实际上是为了给孔子的道德实践理论寻找依据。他试图回答行“仁”、义利之辨、忠恕之道后面那个为什么“行”的问题。在孟子看来,人性善是天然永在的,其作用却受到外在负面因素的干扰,道德实践者的任务在于主动地排除这些干扰,以使善端得到充分扩充,使人成为“圣人”。孔子的道德理论完全是以道德实践为基础的,其认知基于实证性经验。孟子在这方面与孔子相似,其性善论以经验理性主义为基础,以实证性经验为认知之基,但孟子企图在此之外提供理论性证明。也就是说,孟子以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经验作为人性善的证明,但是他又在经验理性之外提出先验的“天”作为道德规则存立所要求的一种因果存在性的假定,亦即其性善论的形而上学的根据。只有“尽心”“知性”方能“知天”,“知天”方能“立命”,而“天”与人又具有某种同质性。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所谓人性皆善。孟子曰: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2](P77-78)
孟子所谓性善,在于人皆有仁、义、礼、智之“四端”。“四端”扩充,则能为“圣人”。人之不善不在于其本性与善人不同,而在于不能扩充其“四端”,故曰: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2](P298)
孟子所说的“端”表示了一种行善的可能性,即天然的倾向可为品德之端,人性可由此不断生发,道德能力遂可在心中育成。因此,孟子的性善论并不是说人性本善,而应该是人性向善,是应然而非实然;如果不能将善端扩充,不仅不能成为善人,甚至可能受到外界的干扰而成为恶人。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要扩充善端,是因为善端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和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故孟子曰: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2](P313)
孟子性善论的缺点在于忽略了社会性与个人性向的互动关系,以为行为表现纯然来自个人天性,这一点是孟子不及孔子的地方。认为善端能够不受外界影响而自然扩充,就等于把社会当做了理想主义的实验场。事实上,人性是在不断成长的,这与其先天的素质和个性倾向有关,但绝不能期待善端自然地扩充而成为一个“圣人”。对大多数人来说,此天性表现是人性潜能和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善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源于生活,只有在社会生活和交往关系中实现的善才是真正的善。汉代董仲舒亦谓人之质中本有善端,不过董仲舒以为若性中仅有善端,则不能谓之善,故曰:
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质,尚安非善?”应之曰:“非也。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比类率然,有何虑焉?”……吾质之命性者,异孟子。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为,故谓性未善,善过性,圣人过善。[4]
针对孟子性善论中的不足,荀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其实,荀子人性论的关键并不在于证明人性恶的事实,而在于他的人性论学说更注重人自身的认识状况、努力状况以及人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使他更自觉地将礼乐作为一种教化手段而制度化。
荀子论人性,首先区分所谓性、伪。荀子曰: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之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3](P477-478)
性是生之所以然者,因而属于“天”。荀子所说之“天”是自然之天,天自有其“常”,其中并无理想和道德的原理,因而人性中也不会有道德的原理。道德乃是人为的,即所谓伪也。荀子云: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3](P475-476)
孟子所谓性善,是指人性中本有善端,扩充之即可为“圣人”。荀子谓人之性恶,是指人性中非但本无善端,而且有恶端。人生而有欲,有了欲望就要得到满足,荀子并不把欲望本身当做恶,而是说“顺是”,即对欲望不加节制而任其扩张,最终必然滑向恶的一端。荀子所谓的恶不是指人性中已经包含了恶的因素,因为荀子看到了所谓的善恶并不是一个人的善或一个人的恶,之所以有善有恶,根本在于人如何通过自身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使自己得到实现——“善”就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而“恶”就是个人利益的实现妨碍或损害了他人利益的实现,使人与人的关系处在一种失当的状态。总之,无论善恶都是不能脱离具体社会生活的。
人虽然没有善端,但荀子对于人的聪明才力很有信心。人有此才力,若告之以“父子之义”、“君臣之正”,则亦可学而“能之”。积学久而成为习惯,“圣人”可积而致也。荀子在教化方面特别重视礼乐的作用,认为这是“化性起伪”、成就善人的关键。荀子曰:
“涂之人可以为禹。”……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3](P487-488)
孟、荀的人性论其实是人本经验主义认知的不同侧面的相关表达。孟子的真正主张是人有行善天性,但此天性被后天因素压制而不得发挥以至于在现实中有恶的表现;荀子则说人的天然欲望不加节制的扩张常常容易导致作恶。两人的直接判断一致:现实的人有作恶的倾向,但通过主观的内外努力可最大限度地增加为善的可能。孟子性善论的实质在于极大地关心行善的可能性,而荀子则更加注重如何积善成善。
三、道德哲学:孟子的反功利与荀子的功利主义
孟、荀哲学的差异在他们思想的出发点上就表现出来了。虽然孟子同样肯定世俗道德的功利价值,但其根本的主张还是反功利的,这可以说是在道德哲学上对孔子之德的继承;而荀子则明显受到墨家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这在其思想的各个方面都有表现。
孟子的反功利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当时世俗功利的不足,是想从行为的动机出发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道德哲学。孟子并不是不要个人功利,只是在孟子看来,讲道德必须是纯粹的,不能出于功利的目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自足性的道德没有外在的功利目的,之所以要去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不安,行善就是要“尽于人心”。行善当然可以产生有利于社会的结果,此结果虽然极为可贵,但终究只是行善的附带结果,不是也不应当是行善的初衷。
从道德起源上来看,孟子认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有人伦以及建立在人伦之上的道德原则。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国家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有用,而是因为它应当存在。
荀子则以另一种方式解释道德实践与社会生活。荀子对“天”持自然主义的态度,而且非常重视人的地位。天行有常,人能够利用自己的才力来认识其规律,因此就会产生“制天命而用之”和“天人相分”的功利主义自然观。应该说荀子的功利主义思想虽然受到墨家的影响,但其根本还是儒家的,只是相对于孟子而言,荀子的思想似乎更加接近人的真实想法和社会生活的现实,因此他在“礼”论方面有了不同的见解。荀子并没有将人的利欲视为恶,而是认为利欲恰恰是促使礼义产生的基础。人们正是为了解决饮食衣帛、饥渴寒暑等问题才结成社会的,道德礼义随之产生。荀子曰: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3](P368)
又云:
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离居而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3](P169)
社会国家和道德礼义是为适应和调解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缘起不是因为它们应该存在,而是不得不存在。没有国家、没有道德,人就不能生存。
总之,在道德哲学方面,孟子从行为动机出发反对功利主义,要求纯粹的道德不能出于功利目的,国家与社会起源于人伦,具有应然性;荀子则坚持“天人相分”的功利主义,以“礼”来规制现实生活,国家与社会起源于人的现实需要,具有必然性。
四、孟、荀哲学思想对后世儒学的影响
儒学的核心在仁学,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仁。在孔子看来,德性必须落实到礼,礼的落实又必须有仁心作为内在的基础,“不知礼无以立”。不仅仁建构礼,而且礼对仁同样具有建构作用。如果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孔子,孔子还是更看重价值论。但没有礼,无以体现仁,仁必须落实到礼,这本身就有功利主义倾向。所以说孔子是现实主义者,在这方面荀子更接近孔子。
孟子发展了孔子仁学的一面,而荀子发展了孔子礼学的一面。但荀子并不排斥仁学,只是主张以礼来建构仁。孟子及后来的儒家心学都排斥外在规范,过于强调人的内在道德自觉。在他们看来,由外在规范对人的强制作用而产生的社会秩序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不是建立在人的内在自觉基础之上的。在孟子与后世儒家心学那里,人与礼处在一个单行道上,只有由仁而礼才是可靠的,只有在内在自觉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外在规范才是有保障的,所以应强调心性的扩充。但事实证明,仅仅以心性作为基础,忽视礼的规范作用,反而是最不可靠的。而孔子的仁与礼更像一条双向道,在人与人之间、礼与仁之间存在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两者是相互建构、互为基础的。说荀子更接近孔子,是因为荀子不仅不排斥欲望,而且提出要养欲养情,称情而立文。
在后世儒家中,宋明理学最能体现这种分歧。朱子一派偏重道问学,象山一派偏重尊德性;朱子一派言性即理,象山一派言心即理。朱子认为心乃理与气相合而生的具体事物,与抽象之理完全不在同一世界之内,心中之理即所谓性,心中虽有礼而心非礼,其所见之实在有两个世界,一不在时空内,一在时空内;而象山所见之实在则只有一世界,即在时空内者,而此世界即与心为一体,所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朱子以为“天下无无性之物”,所以一物之成,皆禀其理,所禀之理即其性也;而象山则认为“四端者,即此心也”,“在天为性,在人为心”。朱子之理虽与荀子之礼不是同一个东西,但他试图把理客观化、概念化、体系化,在作用上与荀子之礼有相通之处,即以礼来建构心性。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0,124.
[2] 史次耘.孟子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3] 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
[4] 赖炎元.春秋繁露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