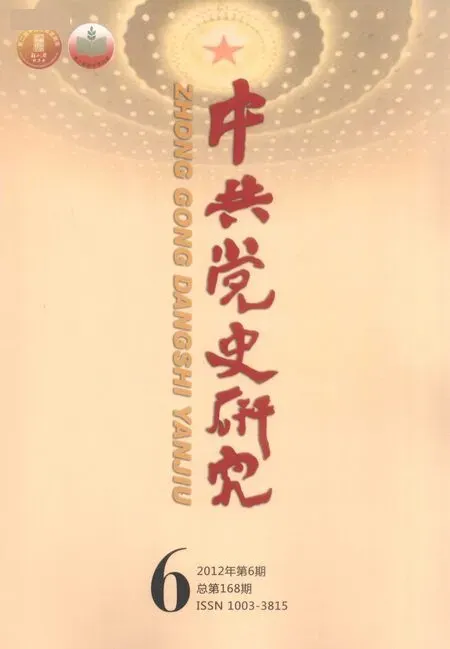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方法
王香平
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方法
王香平
统观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所送文电的批示,从批示性质看,基本上都属肯定性批示,且使用频率最高的三个词是“同意”、“正确”和“很好”;从批示要求看,主要分三个层面:提供工作参考、推广典型经验和寻求决策依据。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透过毛泽东的批示,鲜明地体现了邓小平勤于动笔、善于用笔、重视“用笔杆子”总结和汇报工作、思考经验教训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同时也彰显出他精明强干、善于探索、具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气魄与胆略,反映了邓小平高瞻远瞩,善于抓大事、谋大局的战略眼光和领导风范。
毛泽东;邓小平;批示;主政西南;领导方法
从1949年12月率部进驻重庆至1952年7月调离,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主政西南是他辉煌人生的不朽篇章,也是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起点。正是基于邓小平这一时期所展示的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和卓越不凡的政治智慧,才有了毛泽东那一句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①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页。“一把好手”,“好”在哪里?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赞赏,毛泽东此语绝非虚言。本文拟通过梳理和归纳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各类文电的批示,力求展示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哪些方面的成绩、经验、思想和方法得到毛泽东怎样的首肯和认可,由此探讨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所呈现的特点和风格,这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无启示。
一、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批示的基本特点
所谓毛泽东的批示,主要指针对邓小平以西南局或个人名义向毛泽东或党中央报送的电报、报告、计划和决定等,毛泽东以中央或个人名义起草或审改的各类批复,包括指示、电报、书信等,不包括其他人代中央起草的批示,也不包括毛泽东就某件事直接给邓小平或西南局发出的电报、指示等。根据目前公开的文献,比照《邓小平年谱 (1904—1974)》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相关内容,初步统计,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毛泽东对邓小平所送文电作出的批示共计30份。本文拟以这30份批示作为分析的基础。
1.关于批示的主题。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文电的批示,从涉及的主题或问题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综合性工作报告作出的批示,如《关于西南局综合报告的复电和批语》(1950年11月15日)、《转发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的批语》(1951年5月16日)等;另一类是针对某一问题或事情作出的专题性批示,其中既包括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恢复、社会改造、党的建设、统战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等宏观性的重大问题,也涉及一些微观的具体事情或问题,如《转发西南局关于组织土改工作团下乡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批语》(1951年10月17日)等。总体上看,毛泽东对邓小平西南时期的文电批示所涵盖的工作领域是广泛而多面的,涉及的问题呈现宏观微观兼具的多层次特征。
2.关于批示的性质。所谓批示的性质,主要是针对下级机关报送的文电中所提出的工作计划、建议、意见、方法或总结的经验等,上级机关对其作出的明确 (肯定或否定)答复或具体指示。遍览毛泽东对邓小平文电的批示,基本上都属肯定性批示,且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词语是“同意”、“正确”和“很好”。在毛泽东的30份批示中,有8份用了“同意”,9份用了“正确”,8份用了“很好” (或“均好”、“好的”),除去3份重复用词,共有22份也就是2/3以上篇幅是用这3个词语的任何一个或两个来表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邓小平所送文电的态度。另有一些批示虽未采用这3个词,但同属肯定性批示,如1951年5月4日,毛泽东审改邓小平报送的关于大学对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组织人员处理办法的指示稿时批示:“中央认为,此问题甚为重要”①《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79页。;1951年4月30日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批示西南局“指示是合于上述原则精神的”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68页。;等等。除此之外的其他批示则直接批转各地参考,无疑是对所报文电在更高层次上的肯定,也是下文要述及的内容。
3.关于批示的要求。批示是上级领导用于批转下级工作报告时所使用的一种应用性文体,它不只是对所送文电作出答复或表态,更重要的是进行“转发”或“批转”,这是批示的核心功能,也是批示的主要意图和根本要求。据此,可以将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的批示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提供工作参考。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的批示,除个别批示只是针对西南局单方面的工作予以答复或进行指示、指导外,大部分都进行了“转发”,首要目的是为各地工作提供参考。如1950年11月15日,毛泽东把西南局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参照办理,并可转发给所属省市区党委作参考”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663页。。1952年3月20日,针对邓小平关于“三反”、“五反”、土改、经济等问题的报告,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参酌办理,并可在党刊上登载”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46页。。
第二,推广典型经验。所谓推广典型经验,是指把邓小平所送文电中总结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经验等作为标杆和典范,要求各地直接仿照、研究或采纳。如1950年5月13日,针对西南局关于整风、春耕情况的报告中所提整风步骤,要求各地“亦照此项步骤部署进行,即先整县委书记以上,再整广大干部”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45页。;1951年12月24日,针对西南局关于学校教师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批示要求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也“仿照西南的办法”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627页。,有准备地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等等。
第三,寻求决策依据。毛泽东批转各类文电,一方面为各地提供工作参考和经验方法,同时也考虑为中央的大政方针寻求来自基层的新鲜经验和做法,以求为中央决策提供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1951年11月2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1951年9月和10月的工作情况。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在电报中称,西南地区将把反贪污、反浪费当做1952年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11月30日在批转该报告时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④《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中),第1018页。12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斗争由此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毛泽东11月30日对邓小平电报的批示是他推动和领导“三反”运动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即把“三反”运动作为一场大的斗争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思路是在这一批示中予以明确的。由此可见,邓小平报送的电报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终作出开展“三反”运动决策的重要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之一。
统观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文电批示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且在多数情况下赞赏有加。为什么邓小平报送的文电能得到如此多的肯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为什么西南局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能够走在全国前面,成为各地学习效仿的典范?归根结底,这与邓小平卓尔不群的领导艺术密不可分。
二、从毛泽东的批示看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与工作方法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土改运动中,毛泽东就多次采用邓小平提供的材料和建议,他曾幽默地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就像吃冰糖葫芦。”⑤何立波、宋凤英:《共和国成立前的邓小平与毛泽东》,《党史博览》2004年第8期。可见,邓小平的报告的确有滋有味,耐人咀嚼。透过毛泽东的批示,又能折射出邓小平怎样的领导方法与为政风范呢?
(一)勤于动笔——毛泽东批示的频度折射出邓小平汇报的密度
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报送文电作出的批示为30份,但并不等于邓小平报送给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的文电只有30份。根据《邓小平年谱 (1904—1974)》公布材料的初步统计,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报送给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的文电共计99份 (其中1950年39份,1951年39份,1952年21份),按照邓小平在西南的工作时间32个月计算,平均每个月至少报送3份⑥《邓小平年谱 (1904—1974)》第一次公开出版,不可能穷尽所有资料,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公布全部资料,因此,这里用“至少”应是一种保守估计。,其中明确由邓小平起草的文电达75份之多。换句话说,99份中有2/3以上的文电都是由邓小平亲自起草、修改或审订的。
就邓小平报告的主题来看,不仅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领导西南广大军民开展进行的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大的社会主题,还包括日常工作中关涉行政效率和改进工作作风等一些内容,如1950年8月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致电刘少奇、周恩来,报告关于处理转发文件问题的意见和做法。中共中央8月17日复电:“关于上面文件,凡与本身工作无关的一律不要转发下去,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并已将你们来电转发各中央局、分局、中央各部委,要他们转告各级党委一律照此办理。”①《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中),第935页。
就邓小平报告的时间来说,除了事关重大、复杂或敏感性问题在第一时间向中央汇报外,还严格履行每两个月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的工作惯例,也就是说,邓小平把不定期汇报和定期汇报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前者如1951年4月27日,邓小平在一天之内连续起草三封报送中央的电报:一是西南局批转中共川西区委关于镇反问题的报告,二是西南局批转川北区阆中县镇反工作的报告,三是西南局批转中共川北区委关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情况的简报。②参见《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中),第981—982页。关于后者,以1951年为例,5月9日起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西南局3月、4月两个月的综合报告;6月27日致电报告5月、6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9月10日起草关于7月、8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报告;11月25日致电报告9月、10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1952年1月4日致电报告1951年11月、12月两个月的工作情况。③参见《邓小平年谱 (1904—1974)》 (中),第983、995、1007、1017、1028页。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共中央于1948年1月发出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规定的。邓小平不仅在大别山区的紧张战斗环境中严格执行这一指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仍然一以贯之,实属难能可贵。
不论报告涉及主题的宽泛,还是报送文电时间的密集,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邓小平十分勤于动笔,极其重视用“笔杆子”思考工作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这不仅践行了他主政西南时倡导的“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的思想方法,也充分体现了他高度重视向中央汇报工作,重视让中央及时了解并掌握自己主政地区的各方面情况,基本初衷自然是希望中央能给予更多的指导或更好的建议,以使自己的工作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和方向前进。西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取得各方面的发展成就,得到毛泽东的多次肯定和赞赏,主要是当地干部群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工作的结果,当然,邓小平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善于用笔——毛泽东批示的性质反映出邓小平汇报的质量
为什么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文电批示基本上都表示肯定甚至赞赏有加?是邓小平汇报工作“报喜不报忧”?还是西南地区情况简单、工作易开展?或者说邓小平遭遇复杂、棘手问题的机会较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问题并不在邓小平汇报的是成绩还是问题,喜讯还是困难,关键在于不管成绩还是问题,邓小平都有不同寻常的汇报方式和请示办法。换句话说,邓小平十分善于撰写工作报告,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就像吃冰糖葫芦”的缘由之一。试举几例。
1.关于工作进展的汇报。1950年4月27日,邓小平就部队缩编问题和刘伯承、贺龙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已遵照中央意图确定了将所有干部缩减到八十万的初步实施方案,并决心贯彻执行。估计是不会出大乱子的。现已决定于四月底开全区的军事会议 (各军区负责者都到)讨论上述问题,详情后报。”①《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中),第907页。关于部队缩编,应该说关键是结果,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向中央汇报,一般可能会认为意义不大或没什么必要。而邓小平把西南局的阶段性工作进展向中央汇报,寥寥几语,便把已经做的(“确定初步实施方案”)和将要做的(“召开全区军事会议”),以及西南局领导的主观思想认识(“决心贯彻执行”)和对客观情势的基本判断(“估计不会出大乱子”)交代得一清二楚,充分显示了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和意图的坚定性、及时性以及西南工作部署的有序性。这样的汇报无疑是必要的,也是中央需要并希望了解的。于是,毛泽东在第二天(4月28日)即把该电批转各地参考。一份关于工作阶段性进展的报告能得到毛泽东如此重视,实属鲜见,也充分反映出邓小平汇报工作的不同寻常。
2.关于工作成绩的汇报。1951年1月6日,邓小平和贺龙等致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1950年剿匪情况。28日,毛泽东复电:“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缴枪四十余万枝,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②《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中),第962页。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表彰,“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毛泽东的兴奋与痛快可谓跃然纸上,但他并非只是看重“八十五万”的剿匪战果,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是“路线正确,方法适当”。由此不难推断,邓小平的报告不单是汇报战绩,还总结了取得成绩的主要经验。事实上,邓小平在报告中只用了一两句话来讲成绩,大部分篇幅都用来汇报开展剿匪斗争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采取的措施方法等。如关于措施方法,邓小平总结了五条:组织了一元化的剿匪斗争;集中兵力进剿;组织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之间密切协同;开展捕捉匪首运动与镇压匪首工作;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等。③参见《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中),第962页。可见,关于工作成绩的汇报,邓小平不仅注重结果,更注重过程;不单汇报成绩,更注重分析原因并总结经验方法。成绩是客观事实和具体现象,经验则是由具体到抽象的理性分析和概括;成绩只是归纳过去,经验则可以指导未来。有了好的经验和方法,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做好自己的工作,还可推广开来供他人借鉴学习,其作用和实际效果往往是难以估量的。作为统领全局的中央决策核心,毛泽东无疑会认为阅看这样的报告有味道、耐咀嚼,由此在嘉奖西南局的同时也把此报告批转给了华东、中南、西北各军区以及福建、广东和广西军区供他们参考。
3.关于反映问题的汇报。1952年2月22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及陈云、薄一波等,反映并请示如何处理“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的报告全文1000多言,三个段落。报告第一句话直入主题,“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无论内部和外部,都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接着讲外部问题“工商业停滞现象”并分析“停滞的原因”,第二段提出西南决定采取的五条“紧急措施”,第三段讲内部问题即一些工作“无人接替”、一些部门缺少“骨干”以及西南想到的三个办法。④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490—492页。如果单看报告主题“反映并请示如何处理……问题”,一般会认为报告内容大致是列举一系列问题或困难,目的主要是提请中央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邓小平的报告则完全不然。他不仅提出问题和遭遇的困难,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对症下药地先行提出应对局势解决困难的具体办法和举措。换句话说,邓小平不是在向中央反映问题,而是请示西南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妥当,措施是否合适。邓小平“问题——原因——办法”的严密思维和周到考虑,赢得了中共中央“完全同意”的首肯。“三反”和“五反”是全国性运动,邓小平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个别现象。因此,毛泽东在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专门加写了一句话:“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①《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中),第1041页。邓小平善于抓住带普遍性的问题并主动解决的领导思想和方法由此成为各地学习、效仿的榜样。根据西南局的建议和各地反映的情况,中央及时调整了“五反”运动的工作部署,并在运动后期进行了第二次工商业调整。
4.关于工作计划的汇报。1951年11月24日,毛泽东把西南局1952年工作要点批转各中央局:“西南局委员会于1951年11月9日通过的工作要点很好,请你们加以研究,作为自己规定1952年工作计划的参考。”②毛泽东批示 (1951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工作要点”实际就是工作计划。一般来说,制订工作计划须因地制宜,各省区各地市社情、民情不同,所处的环境各异,面对的问题千差万别,要完成的任务自然也是千差万别;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把邓小平的工作计划批转各地“研究”和“参考”。看来,毛泽东欣赏的不只是邓小平制定的计划本身,更多地是其制订计划的方法和思路。分析邓小平的报告③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47—451页。,不难看出其几个突出特点:第一,大局观念。报告第一段话就提出了制订计划的两个立足点,一个是抗美援朝,一个是1953年全国计划经济建设,前者指向当前,后者指向未来,两者都是全国的大局、中央的大盘。制订地方工作计划,从中央的大政方针着眼,可见邓小平看问题的高度和定计划时的大局观、全局观。第二,计划周密,条分缕析。报告第二段话用一句话“因此,明年须完成下列工作任务”作为过渡,开启报告的主体内容 (共九项):增产节约、土改及农村工作、城市工作、财政经济、教育、镇反、整党整风、干部调配、政治学习。九项内容,全面周到,不穿靴戴帽,不拖泥带水,要言不繁,条分缕析,给人求真务实、果敢干练、真抓实干之感。第三,有办法、有步骤、有时限。尽管只是一个工作要点,且内容简短,但邓小平还是在多项工作中提出了完成任务要采取的步骤、方法或预计时间,如关于农村完成土改后的民主建政问题,报告详述了八条关于建立“乡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举措和考虑事项;关于政治学习,明确提出“与党外人士一道组织《毛泽东选集》学习会或研究会”的具体方法;关于时限,如“省区以上党委一律于明年五月将领导重点转向城市”,镇反中的清理中层“在明年六月以前完成”;等等。有了方法、步骤和时间,就等于在可能与现实、未知与已知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人感到计划本身的可行、可靠与可信。因此,这样的工作计划自然会让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能赢得毛泽东“很好”的赞赏并成为各地“参考”的范本确实是有其充分理由的。
(三)勇于开拓——毛泽东批示的要求彰显邓小平过硬的领导素质和为政风范
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文电的批示,90%以上都属“批转”性质,或为工作参考,或为典型经验,或为决策依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邓小平领导下的西南局工作,开展得不单是到位不到位、合格不合格的问题,而是在多方面已然成为全国的榜样,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引领和表率作用。为什么西南局工作能够达到这种境地,归根结底,这同邓小平一贯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密切相联。换句话说,西南局能取得不菲成就,首先取决于邓小平卓尔不群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1.精明强干,善于探索,具有极强的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办事能力就曾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创造和总结的经验,取得的辉煌战绩和开拓工作的新局面,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欣赏、赞颂、表扬和推广。他这种独立自主地应对复杂局面、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在主政西南时期,更趋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如1950年解决西藏问题。当时西藏情况复杂,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要完成进军西藏任务,却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邓小平指示部队成立政策研究室,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等重要原则,亲自起草进军守则。在西南局向中央报告解决西藏问题4条方针的基础上,亲自主持起草了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10项政策。这份历史性文件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后来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就是以邓小平的10条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再比如,刘邓大军进入西南后,先是消灭了蒋介石的正规部队,解放了重庆、成都重镇,尔后指挥部队追剿土匪顽敌。在剿匪工作中,邓小平特别注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原来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促成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团结,顺利完成了土改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加强了各级政权建设,在西南地区创造了稳定的新局面。毛泽东高度称赞西南地区的剿匪战绩,并把邓小平的剿匪工作报告批转各地学习,还专门致信时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阅看。30多年后,邓小平在同原二野老同志座谈时,仍对西南剿匪感到欣慰:“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①张继禄、周锐京主编:《邓小平与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作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邓小平坚持不等、不靠、不要的基本理念,时刻立足于独立自主探索应对复杂局面、解决棘手问题的思路、办法和途径。可以说,正是这种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锻炼、考验了邓小平,同时也发展、成就了邓小平。
2.敢作敢为,勇于开拓,具有敢为人先的气魄和胆略。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不少文电被毛泽东批转全党,并要求各地或研究邓小平的报告、采纳邓小平的意见,或仿照西南办法、遵照西南步骤,或汲取西南的经验教训等,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在诸多工作方面已然成为“领头羊”。显然,这主要取决于邓小平敢想敢为、勇于开拓与创造的气魄和胆识。如1951年3月13日,邓小平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提出西南军政机关“留用人员非常复杂”、“新招收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也很复杂”这一问题。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不仅较早发现并认识到“军政机关不纯”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同时提出了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法与手段,即从思想观念上“引起高度的警惕”,从行动上“采取妥善而稳重的步骤分清好坏”②《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中),第970—971页。。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3月20日,毛泽东复电:“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已转发全党仿行”,同时批转“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省军区,兵团及军,并告志愿军党委,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加以研究”。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78—179页。一句“完全正确”,一个“全党仿行”,充分反映出邓小平报告的分量和质量,彰显了邓小平所提问题的典型性与普遍性,体现了邓小平高明的政治识见和预断。
再如,1950年12月21日,西南局召开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总结报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虽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大政方针,但具体的城市工作究竟如何开展,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西南局在全国率先召开城市工作专题会议,不仅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工作会议的先河,且邓小平的《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也成为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专门讲城市工作方针政策的不可多得之作。报告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西南地区城市工作实际,系统而又独创性地阐明了党对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领导和管理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措施办法。这篇报告在一定意义上可称得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关于城市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之作。邓小平这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气魄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尽管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处于土改和镇反工作的高潮,毛泽东还是要求各中央局仿照西南做法,再忙也要腾出时间“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9页。同时,毛泽东还致信张澜:“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件,送上请察阅 (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8页。张澜重疾在身,还希望秘书念给他听。如此迫切期待别人看到邓小平的工作成绩,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工作的极端看重,同时也是对邓小平敢作敢为、勇于创造的领导气魄的由衷赞赏。有如此杰出的开拓型领导干部,毛泽东的自豪之情可想而知。
3.高瞻远瞩,虑事周全,具有抓大事、谋大局的战略眼光和领导风范。邓小平的文电,不论是作为工作参考或典型经验被毛泽东批转各地,还是直接作为中央作出重大决策的实践基础和客观依据,都从不同侧面表明了西南局的工作经验以及邓小平的领导思路对全国工作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归根结底,这取决于邓小平善于抓大事、谋大局、看大势的大局观、全局观,这是他战略眼光和领导风范的根本体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于中央的方针、政策或指示、意见等,能够在思想上积极拥护的同时,主动及时、坚定有力地贯彻执行,不管实践中遭遇多大的困难和阻力,都会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去解决问题和落实政策。如1951年5月9日,邓小平就西南地区的土改、退押、镇反和抗美援朝等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不仅批示“报告很好”,还在报告中批注了九条意见,如第一条,在报告谈到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和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胜利处批注:“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第二条,在报告谈到进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须坚持复查、减退、惩治不法地主,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的领导成分的方针处批注:“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第八条,报告谈到通过发动群众实现扩兵如此容易出人意料之外,引发毛泽东对另外两件“出人意料”之事的思考,并写下200多言的批注。③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70—373页。应该说,土改、退押、镇反和抗美援朝是全国性运动,但西南局的做法能得到毛泽东的如此肯定与高度赞赏,要求各中央局负责人以及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负责人都要“研究”邓小平的报告,充分说明邓小平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策和精神的坚定、到位和彻底。
第二,立足全局,看主要矛盾,抓关键环节,以点带面地推动全局工作的展开。1951年12月13日,西南局致电中央,报告开展“三反”运动的部署和安排。根据以往反贪污的教训,报告提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借此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为此西南局研究规定了六项具体办法来避免重蹈覆辙并推动“三反”运动的开展。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是邓小平进军西南伊始就提出的克服困难的三大法宝之一。西南局的认识深得中共中央赏识,毛泽东不仅批示“完全正确”,还把报告批转各地“参考”,并要求“在党内刊物上予以登载,使科长以上的干部都有机会阅读”。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86页。这样,西南局关于“三反”运动的部署和安排就成为全国各地开展“三反”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作为西南局领导人,邓小平这种抓住关键环节,把握主要矛盾,由点到面推动全局工作展开的根本作用得到了有力展现。
第三,想大局、顾大局、为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以大局为重。纵观邓小平的一生,无论在中央工作,还是在地方或军队工作,始终善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和处理问题,一切着眼于战略全局,一切服从战略全局。周恩来曾评价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及赴西南做地方工作的区、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一开始就从战略高度讲了接管西南的艰巨任务:“西南人口七千万,是全国战略的大后方,建设条件也很好,是将来的大工业区之一”。两句话,一个空间,一个时间,一个指向现实,一个指向未来,从纵横两方面说明了建设西南的极端重要,由此提出实现这个伟大而艰巨任务的三个法宝:搞好内部团结、依靠西南人民、搞好统一战线。①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9页。邓小平举重若轻,实质就是把具体工作放手让别人做,以主要精力潜心抓大事、谋全局、把方向。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反、整党、统战到解放西藏、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西南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曾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肯定,充分说明邓小平领导和治理西南作出的杰出贡献。1951年9月3日,毛泽东同梁漱溟共进晚餐,谈到邓小平治理下的西南地区,梁漱溟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大声赞同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②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第17—18页。
一位曾在西南局工作过的新华社记者说:小平同志“高超的领导艺术,使人不禁想起《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他纯熟地掌握了领导的规律,真可谓‘游刃有余’矣”③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8—39页。。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这样描述,1949年,邓小平“负责中国西南部以重庆为中心方圆1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为了执行毛的命令,他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才干。毛为他的工作态度再次受到感动,把邓召回北京”④〔美〕索尔兹伯里著,康军编译:《索尔兹伯里笔下的邓小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主政大西南的确是邓小平展现卓越的领导才能与领导艺术的重要时期,并由此成为邓小平革命生涯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关键阶段,也成为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起点。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北京 100017)
(责任编辑 吴志军)
Deng Xiaoping’s Methods of Leadership When He Was the Chief Administrator of Southwestern China As Seen from Comments and Instructions from Mao Zedong
Wang Xiangping
A general survey of Mao Zedong’s comments and instructions on the documents and telegrams submitted by Deng Xiaoping when he was the chief administrator of Southwestern China shows that Mao Zedong’s comments and instructions were mostly commendatory with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words being“agree,”“right”and“very good.”In Mao Zedong’s view,the documents and telegrams were commendable and might be used as reference materials in the work;as exemplary experience to be spread and as the basis for decision making.Deng Xiaoping’s work in this period was fully affirmed and highly approved by Mao Zedong an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Mao Zedong’s comments and instructions were a clear indication of Deng Xiaoping’s methods of work and leadership:he was diligent and good at writing,attached importance to summarizing and reporting his work and thinking about experience and lessons with the pen.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indicated that he was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brave to blaze a new trail and capable of independently solving problems,and that he always looked far ahead from a high plane,focused his attention on the key problems and had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mind.In short,he was a leader with an overall strategic vision.
D232;K27
A
1003-3815(2012)-06-007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