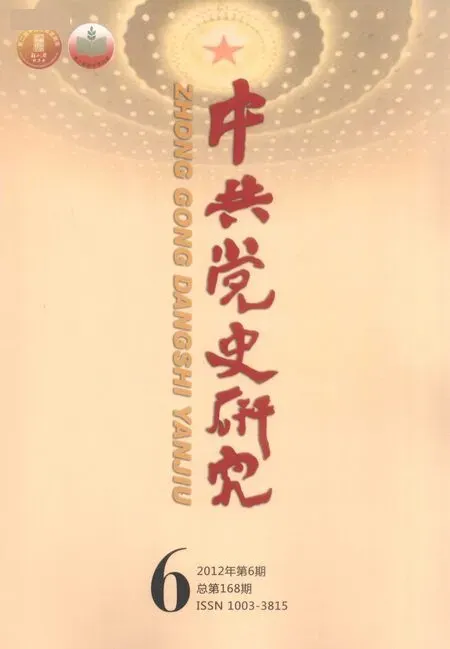中共将妇女解放纳入民族解放的历史必然性及理论支撑
韩贺南
中共将妇女解放纳入民族解放的历史必然性及理论支撑
韩贺南
中共四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首次提出将妇女运动作为民族解放运动要素的理论原则。它顺应了20世纪初劳动解放、民族解放、妇女解放的国际潮流,产生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根植于“我在家国中”的中国文化传统,回应了“一般妇女运动”对待革命的立场与态度等重大问题。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了社会系统理论、人道主义理论等相关理论观点,以国权、人权、民权与女权的相互关系及“女国民”身份建构的相关理论为支撑,呈现出鲜明的历史必然性,而并非仅仅是“收编”妇女运动的策略或对妇女进行革命动员的口号。
妇女解放;民族解放;女国民
妇女与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是妇女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道路。将妇女解放纳入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重大特色。正如胡锦涛所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广大妇女始终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开创了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走出了一条深深植根于我国历史和现实、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鲜明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和发展道路”①胡锦涛:《在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0年3月8日。。寻本溯源,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关系理论提出的历史条件与理论基础,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建设和妇女运动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有不少成果。许多研究着重于中国妇女运动所体现的国家、民族与妇女三者之间的关系,妇女运动伴随民族解放运动进行的利与弊,关注在妇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相伴随的过程中,妇女到底有没有主体性等问题。然而,鲜有对这一理论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基本观点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因而有使这一理论原则抽象化、空洞化的倾向。
本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 (案)、共产党人对妇女与民族解放关系的有关论述,国民运动时期人们对国权、人权、民权与女权的看法以及相关的理论观点进行研究,探寻中国共产党究竟怎样看待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关系,为何将妇女解放纳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进程,这一理论原则之下有哪些理论支撑,从而构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等问题。
一、“领导一般妇女运动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要素”提出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开始了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关于中国妇女解放道路问题,中共二大妇女运动决议主要阐述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①参见韩贺南:《阶级与性别的“联盟”——中共首部妇女运动决议及相关文献研究》,《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②《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页。。中共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案着重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妇女运动进行阶级分析③参见韩贺南:《中国妇女运动的“阶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6期。,将妇女运动分为“劳动妇女运动”和“一般的妇女运动”(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同时基于中共二大以来,劳动妇女运动在罢工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先锋”与“前卫”作用,肯定了劳动妇女“在阶级斗争中之重要与意义”,明确指出“一般妇女运动”“亦甚重要”④《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1—1927)》,第68页。。中共四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了妇女运动以“工农妇女为骨干”的原则,进一步分析了“一般的妇女解放运动”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为了引导各阶级妇女运动到革命的轨道上来,首次提出了妇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问题,指出:“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妇女,包含在整个的被压迫民族之中,时受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的宰割。我们的责任是领导一般妇女运动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要素。”⑤参见《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1—1927)》,第279页。从中共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提出妇女解放“伴着劳动解放进行”,到中共四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指出妇女解放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要素,开启了中国特色妇女解放道路的历史起点,即将妇女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参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寻求自身的解放与发展。
中共四大提出“领导一般妇女运动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要素”,不仅是中共自成立以来对妇女解放运动不懈探索的逻辑发展结果,也是顺应国际社会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与妇女解放三大潮流的聚合,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实现关于争取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基本精神的体现。
(一)国际社会“三大解放潮流”洪波涌起
将妇女运动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要素,是共产党人审慎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根据中共四大的基本精神,针对当时妇女运动的问题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基本主张。共产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对劳工的压迫,性别压迫,都源于资本主义的罪恶之根。民族独立、阶级解放、妇女解放三股力量相遇联袂,已经汇成了世界革命的洪流。
中共四大时,担任中共“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的向警予撰写数篇文章对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她认为妇女运动不能脱离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而独立存在。她在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对全球阶级、民族与性别压迫的状况作出判断。她认为,世界上大约有4/5的人口处在被压迫地位,包括“被列强少数的资本阶级奴属或宰割的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处奴隶地位的两性人口”。她指出:历史的进程“业已踏上人类总解放的时候”,“劳动解放,民族解放,妇女解放的呼声,布满全球”。①参见警予:《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妇女杂志》第10卷第1号,1924年1月1日。在向警予作此论述一年以前,李大钊曾谈到,被压迫阶级寻求解放是20世纪的国际潮流。他指出:“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②守常:《现代的女权运动》,《妇女评论》第25期,1922年1月18日。这是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对当时国际形势判断的共识,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解放纳入民族解放进程的国际背景。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国权至重
许多共产党人在把握国际社会民族解放、阶级解放总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社会状况,认为处于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完整的国权已不复存在,民众亦无民权和人权,妄谈女权。因而,主张中国妇女运动不能效仿西方国家的女权运动,在不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争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必须首先争回国权与民权,方能得到女权。
关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向警予尖锐地指出:中国“就是列强一个殖民地”,中国政治经济问题“无处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主奴结托恣睢横行的把戏”。“政治方面的独立性,久已不复存在”;“经济上只是列强销纳商品的市场,和劳力原料的制造所……中国经济绝少独立发展的可能”。③参见警予:《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妇女杂志》第10卷第1号,1924年1月1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是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解放纳入民族解放进程的现实社会基础。
关于中国民众与妇女的生存处境,时人认为,就整体社会局面而言,中国是个军阀混战的“武人世界”、“兵匪世界”。生活在如此环境下的中国国民,生存尚且难以维系,侈谈女权。向警予曾做如下阐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众“未曾尝过人权民权的滋味”。“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人民偶然发出一点反抗的声音,便冲动了外人和军阀的肝火,不是赶你滚蛋,便要派你坐牢”,④警予:《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妇女杂志》第10卷第1号,1924年1月1日。“简直可怜到一碗安乐茶饭都吃不成,一条残命都保不住”。妇女的处境更加悲惨。“至苦妇女,在普遍的被掳掠被杀伐之外,还要加上一层惨毒的奸淫,那就更其可怜之极了!”⑤警予:《国民会议与妇女》,《妇女周报》第64期,1924年12月14日。王会悟曾经谈到工厂女工的境遇,说道:“尤其不堪的,中国的工厂,多系外人创办,洋监工、洋奴、洋狗所施于女工的奸淫掠夺种种非人待遇,有非言语所能形容的”⑥会悟:《中国妇女运动的新趋向》,《妇女声》第3期,1922年1月10日。。中国国民尤其是妇女的现实处境使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解放纳入民族解放之中成为必然选择。
(三)引导妇女运动在国民运动麾下的“大联合”
中共四大妇女运动决议案对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关系的关注,反映了当时国民运动与妇女运动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共四大是在国民会议运动的背景下召开的。“1924年冬至1925年春,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强烈呼吁由国民决定国家大事,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铲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主共和政体”。⑦《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152—153页。如何促醒妇女投身国民革命运动,又借国民运动良机推动妇女运动,是党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①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157页。。妇女运动决议案据此提出了妇女运动的主体力量与争取对象等重要问题,即如前所言的以工农妇女为中坚,将“一般妇女运动”作为重要力量,而如何实现这两股力量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的联合,是个“困心衡虑” (恽代英语)的问题。当时一些共产党人发现“一般妇女运动”存在忽视“民族运动与改造社会运动”的倾向。恽代英指出:“五四”以来,妇女运动有“此等弊端”,即以“个人主义的精神,以要求他们自身的解放”,“把其他一切社会问题都抛之脑后”,而“我们所希望的是全妇女的解放,是妇女的真正解放”,“一定不是要造就几个女政客,女学者,或者甚至于造就几个政客学者的洋太太,他们必须要努力赞成改造社会的运动”。②参见代英:《妇女运动》,《中国青年》第3集第69期,1925年3月7日。中共四大妇女运动决议案直接回应了“一般妇女运动”的弊端,着重分析了其政治立场和态度,认为贵族妇女运动仅注意于上层妇女运动;教会妇女运动具有买办阶级化的特征;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有倾向革命之可能。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决定“促醒其觉悟”,“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指导”。③《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1—1927)》,第280页。中共所依据的理论原则即是妇女解放是民族解放的要素。
二、社会系统与人道主义视域下的妇女解放之于民族解放
中共四大妇女运动决议案关于“领导一般妇女运动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要素”的思想,建立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首先,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主要体现于前文所述许多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阶级观点、列宁的国家与民族理论等观察国内外形势,分析中国妇女运动的现状与未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妇女解放纳入民族解放之中的理论原则。其次,它借鉴了社会系统理论、进化论、人道主义理论等其他科学的理论观点。
(一)社会是“男女一体”的大系统,没有妇女解放,民族解放运动便“半身不遂”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时人认识妇女解放及其与民族解放关系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李达从“社会系统”的角度阐述了妇女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系统,即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而他所说的个人并非今人所理解的男人和女人每个人,而是“男女一体”的“个人”,换言之,男女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体,成为“个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他主要从人类繁衍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即只有男女两性的结合才能产生组成社会的人。他谈到:“男性与女性结合,成为个人。个人的分裂必成为男女两性,所以社会是由男女两性结合生出新个人。新陈代谢,然后有进化,有创造,有发展。所以社会称为个人的有机体的集合体,即可称为男女两性结合的大系统”。李达旨在说明社会既然由男女两性组成,就不该以男性为中心,而应该以男女两性为中心。他说:“凡是社会上的道德、风俗、习惯、法律、政治、经济,必以男女两性为中心,方可算得真道德、真风俗、真习惯、真法律、真政治、真经济,否则是假的,是半身不遂的”。④参见李鹤鸣:《女子解放论》,《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李大钊在李达此论之前论及欧美女权运动时曾经谈到:“我很盼望我们中国不要长有这‘半身不遂’的社会。我很盼望不要因为世界上有我们中国,就让这新世纪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⑤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上述从“健全社会”的角度来谈女子解放问题,是一种基于中国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而提出的富国强种的诉求。李达也以欧美社会进化为鉴,认为欧美社会之所以强大,得赖于女权运动,女子解放。他指出:“百余年前,欧美的女子,早就有了觉悟,开始热心女权运动——现在虽不敢说,欧美的女子如何比男子高超,但是一般人,都了解欧美新社会的组织,必定以男女两性为本位,这社会真正的价值,立刻就会实现了”①参见李鹤鸣:《女子解放论》,《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关于欧美社会发展得益于伸张人权,陈独秀亦有论述,他认为科学与人权是社会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如“舟车之两轮”。他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②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向警予综合运用了上述观点谈到:“男女两造为社会进化的两车轮”,如果不“增高女子地位”,“社会进化的两车轮将永远不能得着均齐协调的发展。社会将永远陷于半身不遂,颠跛 (簸)迟滞状况中”。③参见警予:《中等以上女学生的读书问题》,《妇女杂志》第10卷第3号,1924年3月1日。时至今日,仍可见人们运用这些观点阐述妇女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总之,时人认为男女为社会进化的“两轮”。女子受压迫,则社会“半身不遂”,欲求社会“均齐协调”发展,必求妇女解放。这些观点成为倡导妇女解放,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没有民族独立,妄谈妇女解放
人道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亦为当时妇女解放的理论依据之一。周作人将人道主义的核心问题界定为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他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比作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各树也茂盛;但要森林盛,首先要各树茂盛。即要使社会强盛,一是个人要有人格,自立于社会;二是要爱人,尊重别人的人格。爱人即为爱己,因为己在人类中。周作人曾经谈到:“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我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④转引自舒芜:《女性的发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6页。李达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倡导女子解放。他认为:“世界惨无人道的事,比男子压迫女子再厉害的恐怕没有了!”⑤李鹤鸣:《女子解放论》,《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叶绍钧将女子解放解释为人格独立,并将其核心含义解释为“一种理性精神”,即自立于社会的能力。叶绍钧说道:“‘人格是个人在大群里头应具的一种精神’。换语来说,就是‘做大群里独立健全的分子的一种精神’”⑥叶绍钧:《女子人格问题》,《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以上可见,人道主义的核心理念即为人要有人格,也要尊重别人的人格;社会强盛则个人强大,社会贫瘠则个人孱弱。这些理念是妇女自我解放和男人反躬自省,倡导妇女解放的理论依据,也是认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一。即遵照人道主义精神,女子应该自立于社会,参与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男人要尊重女性的人格,而不能压迫女性,否则便是“不人道”的。每一个体都强大了,社会也就强盛了;社会强盛了每一个体才会强大。即在当时中国家国危亡的社会背景下,没有强大的中国人 (个人)。所以,每一个人只有投身民族解放运动才能使自己强大。同理,妇女解放运动不可能独立于民族解放运动而取得成功。
以上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要素的理论原则,借鉴了社会系统理论、人道主义理论观点等。这一看起来仅仅是革命动员的口号,其实具有深厚的理论背景。
三、“四权”关系序列视域下的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
从国民革命时期的有关文本来看,对国权、人权、民权与女权“四权”之间复杂关系的辨析,为人们认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关系提供了思路,“四权”关系序列成为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共盟”的理论依据和重要内容。
(一)“四权”的由来与含义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国家的独立、自由之权——国权已经不复存在。时人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辩议国权、人权、民权与女权及其相互关系的。
据日本学者须藤瑞代的研究,“中国‘人权’一词在1902年前就已经出现,至少康有为的《大同书》(1902年左右完成)里曾提到‘夫以人权平等之义则不当为男子苦手 (守——引者注)。”①宋少鹏:《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6期。从一些共产党人的文章中可以洞悉他们对人权含义的看法。陈独秀谈到:“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②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这里的人权是与“奴隶”相对应的概念。主要含义是“自主之权”,所谓自主,即不为奴隶也不奴役他人。陈独秀又言:“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③《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1页。。在这里,陈独秀进一步阐述了人权的要义:人人平等地拥有自主、自由的人格。或者说,自主、自由的人才称得上有人格,有人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权即为自主、自由之权。
有研究发现,“中国的‘民权’一词最早应见于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光绪4年5月18日 (1878年)的记录:‘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曲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民权常重于君”④宋少鹏:《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6期。。这里的民权是与君权相对应的概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民权主义”解释为“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144页。。可见民权即为一般平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而论及妇女的民权则多用独立自主之权。
在中国,“女权”一词“最早出现在《清议报》第38号 (1900年3月11日)上刊登的日本人的译作《男女交际论》的序言中 ‘(福泽)先生喜言女权’一句”。有研究者认为,“作为观念传播,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的著作《女权篇》 (1902年)是第一次以《女权》命名的书”。⑥参见宋少鹏:《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6期。至于女权的含义,从当时的一些文本来看,“女权”即为妇女和男子同样应具有的人权。《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请愿书》开篇即言:“自天赋人权之说兴,而男女平等之意昌。欧战以还。新潮彭〔澎〕湃。女权伸张,不待运动。”⑦《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1—1927)》,第63页。可见,时人据“天赋人权之说”倡导男女人权平等。女权即指妇女的人权。时人认为,妇女和男子享有同样的人权既是“天赋人权”的题中之意,又是社会潮流使然。向警予在论及女权运动的意义时,也涉及女权的要义是妇女的人权。她说:“故女权运动的意义在于免除性的压迫,发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争回妇女应有的人权。”⑧警予:《评王璧华的女权运动谈》,《妇女周报》第8期,1923年10月10日。
虽然女权的要旨是妇女的人权,但在不同的语境下,它也泛指基本人权以外的其他权利。诸如,在民主革命时期,尤其在国民运动中,人们常常把女权与民权联系起来。吴虞将女权解释为“国民平等自由之权”⑨吴虞:《女权评议》(1917年6月1日),《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14页。。向警予认为:“女权运动是妇女的人权运动,也是妇女的民权运动。”⑩警予:《中国妇女运动杂评》,《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可见,在这里女权既指人权又指民权。李达曾谈到:“近代‘天赋人权’四字出世以后,世界的男子,先先后后都拿着这四字做根据,热心的运动恢复民权,后来都渐渐的奏了些效果。于是多数的人都说现在是‘民权世界’了。我说:你们说得也对,但是你们说的‘人’字‘民’字都应改为‘男’字,简直的说‘天赋男权’、‘男权世界’,不要撒诳的好。若不然侵夺了他人的‘人权’,还能说拥护‘人权’吗?”⑪⑪ 李鹤鸣:《女子解放论》,《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李达批评“男权世界”对女权的剥夺,认为“天赋人权”理应包括女权——妇女的人权与民权。
(二)“四权”关系序列中的女权
向警予曾用“三角同盟”概括“妇女、弱小民族、劳动阶级”①何鹄志:《向警予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在寻求解放中的结盟。时人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个人为民族国家尽忠的理念,针对“一般妇女运动”对待国民革命的立场与态度,顺应各社会团体“通力合作”,“打倒军阀,澄清政治,恢复民权”②《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1—1927)》,第145页。的社会主题,提出了人权、民权、女权“三角同盟”,共争国权的主张。
向警予主张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勾结的“兵匪世界”里,妇女们应该首先赴国难,以国权、民权为重为先。她谈到:“若妇女心营目注的只一个‘女权’,而于‘国权’漠不关心,任洋人共管也好,军阀专横也好,是先已自己剥夺了自己的‘人格’和‘民格’,而反觍颜以求女权,岂非天下大愚,可耻之尤!”③警予:《中国妇女运动杂评》,《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她认为,于情于理都应将女权置于国权、民权之中,脱离国权与民权而求女权只是妄谈,是丧失国格与人格的做法。这一观点建立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为国尽忠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之上。换言之,将女权置于国权、民权之中体现了一种民族主义精神,即民族的尊严、国民的品格。
此外,向警予还基于唇亡齿寒、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常理,将妇女运动置于国民运动之中,探究妇女运动的性质,从而进一步阐明女权与民权的关系,认为人权与民权是女权存在的依据。她指出:“就中国政治经济情形说,中国妇女运动,业已带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盖呻吟憔悴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两重压迫之下的中国,并将人权民权首先争回,女权不能有存在的根据”。④警予:《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妇女杂志》第10卷第1号,1924年1月1日。简言之,国将不国,无以为人为民,女权安在。
除上述从妇女与妇女运动角度阐述女权与国权、人权、民权的关系以外,亦有许多论述关注如何处理各社会团体、社会运动的关系,才能使国民革命获得成功。李大钊指出:“中国现当军阀专横之时代,欲为民权的运动,无论那种团体,都须联络一致……可合而不可分,可聚而不可散,可通力合作,而不可独立门户”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1—1927)》,第145页。。可见,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各社会团体的社会运动都围绕国民运动的目标,同心协力,妇女运动也不例外。
以上可知,“四权”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包容中亦有序列。国权为重为先,国权是国民的人权与民权存在的前提,人权与民权又是女权存在的依据。人权、民权与女权的获得又是国民革命的动力与目标,时人主张人权、民权、女权结盟,首先着力共争国权而并图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尽忠民族国家的理念,以及在国民运动背景下,人们对国权、人权、民权与女权关系的理解,成为妇女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要素这一理论原则的“中层理论”。
四、“女国民”身份建构:理论的展开与实践
在国民革命和当时轰轰烈烈的国民会议运动背景下,有两个问题更加凸显,一是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的关系;二是妇女对待国民运动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提出将妇女解放作为民族解放的要素,直接回应了这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或者说,妇女们迫切希望抓住国民运动的契机,践行国民权利义务,提升政治地位,直接催生了这一理论,并使其迅速得以实践。
(一)国民运动是妇女运动的良机
处在国民革命与国民会议运动中的妇女运动如何才能取得成效?向警予总结了国内外妇女运动的经验,认为妇女运动总是伴随着国民运动而发生、发展。诸如,“欧洲的女权运动是跟着欧洲的民权运动一同起来的。我国的女子参政运动也是发轫于辛亥革命民国纪元的时候”。她认为随着国民运动的兴衰而潮起潮落,是妇女运动的规律。“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不能分离,而且妇女运动是要靠着国民运动去做得起来”。她强调“妇女运动必须乘着国民运动的长风才有日进万里的可能”,“妇女运动在平淡寂静的社会情况中是运动不来的”,应该抓住时机,乘势而起。①参见警予:《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觉悟》1924年12月30日。向警予的看法体现了“相机行事”、“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理念。
(二)责任与地位是“女国民”身份的核心
国民身份是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的基本条件,确定妇女的国民身份是唤起妇女投身国民会议运动的策略,也是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契机。
时人关于妇女应该拥有国民身份的主张,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妇女属于民族,或称“民族的妇女”;二是妇女是国民——“女国民”。关于“民族的妇女”的说法,是针对被压迫民族整体处境而言的,即在当时的中国,无论男女毫不例外地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妇女在被压迫民族之中,而不在此外。所以妇女首先必以民族妇女的身份向压迫者索权。《〈中国妇女〉的宗旨和内容》一文谈到:“中国妇女包括于整个的被压迫民族之中。在民族的自由独立未达到以前,绝无妇女自由独立的可能。使中国民族不能独立自由的是帝国主义和附属帝国主义生存的军阀”②《〈中国妇女〉的宗旨和内容》,《中国妇女》第3期,1926年1月20日。。这里明确指出了妇女的民族性和“压迫源”问题。
时人对“女国民”身份的讨论,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妇女与男子同为国民,同担责任。《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对全国女同胞宣言》指出:“我们妇女也是国民一份子,对于国是当然应与男子同负解决的责任。”③《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对全国女同胞宣言》,《妇女周报》第64期,1924年12月14日。这里可见,确认妇女是国民一份子的目的是要与男子同担国是。张挹兰认为在家国危难之际,方显出女国民英雄本色。这体现了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她将人类的理性精神界定为做事要把握“时间性和空间性”,即聚焦于特定时空的社会环境。她认为当时中国妇女所处的“时空”特点,即为遭受“二重压迫”:“列强帝国主义的压迫”和“重男轻女的遗传制度的压迫”。环境要求妇女做“二重的努力”,“求国家解放”,“求自身解放”。求得国民身份,就是为了直接参加救国运动。她指出:“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之一,是被列强所包围的今日的中华民国的国民之一!我们是中国的女子之一,是今日的中国女子之一!我们的使命,是要解放我们的国家,解放我们自己;救我们的国家,救我们自己”,“求国家解放的方法,是要我们认清自己是国民的一份子,应当直接或间接加入救国运动。”④张挹兰:《新妇女的使命》,《妇女之友》第9期,1927年1月15日。她用“褊狭”与“整个”的概念解释个人安逸与民族解放的问题,认为不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是“狭隘的个人主义”,只有民族解放才能得到“整个生活的解放”,妇女才能获得“整个人格上的解放”,“才算是真解放”。
其次,确定“女国民”身份是提升妇女地位的契机。人们认为国民会议运动的热潮是妇女争取国民权的契机。国民会议运动是当时最大的政治运动,妇女解放的“枢纽”即是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争得国民身份,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即可提升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大会报告》指出:“国民会议的运动在目前政治问题中是妇女界争国民资格的一个关键,妇女界放弃了这个运动的参加便是放弃了国民资格……妇女解放的枢纽完全关系于妇女界自身对于经济政治及社会地位之奋斗。数千年来中国妇女受压迫之历史,从此应转入一个新时期,由革命的妇女群众,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⑤《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大会报告》, 《民国日报》1925年5月28日。从中可见,妇女界试图抓住“关键”,获得国民资格,使妇女地位发生历史性的转折。
再次,确定“女国民”身份,以为妇女群体代言。时人认为,国民会议应有全体国民参加,没有妇女的参加不能称为真正的国民会议。《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对全国女同胞宣言》指出:“同人等敢以国民的身份大声主张:国民会议应是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而且因为我们妇女处境的特殊,不得不更进一步的主张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应有妇女团体参加!”①《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对全国女同胞宣言》,《妇女周报》第64期,1924年12月14日。关于为何要有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向警予认为主要出于三点考虑:一是“各职业团体,各政党及学生团体”虽未标明不含妇女,但各团体不可能着重提出参政、教育、职业等妇女的各项权利。二是即便有团体代言,也会因为“要求的主体”不在场而缺乏争辩能力,难以取得多数人的拥护而失败。三是避免“一两个女政客女官僚夫人小姐很漂亮的在国民会议上出几次风头”②警予:《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觉悟》1924年12月30日。,遮蔽半数妇女的权利。这可称为后来中国妇女运动组织模式的雏形。这是一种用“客体化”的方法争取主体性的策略。它一方面基于现实的妇女地位状况,通过妇女团体争取妇女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把妇女排除在各团体之外,难免导致将提高妇女地位的社会责任仅仅责成于妇女组织的偏差。
以上可见,“女国民”概念凝聚着妇女对国家的责任、关乎提升妇女地位的方法与策略,具有多重含义,同时它又是一个承载历史与文化的性别概念。
(三)践行“女国民”身份的路径
妇女争得国民资格后,如何履行国民的权利?又如何通过民权促进女权?时人在当时国民会议运动的背景下,以妇女怎样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为切入点,阐述了这些问题。
首先,在参与中增长“权能”,以“权能”担保妇女利益。向警予指出:“真正热心妇女运动,真正瞭解妇女运动的妇女,必须在每次国民运动中表示妇女的态度,提出妇女的要求,显现妇女的能力,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这样一来,事实上证明了妇女的国民的权能,而同时这个权能又就是妇女本身利益的担保。”③警予:《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觉悟》1924年12月30日。在这里,向警予提出了权能的概念和权能与妇女利益的关系问题。她认为,首先要证明妇女的权能,同时被赋予权力,再进而捍卫妇女的利益。那么,如何彰显权能?她主张在各种运动中要“立刻站一地位”,要表态,提要求,显现能力,而不要“自甘放弃”成为“落伍者”,那样无异于没有权能。或者说,要有有效行动,从而成为权能的主体。
其次,妇女要成为国民运动中的“劲旅”。如果说,彰显权能着重于个体层面的努力,“成为劲旅”则着重于妇女群体力量的凝聚。向警予指出:妇女在国民运动中“要能代表全体妇女的要求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而且这样还不够,还要根据自己的政见与主张大声疾呼力(地)向群众下死力宣传唤起群众的觉悟——尤其是妇女群众的觉悟……大家起来作我们的后盾。这样才能增加国民运动的声势,在国民运动中成为强有力的劲旅”④警予:《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觉悟》1924年12月30日。。向警予多次提到反对一两个上层妇女做点缀的妇女参与方式,主张“下死力”宣传唤起妇女群众。在向警予看来,只有广大妇女群众的广泛参与,妇女们才能成为国民运动的“劲旅”。而一旦妇女们成为“劲旅”,便可为女权运动开路。向警予概要地表达了这一策略,即是“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前驱,以开女权之路”⑤参见警予:《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妇女杂志》第10卷第1号,1924年1月1日。。
以上观点体现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念与方法,呈现了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妇女“增权”的特有方式。首先进入主流社会运动,占据重要位置,表达利益,争取权利,彰显能力,迂回达到成为主体的目标。当时妇女的“增权路线”或可概括为积极参与——突出表现——证明能力——争取权利。这种表达方式根植于中国的家国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序列是“为国为家为我”,家中有我,国中有我;我在国中,我在家中。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互惠文化”,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你谦我让,而不是你抢我夺。在中国文化中,个体的主体性是曲折地予以表达的。而在西方文化中,首先确定个体的权能,然后探讨是什么、怎么样剥夺了个体的权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增权路径不同——中国妇女的增权路线始于建构,西方妇女的增权路线始于批判。
因此,将妇女运动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要素,既是妇女运动的经验,也是寻求妇女解放的策略;以救国救己为目的的“女国民”身份的建构,是对这一理论原则的具体践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某些概念、观点,诸如以“权能担保利益”、妇女的增权路线等或可成为这一理论原则的微观范畴。
综上所述,将妇女解放作为民族解放要素,亦即将妇女解放纳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进程中,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提出的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论原则。它顺应了20世纪劳动解放、民族解放、妇女解放三大国际潮流,立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根植于“我在家国中”的文化土壤,回答了在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中,一般妇女运动对待革命的态度和立场问题。这一理论原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直接借鉴了社会系统理论、人道主义理论等科学理论;国权、人权、民权与女权“四权”的关系与序列既是这一理论的支撑,又可视为其下的“中层理论”。“女国民”身份建构的基本概念、理论观点又是与“四权”关系极为密切的微观理论形态。
国权、人权、民权与女权是国民革命时期的主流话语,是一个互相关联、相互依存的系统。女权的要义是国权之下的人权与民权 (国权是人权与民权的前提),即妇女的独立、自由、平等之权。时人大声疾呼,伸张女权,表达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诉求。在国民运动背景下,“女国民”身份建构成为妇女承担救国大任,提升妇女社会地位、维护妇女利益的关键环节,以“权能担保利益”是妇女的增权路径。而今在发展成为社会主题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妇女的主体性,使男女和谐发展?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关系的理论原则,继承历史经验,推进这一理论的发展创新?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作者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 北京100101)
(责任编辑 朱昌裕)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PC to Bring Women’s Liberation into the Spher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Han Henan
The resolution on women’s movement adopted by the Four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ut forwar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 to treat women’s movement as an element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It conformed to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labor liberation,national liberation and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emerged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a semi- feudal and semi- colonial China,was roo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responded to some major issues such as the stance and attitude of the“general women’s movement”towards the revolution.It took Marxism as a guide,drew on the viewpoints of relevant theories like the social systems theory and the humanitarian theory and was based on theories about the mutual relationships of national rights,human rights,civil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female national”identity,thus taking on a distinct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not just a strategy to“incorporate”the women’s movement into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or a slogan for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of women.
D231;D442.0
A
1003-3815(2012)-06-0049-10
——兼论《民权素》创刊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