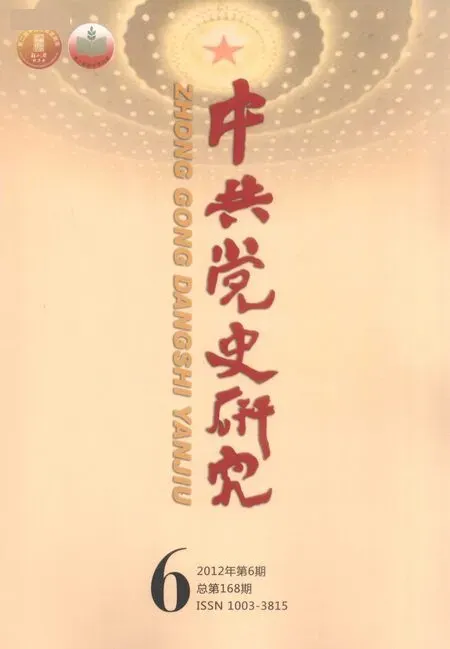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会议方式探析
王海光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通常称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争议也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从中央到地方的与会领导干部对会议都有非常积极的评价。当时毛泽东也称赞“开得好”。但时隔两年后,他对会议就有些看法了,认为“把一些缺点和错误讲得严重了”①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4页。。“文化大革命”中,为“打倒刘少奇”,把七千人大会说成是刘少奇1962年否定“三面红旗”、“右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状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七千人大会的历史价值和积极意义才重新得到认识和肯定。1978年,胡耀邦领导中央党校开展的“三次路线大讨论”,在全党最早拉开了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最初的讨论稿中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作为负面材料,但参加过这次大会的学员马上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意讨论稿的看法②参见拙文《轻雷隐隐初惊蛰——胡耀邦与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下),《领导者》总第36,足见党心所向。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写道: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又说:“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8页。这是中央有关权威文献和著作对大会的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正面肯定。
七千人大会能取得积极成果,是发扬了党内民主的结果,也因此作为发扬民主的楷模载入史册。七千人大会原本是要开成一个反对分散主义、催要粮食的会议,但在一些随机性事情的因应下,会议脱离了原来的议程,最终开成了一个发扬党内民主,充满反省精神的大会。通过这次大会,调整了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党内的紧张关系,上下通了气,情况透了底,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激发了全党克服困难的信心,使一些原本十分纠结的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对动员全党大刀阔斧地调整国民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是在“关键时刻解决了关键问题”的一次历史性会议。这正是发扬民主的伟力。
然而,大会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检讨“大跃进”失误的,这就决定了会议上的发扬民主和自我批评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对经验教训的反省总结实际上停留在了“出气”的层面,很多重大问题没能深究下去,各种意见正面交锋不够,致使一些矛盾积累下来。所以,尽管会议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发扬民主上取得的许多积极成果并没有在会后得到巩固和发扬,反而成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产生政见分歧的开端。这里的经验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本文试图从会议方式的角度,对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的情况及其历史局限性进行历史考察,进而探讨会议程序弹性与民主张力的关系。
一、“大跃进”挫折后的调整困局: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挫折。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大会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而实际情况是远近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产生结果”②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2页。。实际上,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是为了解决调整的困境,粮食问题是其中最迫切的问题。
持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到1960年已是“三鼓而竭”,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危机,不得不“退”了下来。“大跃进”造成的严峻局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正如刘少奇指出:“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③《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5页。1960年的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3700亿斤下降到2870亿斤,1961年也只恢复到2950亿斤。④参见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农业经济资料 (1949—1983)》,内部资料,1983年,第143页。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大量减少。农村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发生地。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000万人,而农村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702万。1961年全国总人口又继续净减少348万人。1961年国家精减职工798万,压缩城镇人口1000万,城镇人口总数净减少366万人在1000万的城镇人口下放农村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只比1960年增加了18万。⑤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另据《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60年全国农业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164万人,非农人口比上年净增加164万人; 1961年全国农业人口比上年净增加970万人,非农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316万人。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1949—1986足见困难形势的严重性。
同时,能不能承认“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从而走出困境,这对执政党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中共是从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党,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情结很重况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是中共和毛泽东试图为社会主义阵营树立的一个赶超“样板”,其“赶英超美”的发展指标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的,要承认挫折更加困难。而且为发动“大跃进”和维护“大跃进”造出来的那些人间神话,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开展党内斗争,把一大批讲实话的干部群众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承认挫折也就等于说这些运动都搞错了,这些人都整错了。所以,如何从“大跃进”高耸入云的台阶上走下来,“退却而不形成溃退”,对执政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央开始认真贯彻“调整”方针,努力恢复奄奄一息的农村经济。在大半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整风整社,纠正了“五风”,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简称“农业六十条”),改变了人民公社体制,缩小了社队规模,取消了公共食堂,改变了基本核算单位。中央还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等条例,做出了大量精减城镇人口的决策。经过这些工作,到1961年八九月间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已经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升了①《毛泽东传 (1949—1976)》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70页。。会议确定,到1963年粮食在中等年景的条件下不再进口。但是,农村形势虽然开始转圜,实际情况仍不乐观。
在工业调整方面,开始总想在重工业生产已经达到的水平上调整,钢产量的高指标没有降下来。中央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地方更是如此,一些上马的基建项目都不愿下马,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也很难落实。直到1961年八九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认识到:工业必须要退够,才能调整②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630—631页。。决心全面下调工业高指标。如周恩来后来所说: “真正的调整,是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③周恩来在1965年7月26日的讲话,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2页。。由于耽误了调整时间,执行情况很差,国民经济的紧张局面继续加剧。城乡居民的食品、棉布消费量比上年续减,吃穿用更加紧张。
同时,作为“大跃进”的后遗症,党内干部的情绪非常大。在第一线工作的干部,怨气更大。事情都是上面压下来的,但承担责任的都是他们。他们抱怨说:“反右倾”运动整了实事求是的干部,整风整社运动又整了听上级话的干部,“取了经是唐僧的,闯了祸是孙猴的”各级干部都有一大堆的疑问:“三面红旗”对不对?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困难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中央有什么责任?消极的情绪在基层干部中悄悄地蔓延。
“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使各级干部吃尽了图虚名而遭实祸的苦头,他们痛心疾首,内疚自责,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不再盲目地听命上级的指示了。对上级布置的任务,他们不能不考虑一下自己单位和地区的利益,再没有过去那种争先恐后的冲劲了。许多工作任务,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很难安排下去这些情况,让中央感到党内有一种灰溜溜的畏难情绪,有分散主义,有本位主义,有自己的“小天地”。为此,中央决定搞一个七年计划中心是解决吃穿用,兼顾国防,把大家的气壮起来④《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68页。。但远水不解近渴。对于已经尝过画饼充饥滋味的各级干部来说,这种传统的鼓气方式很难说能有什么效果。
此外,中央与地方上下不通气的情况仍然很严重。虽然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但人们调查研究的动机和观念不同,调查的效果也不一样。1961年,中央虽然开了几次会议,但并没有集中地系统地对过去的工作失误进行总结。大家对困难情况不摸底,对形势的认识也不一致。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我们头脑太热,违背了客观规律,使本来可能的事变成不可能了被迫退下来⑤《。
上述这些纠结的问题,集中反映到了粮食征购调拨问题上。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亿斤至70亿斤。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中央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但到11月中旬,粮食上调任务只完成了20%多一点。①《中央关于抓紧完成第四季度粮食调出任务的紧急通知》(1961年11月23日),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9页。11月23日,中央下达紧急通知,督促各地努力完成任务。同年还进口了116亿斤粮食。如此大规模地进口粮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的事情。1961年11月上旬,中央召开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落实1962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时,各地领导人都面有难色。邓小平发了狠话,提出了上调粮食的三个方案: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要大家选择。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勉强接受了中间方案。②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9 20页。
下面的干部有畏难思想是不难理解的。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是2870亿斤,征购量是1021亿斤,征购量占产量的35.5%。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是2950亿斤,征购量是809.4亿斤,征购量占产量的27.4%。③参见《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1949—1986)》,第410页。1962年的粮食丰歉情况未卜,再加倍地征调粮食,这意味着还是高征购。李先念1965年2月给书记处汇报时曾说:在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下,征购粮食只能占产量的25%左右,多了就会出问题④参见《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1949—1986)》,第410页。。因此,各大区接受了150亿斤的任务,等于是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作为一个因应之策,陶铸提出开个全国地委书记的会议,让中央帮助打通下面的思想。邓小平接受了这个意见。
1961年11月12日晚,毛泽东听取了书记处的汇报,决定把县委书记都召集来开会,搞一个小整风,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总结一下,鼓鼓劲。检讨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中央的账要讲清楚,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要检讨,地方可以不检讨。他说:“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困难已经走出了谷底,经济形势已经好转,错误都在改正。中央可以说得起话了。下面不是没有东西,而是气不顺,本位主义,给中央“打埋伏”。他说:现在气不壮,很沉闷。东西有,就是收不上来。要搞思想统一,解决小天地过多的问题。开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是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⑤参见《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1949—1986)》,第410页。
在11月16日中央下达的会议通知中,列举了当前的问题——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不讲老实话、征收农产品不照顾大局、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等等。12月21日,在有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说:把大家召集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⑥参见《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 (1949—1986)》,第410页。上述可见,七千人大会的最初动机是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强集中统一。虽然中央表示,过去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实则在现实的具体问题上,矛头是朝下的。
二、从“主题先行”到“主题后行”:大会直接讨论政治局报告的非常之举和应因之道
召开七千人大会,是要总结经验,壮气鼓劲。要“总结经验”,就要说明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和责任。毛泽东指出错误责任第一在中央,并要中央书记处清理这几年的文件,以明确中央的责任和问题出在哪里。这是会议准备的第一步。
“大跃进”是党中央、毛泽东决策的,如何规避毛泽东的责任,是总结经验的首要问题中央书记处很快选编出了两本材料,一本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语录 (后题名为《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并就清理材料的情况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写了报告
邓小平在1961年12月16日书记处会议和12月21日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都讲了清理材料的情况。他说:毛主席的言论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第二本“毛病很多,许多毛病出在这上面”。讲责任是中央第一,省市第二。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书记处的缺点错误主要表现在:没有及时研究和提出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或者具体政策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计划指标过高、多变;几个“大办”不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权力下放过多,体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乱。邓小平还说:过去这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研究的结果,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①参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7、39页;《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下),第 1676—1677、1679页。
中央书记处对中央文件的清理工作及其报告,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肯定,成为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12月20日,在中央小型工作会议召开的当晚,毛泽东对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讲:这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首先应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总说中央正确,英明领导,不符合事实嘛……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②《毛泽东传 (1949—1976)》(下),第1188页。毛泽东这些话,给七千人大会定了调子。中央的责任在书记处,也就是说,不是决策的问题而是贯彻的问题。刘少奇在12月21日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也说:总路线是不错的,是执行中间的错误③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9页。。
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承担了责任,通过编语录和编文件的方式,为大会顺利召开提供了前提条件。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央书记处编选的文件,是有政治上的精心考虑的,并非都是负面文件。当时彭真根据中央要求,让北京市委协助清理了这个时期的文件。共涉及93份文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央下发的文件,共19件。作为负面材料的7件,主要是发动“大跃进”的文件;作为正面材料的12件,都是具有纠偏性质的文件,正确率占63%。第二类是中央批转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地方党委的文件,共74件。其中属于中央和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51件,地方党委的23件。作为负面材料清理的有63件,错误率85%,正确率15%。④傅颐:《重寻“畅观楼事件”的真实》,《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如此看来,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主要的也只是失察和轻信的领导责任,更多的还是下面的问题。
从调整开始,中央一直没有系统总结过“大跃进”挫折的严重性问题,中央领导人之间对总结经验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在常委中,刘少奇在农村真正搞了调查,对下情的了解是最深入的。1961年4月,刘少奇回到家乡,进行了44天的农村调查,亲眼目睹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灾难性后果。“五风”对农村经济的摧残,农民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都给他留下了铭心刻骨的直观印象。⑤参见《刘少奇传 (1898—1969)》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62—875页。在接手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后,他把对一些问题的尖锐看法写到了报告中。
1962年1月10日,毛泽东接到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先是要推迟3天开会,接着又决定报告不先经过政治局讨论,直接印发大会,用3天时间分组讨论。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没有开幕式,直接把中央的报告“披头散发”地发下去,让大家提意见。根据毛泽东提议,会期延长,充分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
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政治局没讨论就发下去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对于毛泽东的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后人评论很多。参加起草工作的胡绳认为:这是毛泽东认为报告的调子太低了,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肯定不够,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讲话,不是少奇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了”⑥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49页。。因为毛泽东对报告不太满意,又不便于自己出面表态,而在省委书记参加的100多人的小型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报告“议论甚多”。某些“大跃进”的急先锋人物尤其不满。毛泽东索性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讨论,投石问路,看大家的反应,让党内思想状态透透底。这是一种“引而不发”的姿态。
但这个不符合以往开会惯例的举动,却暗合了会议的内在要求。以往的大会都是表态性的会议,议题先行,程序固定,少数人决定好了,让多数人表态通过,把规定动作做完了,会议也就开完了。与会者的民主权利很难体现。而这次开会,毛泽东投石问路,首先让大家充分讨论政治局报告,发表自己对报告的意见,于不经意间打开了会议的民主之门,提供了自由讨论的空间,因而使会议出现了充分民主的“情势”。
毛泽东的投石问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与会者,都是“大跃进”运动的各级领导者。这几年,把经济搞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大家都十分困惑。在讨论报告中,大家议论纷纷,提出了各种问题。主要是:当前的困难形势怎么造成的?为什么会犯错误?谁应该对错误负责?有没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三面红旗”对不对?这几年的工作怎么看?相比刘少奇报告的原则性语言,他们的意见更加鲜活具体。有些省直接提出了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①《杨尚昆日记》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大会的主题。
言路一开,堵是堵不住的。大家对报告的修改意见,主要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基调问题。首先是对形势与任务如何估计的问题。毛泽东意识到与会者的情绪,十分明智地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态度。他决定成立21人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从16日起,会议主题从反对分散主义,转到了总结经验上来。
在总结经验阶段,毛泽东和中央采取了让不同意见充分发表的民主讨论原则。他指示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都可以自由发表。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②《毛泽东传 (1949—1976)》(下),第1193页。这是大会最为成功的决策之一。
起草委员会与大会小组讨论采取平行作业的方式,小组讨论的意见都反映到起草委员会上。起草委员会在讨论修改报告稿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争论得很激烈,言论也比较大胆。彭真说:把成绩讲足,把错误讲透,错误有多严重讲多严重,这样才能轻装前进。吴冷西回忆说:像这样起草文件,讨论的意见如此纷纭,争论如此激烈,是他平生的第一次。③吴冷西:《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20页。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起草委员会经过8天紧张工作,于1月24日下午完成了报告第二稿最后第三部分的修改。这时大会已召开了13天。报告第二稿在总结经验上汇集了众议,对报告中的形势和任务的看法,对“大跃进”缺点错误的分析,关于反对分散主义等等问题,都作了重要的修改补充。在不可能彻底总结经验教训的条件下,采取了更加接近事实的态度。报告归纳了4条主要缺点和错误,对其产生原因,把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的错误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作风的滋长联系起来,更具有说服力,比较容易让人接受。④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53、354页。特别是在报告第二稿中,不再提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不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更没有再提城市人民公社。而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倡导起来的,并且作为纲领性的口号一直在宣传。因为实现不了,报告修改稿中不再提及。这表示了中央政策观念的重大转变。
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的修改是很注意策略的。报告肯定的12条成绩是夸大的估计,总结的4条缺点错误是以肯定“三面红旗”为前提的,讨论中对“三面红旗”的质疑和否定意见没有反映进去。还说如果遵循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认真执行毛泽东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①转引自张素华: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14页。。但如果联系到报告中的三个“不再提”,仔细琢磨一下“或者”后面的话,还是很有些意味的。
1月24日晚,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讨论修改报告稿的情况。商定在25日下午召开有各省市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报告稿,然后提交大会通过。②参见《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下),第1685页
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稿,同意提交大会。26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27日下午4时开第一次全体大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在27日上午,毛泽东又临时决定,大会开始时间从下午4点改到2点。刘少奇连夜准备,直到上台讲话前才把报告提纲交毛泽东等人传阅。③吴冷西:《调整时期的中流砥柱——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回忆领袖与战友》,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虽然准备时间仓促,但他对所谈问题早已是块垒在胸,即席讲话反倒是说得透彻,言语也更尖锐。刘少奇说:讲缺点错误和成绩,不能再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套话;现在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有的地方还是倒“三七开”。他还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这些话是书面报告上没有的,毛泽东没有讲过,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没有讲。刘少奇还说:这几年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除了高指标,要求急,瞎指挥,还因为在党内和群众中进行了过火的斗争,使得干部群众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搞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刘少奇还谈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事情,他说:彭德怀的信,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能算犯错误。
刘少奇的口头讲话,给与会者很有些振聋发聩的感觉,甚至还有点惊心动魄④胡绳后来回忆说:刘少奇在台上讲话,毛泽东不断插话,他就担心毛泽东能否接受。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47页。吴冷西也说:刘少奇讲话给大家震动很大,非常兴奋。参见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第158页。。大家由此看到了中央实事求是的态度,倍感鼓舞,群情振奋。次日,大会各小组反映说:“大家一致对少奇同志的报告满意,特别满意会议的开法”⑤《杨尚昆日记》(下),第117页。。
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的报告也表示了肯定对大会的开会方式更是称道。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中说:“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三、因势利导:根据会议局势发展调整会议程序
按照大会日程安排,在刘少奇作完口头报告后,会议就准备结束了。1月24日,起草委员会工作结束,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修改情况,并研究了会议日程,决定会议在月底结束。1月27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宣布说:会议无论如何31日要搞完⑦参见《毛泽东传 (1949—1976)》 (下),第1196—1197页;吴冷西:《实事求是的榜样——回忆七千人大会中少奇同志的作风》,《回忆领袖与战友》,第143。28日,全体与会代表与中央领导人合影,会议进入结束的程序。但由于刘少奇1月27日的口头讲话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使大会出现了欲罢不能的态势。
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实际上打破了肯定“三面红旗”的框框,改变了会议总结经验的基调—— “三面红旗”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道出了大家心中的共同感受,出现了一个会议高潮。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明察秋毫,随之改变了会议的日程。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挫折,曾多次表示过自责态度。1960年11月28日,他在一份批转各地党委的报告中说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64页。。在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对书记处的检查报告发表意见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讲我的缺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真从维护毛泽东领袖威信的善意出发,在起草委员会上发言说: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但遭到了陈伯达等人的激烈反对。②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10页注释1,第108—111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20、721页。实际上,毛泽东的错误缺点,他自己可以讲,其他人是讲不得的。这是当时党内普遍的心态。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在地方和中央两个层面上,都产生了巨大震动。在地方层面,许多干部开始对照自己省区是“倒三七”,还是“十个指头都烂了”。特别是一些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到北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还继续捂盖子,不让讲省委的问题。在刘少奇口头报告的鼓励下,一些干部向中央写匿名信反映情况。中央对这些省委领导人在中央会议上还捂盖子的情况非常震惊,也切实感到了这些地、县干部的愤怒情绪。
在中央层面上,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中把问题讲得这么严重,似乎暗含了某种问责的味道,也让毛泽东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压力。1月29日,林彪作大会讲话。他撇开准备的稿子,即兴讲话,对“三面红旗”大加赞扬,高调挺毛,改变了前天刘少奇报告的调子,让毛泽东“很高兴”③毛泽东1962年3月20日在《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批示道:“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62页。。
两份口头报告,林彪讲的是领袖崇拜的高调,刘少奇讲的是实事求是的低调。其实林彪心里非常清楚,“三面红旗”完全搞糟了,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党内外情绪很大④当时林彪在私下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过分”、“过极”,破坏了人们的积极性。参见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 (材料之一)》(中发〔1974〕1号)。。因为军队与“大跃进”关系不大,林彪一直把着军队不要介入地方工作⑤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356—357页。。在会议前期,林彪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林彪在刘少奇讲话之后的讲话,主动为毛泽东摆脱了尴尬的困境,不单纯是出于投其所好的政治功利目的,实际上也反映了党内的一种护短的狭隘心理:即维护毛泽东威信就是维护党的团结,担心对“三面红旗”的否定过多会造成党心民心的涣散。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很有些基础的。
林彪的口头讲话,用心良苦,可以作为一篇文过饰非的范文,能够解析出许多个人崇拜的信息。如林彪把“大跃进”造成的困难,首先推到了自然灾害的原因上,其次推到工作上的错误,又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交学费”。“交学费”是“代价不可避免论”的最初版本,相类似的说法还有“积累了经验”等等。再如林彪强调,困难时期最大的首要的问题,是党的团结,要求全党更加依靠和相信毛泽东和中央的领导。这种观点,在党内并非林彪独有,是很有思想基础的。林彪的出彩之处,是以他的威望和经历,强调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他说:毛泽东总比其他人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们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毛泽东的思想和意见受到了干扰。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林彪的这段话,当时多数人都认为讲得非常好,并不以为林彪讲话有什么格迕之处⑥当时不仅大会简报反映大家说林彪讲得好,而且一些参会的人,在多年后回忆中,也没有觉得林彪讲话有什么不妥。也有人当时就对林彪讲话有些反感,但多半藏在心里,没有反映出来。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47、303、311页。。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党内一种政治心态,即:越是困难时期,越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包括迁就他的错误,否则就会损害党的团结。其代价是丧失了全党的判断是非的能力。
林彪讲话后,毛泽东当场表扬讲得好,接着又提议延长几天会期,要大家畅所欲言,开一个“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规则是: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可以讲,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①参见《毛泽东传 (1949—1976)》(下),第1199页。林彪的讲话和毛泽东的提议,同样得到热烈响应。
1月30日,大会召开第三次全体大会。毛泽东自己主持,自己发表长篇讲话,高屋建瓴地讲了发扬民主集中制的道理。他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要让人讲话,宣布“出气会”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表示:中央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不点名地把一些省委书记大批了一顿,说他们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不敢担责任,“老虎屁股摸不得”,最后会要“别姬”的。②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6—47页。
从1月31日起,大会转为“出气会”阶段。以省区为单位,让地、县干部给省市委、各部委提意见,各省市进行工作总结并作自我批评。
省委书记一级的干部,是各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很多花样是他们搞出来的。中央要反对的分散主义问题,也主要是指他们。而对地县级的干部来讲,他们执行的错误政策,大都是从省委来的,很清楚省委的具体责任,对省委的意见怨气很大。毛泽东讲话后,大会焦点就集中到了省委书记们的身上。
毛泽东审时度势,以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带头自我批评的高姿态,通过开“出气会”的方式,因势利导,扭转了局面。会议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高潮——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出气”阶段。
四、控制会议的节奏,以“出气”达到“通气”
在会议转入“出气会”阶段后,会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掌握会议的节奏显得更加重要。自“大跃进”以来,各级干部都有一肚子的意见和委屈。毛泽东很清楚,只有让下面出了气,才能上下通气。他从一开始就说:中央不作检讨,不能服众。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都得检讨。意思就是让下面出气。然而,出气口子一旦打开,也容易出现失控的情况。
对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许多人都希望能在刘少奇讲话的基础上,把形势和困难讲得更透彻些。但毛泽东讲的主题是民主集中制问题,这与人们的期望值多少是有些距离的。但就控制会议节奏的角度来讲,如果毛泽东继续把形势和困难讲得更严重,势必带出责任问题。虽然说是中央有中央的账,地方有地方的账,但地方的账是从中央下来的。如果会议开到了算账的地步,烂账难收,也就开不动了。所以,各省委书记们需要有承受批评的肚量,不能上推下卸。
在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讲: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第一书记要“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③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8月19日)。。有些省市部委的第一书记,确实也当了几年“秦始皇”,作风强横,说一不二,大刮“五风”,动辄使用惩办主义的办法,下面干部的怨气很大。在“大跃进”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后,从毛泽东到各省市一把手,这个“罪己诏”都是很难下的。毛泽东从发扬民主的角度讲民主集中制,在会上带头做了检讨,以道德垂范的高姿态,再让省委书记们做点检讨,他们无话可说。
30日当晚,毛泽东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部署“出气会”的问题。毛泽东好言安抚,让那些坐卧不安的省委书记和部长们心里有了底。这些领导干部如能自觉地承担责任,不搞上推下卸,接受批评和检讨自己,会议就能顺利开成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会了。
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会上即兴讲话中,讲了许多必须发扬民主的精彩言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讲话中不约而同地都谈了要让人讲话,要保护少数人的意见。并且认为:恢复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首先就要保障党员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毛泽东说:“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8、24、39—40、43页。
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允许进行打击。这是党章上规定的。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说完他的意见,即使说得不正确,也不能阻止他讲话。如果他最后仍然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还可以让他保留自己的意见。”②《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40页。
邓小平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一定要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党员对党,对工作,对问题,对领导人,都有权按组织原则,在党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和意见,并且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党的会议上或在党的报刊上,党员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7页。
但要让地方大员当众深刻地检讨自己,并非易事。有些省委第一把手跋扈惯了,下级干部畏之如虎,很难放胆直言。所以,一些省的会议出现了哑场的情况。
为了打开“梗阻”的局面,让大家能够把“气”放出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到各省区坐镇。各省“出气”情况很不一样。有的省欠账少,包袱轻,“出气”容易;有的省欠账多,包袱重,“出气”就困难。有的省委书记比较开明,能够做自我批评;有的省委书记比较顽固,“连事后诸葛亮都不愿当”。刘少奇参加的安徽组周恩来参加的福建组,比较快地打开了局面但邓小平参加的四川组,一开始就两次冷场。
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中,批评一些省委书记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表示要摸摸他们的老虎屁股。有的省委书记意识到这指的就是他本人,遂积极响应,在大组当众做检查。虽然检讨仅限于已被暴露的问题,对错误缺乏深刻认识,但已经很出人意料了。一些干部也纷纷检讨自己,主动为省委承担责任。会议便由集中批评省委书记,转成了大家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1月30日的“出气”安排,是用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开让大家提意见,整个会议在春节前结束。2月1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大区“出气会”的情况汇报,决定大会延期到春节之后。2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继续听取西北、中南、西南三个大区的“出气会”情况汇报。这时“出气会”开得比较紧张了,如果继续开下去,涉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会议决定,2月3日由各省负责人做一次检讨,就结束这一段的会议。④这个日期与通常记载的不同。据杨尚昆记载:毛泽东在1月29日大会上说:会议延长几天,到春节前再闭幕;2月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开会,决定会议延长到春节后。参见《杨尚昆日记》,第118、119页;《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下),第1687 1688中央很明白,如果让大家放开提意见,一些省委负责人是怎么也过不了关的,得给这些人承担一下责任。这样,“出气会”一直开到2月6日。
“出气会”从1月31日到2月6日,这一个星期的时间,是这些省委书记们最难熬的一个星期,下面干部的各种意见让他们如坐针毡省委书记们都作了一生中最沉痛的检讨。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到,但会议预期的“出气”目的是达到了。毛泽东感到会上的“气”出得差不多了,遂果断决定结束大会。
2月6日,邓小平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他说: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中央首先负责,而在中央,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我们党有五大优点,但这几年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有严重缺点,其原因,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任务和口号,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大办”①即由大炼钢铁带动起来的各行各业的一系列“全民大办”运动。;二是这几年党内斗争发生了一些偏差,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现在必须要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健全党的生活。为了让一些地方领导人能够过关,邓小平在讲话中还为他们担了担子,说:小组会批评他们的事情,有不少是应该由中央负责的。②参见《邓小平年谱 (1904—1974)》(下),第1688 1689 《
2月7日,七千人大会开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讲了当前的主要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措施,代表国务院做了检讨,同时也为一些地方领导人说了话。大会通过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七千人大会只是为清理“大跃进”造成的这些问题破了题,重点还是要放在以后如何收拾残局的调整方面。“出气”阶段的许多问题只是刚刚揭开盖子,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关于调整工作,也没在最高层统一思想和意见,会议就结束了。这让人感到有些意犹未尽,有些“匆匆”,甚至还有些“夹生”。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会议也只能是对“大跃进”的初步反省而已。
从审时度势的方面讲,毛泽东对“出气”的“度”的把握,是要通过烧一烧各路“诸侯”,形成上下共同反省和“分担”责任的气氛,但又不能因反省错误而形成否定“三面红旗”的群情。目的还是要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达到全党的团结统一。从这一点讲,七千人大会对许多问题只能是点到为止,不可能期望彻底清理和改正“大跃进”的错误。
七千人大会从原来计划的10天,最后开到了28天,由一个表态性会议开成了一个讨论性的会议;从原来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集权的会议,最后开成了一个通过发扬党内民主促进党内思想统一的会议。促成这个主题变化的,首先是刘少奇。他在报告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责任感,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从而影响了会议的进程。毛泽东审时度势,体现了掌控全局的能力。他根据刘少奇带来的会议气氛的变化,因势利导,临场发挥,不断地调整会议议程,把握会议的节奏,把会议从一个高潮推到另一个高潮。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毛泽东表现出更多的是政治家的策略艺术,刘少奇表现出更多的是政治家的道德原则。
毛泽东对会议节奏变化的把握,从讨论刘少奇的报告,到开省委书记的“出气会”,始终贯彻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通过“出气”达到“上下通气”,重新振奋各级干部的精神,加强全党对中央的向心力。虽然七千人大会“跑了题”,对“三面红旗”和困难形势的认识与毛泽东未必一致,但通过七千人大会,中央了解了各地的困难情况,调整工作比较贴近实际了各地干部看到了中央敢于正视困难的实事求是态度,增强了信心。这对动员全党同心同德克服“大跃进”带来的困难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七千人大会虽然让下面的干部“出了一口气”,但许多问题只是“破了题”,有的只是刚刚“点了题”,没有再继续探究。而“通气的情况又更逊之。特别是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人对困难形势的认识,对调整的部署,都缺乏足够的沟通,没有形成共识,埋下了隐患从这一点看,七千人大会也有很重的“夹生饭味道。气出而不通,通而不透,透而不达,这是大会在发扬民主上的某种历史局限性。
五、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在发扬民主上的创新表现及其历史局限性
七千人大会之所以能够从原定的反对分散主义的大会,开成一个发扬民主的大会,初步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大会,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动员大会,这是与大会的会议方式密不可分的。这次大会改变了以往“主题先行”的开会模式,开创了一个“主题后行”的新模式。先把报告“披头散发”地发给大会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从而打开了会议的民主空间,使党内各种意见得以表达出来,开出了一个生龙活虎的会议。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来调整会期的长短,原定10天的会议时间一推再推,一直开了28天。
毛泽东当时非常赞许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他在1月30日的讲话中,首先称赞这次会议的开法:“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个开会方法,“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建议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委、地委、县委,也要试试这个开会方法。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页。
毛泽东亲自审阅和修改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周恩来的讲话稿,都给予了肯定的批示。他对自己在大会上的讲话,从2月下旬到3月20日,先后亲自修改了7遍。到4月初,又让陈伯达等作了修改,这才最后定稿。②参见《毛泽东传 (1949—1976)》 (下),第1210—1212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当时对七千人大会的基本肯定的态度。
但是,毛泽东十分推崇的这个会议方法,并没有延续下去。以后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再也没有开成过这样的会议。这倒并不是像毛泽东所说的, “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而是因为采取这样的开会方式,代表们成了会议主体,虽然符合了会议的民主之道,却对领导的集中统一带来了难度。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代表们说话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一旦得到了尊重,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七千人大会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七千人大会也产生了60年代党内政见分歧的最初裂痕,“打下了毛刘分歧的楔子”,投射出了以后党内斗争的阴影。这个情况,也是和它的会议方式分不开的。
“大跃进”挫折以后,党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收拾残局的思路。一种是不愿意讲困难,回避讲问题,不愿讲错误,担心讲这些会让人悲观,丧失信心,不利于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另一种是敢于面对困难,要求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只有把实际情况告诉全党同志,才能动员大家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难作为一个从战争中走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动员型政党,在中共党内持第一种观念的人非常普遍。第二种观念更符合现代政党的执政理念刘少奇无疑是后者的代表。他在主持起草修改报告时说:4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
七千人大会最大的亮点是发扬民主。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是他一生中最精彩的讲话之一。毛泽东认为,经过1961年的政策调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一天天在好转。这是他决定要召开这么大规模会议的一个前提认识。即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通过这次大会,总结一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重新鼓舞全党信心。道理很简单如果“错误”属于过去式,“出气”也好,“通气”也好,承担错误也好,是相对比较容易进行的。但是,在刘少奇口头报告讲了两个“三七开”的问题后,客观上带出了一个“问责的问题,即这些困难局面是怎么造成的?谁应该对此负责?讲到责任,从中央到地方,各有各的账。毛泽东是最高决策者,第一责任人从“大跃进”的轻率发动,到庐山会议的风云突变,毛泽东都是难脱其咎的。所以,毛泽东要维护的基调是:“三面红旗”是正确的,问题是缺乏具体政策,主要是贯彻执行中的问题。这样,“问责”的重点就落在部门和省市一级上了。实事求是地讲,部门和省市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他们以自己利益绑架中央,用虚假数字误导中央,甚至中央开始纠“左”了,一些地方还迟迟不动。人们对这些领导人的意见也是最大的。毛泽东讲民主集中制,在宏观上承担了领导责任,作了自我批评,随之要求地方领导人作自我批评,达到了“上下通气”的会议效果。
在七千人大会上,无论是会议的报告,还是各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是把毛泽东作为正确路线的象征,自觉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曲意为毛泽东解脱责任的,不仅仅是林彪,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意识。首先是中央书记处精心选编的《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选的都是毛泽东这几年一些比较正确的话,以说明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刘少奇也是非常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他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说了一些对彭德怀很不公道的话,这也是出于为毛泽东开脱责任的需要。同时,毛泽东也表现出了包容性的开明姿态,使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的党内紧张空气得到了舒缓。
但是,就民主和集中关系的处理而言,毛泽东是把发扬民主作为实现集中的方法。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发扬民主的方式,是让大家“出气”,通过“出气”达到“通气”,实现上下交融的团结。在这个“出气”过程中,毛泽东对会议气氛和开会节奏的把握,犹如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顺水推舟,因势利导,显现了领袖的政治艺术。在这种情况下,七千人大会的发扬民主是比较有限的。基本达到了“出气”的效果,通了气,鼓了气,见好就收了。因此,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讲清楚,许多情况还没有透底,中央高层对如何调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七千人大会后部署调整工作中,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与毛泽东的思路发生了抵牾。
刘少奇由于受七千人大会的鼓舞,在主持调整工作时,对形势的看法更客观也更严重采取的调整措施更彻底也更坚决。在“西楼会议”上,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意揭,怕说成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还说,现在处于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一开始就讲,形势很严峻,很困难,如果当前这个趋势不扭转国民经济要崩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刘少奇传》,第898、904、905页。。正是因为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央才能以“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工作。也正是把形势的严重性向全党交了底,这些“伤筋动骨的调整措施,才能得到坚决贯彻执行。如在1961年至1963年6月间,减少2600万城镇人口,精减职工1887万人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第602页。。这么大的人口迁徙规模,没有出现乱子,如果没有同心同德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虽然也承认“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他认为“困难正在被克服中”③《毛泽东传 (1949—1976)》(下),第1215页。。对刘少奇一再讲形势严峻,他是很不高兴的。1962年7月20日,毛泽东同各中央局书记谈话时责问道:“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7月2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④《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严厉批评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重新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外的矛盾。从此,中共失去了通过深化调整,进而走上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的可能。
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的会议方式及其局限性,对今天党内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有非常现实的启示意义。
1.执政党要实现从革命党向法理型政党的转型。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已经提出了建立党内民主制度的若干基本问题,如少数服从多数;保护少数人权利;让人讲话,言者无罪;建立党员与党组织的正确关系,保障党员权利;任何一个党员有权利批评任何一个党组织领导人,向上级反映负责干部的缺点和错误;各级领导人应该接受监督;党委会内部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相互监督;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察权;一切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要按照党章办事等等。但是,在会后不久,毛泽东就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在调整方针上发生了分歧,他断然否定了中央的集体决定。这些发扬民主的不无精彩的思想观点也就束之高阁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新举起了阶级斗争的旗帜,党内民主的大门关闭了,而通往“文化大革命”的大门却缓缓打开了。可见,民主建设必须建立制度的法理型权威。
2.执政党能否实事求是看待困难和认识错误,既是政党的历史责任感的体现,自信和力量的体现,也是争取历史主动权的需要。
七千人大会在如何端正克服困难的态度问题上,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如何增强信心?是采取遮遮掩掩的态度,还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当时中共各级领导人,都比较熟悉战争动员型的工作方式,习惯于以未来的美好愿景动员和鼓舞群众。 “大跃进”把这种战争动员方式推到了极端,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泛滥,造成虚火炽盛,自欺欺人危害十分严重,带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很多干部并没有从这种工作方式中走出来。他们担心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会使人们丧失信心,总想把成绩夸大一些,把缺点错误缩小一些,甚至对缺点错误讳莫如深不让人们反映意见。七千人大会的历史经验证明:以执政党负责任的担当态度,实事求是地把困难和问题摆出来,并不会让人灰心丧气反而会提高执政党的公信力,有助于增强信心形成齐心合力战胜困难的力量。
3.实现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首先要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建立正常的意见沟通渠道让党内的政见分歧有畅通的表达渠道,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实现党的团结统一。
“大跃进”运动遭到严重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断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阻塞了党内言路,信息严重扭曲。七千人大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把党内淤塞已久的言路进行了初步的疏通。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意识到要保障言路畅通,关键是要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建立党员和党组织的正常关系。
固然,在今天这样总结历史,是有些苛求前人了。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发掘党内存量的政治资源上讲,这种对历史的追问也并非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