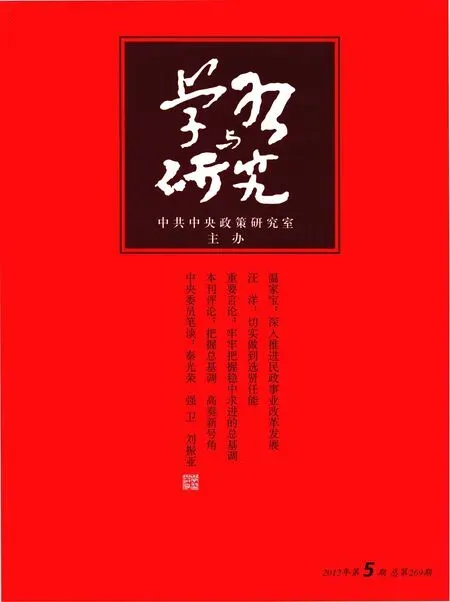材料、事实与反思:有关沈光文的“一桩文化史公案”——兼与潘承玉先生商榷
乐承耀
(宁波市行政学院,浙江 宁波 315012)
沈光文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地位,早已被海峡两岸的学者所认同。绍兴文理学院的潘承玉教授在2005年“海峡两岸越文化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中,提交过《越地三哲与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论文中提出“沈光文:中华文化在台湾系统传播的开创者”的观点。时隔二三年,潘先生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相继发表了《神话的消解:诗史互证澄清一桩文化史公案》、《真相、遮蔽与反思——关于一桩文化史公案的后续考察》,一反其原来的观点,说沈光文是“卑卑无足道的人物”,在台20年中除了骂郑氏政权外,就是想“投诚清廷”,晚年“极为热心和卖力地充当满清‘赤子’的角色”,是一个“半路投清的变节遗民”。他还认为,三百年来之所以把沈光文推到“台湾文献初祖”的地位,是由于全祖望的“回护”,另外的原因是“同乡情节和政治关怀”,正是这些原因,出现了沈光文的“造神”运动。事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一些是非曲直应该怎样认识?本文谈一些看法,以与潘承玉先生商榷。2012年是沈光文诞辰400周年纪念,笔者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为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先人。
一、沈光文在台是“二十余年”,还是“三十余年”?
沈光文到台的时间,在台湾文化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海峡两岸学者对此做过研究。沈光文在台二十余年还是三十余年,是早于还是晚于郑成功到达台湾?潘承玉先生将此作为“澄清一桩文化史公案”的重要内容来看待。他认为沈光文到达台湾的时间是康熙元年(1662年),按此推算沈光文在台湾20余年,“沈光文绝没有早于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十年左右即到台湾”。他在“康熙元年底因投诚清廷发生意外到台湾,未曾早于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十年左右到台湾,已断无半点可疑。”“沈光文到达的准确时间在台湾已为明郑所有的康熙元年(底),而且是因为向清廷投诚生意外的结果。”浙东史学名家全祖望则“采信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与沈光文相见’为正确,而把‘康熙元年壬寅沈光文到台湾’判定为错误”。并提出沈光文在辛卯(1651年)或壬辰(1652年)到达台湾,其目的是“对沈光文回应招降之举的曲为回护”。
综观上述引文,可见潘先生有三层意思:一是沈光文在康熙元年(1662年)到台湾,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二是沈光文因投诚清廷发生意外而到台湾。三是全祖望的《沈太仆传》是沈光文先于郑成功十年左右到达台湾的依据所在,其目的是为沈光文投诚清廷“回护”。
对于潘先生的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在此,就有关史实谈点看法。
研究历史人物要实事求是,这就要从事实出发,详细占有材料,从事实中形成观点。对于这点,潘先生在他的文中也有提到。他说:“从事古代文史研究必须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将感情和政治考虑摈弃在外,否则即使出于‘善意’考虑,也将在严重歪曲历史的同时大违‘善意’之初衷。”看来,潘先生尽管提到从事古代文史研究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但他自己并没有这样做。只要考察有关文献,我们能够看出潘先生的说法是违背客观事实的。
按潘先生的说法,沈光文到达台湾的时间是“康熙元年”(1662年),是“在郑成功攻占台湾后第二年”,在台二十年余。但有关史料否定了这种说法。这在沈光文的《题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诗文序》,及其好友季麒光的《沈斯庵诗序》中有答案。这两篇序刊在季麒光的《蓉洲诗文稿》之中。该书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刻本,卷首有沈光文等人所作序文。沈光文《序》作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沈光文在《题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诗文序》中说:“先生与余海外交也。忆余飘泊台湾三十余载,苦趣交集,则托之于诗。”明确表明作者在台湾30余年。季麒光,字圣昭,江苏无锡人,康熙二十二年任台湾府诸罗县县令,是沈光文的“海外知己”,他的《蓉洲诗文稿》中,诗与沈光文“倡和过半”。沈光文的这位“海外知己”在他的《〈沈斯庵诗〉叙》中也云:“余自甲子冬月渡海,僦居僧舍,即晤斯菴先生。见其修髯古貌,骨劲神越,虽野服僧冠,自非风尘物色。叩之,知为四明旧冏卿,当酉戍以后播迁锁尾,卒乃遁迹海外,以寄其去国之孤踪者也。与之言,则咳吐风生,议论云发,如霏玉屑,如泻瓶水。当是时也,焚撞灯荧,雨窗烟冷,坐对午夜,若遇素交,及各出所著诗文相指示,并纵谈宗旨内典、诸家外史,多所证可。在斯庵三十年来飘零番岛,故人凋谢,地无同志,以余非聋非瞽,能伸纸濡毫,略知古今遗事,遂不我遐弃,忘年缔好。”“冏卿”指太仆寺卿。因沈光文曾任太仆寺少卿,故称之外“旧冏卿”。酉戍指乙酉、丙戌年(即顺治二、三年,1645~1646年)。季麒光在“叙”中,除叙述两人交往及诗文的切磨以外,也明确提到“斯庵三十年来飘零番岛”。“斯庵”为沈光文号;“番岛”即指台湾岛。季麒光与沈光文是同时代人,且有诗文交往,是为直接材料。沈光文本人及季麒光的《序》都明明白白地说沈光文在台三十余年,应该是可信的,也是最权威的说法。
潘先生之所以提出沈光文在台二十年余的说法,可能是没有看过季麒光的《蓉洲诗文稿》。据《蓉洲诗文稿选辑》出版说明记述,季麒光的著述流传并不广,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著作逐渐佚失。乾隆十七年,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时,包括季麒光的《台湾杂记》、《蓉洲文稿》、《山川考略》、《海外集》等在内的38种著作已被列为“邑无藏版,亦少悬签,年代未遥,散失过半”的图书之列。20世纪六十年代,台湾著名学者、编辑出版家吴幅员先生,在《台湾舆地汇钞》一书的《弁言》中也指出,除季麒光的《台湾杂记》外,其他的《台湾郡志稿》6卷、《山川考略》1卷、《海外集》1卷、《蓉洲文稿》1卷,“惜均已佚”。至今,季麒光的相关著作,诸如《蓉洲诗文稿》仅在上海图书馆可以看到,另外厦门市图书馆有《蓉洲文稿》的手抄本,2005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李祖基研究员作了编辑整理,并由香港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1月出版。潘先生在没有见到季麒光的《蓉洲诗文稿》的情况下,就匆忙提出沈光文在台二十年的观点,这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潘先生读过沈光文《题梁溪蓉洲先生海外诗文序》后,体会一下沈光文本人“忆余飘泊台湾三十余载”说法,我想他是不会轻易提出沈光文在台二十余年说法。
如果笔者上述论点成立,余下的两个问题,应能迎刃而解。既然沈光文在台30多年,那么康熙元年(1662年)到台湾的说法是不可能的。沈光文作《题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诗文序》的时间为“康熙丁卯”。“康熙丁卯”,为康熙二十六年,即西历1687年,按此计算,减去30多年的话,应该是1657年(顺治十四年)以前,一般认为是辛卯(顺治八年)或壬辰(顺治九年),即西历1651年或1652年。这里已经十分明确说明,沈光文是先于郑成功十年左右到台湾,在荷人统治下艰辛地传播中华文化,其他的不少资料都有记载,沈氏确在郑氏到台之前已在台湾。
潘先生在文中也多次引所谓沈光文的《东吟社序》:“余自壬寅,将应李部台之召,舟至围头洋遇飓,飘苹至斯”,因此认为“沈光文乃在康熙元年底因投诚清廷发生意外到台湾,未曾早于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十年左右到台湾,已断无半点可疑”。《东吟社序》刊在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二《艺文三》之中。范咸《重修台湾府志》纂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离沈光文《题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诗文序》的“康熙丁卯”(1687年)近60年时间。沈光文与季麒光的《序》为直接材料,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且康熙间的《蓉洲文稿》等文献并没有《东吟社序》的记载;而近60年后的《东吟社序》,尽管序沈光文之名,其史料价值就低了,因为范咸的《重修台湾府志》毕竟是乾隆时的史料。对于《东吟社序》,台湾的不少学者,诸如台湾大学教授盛成就有疑问,盛成认为《东吟社序》“极其浇乱”、“酌改过甚”,“略润太多”,“似乎值不得作为研究沈光文之直接材料”。当然,一些学者还认为“壬寅“为”壬辰“之误。高一萍就说:“今所见‘壬寅’,乃‘壬辰’之误。因辛卯后当为壬辰也(即永历六年)”。
至于全祖望《沈太仆传》中提到的“公居三十余年,及见延平三世盛衰”和“辛丑,成功克台湾,知公在,大喜,以客礼见”的说法,随着沈光文在台30余年的命题成立,可以肯定没有错。其实,全祖望曾托人去台取过沈光文诗文,他在《沈太仆传》中说:“会鄞人有游台者,予令访公集,竟得之以归,凡十卷,遂录入《甬上耆旧诗》。”他在《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诗集序》中亦说:“吾友张侍御柳渔持节东宁,其归也,为予言太仆之后人颇盛,其集完好无恙。予乃有意求之,适里中李生昌潮客于东宁,乃以太仆诗集为属,则果抄以来,予大喜,为南向酹于太仆之灵。”这表明全祖望见过沈光文的诗,可能也见过沈光文的《题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诗序》,因此有“公居台三十余年,及见延平三世盛衰”说法。他在《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诗集序》中亦有“太仆居海外者四十余年,竟卒于岛”的说法,这里的四十余年是包括在金门等地的10余年及在台的30余年。全祖望的沈光文在台30余年说法,与沈光文的本人及其友人季麒光说法一致,应该是可信的,而潘先生对全氏的指责,极不可取。
二、沈光文是“变节遗民”,还是顺乎历史?
潘先生认为沈光文是“向清廷投诚”者,“极为热心和卖力充当起了满清新朝‘赤子’的角色”。是“一个半路投清的变节遗民”。笔者认为这个观点也值得商榷。
沈光文的晚年,处于康熙的中期。康熙皇帝是政风卓越的政治家,为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高峰“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清朝初期,中国的版图之所以能得以最后奠定,康熙帝功不可没。此外,康熙借鉴历代王朝的兴亡盛衰的经验和教训,励精图治,广纳贤才,发展生产,振兴文化,崇尚儒学,使得社会经济发展,民心安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收复台湾,振兴中华文化更是名垂千古的佳话。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一个部分。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他所实行的和大陆一致的典章制度和府县制政治统治以及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郑成功据守台湾所打的旗号是“反清复明”,而事实上则保持着一时的割据局面,郑成功去世后,其子郑经、其孙郑克塽保持其割据局面,海峡两岸的对峙,阻碍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当时,在全国统一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情况下,郑氏集团想“复明”实际上已是不可能。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任何“反清复明”的名义所进行的活动是不实际的,这种分裂、对峙的局面已经不适时宜,只能日益成为全国统一的障碍。统一台湾,是正义、进步之举措。一些有爱国之心的士人,都会顺应时代潮流,支持康熙帝统一台湾决策。而康熙帝统一台湾后,即于次年开海禁,这一政策措施,有利于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和发展,有利于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起,台湾商人开始向福建、广东等地输出粮食,向宁波、苏州、上海、天津、盛京等地输出蔗糖。
康熙中期前后,清廷的文化政策也有调整。康熙帝大力提倡汉族的传统文化,崇儒重道,孜孜于圣贤之学,朝野上下,乃至思想文化界纷纷仿效。为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康熙帝于康熙十三年(1673年)起使用怀柔政策,以科举考试办法,网罗江南的知识分子,还以“特种”政策,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博学鸿儒科”,以罗致江南汉族知识分子,其中“名儒”朱彝尊、汤斌、毛奇龄等,分别授以编修、检讨等官职。康熙十八年修明史,开局于内东华门外。在此背景下,明史监修徐元文,邀万斯同和万言北上修史。
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富有良知、爱国之心的知识分子必定会与时俱进,顺乎历史潮流,希望祖国繁荣富强,融入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之中,从传承中华文化出发,支持康熙帝文化活动。曾经持节不仕的一些明遗民开始转变其对清廷的原来看法,参加了清廷组织的一些文化活动,诸如朱彝尊、毛奇龄、黄宗羲、万斯同。比如,浙东的著名学者黄宗羲、万斯同对清廷的态度有所改变,万斯同以“布衣”参与修明史。黄宗羲云:“诏修明史,总裁令其以白衣领事,见之者无不咨其博给。尝补《二十一史表》五十四卷,朝士奇之,欲与刊行,诚不朽之盛事也。”黄宗羲对清廷修明史是赞同的,他虽拒绝朝廷诏聘,不入史局,但也采取灵活方式,在行动上表现出对清廷修史举措的理解与支持,把其父黄尊素所著的明朝《大事记》、《时略》和他自己所作的《三史钞》、《续时略》以作修史之用。黄宗羲还肯定危素修《元史》。危素为元遗民,元亡后,原打算以身殉国,僧大梓劝阻危素要忍辱负重,编修《元史》。黄宗羲为此说:“元之亡也,危素趋赴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黄宗羲肯定危素的做法以道出其内心深处的想法。并以此支持万斯同修明史。“及明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梁启超十分理解黄氏的想法。他说:“前明遗献,大率皆惓惓于国史,梨洲这条话,足见其感慨之深。他虽不应史馆之聘,然馆员都是他的后学,每有疑难问题,都是咨询他取决。”黄炳垕在《黄梨洲先生年谱》中亦说:“公长于史学,尝欲重修《宋史》,而未就。有《丛目补遗》三卷,又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故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上述事例表明,康熙开《明史》馆是成功的。梁启超说:“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只得勉强将就了。”
作为江南士人,沈光文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他体验了明亡的痛苦和悲哀,于是怀念故国故君,他的诗作中不少是思念故国的,带有强烈的思明情怀。明末遗民常以月为明之半壁江山,以“思月”、“听月”为思明的象征。比如,沈光文的《望月》、《中秋夜坐》等。还有一些是直接怀念祖国的,他的《葛衣吟》就表达这种情感:“岁月复相从,中原起战烽,难违昔日志,未能一时踪。故国山河在,他乡幽恨重,葛衣宁最弃,有逊鲁家佣。”沈光文服明衣冠,行明礼仪,都表明对故国的思念。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都具有所谓爱国和捍卫传统文明的气节。
但从康熙中期起,随着台湾复归,国家统一的进一步巩固和康熙帝的怀柔政策实施及文化政策的调整,作为遗民故老的沈光文,他的爱国情感内涵有所变化。面对现实,他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毅然放弃传统的对“一家一姓”的愚忠原则,对清廷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支持康熙的统一台湾等政策。不仅不反对同道出仕为官,而且对一些清代官吏保持良好关系,和施琅、姚启圣等人有所交往,与诸罗县令季麒光、台湾镇标左营济南韩有琦等诗人有所唱和。他曾给季麒光较高评价。说他奉调赴台任诸罗县令后“往来筹划,日无停晷”,“凡民间利弊有所指划,不为强力者少屈,以一宰而综三邑之烦赜,条议详明,为台湾定亿万年之规划”。为此,沈光文以季麒光为“海外知己”。并对康熙帝统一台湾更有所认识,因此称康熙帝为“圣天子声灵赫濯”,使“岛上效吴越之归诚,使从前未通之疆域,悉入版图,设立郡县”。自台归入版图后,沈光文除肯定了康熙统一台湾的业绩,所写文章也用“康熙”年号,这与黄宗羲有相似之处。在《东吟社序》最后,沈光文题启是“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岁、梅月、甬上流寓台湾野老沈光文斯庵氏题,时年七十有四”。康熙二十四年,即公历1685年。他的《题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诗文序》中,其题启为“康熙丁卯孟夏望日,甬上年家教弟沈光文题,时年七十有六也。”康熙丁卯为康熙二十六年,即公历1687年。用康熙的年号,表明沈光文承认清统治的合法性。这些都说明沈光文是顺乎历史潮流的。
对于沈光文晚年的所作所为,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考虑,不应该把是否支持新朝作为裁决是非的依据,应该看其是否顺乎历史潮流,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否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沈光文在早期对清廷持反抗态度,直到晚年,在不仕前提下对朝廷采取了灵活的姿态,他对康熙帝统一台湾加以肯定,参与创办“东吟诗社”和台湾的文化建设,不但不能对他抛弃原有的立场加以指责,而且应该肯定其顺应历史发展,融入祖国大家庭的行为。潘先生说沈光文“投诚清朝”,是“半路投清的变节遗民”,这种说法是不足取的,也违背历史事实。如果因此而对沈光文加以否定,那么,当时江南汉族知识分子都应该被否定。黄宗羲、万斯同支持清廷的《明史》编纂难道是“晚节有疵”?这似乎是一种苛求。既然黄宗羲、万斯同对清廷的修《明史》的支持能得到理解,为什么对沈光文支持康熙统一台湾,与诸罗县令季麒光等清朝官吏创办“东吟社”就要苛求?笔者认为,沈光文经历反清复明到康熙帝的政绩和清政府执政的合法性认定和支持,这绝不是“投诚清朝”,是“半路投清的变节遗民”,而恰恰是沈光文是面对变化了的实际所作出的明智与正确的选择,是顺乎历史潮流,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这一点,可与潘先生对待绍兴籍的姚启圣的平台及其事奉“新朝”的认识相比较。同样是事奉“新朝”,但潘先生认为,姚启圣结束两岸对峙,有利于造福民生,实现国家在文化教育上的大统一,应该“大书特书”。潘先生还认为,郑成功及其后裔在台湾的统治,只是个“割据的分裂的地方政权”。其理由是:其时,已经完成了明清易代的转变,完成了明代万历以后,女真贵族的汉化过程,从关外“野蛮”的“异族”转变为一个相当“正常”的中原大一统政权。潘先生还从地理正统观和道德正统观的视角出发,认为“三藩之乱”前后,清王朝“已成为中国正统所在,成为中华文化的合法继承者和当代象征”。那些曾经持节不仕的明代遗民,诸如朱彝尊、陈维崧、屈大均、顾炎武等,纷纷放弃当初的立场。这些都“反映了清廷正统的地位的被接受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和人们所向”。正因为如此,潘承玉先生说:“在民族矛盾已经不再成为最迫切的社会问题的时代,明郑势力以反抗民族压迫为借口继续存在,使两岸人民继续‘不遑宁处’,这种分裂对峙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合时宜。姚启圣顺历史适时地结束了这一局面,也帮助台湾和中华文化母体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团聚。”笔者认为,潘先生这一立论原则,应该同样适用于沈光文,而不能徇私偏曲而随意割裂。
既然清朝在当时是“中国正统所在,成为中华文化的合法继承者和当代象征”,姚启圣事奉“新朝”是合符情理的事,他为清廷平定台湾,结束两岸对峙局面是“顺应历史”,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那么沈光文在晚年对清廷的支持,歌颂康熙帝平定台湾是“圣主”,用清代的年号,结交施琅、姚启圣、季麒光等清廷官吏,为何却“不适合时宜”?如果说沈光文是“变质遗民”,那么,与他处在同一社会背景,且其行为取向极为相似的姚启圣又算什么呢?潘先生用双重的标准来看待同一时代的历史人物,这决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做法。以历史的态度考察人物,应将历史的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以客观事实作为其依据,客观地、具体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给予功过评述,切不能主观臆断,进行无端的指责和贬低。
三、肯定沈光文地位,是“造神”还是符合实际?
沈光文在台30余年,传播中华文化富有业绩。他播下爱国精神种子,推行大陆教育制度,进行汉语教育,给台湾留下了一批汉文文献,被推崇为“海东文献初祖”,并以杰出才艺、参与首创诗社,成为台湾文学始祖。对于他在台湾系统传播中华文化和对台湾文化建设开拓性的贡献,自康熙以来,一直得到肯定。潘承玉教授也曾在其论文中,也认为沈光文“给台湾留下了第一批汉文文献”,“数十年实际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是第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将中华文化播到底层原住民者”,由于他的“雄于词赋”的杰出才艺,而“成为台湾文学的始祖”,为“蛮荒的台湾带来中国文学的曙光和芬香”,是“传播中华文化事业取得了台岛第一人的成就”。当时,潘先生曾给沈光文戴上一顶顶桂冠。但时隔二年却把沈光文说成“变节遗民”、“卑卑无足道的人物”。并认为把沈光文推许为“中华文化在台湾的第一个播种者”、“台湾孔子”,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而且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是由于“造神运动”,除“学风不够严谨”外,其另外原因是“同乡情节与政治关怀”。笔者对此不甘苟同。
对于沈光文在台湾文化建设的业绩,许多文章都有阐述,潘先生在他的《越地三哲与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中也有记述。其主要论点,上面已有引用。这些都是客观事实。由于沈光文在台湾文化建设中的贡献,获得了人们的赞扬和讴歌。事实表明,这一举动是符合实际的,并不是什么“造神”。其实,说沈光文与郑成功“同垂千古”,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种子散播在台湾岛上第一人”、“台湾文化的启明导师”、“台湾孔子”,见仁见智,是学术上的问题,或者是民间的说法。正像潘先生说沈光文是“卑卑无足道的人物”、“变节遗民”一样,这也是他的自由。奇怪的是潘先生在二年左右时间内,在同样材料的基础上又没有新的材料占有,更无令人信服的分析,竟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提出南辕北辙的观点,使人感到纳闷:这究竟是为什么?
提出沈光文是“现代孔子”的是台南善化镇(古为加溜湾社)民。他们的目的是肯定沈光文在善化教育业绩,是为了纪念,因为沈光文长期在善化从事教育,造福于善化民众。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陈炎生就提到:“你听过‘台湾孔子’的故事吗?明末遗臣沈光文在荷兰据台时期飘海来台,历经荷兰、明郑及满清三个时期,也曾因作诗写赋得罪郑经而不得不隐性埋名在善化镇教导生蕃汉文,这位在连横所著《台湾通史》书中有台湾文献鼻祖的文人的文人个性,也将他升格为神。”“在善化百年老庙庆安宫的后殿,沈光文也被善化镇民尊奉为‘台湾孔子’及文神,每年进入考试季节,总有大批善化子弟将准考证影本摆放在其神像前膜拜,祈望庇佑金榜题名”。为纪念这位伟人,因此,每逢中秋节,善化镇民总以具有乡土风味的“牛车之旅”、沈公诗词朗诵及征文比赛等形式纪念这位“台湾孔子”,就是因为沈光文“后半生与善化结缘,因此善化镇为纪念他,将他去世地点附近的一条道路为光文路,也设有光文里及光文桥”。明确指出善化民众对沈光文神格化的认识应该“见仁见智”。他认为“沈光文升格为神是否适当也见仁见智,尤其台南市延平郡王祠也供奉太仆寺卿沈光文的牌位,因此,沈公神格化仅是供后人追思崇拜而已。”这些事实表明,提出“台湾孔子”观点的是台南善化民众的民间行为,潘先生无须吹毛求疵,严苛推究。
潘先生还认为,对沈光文的“无限神化”,其主要原因是“同乡情节”与“政治关系”。他说:“考察沈光文神话建构的不同历史阶段,我们会发现,同乡情节和政治关怀确是其中贯穿始终的两大因素;正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虚美乡贤和满足政治需要的双重作用中,或双管齐下,或合二而一,沈光文‘台湾孔子’的神话才被建构而成。”潘先生的说法不完全对。我们试作分析。
最早推崇沈光文的不是宁波同乡,而是他的好友季麒光。季麒光,字圣昭,江苏无锡人,康熙十五年进士。康熙二十三年,台湾设立1府3县,隶福建省,季麒光任诸罗县令,与沈光文为“海外知己”,他的著作《蓉洲诗文稿》中诗,与沈光文“倡和过半”。作为沈光文好友季麒光十分了解沈光文在台湾文化建设中的贡献,他在《跋沈斯庵杂记诗》中,把沈光文寓台湾,比作杜甫去巴蜀,柳宗元谪岭南,并且说:“从来台湾无人也,斯庵来而始有人矣;台湾无文也,斯庵来而又始有文矣。”其中可能有些过誉之词,但从中可以看出沈光文在当时台湾文坛、诗坛的地位以及沈光文在台湾文化建设中的贡献。
对于沈光文业绩加以推崇的还有邓传安、连横等人,他们也不是宁波乡贤。邓传宗为江西浮梁人,曾任鹿仔港(今属彰化)同知,道光八年升任台湾知府,动员民众历经四年建成书院,以“文开”为名。他在《新建鹿港文开书院记》中云:“传安前以沈太仆表德名书院,已为从祀朱子权舆;况宜卒葬俱在台,子孙又家于台,今虽未见《诗庵诗集》,而读府志所载诸诗文,概然慕焉”。连横在他《台湾通史》中亦云:“光文居台三十余年,自荷兰以至郑氏盛衰,皆目击其事。前此寓公著述,多佚于兵火,惟光文独保天年,以传斯世,海东文献,推为初祖。”邓传安、连横都不是宁波同乡,他们同样给沈光文文化建设成就、地位给予较高评价,怎么能说是同乡“造神”呢?
至于说到“同乡情节”,推崇沈光文的成就和业绩,并无不可。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来赐予浙江的宝贵财物,也是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近年来,浙江及全省各地,都在搞文化研究工程,弘扬浙江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一个重大项目是“名人研究”,比如,“浙江名商研究”。难道研究、推崇浙江的历史人物也是在“造神”?
宁波、绍兴同样如此。这两个城市是我国首批被命名为历史名城,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名人。正因为如此,宁波文化工程中就有“历史名人研究”项目,沈光文也在其中。宁波乡贤历来重视对沈光文的研究和资料搜集。清乾隆年间,全祖望就托人到台搜集沈光文的诗27首,编入《续甬上耆旧诗》卷十五《从亡诸公》之二中。并写《沈太仆传》和《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诗集序》。在《沈太仆传》中赞扬沈光文“海东文献,推为初祖”。上世纪50年代后,宁波旅台同乡会十分重视对沈光文的研究。台北宁波同乡会理事王善卿于1953年发表《同乡旅台之鼻祖——斯庵先生传略》。台北宁波同乡会在广泛搜集沈光文事迹和遗著的基础上,编写了《台湾文献初祖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于1977年由台北宁波同乡月刊社出版。在宁波同乡会关心下,经过地方人士热心奔波,于1979年建立了沈光文纪念碑。自90年代起,台北宁波同乡会及沈光文后裔到故乡宁波寻根。宁波当地也掀起研究沈光文热潮,1992年还召开了沈光文诞辰3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了《台湾文化初祖沈光文》、《开发台湾、名垂青史——纪念沈光文诞辰380周年》、《台湾文学拓荒者沈光文》等文章。宁波乡贤研究沈光文,不但是肯定其台湾文化建设中贡献,更重要的是弘扬浙东的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宁波城市品质。这怎么能说是把沈光文“无限神格化”,是“造神运动”呢?对此,作为学人应该有宽阔的胸怀和视野,要以宽松、宽容的态度,来理解和对待历史人物。
绍兴是具有2500年历史的历史名城。自古以来,名人辈出,名流荟萃。为提高绍兴的城市品位,绍兴多次召开越文化学术研讨会,对绍兴城市和绍兴名人进行研究,诸如陆游、章学诚、蔡元培研究等,这不能当作“造神”吧?也因此,潘承玉先生身处绍兴,开展绍兴名人研究,高推绍兴籍人士如姚启圣,这也无足为怪。姚启圣,字熙止,号忧庵,明清间绍兴会稽马山姚家棣人,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十三岁中秀才,后归清,于康熙十年,晋福建总督。康熙二十年,郑克塽继位,姚上疏以为收复台湾时不可失,荐施琅为水师提督平台。潘先生认为,“文武双全”的姚启圣在清朝收复台湾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更认为:“康熙皇帝和施琅,前者是决策者,后者是这一军事行动的直接指挥者。”但是“姚启圣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他是亘立他们二人之后、之间的一个人物,是清朝收复台湾的提倡者、策划准备者和两位主要军事统帅之一,是台湾与中华文化母体首次正式团聚的设计师。”姚启圣“促成台湾归于中原大一统政权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某种程度上比郑成功收复台湾还重要。”潘先生以为,姚启圣的作用远远超过郑成功和康熙帝,这就把姚启圣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用他自己的原则来衡量,这岂非也成了“造神”?
潘先生还认为,对沈光文的“政治关怀”是导致沈光文“无限神格化”另一个原因。他说:“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而言,与迁台国民党政府高层多为浙江人,甚至最高领导人为沈光文宁波同乡有关”。这一点,需要具体分析。
所谓“政治关怀”,应从季麒光说起。清初的季麒光对沈光文的评述,是鉴于沈光文在台湾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或者是两人间的友情;同样,作为地方官吏,这也是清统治者的执政需要。邀请沈光文参与清初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活动,这是季麒光执行康熙帝的文化政策,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同样,20世纪50年代后所出现的研究沈光文,也与当时实际情况有关。
历史记载,1894年的清廷甲午战争失败和次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祖国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使台湾人民受到剥削、压迫和凌辱长达半个世纪。1945年,台湾重归于中国主权的管辖下,但光复的台湾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战后的台湾经济文化必须进行重建。“在文化上,一方面对殖民主义文化进行扫荡、摒除,一方面则着手恢复和重建中华传统文化。”1945年11月18日,台湾省籍知识分子游弥坚、许乃昌、杨云萍等成立“台湾文化协进会”,其目的是“铲除殖民地统治所遗留下来的遗毒,创造民主的台湾新文化”。开展促进国语运动,宣传祖国文化,努力肃清日本殖民文化的残余。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为进一步清除日本殖民者的奴化教育影响,揭穿少数搞台湾独立的民族败类的阴谋,台湾当局于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进行所谓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70年代初达到高潮,为保存传播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做了一些工作,使台湾出现了重视传统、回归传统的趋势。比如,请托一批爱国学者,以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宪文教授为首,组织了台湾研究学者、专家,自1957年至1972年历经15年时间,先后有1000余名专家参与了编辑《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深刻揭示台湾历史发展变迁,特别是海峡两岸中华儿女的血缘关系和不可分割的文化渊源关系。丛刊编者杨亮功曾在“跋语”中说:“从本刊整个资料中,更可看出台湾对于祖国在民族历史上、文化上、政治上实有不可分割之关系。”另一位主要编纂者吴幅员也说:“台湾之于大陆,不论从地缘以至血缘,都属一体,虽先后遭受异族侵凌的影响,而这种‘血浓于水’的相互关系,永难磨。”推崇台湾文献的初祖沈光文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沈光文作为开发台湾的早期人物之一,且在台湾留下了诗文,对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及对台湾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中”必定会有一定的地位。沈光文传等5篇被收入《台湾文献丛刊》第8辑、第162种之中。这一时期,台湾的一些学者也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如台大教授杨云萍1954年发表了《台湾的寓贤沈光文》,另一位台大教授盛成也在1960年至1961年先后发表《沈光文自荐诗文中自述》、《史乘与方志中的沈光文资料》、《沈光文之家学与师传》和《沈光文公年表及明清时代有关史实》等。通过对沈光文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的记述,这正好证明海峡两岸中华儿女的血缘关系和不可分割的文化渊源关系。这就表明,对沈光文的文化成就的宣传,是符合当时保存、传播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并不是当时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关怀”,更不是“最高领导人为沈光文同乡相关”。
潘承玉先生还说:“当我们高唱沈光文是‘台湾文化的启明导师’,是‘台湾孔子’,以证明台湾与中华文化的紧密关系时,有没有想到,这实际上极大地缩短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史,从而实际上极大割裂了台湾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呢?”这可能是潘先生的善意推测。沈光文在台湾文化建设中的贡献对于社会发展起过某种进步作用,正好说明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正是体现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史,其个人作用绝对不能否认。其实,我们在讲沈光文的台湾文化建设中作用时,也并没有否定其他人在文化建设上贡献。至于有学者提出沈光文是“台湾文化启明导师”和民间所说的“台湾孔子”,这是个人的看法,也没有必要过于较劲。
[注释]
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汇编》第642页,台南县立文化中心出版,1998年。(民国)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九《列传·诸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记我与潘懋元先生交往的点滴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