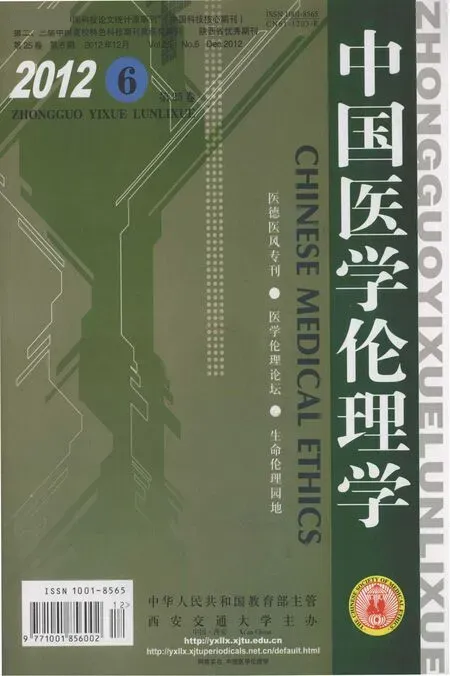无随潮浪违心语——杜治政教授访谈录
采访:李恩昌 《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编辑部
李恩昌:在庆祝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30周年的时候,我学习了您的有关文章、专著,特别是《医学伦理学探新》一书。它虽是一本论文集,但自成体系,较完整的反映了您从开始学术研究到70岁左右时的学术思想。您在医疗市场化的大潮中,发出的那些呼唤道德,呼唤医学伦理学的声音,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我在阅读时,其心情不仅仅是感动,还有一种景仰。是什么精神鼓励着您,是什么信念支持着您发出那些警世之言?非常高兴能借这次《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医学伦理学卷》编写会的机会采访您。
杜治政:市场机制问题是1985年或者1986年提出的。当时的卫生部钱信忠部长讲到卫生事业越办越穷,越办越破,医务人员生活很清苦。当时正好企业搞改革,引入市场机制,收益跟个人挂钩,所以钱信忠部长提出可以将企业的机制引进来。后来卫生部发了几个文件,其目的是调动医务人员和医院的积极性。当时我们看到一个材料,是天津市和平医院,他们这样做了后,医院的收入一下子就翻了一两番,我当时有些困惑不解:市场机制能够引入到卫生部门吗?随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出发点是:医药卫生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是救死扶伤的,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如果医疗市场化,老百姓看病要拿钱去买,看病变成了商品交换的行为,医院要多少钱你就得给多少线。那就和我们传统的救死扶伤的精神相违背。病人要是没有钱,医生给不给看病?他要是钱不够你给不给他看病?他快要死了,但没有钱,你给不给他看病?当时我凭直觉感觉可能不妥,对医疗卫生商业化要画个问号。后来我就查了一些书,学了点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讲,资本和商品是有区别的。简单的商品生产,卖是为了买,比如说我今年生产了一批粮食,但是我没有棉花,没有布,没有衣服,没有盐,我出卖这些粮食是为了换取生活必需品,它的落脚点还是归到这上面去了。那么我们医疗卫生如果市场化,就意味着把医疗卫生作为商品卖出去,卖给病人这个商品,收回货币,然后又通过药品、手术、检查又卖给病人。因为是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和医生的收入挂钩,似乎像联产承包。所以我就想到,医疗卫生是不是商品呢?商品有二重性,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从群众来看,教育、文化属于公益事业,医疗,或者是准确一点说,基本医疗也是一种公益性事业。因为医院的产生不像房地产开发,造出房子是为了卖。医院是从中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十字军东征,流浪人没人管,教会把他们收容起来,安置在救灾所,慢慢发展到17、18世纪的医院,始终是坚持为病人服务的宗旨。我们今天的医院,要把它变成商品,好像有点不对。后来我写了篇文章,从医务劳动的性质、医疗卫生的根本性质,说医疗卫生服务不能商品化。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医疗卫生就是要引进市场机制,而且应该彻底地、完全地引进,只有这样才能够繁荣医疗卫生服务。这些文章我们也登了,随后《医学与哲学》搞了个专栏讨论:医疗卫生能引进市场机制吗?前后发了将近有十八、九篇文章。当时我没有答复,1991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一些同志的不同意见,同时作了一些修正,就是某些特殊服务可以考虑引进市场机制,而且引进有一个限度。具体的、最基本的老百姓看病的这一部分不能作为商品交换,这是涉及老百姓的生命攸关的大事;同时,医疗卫生服务也没办法衡量它的价值,救了一条命,用多少钱衡量合适呢?比如一个急性阑尾炎,不治就会死亡,治了的话就救回来了。那你说付给多少钱、卖多少钱?这个价没办法定。它不像马克思说的由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衡量它的价值。这个阑尾炎,你要他一万块钱他也没有话说,你不救他他会死。你要他一千块钱,也交代得过去。按照群众的话来说,他就算没有钱你也应该给他治,像这样的基本服务就应该这样。但是那些高级服务,比如住房要大一点,要一个人一个房间,要药品好一点,你愿意拿这个钱是可以的。如果对这些基本医疗,坚持不给钱就不给看病,就会有一部分病人被挡在医院的外面,就必然出现医院见死不救的情况。一个医院把病人挡在外面不管其死活,这叫医院吗?不会挨骂吗?革命人道主义到哪儿去了?邱仁宗先生的想法跟我一样,也不赞成这种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香港的一个学术机构合编了一本书,我的这两篇文章都收进去了。在我任医学伦理学会主任委员的时候,1988年在西安开会的时候已经涉及这个问题,后来在成都,专门搞了一个卫生改革讨论会,编了一本书,其中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后来在曲阜开会,更是专门讨论卫生部门能不能市场化运营的问题,大多数学者不同意,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医疗是可以市场化的。后来问题多了,市场化经营以后,医院越办越破的情况有所改变,硬件建设好了,但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个时候我的信心就更充足了,医院市场运营恐怕是不行的。后来学了点国外经济学理论,将产品区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非公共产品,非公共产品是市场那一部分。基本卫生服务、初级卫生保健这些属于基本公共产品,还有一些准公共产品,介于二者之间,不一定市场化。至于特需服务,那是可以的;但是特需服务在医疗卫生服务中是少数。现在看来,医院也不能完全拒绝市场,特别是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费用越来越大,要装备这样一个医院,没有巨额的资金是不行的,这个巨额资金完全靠国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主张可以适当地、有节制地在医院引入市场机制,不应该绝对拒绝市场,但是也不是绝对地全盘市场化。有一些同志说目前卫生部门出现的问题,是市场化不够所致,如果彻底市场化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市场是唯利是图的,这是市场的本性。你让他市场化,就必然唯利是图,这是资本的一个根本特性。不只是卫生部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也认识到,资本要有国家的干预,要有国家调节。我们回顾历史,1945年以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国家调节经济,凯恩斯主义也出现了,但没多久,经济上不去,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私有化,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否定了凯恩斯主义,开始搞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搞了一、二十年,爆发了经济危机,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还是要有控制,要有调节,不能没有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还要进行国家干预,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医院,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还能彻底资本化?有人认为,彻底资本化可以自由竞争,竞争之后价格会下降;但现实与此相反,因为医疗服务业有个很大的特点:他不是说你有什么高级设备就能竞争过对手。没有高级的科学技术人才,你有再好的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看一个片子,照一个CT,你要有高明的放射科医生才能判断出来,不是说照出来就完了。医疗卫生技术服务始终是和高级的医学人才绑在一块儿的。它不像制造电视机,谁家的清晰,老百姓就买谁家的,竞争之后价格就会下降。医疗服务的价格是降不下来的,这是个根本特点。比如说我们大连市,现在有几十家医院,都买了核磁共振,而且是最新的,但是他们没有人才啊。大连医科大学的两家医院有这样的人才,能降下来吗?你爱来不来,价格就是一千块,哪里有二百块的你去哪里。如果我是一个病人的话,我还得到收一千块的地方来。设备先进必须有会运用这个设备的人才行。不要以为医疗卫生服务充分的市场化,医疗卫生服务价格就能降下来。美国的医疗,市场开放度是很大的,但是美国医疗价格是最贵的。完全锁死医疗卫生市场化也不可能,在某些方面,需要用市场手段弥补它的不足。比如某些特殊人群需要,这一部分人的需求可以特殊点,可以高价点。但是基本医疗,广大群众的这一块不能这么搞。我始终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不能完全走市场化的道路,它没有什么太复杂的理论,因为人有生存的权利,不像看电视,没有钱就可以不看。但是生病了就要治疗,不能因为没有钱就不给治。现在国家已经明确初级基本医疗卫生、基本医疗、公共卫生这一块由国家负责。
李恩昌:在庆祝医学伦理学30周年的时候,我注意到,您重提了病人第一原则,讲到了普世价值和特殊性等问题,想请您结合新资料和新形势,就这些医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再讲一下。
杜治政:你在这次会上的发言,讲要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原则”,我很赞成。1981年,全国首届医学道德学术会议,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基本原则,后来的几次会议仍然坚持这一观点。现在看来,这种认识还是对的,我们还是应该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但现实的医务人员利益也要考虑,没有他们的积极性是不行的。所以,在考虑病人利益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医务人员的利益。后来,我们学了西方生命伦理学的四项原则。这些年我多次反思,医患纠纷如此之多,和我们医学伦理学工作有没有关系?当然,不能说医学伦理学搞得好,就不会有医患关系的恶化,我们没那么大的本领。但和这些年我们忽视了这个基本原则有没有关系?我们写文章、给学生讲课,只谈自主、公正,而不大谈或不谈病人利益第一。须知,一个谋求个人利益的医生,也是能够履行这四项原则的,一个将医院作为资本经营的医院也是能够接受这四项原则的,但是要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在这次《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医学伦理学卷》编写中,我提议在四项原则前加上这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你看美国和欧洲搞的那个《医师宣言》,第一条就是病人利益放在首位,第二条是自主,第三条是公正。它是很清楚的,这三条是基本原则,下面有十条,保密、好好学习技术等,而且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无误的解释。《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登的那个《宣言》(《医师宣言》),我放在桌子上,是经常要看,我始终认为是好的。它后面那段和前面那段解释得很好。前些日子,一些学者写文章,主张加强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建设,我以为这是对的,我们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医学伦理领域的理论建树确实不多。但我以为,理论和实践比较起来,似乎实践更重要。随后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医学伦理学魂归何处》。我说的魂归何处,就是认为医学伦理学的落脚点应当是医疗实践,是病房,是卫生保健政策,是医学的宗旨。实践上升到理论,最终还是要为实践服务,还是要落脚到医学的宗旨;第二篇就是《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原则不能变》。我们的医院常常将“医院工作要以病人为中心”的标语挂在显眼的位置,但没有看到“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标语。我有一次问某院长:能不能将“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标语挂出来,院长摇头。的确,病人利益第一位对医院来说,是一个风口浪尖的问题,这是一条红线,院长们既不敢否定它,也不敢亮出来,因为实际上现在不是病人利益第一,而是以医院利益第一。现在的医院实行科室承包,你这个科今年任务量是一百万,另一科室是两百万,然后一一落到医生的头上。这样,医院和医生都得围着这个指标转,而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从病人身上下工夫,比如开大处方、扩大手术指征、开高精尖的贵药,这哪能实现病人利益第一呢?坚持病人利益第一,比讲自主、公正要难得多,也重要得多。我觉得我们的医学伦理学应该加强这方面的问题。医学伦理学的内容,无非是四个方面,即职业道德、技术道德、研究道德和政策体制道德。职业道德,也就是职业操守,是医学伦理学最基础的部分,可惜这些年我们不大讲了。其实,西方对四项原则持批评态度并非少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不是能说医学伦理学有四项原则就够了。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仍是很重要的。孔子也不反对“取”,但他认为应“义然后取”,所以,要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然后再考虑医生个人的利益。美国经济学家罗德曼也提出,不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不知道个人利益的重要,但是不读《道德情操论》,就不知道为他人牟利就是最好的个人利益,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吃小亏占大便宜”。为他人服务就是最好的为个人的服务。这和孔夫子讲的“义然后取”差不多。你只有让他人满意了,你的利益才能心安理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伦理学的一个宗旨。当然,不一定我们讲了这个问题,人家就不开大处方,不搞过度医疗,不收红包了,但这是面旗帜,旗帜在,没有倒,就有方向,医院、医务人员就不能不考虑。而且,病人利益和医生利益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只要你把服务做得非常好,患者满意,差错少发生,即使多收点钱,病人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如果你做的又不好,语言又生硬,又要那么多钱,大家肯定就有意见了。有一次,我们召开一个座谈会,关于医生职业精神调查,来了十几个医生,一肚子牢骚,对自己的地位一肚子不满意。医生也有他们的苦衷,他们很辛苦,他们现在的工资报酬是比较低的,有些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学会、医院管理协会都统计有多少医院被打和砸,但是有谁统计过有多少不该死的病人死了呢?有谁统计过有多少病人花了冤枉钱?没有人统计。我觉得,病人的苦衷,远远大于医方。我认识一个病人,是我的邻居,他的母亲,早上我遇见了,问她去哪儿,她说头疼,去医院看看。医院要她做脑动脉造影,出现严重的药物反应,不到一小时,死在医院了。因为放射科和急诊科隔得很远,走廊又拥挤不堪,需要走十几分钟,人送到急诊科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她的儿子跟我讲了一下情景,认为可能是医院的问题。我说那肯定是医院的问题,这种有风险的检查,他们应该有准备。我问是不是让医院赔偿。他说算了吧,妈妈已经去世,追究他们的责任也不过是赔点钱。病人跟医院打官司,没有几个赢的,就算赢了也要脱层皮。所以总的来讲,患者还是弱势的一方,患者和医生相比,医生还是比较强势的,这是第一。第二,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认为医疗机构有问题,我们做了调查,百分之三十几的患者对医院非常满意,百分之五十几的患者基本满意,两个加起来是86%。86%的病人,包括大医院、县医院、农村医院、城市医院。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对医院还是满意的,像医生被病人杀害的事情只是极端事件,还是很少的。当然应该研究预防。我觉得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把“病人利益第一”这个问题处理好。当今社会比较浮躁,各种矛盾交集,很多人一遇到问题就一触即发,这也是医闹产生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医疗部门要冷静地对待,不能说配备警棍,钟南山院士首先反对这样,这样是不行的。病人利益原则对于我们伦理学来说,永远不能丢,而且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原则,说明了医学是干什么的,是赚钱的还是为病人服务的。我讲的是病人的利益第一啊,没有说不要医院的利益,你可以第二、第三啊。过去的医生也不是不要钱,他也要吃饭,但是解放前的医生到家里看病,也不是马上给钱的,常是年终的时候一块儿给。看完病开完药,包括理发的,都是如此。《红楼梦》里的贾母看病,也是看完之后才给一点钱,大夫也没说少了或者多了。所以你提的问题,病人利益置于首位,我以为应当视为一种普世价值,这个没有国家、民族的区别。1997年我到休斯顿,和恩格尔哈特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他家里吃饭的时候,又谈起这个问题,他比较强调价值的多元性,都是道德异乡人,他提出了允许原则,认为没有多少普世价值,他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坚决否定者,他总是批评他。但是我看了斯密特——德国前总理写的一本书《全球化与道德》,他可能也是个学者,他有几章我觉得不错,他讲到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要大力提倡共同道德,普世道德,这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没有基础就无法和平共处。我在为一本书的序言中也讲了这个问题,后来科学院的《文化评论》通过张大庆教授,约我写篇文章,我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你们纪念医学伦理学研究30周年的会上,我也讲了这个问题。国际伦理学会的第三届主席DanielWikler,他和恩格尔哈特的观念不太一样,他对于多元和一元问题的观点,我还是赞同的,他认为多元只是在个别的情况下存在的,普世价值是在人们社会交往之间要共同遵守的东西,没有这个价值就没办法交往。作为伦理学,应该首先提倡普世价值,不宜首先提倡特殊性。这和文化、艺术似有不同,艺术是越特殊越好,越特殊越有风味,老是看一样的东西就没意思了。但是总的来讲,文化艺术也在趋同。比方说汉堡包、快餐店,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现在我们都接受了。特殊和普世有各自的活动领域,普世价值在人们的公共交往中存在,比如经商、教育等,必然要遵守共同的东西,不然就没办法达成共识。但是在某些不是很特殊的生活领域,比如少数群体,那特殊一点就特殊一点呗,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他接受普世的价值。所以,我以为伦理学还是要强调普世,尊重特殊,提倡普世价值。在家庭和自主性上,中国家族影响大,家庭亲情关系,这个是好的。我来自一个封建家庭,在现在看来,我是不喜欢那样的家庭的,家长制,一点都不尊重妇女,人情味很少。现在的家庭和过去的家庭不一样,家庭也要民主啊,家长制的家庭在现在也行不通。现在有些病人自主不了,因为经济、文化等各种原因;即使能自主,遇到一些重病,他也要听听家属的意见,这是对的,因为尊重家属的意见可以让他心里安稳一点。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朝着尊重自主这方面发展。总体趋势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家庭越来越小了,一个人一个账号,工资都汇到个人的口袋里面了,现在连结婚的时候婚前财产都要鉴定。有人提出要重视家庭的作用是对的,但是现在家庭的作用在减少,很难再绑在一起了。但是,家庭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重视家庭作用是对的。家庭是社会发展一个侧面的反映。当然,普世不能绝对化,各有各的用场。但趋势来看,由于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越多,民族在交融,文化在交流中取长补短,这种共识的层面可能越多。不受外界干预的群体的特殊性的地方会越来越小,恐怕这是个趋势。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西方和东方,我们不能绝对地说西方的东西不好,或者说东方的东西就是好。一切都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时代变化、生活实际也在变化,像达尔文进化论一样,会逐渐适应选择;哪些被接受,哪些被淘汰,不是由我们学者决定的,人们会按照实际社会生活和经济的发展,作出正确的选择的。某些事暂时没有被选择,但打几个转还是会回来的。不能因为这个东西是人家那边来的,我们就不采用。同样,现在我们在国外办孔子学院,国外人学习孔夫子思想。比如,日本某企业培训员工,还选择了51条论语,请研究论语的老师来上课。
李恩昌:在我从事社会医学、医学伦理学研究和编辑30多年工作中,您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前辈之一,我由学习中医到后来研究社会医学、医学伦理学是受了中医学“中知人事”的影响。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经于光远同志推荐发表在《医学与哲学》杂志1981年3期上。1981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医学辩证法研讨会议上,您和马文元老师特意找到我对我说:“你这条路走的对。”对我鼓舞很大。30多年来,您及您主持的杂志培养了一大批人,这些人今天正活跃在医学伦理学、医学辩证法的舞台上,成为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和我一样,想知道是什么把您从一个学医者引上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之路,其中一定有一些有趣的情节和事由?
杜治政: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主观想象的,现在年轻人可以自己设计自己未来,我们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的。那时是一切听组织安排,抗美援朝参军,我报的志愿是学坦克,因手的握力不够,没学成,被批准学医,上了两年课,又要我学习政治理论,回来以后,转了业,当了政治理论教员;还下乡两年,当农民,当了9个月的代理生产队长,后来回到城市,先到卫生局工作,要我办刊物,先是办《医师进修杂志》、《实用护理杂志》,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要我办《医学与哲学》,后又调我到大连市科协工作,同时还兼任大连理论医学研究所所长,继续办杂志。这些事情完全是偶然的,没有任何主观设计,都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那么,如何对待呢?我以为,任何事情、工作,只要认真去干,都是能干出趣味、干出成效的。任何工作都有发展空间,你可以去挖掘它。大跃进年代,学校也搞大跃进,当时大连医学院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方面有点名气,要写书,市委文教部把我与另一同志调去写序言,写如何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西医结合,写了几稿,总算完成了任务。1977年办杂志时,我写了一篇关于如何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医疗工作的文章,当时军代表的党委张书记看到了,说此文章重要,党委开会时还要我去念了一遍,说要好好研究,杂志要好好办。后来这篇文章被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会的一个刊物转载了,并向北京一些单位推荐这篇文章。筹划广州医学辩证讲习会时,把我叫去了,开了几次会,决定要办一个医学辩证法方面的刊物,几经酝酿,最后由于光远同志拍板,刊名就叫《医学与哲学》;彭瑞骢同志被推举为主编,我与邱仁宗同志被推举为副主编,在他们的支持下,这个刊物慢慢办起来了。开始几期,都是到北京讨论定稿的。这里还必须提到的是,这个杂志能够存在和发展,与大连市有关领导支持是分不开的。大连市卫生局的领导很支持,在编制、经费、人员、办公场所等方面,都是开绿灯,从来没有遇到困难;大连市委也很支持。当时的市委书记杜李,一位很好的长征老干部。他在临终前,他的秘书通知我,说杜书记想见你,我来到他床边,他说:我经常住医院,深感医生的思想方法很重要,你写的那本《护理学新论》我也翻了,你一定把那本《医学与哲学》杂志办好,多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也是为病人服务。他的话对我影响很大。这次谈话后第三天,他去世了,此事我始终没有忘。吊唁他时,我还写了一首诗:不惑年华赴港城,谆谆诲抚育英灵。无随潮浪违心语,只为人前作正人。病染沉疴日坐巡,蒙蒙垂念友人情。叮咛作句扬医哲,泪洒山前别故人。现在杂志由大连医科大学承办,我们过来后,学校的领导、各个部门也很支持。这种支持很重要,没有这种支持,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李恩昌:今年是您及邱仁宗教授、胡庆澧教授三位医学伦理界的前辈80大寿,我刊已发文祝贺,祝你们“三老”健康长寿。上世纪90年代,我曾以《一片冰心在玉壶》为题报道您的学术简况。您的不少有影响的文章都发表在我刊上,我代表杂志编辑部深致谢意。我们知道,是您三位与石大璞、张鸿铸、徐善兴、催华、李本富等一批前辈开拓了我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荒野之地,使之成为学科成群如百花绚丽的百花园。今天,我国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正在进行着一场接力赛,新人辈出。但他们要成为对社会犹如在航海中瞭望的前哨者,不但需要自己的坚守、执著和甘于寂寞,也需要像您这样的前辈的指导,请您根据自己成长经历,对中青年一代讲些提醒、勉励的话。
杜治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现在年轻的学者肯定能比我们做得好。《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这几年越办越好,这个对学科发展很重要。现在人文医学还比较困难,各方面的认识并未真正到位,这与当前经济利益第一的浪潮相关。转变需要时间,这就需要有耐性,我们不要灰心,因为当前医学的确需要伦理学;其次,我们要多和医生交朋友,多到病房走走,听听他们的查房,争取将我们的认识变成医生们的认识。因为我们不直接接触病人,不给病人看病,不开处方,不为患者做手术。我们只是二传手,将医学伦理学传给他们,通过他们施惠于病人。这方面工作我觉得少了一点;我们制定规则,但更多的是要让医生认识到这些,不是应付,而是发自内心的认识到。所以我在会上提到,医学人文要深入到临床实践中去,搭建与医学结合的平台。比如,我们到日本考察,发现日本很多伦理课是临床医生在讲,看到了他们的课程表。我以为像四项原则这些理论我们讲,医学技术实践中的伦理问题,最好由临床医生讲,我们可以帮着讨论。还有,在医学专业杂志里开辟人文的栏目;医学学术会议,也可以搞些人文论坛。要设法开创结合的平台,不要总是停留在人文学者这个圈子里,不要封闭在这个圈子里,所以伦理学要走出困境,打通这条渠道,我们就不是孤军作战了;再一个问题是,伦理学工作者要多研究实际问题,扎根实践。如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上,一个村有两三个肿瘤就没钱了,大家交钱积极性就不高。如何处理大病救治与大多数人保健的矛盾,就是现实的伦理学问题。这类问题多得很,如大型公立医院公益性如何回归,就是大课题;一些医院对特需医疗很有兴趣,如何看,也是伦理学问题;医院为了维持秩序,设置警务室,是好还是不大好,也是伦理学应当回答的问题。总之,我觉得,我们要多研究实际问题。现在写教科书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要多研究实际问题。
李恩昌:对您的采访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相信读过这个采访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您给杜李书记写的诗中有两句:“无随潮浪违心语,只为人前作正人。”我觉得这也是您自身人品和学术追求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