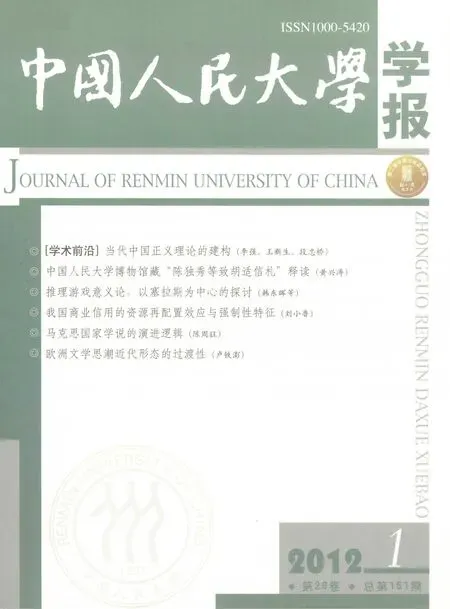中国近代神话传说研究与民族文化问题
高有鹏
以原始信仰为核心内容的神话,是一个民族最为古老的记忆,其流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神话的概念不断被述说,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这是学术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中国古代有没有 “神话”这个概念?到底是谁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
一、中国古代的 “神话”概念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是有 “神话”这个概念的,而且其体现的内容就是民族古老的历史这一特定含义,与今天的意义相同。神话的名称在明代社会之前曾经以 “神异”、 “神怪”等词汇被表现。“神话”的概念最早明确出现在明代汤显祖 《虞初志》卷八 《任氏传》中。在1890年之前,也已经有中国人在海外使用了这个概念,如陈季同的著述中就多次出现神话的概念,并且专门论述神话传说的 “史前 (史传)时代”。陈季同指出,“神话总是包含一些迷信的东西,但也很懂得在里面掺 进 一 些 智 慧”[1](P30);他 在 《中 国 人 自 画像》(1884年)“史前时代”一章论述了 “在民间想象中,此第一人力大无穷,双手各执太阳和月亮”[2](P80),以及伏羲、神农、黄帝等神话人物。科学研究的价值正在于不断走近真理,能够不断有所发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民间文学史料的发掘总是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努力,而每一种发现都充满艰辛。
中国近代社会的门户开放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逼迫下发生的,在学术思想与学术方式上,以社会进化思想为重要理论基础的人类学理论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人类学强调的注重历史文化遗留物的理论方法,极大地启发了我国近代社会学者对神话传说这一特殊话题的关注。
中国近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古史重建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而神话传说是传统历史构成观的起源,诸如三皇五帝的阐释,形成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文化体系的主体。而在论及神话这一概念的时候,许多学者都一再强调我国古代没有 “神话”这个概念。应该说,这正是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历史理解不够深入的表现。
关于 “虞初体”(《虞初志》以 “虞初”人名为文体)问题,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讨论。一般认为,虞初是西汉时期的洛阳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 “黄车使者”。他将 《周书》改写成 《周说》,人称 《虞初周说》。此 《周书》并非唐代令狐德棻所编 《周书》,而是 《逸周书》。曾有人说《逸周书》是因为孔子删定 《尚书》之后所剩材料,为 “周书”的逸篇,其原名 《周书》、《周史记》,其主要内容是周代历史文献汇编,分别记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周成王、周康王、周穆王、周厉王和周景王时期的历史,并且保存许多上古时期的历史传说内容。许慎著 《说文解字》时,才称之为 《逸周书》。可能是原文不容易懂,所以虞初把这些内容作了故事性较强的改写,即此 《虞初周说》。班固 《汉书·艺文志》录小说十五家中有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张衡 《西京赋》称 “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这九百篇 《虞初周说》早已亡佚,清代学者朱右曾考证,《山海经》、《文选》、《太平御览》等文献曾经引述 《周书》内容,实际上是 《虞初周说》一书的逸文,诸如 “天狗所止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十数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其光如电”,“穆王田,有黑鸟若鸠,翩飞而跱于衡,御者毙之以策马佚,不克止之,踬于乘,伤帝左股”,“岕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圆,神经光之所司也”等,当为 “稗官”所讲述的故事。由汉代的 《虞初周说》到明代的 《虞初志》,再到清代的 《虞初新志》,经过许多历史变迁。明代汤显祖 《虞初志》和 《续虞初志》、张潮 《虞初新志》、黄承增 《广虞初新志》用 “虞初”之名,就是讲述传说故事的意思。也有学者考证,汤显祖点校本 《虞初志》与今通行本 《虞初志》(诸家汇评本)以及汤氏的《续虞初志》不是一回事。[3]无论如何, “神话”一词见之于 《任氏传》末尾[4],这是一个事实。《虞初志》卷八存 《任氏传》、《蒋琛传》、《东阳夜怪录》、《白猿传》诸篇,各篇内容相同,所以此 “神话”作为神奇、奇异的故事的概括,内容上表现出对社会生活与自然世界的超越,与今天的神话含义相同,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任氏传》讲述了贫士郑六与狐精幻化的美女任氏相爱,任氏忠贞不渝,郑六携任氏赴外地就职时,任氏在途中为猎犬所害的故事。汤显祖此类论述甚多,如 “奇诞之极”(《裴沅传》评),“恍忽幽奇,自是神侠”(《贾人妻传》评), “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点校 〈虞初志〉序言》),“奇物足拓人胸臆,起人精神”(《月支使者传》评),“虎媒事奇,便觉青鸾彩凤语不堪染指”(《裴越客传》评),“此等传幽异可玩,小说家不易得者”(《刘景复传》评),“神僧巧算,思味幽玄”(《一行传》评),“咄咄怪事,使人读之闷叹”(《崔汾传》评),“真所谓弥天造谎,死中求活”(《松滋县士人传》评),“传甚奇谑而雅饬闲善,所谓弄戏谑者也”(《却要传》评),“亦复可喜可愕”(《吕生传》评)。所以,这个词在汤显祖笔下出现,便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可见, “神话”的概念并非在古代典籍中没有出现过。
二、中国近代民间文学理论体系中的“神话”概念与古史重建
从现代学术发端上讲,神话的旧题新说与神话学的出现属于梁启超的 “新史学”。梁启超较早使用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 “神话”这一概念,其古史重建的方式主要表现为神话传说的民俗学研究。
梁启超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逃往日本,在横滨创办 《新民丛报》,连载 “新史学”系列论著,其中有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及 “当希腊人文发达之始,其政治学术宗教卓然笼罩一世之概者,厥惟亚西里亚 (或译作亚述)、巴比仑、腓尼西亚诸国。沁密忒人 (今译闪族人——引者注),实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犹太教起于是,基督教起于是,回回教起于是。希腊古代之神话,其神名及其祭礼,无一不自亚西里亚、腓尼西亚而来”[5](P11)问题。他尤为重视神话传说中的洪水问题,其 《太古及三代载记》举 “伏羲神农间,所谓女娲氏积芦灰以止淫水”与 “鲧禹所治”等神话传说为例,论述 “洪水曾有三度,相距各数百年,每度祸皆甚烈”,称:“初民蒙昧,不能明斯理,则以其原因归诸神秘,固所当然。惟就其神话剖析比较之,亦可见彼我民族思想之渊源,从古即有差别。彼中类皆言末俗堕落,婴帝之怒,降罚以剿绝人类,我先民亦知畏天,然谓天威自有分际,一怒而尽歼含生之族,我国古来教宗,无此理想也,故不言干天怒而水发,乃言得天佑而水平……彼中纯视此等巨劫为出于一种不可抗力,绝非人事所能挽救,获全者惟归诸天幸。我则反是,其在邃古,所谓炼石补天积灰止水,言诚夸诞,然隐然示人类万能之理想焉。唐虞之朝,君臣孳孳,以治水为业,共工鲧禹,相继从事,前蹶后起,务底厥成,盖不甘屈服于自然,而常欲以人力抗制自然。我先民之特性,盖如是也。”[6](P19)他特别强调 “研究一切神话”的方法,详细论述道:“语言文字之后,发表思想的工具,最重要的是神话,由民间无意识中渐渐发生。某神话到某时代断绝了,到某时代,新的神话又发生。和神话相连的是礼俗。神话和礼俗合起来讲,系统的思想可以看得出来。欧洲方面,研究神话的很多,中国人对于神话有两种态度。一种把神话与历史合在一起,以致历史很不正确。一种因为神话扰乱历史真相,便加以排斥。前者不足责,后者若从历史着眼是对的,但不能完全排斥,应另换一方面,专门研究。最近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孟姜女的故事,成绩很好,但范围很狭窄,应该大规模的去研究一切神话。其在古代,可以年代分;在近代,可以地方分或以性质分。有种神话竟变成一种地方风俗,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此地的社会心理。”[7](P74)
梁启超的神话理论是其新民思想的一部分,如其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所述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其言 “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小说;“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8](P6)。其所说诸种 “惑”,就是社会风俗生活中的民间信仰,自然也包括那些蕴含其中的神话传说。同时,他在 《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中论及 “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与 “同其风俗”等民族 “特质”,称 “民族者,有同一言语风俗”[9](P71),其中涉及 “化俗”与民族主义等问题。其所论重点在于通过包括神话传说在内的风俗建设,新一国之民,即通过现代文化思想教育使国民精神与国民素质不断提高。梁启超的新民学说融入其神话学思想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1904年,夏曾佑的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出版,此为我国近世第一部史学专著。他也是从历史文化演进角度理解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如对盘古神话的考证,称 “今案盘古之名,古籍不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或盘古、盘瓠音近,盘瓠为南蛮之祖。(《后汉书·南蛮传》)此为南蛮自说其天地开辟之文,吾人误以为己有也。故南海独有盘古墓,桂林又有盘古祠。(任昉 《述异记》)不然,吾族古皇并在北方,何盘古独居南荒哉”。他提出 “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在社会历史进化中管窥伏羲、女娲、神农等神话时代作为 “传疑”与 “言古代则详于神话”的意义,论述道:“包牺之义,正为出渔猎社会,而进游牧社会之期。此为万国各族所必历,但为时有迟速,而我国之出渔猎社会为较早也。故制嫁娶,则离去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之陋习,而变为家族,亦为进化必历之阶级,而其中至大之一端,则为作八卦”,“抟黄土作人,与巴比伦神话合。(《创世记》亦出于巴比伦)其故未详。共工之役,为古人兵争之始。其战也殆有决水灌城之举,补天杀龙,均指此耳”, “一为医药,一为耕稼。而耕稼一端,尤为社会中至大之因缘。盖民生而有饮食,饮食不能无所取,取之之道,渔猎而已。然其得之也,无一定之时,亦无一定之数。民日冒风雨,蓦溪山,以从事于饮食,饥饱生死,不可预决。若是之群,其文化必不足开发,故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他总结道:“综观伏羲、女娲、神农,三世之纪载,则有一理可明。大凡人类初生,由野番以成部落,养生之事,次第而备,而其造文字,必在生事略备之后。其初,族之古事,但凭口舌之传,其后乃绘以为画,再后则画变为字。字者,画之精者也。故一群之中,既有文字,其第一种书,必为纪载其族之古事,必言天地如何开辟,古人如何创制,往往年代杳邈神人杂糅,不可以理求也。然既为其族至古之书,则其族之性情、风俗、法律、政治,莫不出乎其间。而此等书,当为其俗之所尊信,胥文明野蛮之种族,莫不然也。中国自黄帝以上,包牺、女娲、神农、诸帝,其人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故言中国信史 者, 必 自 炎 黄 之 际 始 ”[10](P13)。 他 特 别 强 调“今日中国所有之文化,尚皆黄帝所发明也”[11](P14),明显具有正本清源意义。
三、中国近代神话学的开端
中国近代神话学建立伊始即表现出理论研究多元并存的态势。
学者们多以蒋观云 (智由)的 《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为 “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最早的论文”[12]。蒋氏文章最早名为 《风俗篇》,存于其《海 上 观 云 集 初 编》。[13]《新 民 丛 报》 “丛 谈”1903年第36号发表了这篇文章。
蒋观云曾经对中国民族种类进行历史文化的求证,其立足点不仅仅在于古史重建的文化修复,而是看到 “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即神话传说对民族性格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作用。
蒋观云对中外神话传说故事中的洪水问题做比较,着意述说 “上古神话之时代,其言多想象附会,荒诞盖不足怪”的道理。他论述道:“大洪水之说,不仅于基督教经典中见之,今日发现巴比伦最古之典籍,其所言洪水之事,于基督教中所言略同。当时希伯来人,实居于幼发拉底河之上流,其后由亚伯拉罕始率其众,迁徙而居于迦南之地,故希伯来人所传之古说,实从幼发拉底河流域而来,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士两河间,为太古时代最多古国之地,而巴比伦立国早于以色列族,然则基督教经典所言,或从巴比伦记录转载而来,或则与巴比伦人同记其太古传说之事而已。且又考之大洪水之说,不仅基督教经典及巴比伦之古书而已也,希腊神话中,亦记洪水之事,与 《旧约》之所记者,殆无所异。由是言之,大洪水之说,或者当日从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迄地中海一带海岸诸国,皆同有此说法,而后记事之徒,乃各据以载之一国古史中也。”同时,举例论述 “洪水历史未可信也”,并对中外洪水神话作比较:“基督教中洪水之说,曾有人谓在纪元前二千三百四十九年,而与中国尧时之洪水,为同一时期之事,其前后相差,仅不过五十余年。西方洪水,以泛滥潴蓄之余,越巴米尔高原,超阿尔泰山,汇合于戈壁沙漠,而从甘肃之低地,进于陕西山西之低地,以出于河南直隶之平原,余势横溢以及南方,其间或费五十余年之岁月,而后西方之洪水,东方始见其影响。顾是说也,以为太古不知何年代之事,则戈壁一带曾有人认为太古时一大海,故西藏今日尚存有咸水之湖,与有人认阿菲利亚加撒哈拉之大沙漠,为太古时一大海者,其说相同。如是,则由戈壁之水,以淹中国之大陆者,于地势为顺。若当尧之时代,则地壳之皱纹亦以大定,山海凸凹之形势,与今日或小有变迁,而必无大相异同之事。然则,据地势而论,中亚洲一带山脉,地脊隆起,必无西方洪水,超越高地,而以东方为尾闾之事。即据一说,谓巴喀什湖,昔时曾与里海相通,此亦非荒远时代之事,然此正可验中亚洲山脉以西,水皆西流,而黄河长江经中国地面以归海之水,其源皆发于昆仑山脉以东,且当日西方之洪水,既在小亚细亚一隅,则西必归于黑海、地中海,而东南可由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之下流,以出波斯海湾,必下至逆流而反越高岭者,势也。且尧时洪水,或不过中国一部分之事,未必当其时,而谓全地球俱浸没于浩浩滔天之中,即征之各国古书,载洪水之事,亦见不一见;然多系一方之小洪水,而不足以当挪亚之大洪水。若必欲据中国之事以实之乎?古史中有云:‘共工氏以水乘水,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似明言上古有一大洪水之事,其云天柱折者,犹后世之言天漏,地维缺者,犹言大地陆沉,雨息而得再见日月云霞,则以为炼五色石而补之矣;水退而地体奠定,则以为立鳌足以扶之矣。上古神话之时代,其言多想象附会,荒诞盖不足怪。”[14]
蒋观云立足于 “神话”作为 “历史养成之人物”,进一步论述道:“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上有莫大之影响。印度之神话深玄,故印度多深玄之思。希腊之神话优美,故希腊尚美之风。”“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然神话,历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国人天才所发显之处。其神话历史,不足以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则其国人天才之短可知也。” “神话之事,世界文明,多以为荒诞而不足道,然近世欧洲之文学之思潮,多受影响于北欧神话与歌谣之复活。”“中国神话,如 ‘盘古开天辟地,头为山丘,肉为原野,血为江河,毛发为草木,目为日月,声为雷霆,呼吸为风云’等类,最简洁而乏崇大高秀壮言灵异之致。”“至历史,又呆举事实,为泥塑木雕之历史。非龙跳虎掷之历史。故人才之生,其规模志趣,代降而愈趋于狭小。(如汉不及周,唐不及汉,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明,是其征)盖无历史以引其趣向也。(如近世曾文正之所造止,其眼光全为中国历史上之人物所囿)且以其无兴象,无趣味也。不能普及与全社会,由是起而代历史者,则有 《三国演义》、《水浒传》;起而代神话者,则有 《封神传》、 《西游记》。而后世用兵,多仿 《三国》、《水浒》,盖 《三国》、《水浒》产出人物也;若近时之义和团,则 《封神传》、《西游记》产出之人物也。故欲改进其一国之人心者,必先改进其能教导一国人心之书始。”[15]这种研究方法是历史递进的视角,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相似。
如此把神话传说视作特殊的历史文化者,还有刘师培。其论述道:“昔郭璞之序 《山海经》也,谓世之览 《山海经》者,皆迂其闳诞夸迂,多奇怪傲傥之言。呜呼!此岂知 《山海经》者哉!考西人地质学谓:动植庶品,递有变迁。观《山海经》一书,有言人面兽神者,有言兽面人身者,而所举邦国草木,又有非后人所及见者,谓之不知可也,谓之妄诞不可也。夫地球之初,为草木禽兽之世界。观汉代武梁祠所画,其绘上古帝王,亦人首蛇身及人面龙躯者,足证 《山海经》所言皆有确据,即西人动物演为人类之说也。观西国古书,多紧人兽相交。而中国古书,亦多言人禽之界。董子亦曰:‘人当知自贵于万物。’则上古之时,人类去物未远,亦漳漳明矣,《山海经》成书之时,人类及动物之争,仍未尽泯。此书中所由多记奇禽怪兽也。又 《孟子》言:‘帝尧之时,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左传》言:‘禹铸九鼎,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则当时兽患仍未尽除也。故益焚山泽而禽兽逃匿,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皆人物竞争之关键也。安得以 《山海经》所言为可疑乎!”[16]
章太炎是一位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其神话理论以比较研究为主,论及神话与图腾等问题,集中表现在 《訄书》等论著中。章太炎称:“然自皇世,民未知父,独有母系丛部,数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动植而为女神者,相与葆祠之,英名曰托德模……野人天性阔诞,其语言简寡,见虚墓间穴宅动物,则眩以死者所化。故埃及人信蝙蝠,亚拉伯人称海麻。海麻者,枭一种也。皆因其翔舞基地,以为祖父神灵所托。其有称号名溢,各从其性行者,若加伦民族,常举鹭、虎、狼、羚自名……植物亦然。加伦民族,常以絮名其妇人;亚拉画科民族,常以淡巴苽名,久亦为祖。剖哀柏落人,有淡巴苽、芦苇二族,谓其自二卉生也。其近而邻夏者,蒙古、满洲,推本其祖,一自以为狼、鹿,一自以为朱果,借其宠神久矣。中国虽文明,古者母系未废,契之子姓自鸟乙名,禹之姒姓自蕙苡名,知其母吞食而不为祖,亦就草昧之循风也。夏后兴,母系始绝。”[17](P171)又如其运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法解剖神话的历史文化内蕴,论述道:“六书初造,形、事、意、声,皆以组成本义,惟言语笔札只用,则假借为多。”[18](P493)章太炎引杨泉《物理论》“在金石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称 “此谓本繇一语,甲乇而为数文者。然特就简毕常言,以为条别,已不尽得其本义”,并称 “言语不能无病。然则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是其分际,则在文言质言而已。文辞虽以存质为本干,然业曰 ‘文’矣,其不能一从质言,可知也;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斯非直魏、晋以后然也,虽上自周、孔,下逮嬴、刘,其病已淹久矣”,“是则表象之病,自古为昭。去昏就明,亦尚训说求是而已”[19](P495)。这种方式其实是一种神话传说的文献考证,在语言文字的历史演变中寻求神话传说的蛛丝马迹,或者可以看做后来 《古史辩》神话学派的先声。
除章太炎如此考据,还有梁绍壬与李慈铭等学者,这是乾嘉学派的遗风。如梁绍壬所述:“金桧门宗伯奉命祭古帝陵,归奏:‘女娲圣皇,乃陵殿塑女像,村妇咸往祈祀,殊骇见闻,请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请行。后数年,中州人至京,好事者问之,曰:‘像虽议改,尚未举行。缘彼处香火旺盛,皆由女像,故可耸动妇女,庙祝以为奇货,即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顿衰。’于冰璜云:‘何不另立男像,而以原像为帝后,其香税不更盛耶!’事见阮吾山 《茶余客话》。调停之论,实足解颐。然考女娲氏,《三坟》以为伏羲后。卢仝与马异结交诗以为伏羲妇。《风俗通》以为伏羲妹。而 《路史》称为皇母。《易系疏》引 《世纪》称为女皇。《外纪》称曰女帝。《淮南·览冥》注称曰阴帝。《须弥四域经》称为宝吉祥菩萨。《列子》注云:‘女娲古天子。’ 《山海经》注云:‘女娲,古神女而帝者。’而唐人贡媚武氏,遂有吉祥御宇之语。又《论衡·顺鼓》云:‘董仲舒言久雨不霁,则攻社祭女娲,俗图女娲之像作妇人形。’审是则以女娲为女,自汉已然,不自近世始也,积重难返,更之匪易矣。”[20](P172)
李慈铭力图辨证盘古神话真伪,称:“《爻山笔话》十四卷,粤西藤人苏时学教元所著。辨之讹,谓此说起于三国时徐整 《历纪》,其言怪诞。至梁任昉 《述异记》,乃曰:‘南海有盘古氏墓,直三百余里。桂林有盘古墓,今人祝祀’,云云。周秦古书,未有言及盘古者,而任氏言其墓,乃皆在桂林、南海。盖徭人之先所谓盘瓠者致讹而然。今西粤土音读瓠字音与古阂。徭峒中往往有盘古庙,徭人族类尤多姓盘者。以此征之可信”,“盘古之说,汉唐诸儒所不道,宋邵康节作 《皇极经世》,始凿凿言之。马宛斯 《绎史》历引《五运历年绝》、《述异记》、《三五历记》,诸书言盘古事者,而断之曰:盘古氏名,起自杂书,恍惚之论;荒唐之说耳。作史者日为主才首君,何异说梦。苏君证其为盘瓠之讹,尤是破千古之惑”[21](P690)。
与章太炎等神话理论相近者,还有严复,其论述神话传说与图腾的联系问题,称 “图腾者,蛮夷之徽帜,用以自别其众于余众者也。此美之赤狄澳洲之土人,常画刻鸟兽虫鱼或草木之形,揭之为桓表,而台湾生番,亦有牡丹、槟榔诸社名,皆图腾也。由此推之,古书称闽为蛇种,盘瓠犬种,诸此类说,皆以宗法之意,推言图腾,而蛮夷之馈,实亦有笃信图腾为其先者。十口相传,不知其怪诞也”[22](P685),云云。
关于章太炎与夏曾佑等的神话学理论,顾颉刚曾经论述道:“我们从小读书,读的都是儒家的经典,只看见古代有很多的圣帝明王、贤人隐士,却看不见人民群众,更看不见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神话传说。因此,一般人都不觉得中国古代有过一段神话时期。”他举1913年章太炎所说“中国没有宗教是中国的国民性”,及其 “我国的国民性只注意日常生活的技术,凡是没法实践的神怪空谈都是不相信”论,说 “这种思想不但章炳麟先生有,凡是熟读儒家经典的人都可以有”,而且他进一步述说道:“神话固然不像石器一般,可以在土里把原物发掘出来,然而外国的神话既经传入中国,读古书的人只要稍微转移一点角度,就必然会在比较资料里得到启发,再从古代记载里搜索出若干在二三千年前普遍流行的神话”。他特别举出 “第一个做这工作的人是夏曾佑先生”,称 “他在清末先读了 《旧约》的 《创世纪》等等,知道希伯来诸族有洪水神话,又看到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也有洪水神话,于是联想起儒家经典里的洪水记载,仿佛是一件事情”,并论述道:“他说明了对于远古情状的观察,古人和今人的意图是绝对相反的。他的 《中国古代史》大约出版于1907年,这些话从现在看来固然很平常,但在当时的思想界则无异于霹雳一声的革命爆发,使人们陡然认识了我国的古代史是具有宗教性的,其中有不少神话的成分,而中国的神话和别国的神话也有其共同性,所以春秋以前的传统历史只能当作 ‘传疑时代’看,不能因为它载在儒家的经典里而无条件地接受。”当年,他曾经痛斥夏曾佑等不懂得历史文化的真相,而此时,他颇为感慨地说,关于 “搜集我国古代的神话资料,要从儒家的粉饰和曲解里解放出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夏曾佑先生开始发现了这个问题”,“夏先生的 《中国古代史》永远为人民所记忆”[23]。的确,夏曾佑等的贡献会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而显示出其修复古史的特殊价值。
四、关于中国神话的文学研究
神话传说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但是,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近代神话研究基本上是六经皆史意义上的历史文化研究,而作为文学研究的神话学理论,直到1910年后孙毓修编辑中国民间童话寓言故事所做理论研究,才形成真正民间文学意义上的神话研究。
在中国近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体系中,神话传说能够成为一个亮点,最重要的原因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对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的影响作用。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家们以神话管窥历史文化的发展与国民精神建设等问题,梁启超、章太炎是这样,鲁迅、周作人兄弟等也是这样。这是这个时代所表现出的学术特色与思想文化特色。
孙毓修在 《中国寓言初编》的 “序言”中对中国神话传说的研究有许多重要发现,特别是他对 《路史》等历史文化典籍的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学理价值,1910年后,他在 《欧美小说丛谈》中论及 “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问题,称 “披萝带荔,三闾见之为骚;牛鬼蛇神,长吉感之作赋。其后搜神有记,诺皋成书。语怪之书,在中国发达最早。英语名此为Fairy Tales,其风始于希腊。益以闾巷谣俗,代有流传,虽无益于事实而有裨于词章,遂于小说界中,独树一帜。古时真理未明,处处以神道设教,狐鬼之谈,感人尤易,故恒以语小儿,为蒙养之基。小儿亦乐其诞而爱听之”。又言: “神怪小说(Fairy Tales)者,其小说之始祖乎。生民之初,智识愚昧,见禽兽亦有知觉,而不能与人接音词、通款曲也,遂疑此中有大秘密存,而牛鬼蛇神之说起焉。山川险阻,风云雷雨,并足限制人之活动,心疑冥漠之中,必有一种杰出之人类,足以挥斥八极、宰制万物者,而神仙妖怪之说起焉。后世科学发达,先民臆度之见,既已辞而辟之,宜乎神怪小说,可以不作,借曰有之,亦只宜于豆棚架侧,见悦于里巷之人,与无知之小儿而已。不知小说本于文学,而神怪小说,又文学之原素也。天下之事,因易而创难。神怪小说,则皆创而非因,且此创之一字,仅上古无名之人,足以当之。而今日文学史上赫赫之巨子,惟掇拾人之唾余,附于述而不作之列,尚无术以自创也。由此言之,神怪小说,岂易言哉,岂易言哉。”孙毓修指出:“神话者,未有文学以前之历史,各国皆有之。我国一部 《路史》,大足为此类之代表。后人觉其荒唐,斥为不典,当时视之,则固金匮石室之秘史,即今日粤若籍古,亦不能尽废其书。神怪小说起于晚近,尽知其寓言八九而已。神话史谓之有小说滋味则可,竟隶之于小说,则不可也”[24](P23),这些论断都是在具体的比较中显示神话传说故事文学特性。孙毓修不但是我国童话学理论的重要开拓者,也是我国神话学的重要拓展者,其视野开阔,较早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进行神话研究,标志着近代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就。
总之,神话传说概念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出现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研究相关,其关注点在恢复和强调以古史重建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原点与本位系统。各家述说,总是围绕民族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培育所展开,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学术自觉,也是一种文化自觉。今天,我们强调民族文化复兴,应该关注到神话在我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特殊的源头意义及其流传意义,应该从当年古史重建的学术演进中得到启发,从而更好地修复和建设民族文化传统。
[1]陈季同:《中国人的快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秦川:《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的历史变迁》,载 《明清小说研究》,2002(2)。
[4]汤显祖:《虞初志》卷八 《任氏传》,清扫叶山房刻本。
[5]梁启超:《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九,上海,中华书局,1936。
[6]梁启超:《太古三代载记·洪水》,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 “附录”,上海,中华书局,1936。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三,上海,中华书局,1936。
[8]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上海,中华书局,1936。
[9]梁启超:《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三,上海,中华书局,1936。
[10][11]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上),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12]刘锡诚:《世纪回顾:中国民俗学面临的选择》,载 《民俗研究》,1995(3)。
[13]蒋观云:《海上观云集初编》,上海,广益书局,1902。
[14][15]蒋观云 (智由):《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载 《新民丛报》,1903年第36号。
[16]刘光汉:《山海经不可疑》,载 《国粹学报》,1905年第10号。
[17]章太炎:《訄书》重订本 《序种姓》(上),载 《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81984。
[18][19]章太炎:《检论》(五),载 《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0]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载 《笔记小说大观》第廿二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21]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月记》乙集,同治三年版。转引自钟敬文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民间文学”卷,上海,上海书店,1995。
[22]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译)“按语”,1904年初刊。转引自钟敬文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民间文学”卷,上海,上海书店,1995。
[23]顾颉刚:《〈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序》,载 《博览群书》,1993(11)。
[24]孙毓修:《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载 《欧美小说丛谈》,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