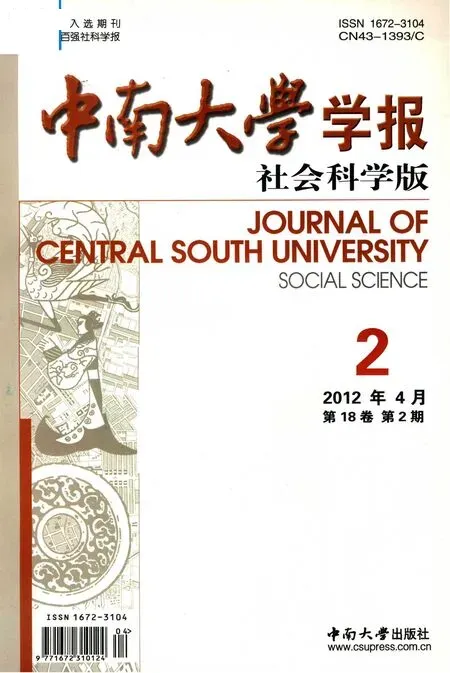广松涉的“物象化”论简评
孟飞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
一、前期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的界划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诸多分歧和意义扩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富异质性的场阈之一。广松涉打出的物象化论旗帜参与的讨论使其戏剧性更强。
广松涉对正统派自诩为科学主义的教义体系马克思主义嗤之以鼻。他认为,苏联斯大林式教科书哲学没有超越主−客的认识图式,陷入了旧唯物主义的“摹写说”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广松涉还批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源流。他们很大程度建立在对青年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异化史观的高扬,广松涉给他们贴上了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标签。鲍威尔、费尔巴哈等关于类本质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复归的“大循环”是断然需要否弃的。而聚焦于个人生存的“小循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异化的援引中得到共鸣,于是衍生出众多关注当下事态、关注个人体验、关注人的存在的著述。广松涉认为,“小循环”的最终逻辑结果必然终结于个体的肉体消亡,“小循环”的代数和又不能作为人的历史的“大循环”的叙事理由。所以,异化史观只能是关注价值悬设的理论模型态,落脚于“应该”与“是”矛盾的纯逻辑推演。
有趣的是,广松涉对异化史观的批驳在事实上忽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个进展方向,即阿尔都塞肇始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广松涉在东方提出其对异化论逻辑扬弃切近的时间,西方的阿尔都塞抛出了著名的“认识论断裂”学说,另一方面,广松涉和阿尔都塞在指认马克思发生“转变”的具体文本上也达到了契合——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里,我所说的“转变”是通泛性质的词汇,因为,对于马克思的哲学“转变”,两位思想家虽然都秉持一种所谓的“一次转变说”,但见地是不可化约的。阿尔都塞否认了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的存在,而是出现了范式的转换,成熟的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的对峙=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意识形态的非科学话语的对峙。[1]广松涉指出,马克思意识到了异化复归的概念装置所蕴含的悖理性,和意识形态的倒错性,于是废止此逻辑而发生了新的概念装置。[2](57)但是,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逻辑反转不是线性的,连续性和飞跃性交错构成了复杂的发生语境。广松对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提醒我们《手稿》中的观念和之后的《形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共同之处。[3](34)人的心理过程具有连续性,异化论建构是后来其体系一个很重要的逻辑节点。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异化论的“启动说明概念”和机能效力消失了,但是自我扬弃被“为我化”了。广松涉的解释是:不科学的价值预设造成了价值判断的二律背反,“马克思、恩格斯向前迈进一步,力图对这个二律背反的标准进行自觉的、实践的扬弃,并将它也嵌入判断论,价值判断论,进而言之,嵌入体系构成法之中。”[2](59)
广松涉的结论是:物象化论是在对异化论进行辩证扬弃基础上成立的,物象化论的确立标志唯物史观本史的成形,以取代近代的世界观地平。以1845年为界限,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思想地平、世界观的“结构的把握方法”都有着飞跃的发展。[3](35)早期马克思后期马克思的界划是异化论的逻辑到物象化论逻辑的转变。
二、物象化概念义辨
广松涉批评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再发现[4−5]造成了欧美论者对物化、外化、异化、对象化、客体化等概念的混同。
卢卡奇对物化的勘定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意味。首先是作为对象化的外化,这是物化的形成的序幕阶段。第二,卢卡奇的物化等于《手稿》中的异化。这是一种我们熟识的,所谓客体以反制于人的力量来奴役主体的见解。第三,物化包含了合理性的无价值判断成分。这一点不外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实存资本主义运行过程的合理化和工具理性的精确计量化的认同。广松涉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卢卡奇显然犯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概念僭越的错误——把《手稿》和《资本论》中都出现的“异化”这个词混同,[6]而卢卡奇(还有弗罗姆)秉持一个完整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倾向,对不同时期的文本引用是非法的。
一般意义上的物化概念的使用都是基于主体的东西转化成物的东西,将物化当作异化的特殊形态或下属概念。比如,科西克把资本主义总体物象化和异化的再生产机制的动力系统解释为,“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7](137)按照广松涉的说法,这样永远都囿于前现代的主—客认识论图式,这显然有悖于其前期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的分野。
为此,广松涉明确区分了两个德文词——物化Verdinglichung以及物象化Versachlichung。前者的德文原意为,使之具体化,成为东西,而后者,作为广松哲学的核心概念,则指称使之具体化而成为某事情。广松涉把物象化界定为马克思思想的本真品格,并弃绝了自我异化等等相近似的一系列概念。《物象化论的构图》跋文中,广松写道:“所谓物象化,倘若按照日常性的词义来理解的话,大概是对‘某种东西’朝着‘物象’而‘演(变)化’的称谓吧。”[2](217)广松涉认为晚期马克思的物象化不是立足于主体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转成物的客体存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的性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社会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对马克思物化的理解如果用物象化理论来中介那就是“作为立足于主体间性关系曲折颠倒的看法,来加以自为地把握的东西”。[3](37)这里,他对物象化的理解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拜物教的判定很相近,但是其实绝非一致,后文我还将提及广松涉曲解马克思的主因。我倒发现广松与齐泽克的看法是同构的。齐泽克认为,商品拜物教的奥秘不在于物对人的遮蔽,而是结构网络和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齐泽克式颠覆商品拜物教本意的解读与镜像阶段理论巧妙嫁接起来,这一结化转换从根本上完成了对马克思商品拜教的拉康化解读。比较关系化的他者的镜像倒映和广松涉的关系存在本体论可以成为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总结一下,如果把庸俗的物化论以物象化论来理解,那么物象化了的某物即为某种关系,这是广松哲学关系存在本体论的要义,反过来说,关系存在本体论是物化向物象化的跃迁的中介。广松涉不断提醒我们关系的基始性,因为它扬弃了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实在论的对立,也扬弃了主—客图式的近代思维模式。他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新地平的理论面貌本身——将关系状态的物象化进行自省,关系不是广松认为的社会肌体的结论,而是科学地进行社会研究的触发点。
三、物象化论何为?
广松涉明确把物象化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物象化理论”并不只是广松涉对他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理论方法论基础的表征,而首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这是他经过对哲学史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演变发展过程的详尽考察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研究和宏大理论体系建构所依据的方法论基础。
那么马克思主义,或者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物象化,作为其基础关系本体论和作为其逻辑进展的事的世界观)到底意欲何为呢?
广松涉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方法独具匠心,著者马克思所体现的学识是一个积极的舞台。“在马克思的叙述—批判的系统进展中,读者也不仅是共观者,而是根据马克思的舞台转动,在每次的水准上被形成著者马克思和‘我们’。”[2](112)这个舞台和布莱希特戏剧舞台的演员—观众关系模式很相似。布莱希特在其唯物主义剧作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框架推翻了一切旧唯心主义戏剧的“总问题”——即他不试图用自我意识来表达剧本的内涵和戏剧的潜在意义。观众和演出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模式——批判的和能动的关系。当然,现代叙事学和哲学解释学也在不同的文本层面表达了相近的洞见。而马克思或者广松涉通过马克思搭建这个舞台(叙述—系统)来让马克思的全体系在实践中完结,开拓了实践论和革命论。
野家启一在《“广松哲学”的发生学研究》中认为,物象化论具有意识形态批判效用。广松涉自己不否认这一点,而是强调了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础上的。的确,看似异化论的意识形态性强,易于激发群众的战斗热情,但总是与乌托邦幻念栓系在一起,再进一步说,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相比,《资本论》以批判商品拜物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才是更具体和更重要的。比如,广松涉自己对物象化的扩展中所涉及的范围已经触及到了语言、道德规则、制度权力、社会角色等等诸方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物象化不是意识形态的退场,而是对资本主义形而上学意识形态原罪的超越。
从商品拜物教到资本拜物教,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中解开了“抽象成为统治”(这种抽象不是主观的,而是历史的抽象)的死结,工业生产的物质机制直接物化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客观的抽象以物的形式统治社会存在,似乎是公正的“无人统治”(汉娜·阿伦特语)的客观支配。拜物教为核心的抽象理性批判在当代左派的批评话语中产生了相当多的意义再生产,阿多诺开启新的所谓否定性向度以来,许多后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打出了符号拜物教等多元的个性斗争方式。
我以为,广松涉提出物象化论是意识形态批判视阈内对被误视的世界的祛魅,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进行补充则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下的无产阶级实践相联结。广松涉的意图是,不仅要颠倒被物象化中介的倒错现象,还原本真的关系,更要通过冲破物象化误认而抵及科学的革命论路径。“要克服物象化,变革构成其存在根据的现实的诸关系乃必要条件。如果不瓦解以往的现实诸关系,物象化现象将不断地被生产、再生产。”[2](123)广松涉的理解是忠实于马克思的原意的,这一点在其《唯物史观的原像》第三章对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与物象化了的群众运动中表现无遗。对物象化论的扬弃不是观念的消解而是生产关系的克服。比如“货币力量”“国家权力”这样的物象化产品,如果不拆除社会编制、不改组生产方式,光靠消灭其外观是不能与乌托邦性区分的。
最后,物象化论作为广松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透视,这条马克思主义逻辑贯穿了广松涉一生艰难的理论求索历程,除了《唯物史观的原像》,还有中文版的《物象化论的构图》,以及一系列未被译介的著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地平》《马克思主义的理路》《马克思的思想圈》《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资本论的哲学》《青年马克思论》《恩格斯论》《辩证法的理论》等等。我想,一方面这是作为政治左翼的思想自觉,另一方面,毋宁说是广松涉越来越明晰地服务于他更宏大的战略部署——《存在与意义》的阐发,物象化论既是本体论意义的关系存在论的具体布展,又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四肢理论和存在论意义上的事的世界观的逻辑支撑。
四、物象化论的失误
我以为,青年马克思从早期的异化论的隐性唯心主义逻辑出发,步步推演到关注物质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架构,而没有走向主观化的“物象化”歧途。马克思所涉及的颠倒其实是客观的向度,虽然想象学批判在早期马克思那里有一定的展开,但至多是一个维度而已,无法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判断。广松涉承认,马克思没有定义所谓“物象化”概念,也没有高频次地使用该概念。南京大学张异宾教授的观点是,即使有所谓物象化理论,其形成与三大拜物教的提出也应是同体的,广松把这个时间点大大前置了。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虽然发明了广义的唯物史观,但是没有真正科学地还原历史世界存在与发展的图景。只有到了后期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57、58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的发表),才得以在狭义的资本主义生活史中,通过物象化视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本质。
虽然广松涉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物化)是一般意义的理解,它屈从于前现代的认识论构架,但是他对于《手稿》和《资本论》中异化和物象化存在混乱的表述。比如,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地平和物象化论》中言及对象性时,完全否定了对象化的客观存在,“作为对象性而呈现的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自在存在的人们的某种共同主观的关系”。[3](238)我认为,他的泛物象化论证是不精致的。晚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严格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中的两种物化:一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二是个人在社会规定上的物化。[8,9]第一种物化带有主体(人)对客体(自然存在物)的占有,这种对象化生产是社会发生、发展的基底。所以,马克思称之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肯定性的力量。第二种物化即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谜一样的形式的经典描述: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逆反的奴役性力量是早期马克思“异化”的科学叙述形式。
另一方面,广松涉世界观的关系本体论也有待完善。广松涉视实体性物象是假象性的存在。“物”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自在的实体物,也不是抽象的物质概念之物,而是历史地、社会性地发生关系的关系存在物,是人们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函数性、功能性、文化性的实践关联关系的‘场’”。在这里,他通过相对主义的关系态完全抹去了动态的历史存在之物,即自然的且历史的关系存在之物的物质性,物质成了不具有现实存在可能而只是纯思维抽象的、不为人所理解的物质。这一点违背了马克思的初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只通过抛弃笛卡尔以来的心—物、灵—肉二分,转向关系本体就可以实现,根本没有先在的纯关系。
出现失误,是否因为广松涉跳过了马克思一系列的重要本文,而没有体察到马克思在建立狭义唯物史观过程中的细微演进? 广松涉在论述他的马克思主义时,使用大量晚近的思想家或者哲学家的理论资源,最突出的是马赫的“复合感觉要素一元论”、胡塞尔的“意义性意向的本质”和海德格尔的“上手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在用马赫、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目光来检视马克思。这又是否隐含着广松涉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需要补充还是其本身哲学内容的缺乏? 物象化到底是不是马克思完成态的理论范式?掩藏在被误视的物象化关系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广松涉没有回答。
[1]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2]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广松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像[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5]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6]克林尼克斯.阿图塞的马克思主义[M].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1990.
[7]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8]张一兵.物象化论的构图代译序[C]//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9]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