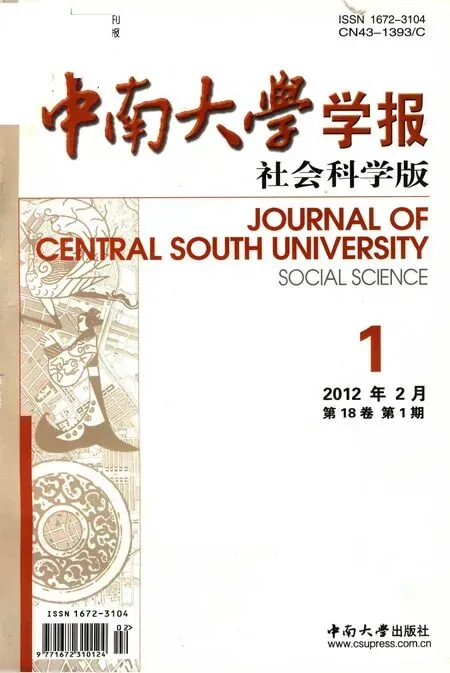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
金龙云
(1.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2.长春师范学院历史学院,长春,130032)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是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出台大政方针提供谋略、思想、观点、建议的具有政策筹划、咨询和协调性质的外交思想库。作为以美国外交政策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外交型思想库,其在美国政、经、军三界声名赫赫。
在中美关系解冻前,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对中国问题已经关注多时,并作了大量的研究。20世纪 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在酝酿着重大的调整。中美两国在这一时期的尖锐对抗和在越南战场进行的间接战争,无疑推迟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进程和步伐,但同时亦为美国政府改变其政策造成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一直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出版有关中国问题的学术著作,在《外交季刊》发表了不少关注中国问题的文章,力图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尽管外交关系委员会内部个别人士在对华政策方面持消极立场,但希望打开中国大门,与中国进行交往是主流。可以说,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问题上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
一、对中国问题的密切关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有关人士就开始关注与中国接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问题。委员会对这些问题的持续关注、跟踪研究从一个侧面有助于加快发展中美关系的步伐。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些有识之士或与委员会关系密切的政府官员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公开呼吁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建议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7年,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旗舰刊物《外交季刊》上撰文《一位民主党人的外交政策观》,他在文中严厉批判了美国对华政策过于僵硬和使用武力的倾向。[1](118−120)1960年4月,《外交季刊》发表了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后来在肯尼迪政府担任副国务卿的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els)的文章,题为《重新考虑中国问题》。鲍尔斯在文章中提出:“美国应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目前的中国政权已经稳固,而且实力日增。美国在处理有关地区性的事务(如东南亚问题)和全球性事务(如裁军问题)时,如没有中国的参与,其成效是值得怀疑的。”至于如何解决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鲍尔斯提出了所谓的“中华福摩萨国(China-Formosa Nation)方案”,其内容包括台湾当局从金门、马祖撤军,大陆沿海岛屿中立化以及台湾成立独立的“中华福摩萨国”。[2](476−487)鲍尔斯的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的主流意见。
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在1963年12月13日的演讲中表示国务院已经放弃了等待中国发生某种奇迹的立场,积极准备在更为现实的基础上打开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大门。[3](225)希尔斯曼的讲话实质上是国务院抛出的试探气球,目的是试探媒体和民众对此的反应。国务院对可能出现的风暴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即便是被视为对华强硬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的国会也出现了某些明显的转变与松动。1964年3月2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与外交关系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威廉·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了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著名长篇演说。全面抨击了美国现行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指出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陈腐的观念和过时“神话”的基础之上,与变化了的现实脱节。他没有就对华政策提出具体主张,但特别强调指出,国际关系史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化敌为友不乏先例,因此,不排除一段时期后,美国和中国的敌对关系有所改变,即使不是形成友好关系,至少可以“竞争共处”。美国对华政策中应该注入灵活的成分,以便在机会到来时有执行灵活政策的能力。[4](273−278)
在美国卷入东南亚冲突,深陷越南战争泥淖之时,中国对北越方面的援助无疑加深了美国最高决策层和公众这一印象,即认为东南亚问题与中国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肯尼迪总统及其继任者约翰逊总统一直坚信,中国由于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缘故对东南亚一直存有野心,力图染指这一区域,而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目标是为了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强力扩张。所以,在越南问题上,无论是肯尼迪政府还是约翰逊政府在做出战略决策之时均要对中国因素认真考虑,不敢大意,担心会招致中国的直接介入,这是美国政府和公众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美国公众对中国是否会派兵介入越南战争亦十分关切,对中美再次兵刃相见的可能性深感恐惧和不安。[5](114)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托马斯·盖茨(Thomas F.Gates)曾在旧金山一个商业集会上宣称,倘若美国能与中国举行公开的双边谈判,那么,美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势必会得到加强。[6](186)但中国对北越方面的积极援助和支持北越抵制谈判的立场打击了美国借助国际社会调停越战的努力和信心,同时这亦导致美国认为中国政府直接介入了越共的决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陶文钊认为,中国支持北越坚决抵抗和顽强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两手政策,使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进退两难。这决定了美国如要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就有必要改变其对华政策,不能将遏制中国作为主要目标。[7](316)在这一历史时期,外交关系委员会集中关注中国问题和东南亚问题,并将重点放在中国问题上,显然它认为东南亚问题与中国问题密切相关。
二、对“两个中国”立场的论争
比起美国卷入东南亚冲突和战争,如何应对中国则吸引了外交关系委员会更多人的关注。北京咄咄逼人的计划令他们担忧,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排斥共产主义政府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他们介入并成为一场运动的主要力量,这是一场支持“两个中国”的运动,在外交上承认北京但又坚持台湾的独立。尽管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坚持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发表的意见认为承认两个中国政府的存在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亨利·罗伯茨(Henry Roberts)在他1956年的研究报告《俄国与美国》中,建议远离非理性的反共主义,这些反共主义者认为派大使到北京违背了基本的道德价值。承认北京政府在原则上并不违背什么,但是只要认为承认北京政府会使我们与共产主义力量的关系达到常态的错误观念得以延续,只要承认北京政府加深了一种假象……即共产主义中国将会成为亚洲的主要力量,那么承认北京政府就不符合美国利益。[8](237)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具体是谁对承认政府就意味着“常态”抱有幻想,但他承认美国不可能永远在联合国大会占据必然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都有可能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并要求在世界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他鼓动美国规划者将北京和台北同时纳入联合国。
罗伯茨的研究报告问世一年以后,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了关涉中国的一系列书籍中的第一辑。它是由经济学家霍华德·布尔曼(Howard Boorman)、亚历山大·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及政治学家本杰明·施瓦兹(Benjamin Schwartz)编辑,有着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叫做《莫斯科——北京轴心:权力与张力》(1957)。研究小组主席、资深的外交家阿瑟·迪恩(Arthur Dean)在前言中写道:“如今莫斯科——北京轴心代表了世界政治中一种可怕而又难测的力量。”这又一次证明了委员会只会大量陈词滥调的名声,他想弄明白到底中苏能否分离。[9](vii)本杰明·施瓦兹警告,要离间二者实属不易。在一份关于“意识形态和中苏联盟”的长论中,他认为随着时间的迁移,意识形态将会瓦解。“这种意识形态的剧烈改变已经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意识形态作为联接结构的作用,这不仅发生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也存在于共产主义世界的其它国家。”[10](140)
菲利普·莫斯利(Philip Mosely)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究部主任,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他同意轴心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一观点。他极力主张美国允许越南大选,以换取苏联在朝鲜、德国允许大选的承诺。他还偏向采用“两个中国”政策。“尽管对于希望恢复大陆统治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来说是沮丧的,这一步可能促使许多第三世界联盟的积极拥护者团结起来,并可能赢得未承诺国家的的赞赏。”[11](207)
莫斯利支持两个中国政策,认为这是最佳的选择,它能让美国在影响各项事务上具有最大的伸缩性。美国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被动的等待,静观其变。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 A.多克·巴尼特(A.Doak Barnett)曾在中共取得最后胜利前担任过美国驻中国最后一任领事,在一本名为《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对美国政策的影响》的详尽的研究报告中,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基于一个1958~1959的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领导的研究团队,巴尼特追溯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例如,在越南,他解释道:“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改革热情不断助长了他的雄心。”[12](304)这种解释紧随着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对苏联行为原因描述之后。其结果可能会有一场有限的战争,但它不会涉及中美全面的冲突。他对两个中国方案,比之前任何一个人都更为坚定。他确立了四种方法:美国可以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追求台湾所想要的“解放”;设法进一步孤立北京;或者是,采用“两个中国”方法。比如说在联合国,不管美国政府如何设法制造障碍,大部分联合国成员国都很有可能会在今后投票给北京使其占有一席位。联合国大会或者会将台湾逐出,或者会承认两个中国,而后者是美国的目标。尽管支撑国民党政体实施对全中国的管辖这种空空的虚构是不可取的,但同样不可取的是承认北京政府且将台湾丢给共产主义。相反,美国应该期盼着一种基于中国存在着两种政权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的新现状稳定下来。这需要努力使国际认可并使联合国和大范围的世界都接受这两种政体。
在美国亚洲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lum)看来,尽管辩护、支持和鼓励国民党,但美国毫无帮助蒋介石军队打回大陆的念头,他毫无反攻的可能。美国现在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它“支持了一种政体来统治中国,却看不到任何希望使其权势扩张到台湾之外及附近的岛屿”。[13](145)布鲁姆批判了当前盲目的政策制定者。和其它专家一样,他谴责过度的感情主义,这已使对中国政策的争论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他批判政府官员导致当前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走进了死胡同。“美国的急性子和政治情感的强流经常使提前以一种坚韧而又灵活的方式来管理政策变得不可能。一些允诺的承诺根本没有考虑到其后果。我们一直不愿意认可共产主义中国的抱负可能有部分是合理的。”[14](180−183)
布鲁姆赞成审视每一项现有政策是否已生效或失败。例如,对北京的禁运没有达到任何政治或经济目的。不承认中国,显然也是失败的。美国不得不承认,试图束缚住中国政府是远在美国能力范围之外的事。美国应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承认北京的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执政地位。美国将如何对待台湾?首先,它要让台北政府消除它很快会重新掌权的幻想。谋求重新掌政大陆政策的可能性极其渺茫,继续虚构漏洞百出的事实的效力遭到严重质疑,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其它因素,对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应参照其它因素做出评估。而解决的途径就是“两个中国”政策,确保大陆以及台湾两个政府在联合国都拥有席位。当前美国的立场是钳制大陆政府,因为它不够爱好和平……它也许伸张正义,但是却不能提出解决联合国内外重大问题的有效方法。在默许大陆政府在联合国席位的同时,美国同样也倾向于保留台湾的席位。并且,继续对共产党国家采取排斥态度也更加严重地损害了与其它国家的感情。一旦大陆政府进入世界舞台,美国将不可避免地采取措施,“美国将致力于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坚持大陆与台湾分离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得不“放弃之前的努力:捏造事实,宣称台湾国民政府即中国政府”。[15](208−210)
三、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运用
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和态度上并没有明显的改观。但是,如前文所述,早在50年代末,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些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中国在美国全球冷战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外交关系委员会开展了大量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这些研究报告和对华政策规划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终于发挥了效用。
1962年1月,美国政府由于迫切希望了解有关中苏分裂的情况,认为有必要动员非政府的智力资源,展开相关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在国务院的授意下,外交关系委员会于同年2月起广邀大批专家学者,就中苏分裂和美国的对策进行讨论。与此同时,由于冷战思维的局限,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还是认为中国将威胁美国的亚洲利益。出于这种考虑,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外交关系委员会于1962年 4月提出了一项研究中国的宏大项目——“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16](178)外交关系委员会设计这一项目的原因是该委员会认为:“中国对西方在亚洲的地位构成的威胁,是美国在 60年代面临的两大挑战之一,必须给予关注并对那里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检讨过去10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17](180−181)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提供政策备忘录供决策者参考;在《外交季刊》和其它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有关的文章;出版有关的小册子以及出版正式的系列著作。根据该项目的计划,1966年陆续出齐的8部著作涵盖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各国的对华政策等。这8本著作分别是: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lum)的《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阿奇博尔德·斯蒂尔(Archbald T.Steel)的《美国人民与中国》、亚伯拉罕·哈尔本(Abraham M.Halpern)的《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美国政策的蕴涵》、塞缪尔·格里菲思(Samuel Griffith)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肯尼思·杨(Kenneth Young)的《与中国共产党人谈判:美国的经历1957~1967》、李·威廉姆斯(Lea E.Williams)的《东南亚海外华人的前途》、弗雷德·格林(Fred Greene)的《美国政策与亚洲安全》。①
虽然上述8部著作的内容不同,观点各异,但其出发点都是要重新研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及对中美关系的意义,其归宿则在于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尽管有的作者还没有摆脱对中国的偏见,但至少要力求客观。作者们全力收集所需研究资料,以阿奇博尔德 ·斯蒂尔的著作《美国人民与中国》一书为例,作者在研究中加入了一系列他在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民意调查,反映美国民众对中国当前重大事件所采取的态度。他发现,国民已经用新的幻想代替了旧的幻想。它主要表现为理想幻灭所带来的冲击,挥之不去的无名恐惧,七亿中国人被策动的各类反美运动引起阴霾,对于朝鲜的人潮涌动、洗脑以及阵亡战士的记忆,这些以及许多其它的出乎意料的变化给美国民众留下了沉痛的心理和精神创伤。如今,辽阔的中国疆域令许多美国人不寒而栗。也许,当代中国令美国民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它庞大的人口。这种压倒性的庞大力量加之以大陆政府对美无法消解的仇恨使中国问题成为无数美国人的梦靥。几乎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深表对庞大中国人口的担忧。这个广袤的国度正向亚洲其它国家施展强大的向心力。中国对于日本而言就如一块磁铁。有人担忧“如果中国成功震慑日本,我们将首先陷入麻烦之中”。一位已经退伍的将军“感觉中日必然联手”,并且遇见“这种科技力量与庞大人力的结合将对美国构成巨大威胁”。[18](60−65)
这种对中国敌对的口吻引发美国民众强烈的愤慨,他们已经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为不可避免的祸根。有些人将中国称作“怪物”,也有些人猜测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动?与此同时,许多其它受访者似乎忘记了它丰富的文化,包括她的艺术和哲学。总之,对于中国的总体感觉是困惑,为什么曾经的朋友突然间反目成仇。1964年秋中国首枚原子弹爆炸使情况恶化。美国政府曾预料大陆政府很快就会着手进行原子弹爆炸工作,因此国内并未产生恐慌。然而,许多美国人似乎坚信“中共政府将采取更多侵略和战争行动”。[19](72−73)
斯蒂尔曾对这种不经证实就产生的反华情绪是否能够促进国家利益或者使民众对国际关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表示怀疑。同时他也感到遗憾,因为他的同胞们已经陷入错综复杂情境之中而很难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待问题。整个国家陷入这样一种局面:所有人都相信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最糟糕的。“也很少有人愿意挑战基要主义者们所设定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及其同伙正蠢蠢欲动,准备侵犯我们。”[20](234)只要冷战一天不结束,这种认识就将持续下去。斯蒂尔表示,媒体的影响力不能单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报纸来判断,而应更多地关注数以千计的地方报刊,它们通常会更保守地看问题。这些新闻媒介为立法人提供参考,让他们了解时下流行的对外政策观究竟是什么,从而形成自己的主张。华盛顿的立法者们也许会阅读《纽约时报》来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但当他们想了解对于这一话题的民意动向时,他们往往选择地方报纸。从中难以产生分歧,因为“对华政策已经遭遇上时间‘冷藏’,以致大多数美国人都对此感到生疏,从而更愿意相信报纸中陈述的内容。他们不太可能就那些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进行争论”。[21](238)
当然,也有例外。许多活跃于一个半世纪前的辩论家已经过时,或者他们的观点已经落伍。由此,任何一次新的争论都会产生一些新的辩手。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在1964年3月发表的演说中就呼吁人们要转变旧观念,开始面对现实,这番言论同时也激励了他的同伴。斯蒂尔同时指出,从1964年中开始,民众对于对华政策的兴趣以及相关讨论呈上升态势。旧金山的一个贸易协会就曾提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贸易往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前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也曾在众多经济领导人面前建议恢复与中国的洽谈将会巩固美国在东南亚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中国以及越南问题。毫无疑问地,学术界的力量足以开展一次空前的论坛,就中国、越南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它同时可以保证讨论在公正客观的氛围下进行,并结合专家们的特殊经历和知识及学生们开放的见解。然而,校园讨论中激烈的对峙与他之前所预期的良好的氛围有很大差距。他所引用的关于越南问题的讨论会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它成了发泄情感以及煽动反对意见的地方”。[22](242)
斯蒂尔提出的解决途径包括在台湾问题的考虑上加入前所未有的内容:是否充分考虑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持有的观点?美国不得不承认,就像任何其它国家一样,中国也享有合法的国家利益。或许就如同公开应对来自国外的嘲讽:“如果共产党的军队驻守在格兰德河或他们的舰队在卡特琳娜海峡巡查,美国将作何感想?如果总统不参与其中,即使是公开发表的对华政策将毫无作用。斯蒂尔回忆起当年肯尼迪总统曾说过的话,在突破界限时,总统同样受到种种限制。”[23](249)或许总统能够在公开讨论时更加放心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这些著作建议改善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由于这些书的热销,它们一定程度上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制造了舆论。就在“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项目组正在研究的过程中,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外交关系委员会开始关注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尤其是在《外交季刊》中刊发了很多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文章。1965 年塞缪尔· 格里菲思在《共产主义中国作战能力》一文中坚定地认为:“中国陆军的总体水平相当于欧洲大国1941——1942 年的水平,当然它仍然比亚洲其它国家强大。中国海空军的战斗实力也不很强大,尤其是空军,甚至都难以保卫中国大陆免受台湾的骚扰。若无苏联的大规模援助,中国很难在短期内有重大的改变与进步。”[24](224−226)拉尔夫·鲍威尔(Ralph L.Powell)在《中国炸弹:探索与反应》一文中声称:“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开启了原子时代一个新的和危险的阶段。其最初的核试验并没有立即产生军事上的重要性,但却具有相当重要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都有重要影响。因为之前的核试验都是由工业强国完成的,但共产党中国却是一个非西方的、非白人的半工业化国家。”[25](616)另外,鲍威尔还指出:“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成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其在国际政治、军事和技术上的声望和影响力,这一点已越来越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甚至是美国的盟友都如此认为。这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担忧。”[26](618)
与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几乎同时,由于不满中美关系的僵持状态,1964年,外交关系委员会成立了“亚洲社会”研究小组,负责系统地研究美中关系。[27]该小组第一任主任、亚洲问题研究会的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lum)认为:“美国理应向世界表明,情愿在不牺牲其根本利益的情形之下调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与其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美国可以改变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关系,但仅视其为台湾政府而非全中国的政府……有关政策施行伊始,台湾与大陆都会对两个中国表示反对,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接受此一现实。”[28](254−256)该研究小组提出的非常重要的建议之一就是支持中国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享有合法席位。1969年,外交关系委员会对这一研究项目做出总结,结题报告的题目为《国际事务中的美中关系》。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向来主张改善对华关系,调整对华政策。早在他1967年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越南战争后的亚洲》一文中,尼克松就论述了把中国接纳到国际社会中来的必要性:“美国对亚洲的任何一项政策都要一开始就面对中国的现实。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不能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否则,这样就会助长它的狂热性,使它怀抱仇恨而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不容许可能是最有智慧的人民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生活。但是,在追求这个长远目标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期内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就会犯下灾难性的错误。我们再也不能无视一个8亿人口的大国了,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带头寻求和解可能更好,可能产生某些对美国有利的影响。”[29](121−125)该文一经发表,就得到了有关各方的广泛关注。1971年7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奉命秘访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探索性的接触。②尼克松本人在随后的1972年2月21日至28日亲自访问中国。若干年后,尼克松亦承认《外交季刊》是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具有总体认识新视角的论坛。
尽管在对华外交方面,外交关系委员会内部也曾经出现了不一致的声音,但主张发展对华外交的是主流。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在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研究极大地加强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更快地打开中美友好的大门,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推手和助力。
注释:
①Abraham Meyer Halpern ed.,Policies Toward China: 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1965; Robert Blum,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New York:McGraw-Hill,1966; Archbald T.Steel,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New York: McGraw-Hill,1966; Alexander Eckstein,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New York: McGraw-Hill,1966;Lea E.Williams,The Future of Oversea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New York: McGraw-Hill,1966; Samuel Griffith,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New York: McGraw-Hill,1967; Fred Greene,U.S.Policy and The Security of Asia,New York: McGraw-Hill,1968; Kenneth Young,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U.S .Experience1953-1967,New York:McGraw-Hill,1968.
②伴随基辛格进行这次历史性飞行之旅的是它的助手,温斯顿·洛德,曾为美国国务院派驻国外的外交官员,于1977年成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陪同基辛格秘访北京的飞机上,他宣称他是第一个跨越共产主义中国的美国人。
[1]JOHN F.Kennedy,“A Democrat Looks at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1957,36(1):118−120.
[2]CHESTER B.“The China Problem Reconsidered”,Foreign Affairs,1960,38(3): 476−487.
[3]ARCHBALD T.Steel,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
[4]CONGRESSIONAL Q.China and U.S.Far East Policy,1945-1966,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Service,1967.
[5]LEONARD A.Kusnitz,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America’s China Policy1949~1979,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84.
[6]ROBERT D.Schulzinger,the Wise Men of Foreign Affairs: The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7]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8]HENRY R.Russia and America: Dangers and Prospects,New Yor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56.
[9]ARTHUR H.Dean,foreword to Howard Boorman,Alexander Eckstein,and Benjamin Schwartz,Moscow-Peking Axis:Strengths and Strains,p.vii.
[10]HOWARD B,Alexander Eckstein,Philip Mosely,and Benjamin Schwartz,Moscow-Peking Axis: Strengths and Strains,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1957.
[11]A.Doak Barnett,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Challenges to American Policy,Harper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
[12]ROBERT B.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
[13]SAMUEL B.Griffith II,“Communist China’s Capacity to Make War,” Foreign Affairs,1965,43(2):145.
[14]RALPH L.Powell,“China’s Bomb: Exploitation and Reaction,”Foreign Affairs,1965,43(4):180−183.
[15]SAMUEL B.Griffith II,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7.
[16]RICHARD M.Nixon,Asia after the Vietnam War,Foreign Affairs,1967,46(1):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