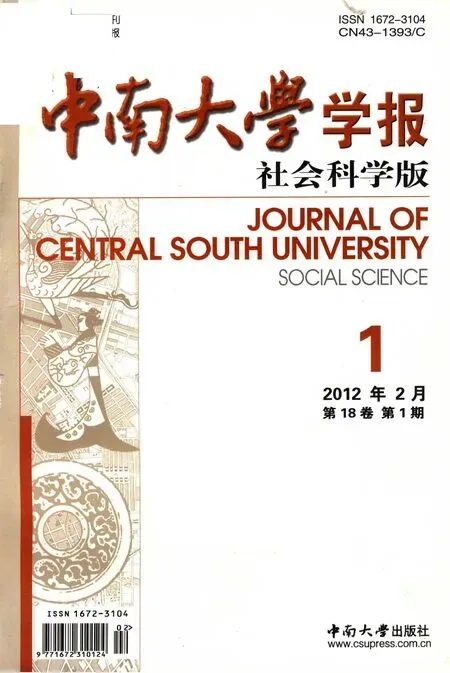英国汉学家杜德桥与《西游记》研究
许浩然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杜德桥(Glen Dudbridge, 1938−),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曾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讲座教授,兼任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所长,入选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院士,当代著名汉学家,现已荣休。《西游记》研究是杜德桥重要的学术方向之一。1964年他在《新亚学报》上用中文发表《<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1967年以论文《<西游记>前身考及其早期版本》(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dents and Early versions)取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69年在《泰东》(Asia Major)上发表《百回本<西游记>及其早期版本》(The Hundred-chapter Hsi-yu Chi and Its Early Versions),该文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被台湾学界翻译;1970年其专著《十六世纪中国小说<西游记>前身考》(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被列入“剑桥中华文史 丛 刊 ”(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自其博士论文的另一部分;1988年杜氏又有论文《<西游记>的猴子与最近十年的成果》(The Hsi-yu Chi Monkey and the Fruits of the Last Ten Years)发表于《汉学研究》(Chinese Studies)。杜德桥对《西游记》的版本演变、章回分合、形成源流、人物原型均有深入探讨,这些探讨并非封闭自足的体系,而是充满了对研究同行观点的反思、商榷与借鉴,同时他的观点也被同行反馈和讨论,这种互动促进了《西游记》学术的进程,值得国内学界重视,今特撰文述评如下。
一、《西游记》版本考证及明刻阳本的发现
学界对《西游记》版本的考证,一直都在争论百回本、阳本、朱本的相互关系。百回本《西游记》现存最早者是明代金陵唐氏世德堂本。阳本(亦称杨本)原名《三藏出生全传》,题“齐云阳志和(亦作杨致和)编”,四十则,不称回,后被收入《四游记》,称《西游记传》,一直翻刻不缀。朱本原名《唐三藏西游释厄传》,题“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十卷,分则不称回,朱本最早存本为明万历初年本,曾在日本村口书店出售,后此本被北平图书馆收购,后又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制有缩影微卷。阳本与朱本相似,可以视为同一系统的本子,这两个本子较之百回本明显简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已对以上三种本子的关系作出讨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阳本为百回本的一种祖本。胡适《跋<四游记>本的<西游记传>》予以反驳,认为阳本是妄人割裂百回本而成。孙楷第于村口书店、郑振铎于北平图书馆亲见朱本最早存本,分别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西游记的演化》中作出分析,在观点上都倾向于胡适之说,郑振铎更是列出版本源流图示,明示了朱、阳二本从百回本删削而来。鲁迅后来也依郑著订正了己说。[1](166−173)
时至60年代,阳本、朱本与百回本的关系问题又起争议。澳大利亚籍华裔学者柳存仁获睹美国国会图书馆朱本缩影微卷,于1963年、1964年在《新亚学报》和《通报》(T’oung Pao)上分别用中、英文发表论文《<四游记>的明刻本》[2](323-375)、《<西游记>的祖本》(The Prototypes of “Monkey(Hsi Yu Chi)”)[3](55−71)试图推翻前说,论证朱本、阳本为早,百回本后出,对以上两本都有承袭。在这一背景下,杜德桥撰成《<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4](497−519)、《百回本<西游记>及其早期版本》[5](337−400)两文与之商榷。杜氏同意孙楷第、郑振铎的观点,并用更为严谨的论证来巩固它。他提出:“省略之处不足为证,可能是装订疏忽造成的漏洞更不能用做证据。”这是说文本间单纯的详略比较对于考证版本前后没有作用,既可以说版本源流是由繁删简,又可以说是由简增繁。他认为“表面上流畅、完整的散文叙述中极不通的地方才能用为检验的有效标准”。[5](352)其意是要由文本内在的文义矛盾来考索删削的痕迹。在这一标准之下,他用很长的篇幅详举数例论证阳、朱二本的删削之处。可以说杜、柳二氏的商榷文章将《西游记》版本考证推向了更为精密的层次。
杜德桥在版本研究中更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和汉学前辈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于60年代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明刻阳本,该本原是一位英国爵士在1679年以前捐赠给牛津的。此前中外学者考证《西游记》版本,所据阳本最早者是胡适所藏的嘉庆坊本,接触不到该本的学者只能利用近现代的排印本。[6](702)牛津本的发现无疑使学界能够更为清晰地了解阳本的原貌。杜氏将这一发现的成果公布在《百回本<西游记>及其早期版本》中,他这样描述:“新锲三藏出身全传,共四卷,正文分为四十则,不称‘回’。半页十行,行十九字。上图下文,图两边有题词;首页插图旁题:‘彭氏’。首卷前题‘齐云阳至和编,天水赵毓真校’,紧接前题有一题记:‘芝潭朱苍岭梓行’。”[5](348)他考证芝潭是建宁府建阳县,认为朱苍岭极有可能是当地从事专业出版的朱氏家族的一分子。[5](385−386)而就“其版式看来,乃彼时典型之闽刻。”
1988年柳存仁新撰《<西游记>简本阳本、朱本之先后及简繁本之先后》发表于《汉学研究》,根据以上牛津本对《西游记》版本又作了重新考证,虽然具体观点仍与杜氏不同,但是他极其称道两位牛津学者的发现,说:“牛津大学龙彼得和杜德桥两位先生发现在牛津收藏的明刻本,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一件大事,特别是研究《西游记》的早期版本的里程碑。他们的发现的功绩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在他们没有发现这一部重要的刻本之前,从中国老辈的学者们数起直到现在的我们,几十年间,大家不免走了不少冤枉路。”[6](702)
二、从版本考证到文学批评:《西游记》第九回问题
杜德桥《西游记》的版本研究还涉及“第九回问题”:通行本《西游记》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儿复仇报本”(简称“陈光蕊故事”),明代所有百回本皆不载,而最早载于明刻朱本,它是否为小说内容原有,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杜德桥考证朱本后于百回本,故倾向于认为“陈光蕊故事”并非小说原有,是后人所加。该问题原属版本考证范畴,然而杜氏的研究另多出一段评述文字:“‘陈光蕊故事’无论就结构及戏剧性来讲,与整部小说风格并不谐洽。组成前十二回的各节故事中,只有此‘陈光蕊故事’对整个故事情节的推展没有贡献。此节故事自成一体,强调伦理孝道。性喜诙谐,落拓不羁的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若写了这节故事来寓托这么严肃的主题,实在令人难以想象。”[5](374−375)该段评述的性质超出了版本考证而涉及到文学的评论。这一点被他敏锐的欧美同行们发觉,使他们受到启发,反向思考,撰写文章与其商榷,从叙事结构、母题意义、改编技巧等文学的角度挖掘“陈光蕊故事”对于整部《西游记》的重要性。于是在欧美汉学界里,《西游记》第九回的去取由版本问题一变而成为文学批评的话题。
1975年,芝加哥大学《西游记》研究名家余国藩在《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西游记>的叙事结构与第九回问题》(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Problem of Chapter Nine in The“Hsi-Yu Chi”)首先与杜氏商榷。余文对“陈光蕊故事”中两个情节的论述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玄奘刚一出生就被弃置江上,蒙金山寺长老救养,皈依佛门的情节。他认为小说至六十七回有一诗句“幸遇金山脱本骸”是对该情节回应,暗示着玄奘以出家作为救赎,即“脱本骸”的象征。至九十八回师徒即将功德圆满之时,又出现了“脱本骸”情节:玄奘以无底船过凌云渡时,真正捐弃了本骸,得到了救赎。从江流出家到凌云渡修成正果,余氏指出《西游记》里有一个贯穿全篇的河流母题:“河流不但是毁灭的象征,也是再生的征兆。毋庸置疑,玄奘心里的河流经验乃包括生前的灾难、出世后的遗弃,以及最后的获救等等。”[7](227)其二是:玄奘母亲抛绣球选婿的情节,小说叙至天竺国故事时,玄奘观览国风,追念此事,且更被绣球打中,被逼与公主成亲,余氏认为这正是“陈光蕊故事的回应与嘲讽”。[7](228)基于以上论述,余氏认为杜氏所下的“‘陈光蕊故事’对整个故事情节的推展没有贡献”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
1979年,威斯康辛大学学者阿尔萨斯·严(Alsace Yen)在《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Reviews)上发表《中国小说的技巧:<西游记>里的改编——以第九回为中心》(A Technique of Chinese Fiction: Adaptation in the “Hsi-yu chi” with Focus on Chapter Nine)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严分析了“陈光蕊故事”的模式:“事业有成的父亲/儿子——恶人试图谋杀父亲——父亲复生:恶人受惩:家庭团聚”。严认为这种模式在中国小说戏剧中十分流行,他例举元代张国宾《相国寺公孙合汗衫杂剧》也有极其相似的模式。[8](206-212)严发现《西游记》中,这种模式其实出现了多次,以后章回里的乌鸡国故事与天竺国故事也呈现了相同的模式:“乌鸡国国王/王子:恶人试图谋杀国王:国王复生:恶人受惩:家庭团聚”以及“天竺国王/公主:邪恶妖精试图谋杀公主(妖精用风将公主运走):公主归来:妖精受惩:家庭团聚”。严认为这种模式的重复“似乎暗示着《西游记》作者在写作技法上有意识地接受了流行传统中一种固定的形式”。而运用这种固定的形式来写不同的故事正可以体现《西游记》作者一种文学改编的技巧。[8](201)
三、《西游记》前身考与“帕里—洛德口头理论”
杜德桥著作《十六世纪中国小说<西游记>前身考》以相当篇幅梳理了业已被发现的十六世纪小说《西游记》形成以前的“西游记”文本、图像材料:《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刘克庄《释老六言十首(其四)》、泉州开元寺南宋西塔猴形神将图及“龙太子”图、永乐大典本“魏征梦斩泾河龙”平话残文、朝鲜崔士珍《朴通事谚解》以及一些“西游记”戏剧和宝卷等。[9](25−100)这些材料已为学界知悉,无需详述。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材料的态度。杜氏在其书导论中引述到西方口头文学研究领域著名的“帕里—洛德口头理论”(the Parry-Lord Oral Theory),其为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与其学生阿尔伯特·贝茨·洛德(Albert B.Lord)共同提出,反映在洛德1960年出版的著作《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之中。该理论通过对南斯拉夫史诗歌手的田野考察研究了口头文学传统:口头传统远离书写传统,歌手吸取同行优点、根据听众需要、或是即兴发挥,在表演中随时对作品进行再创造,史诗在他们口里的传承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10](17−39)如果歌手利用固定文本来识记歌词,被书写传统限定的形式和措辞所束缚,就意味着口头文学的消亡。[10](197−198)根据这个理论,杜氏认为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亦包括口头传统和书写传统,只是后来随着印刷业的繁荣,固定划一的文本抹去了口头传承的特色,逐渐使其消失,例如固定的话本就抹去了口头文学传统中说话艺术的多变性。杜氏指出,在某些白话故事形成的源流中,有许许多多的人物曾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发挥了作用,但当我们追溯这个源流的时候,“采用书写和印刷方式之人轻易地在我们心中占据不公平的优势:他们有力地垄断了我们使用的材料。”[9](10−11)而源流中那些口头传承者则大多湮灭不闻。杜氏认为《西游记》的形成过程就有这样的情况,研究者在考察其书前身源流的时候,资料的获取只能依靠手写或印刷的书面材料,但必须认识到口头文学对于《西游记》的重要,承认书面文献的局限。[9](11)
这种态度使得杜德桥对学界有关孙悟空原型的种种推测深表怀疑。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日本、欧美学界对孙悟空原型作出种种推测:有《补江总白猿记》中的白猿、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龙济山野猿听经》的猴精、神话中水怪无支奇、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9](114−164)杜氏认为这些推测仅在书面文献之间作平行的对比,阐述一些所谓的相似性来作出推论,难令人信服。这些推测缺乏口头材料来描述从原型演变到现状的过程,书面文献较之口头文学的多样性远为简省,很可能会忽略、歪曲人物原型的演变过程中某些重要的元素。杜氏说:“口头媒介有其自身的规律。有了足够的第一手材料,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我们或许就能追踪不同口头故事之间主题的传承;在一个更广的范围,我们或许还能追踪某些神话从一个文明到另一个文明的传播。但是我们只能使用与口头材料截然不同的书面小说……特定故事基本要素的形式就会显得简单概括得多,这在更后的书面版本中还可能常显出意义的扭曲失衡。所有这些就是说,仅有书面剧本和小说文本构成我们现在的《西游记》以及与之类似传说的材料体,我们可能不能指望开展一项有效的人物原型研究,如孙悟空原型研究。”[9](154)
杜德桥以上观点在欧美学界引起过质疑,1971年8 月、1972 年 8 月,夏志清[11](887−888)、余国藩[12](90−94)有该书书评发表,认为“帕里—洛德理论”产生的背景与中国口头文学环境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该理论是基于对许多彻底与文本世界隔离的南斯拉夫歌手所作的调查而提出的,这些歌手很多不认字,但是中国口头文学艺人普遍识字断文,而且与书面文献紧密相连。两篇书评发表间隔的1972年2月,杜氏在《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过一封公开信,承认中国口头文学艺人的文化程度,他解释说:“我并非如书评宣称将‘与书写传统的脱离’归于‘口头艺人’,而是归于‘口头传播’。” 他认为“帕里—洛德理论”可以为中国口头文学研究者带来如此一种“中肯的警示”,即强调口头、书写文学是两种彼此脱离的传承,而“真正的职业口头艺人,不管识字与否,即使有著名的书面版本存在,也会保持有自己的艺术独立以及超越文本束缚的自由。”[13](351)平心而论,在“帕里—洛德理论”提出刚刚十年之后,杜德桥就将它引入中国文学研究,揭示口头文学在考察故事源流时的重要性,指出传统学术在依靠实物、书面文献方面的局限性,此一作用是积极的。不过如何恰切使用该西方理论去处理中国文化的问题,尚需仔细琢磨,杜氏书中使用“帕里—洛德理论”有过于机械之处,如果没有后来的解释,确实会让人产生如夏、余二先生的感觉。
四、孙悟空原型研究的反思与新解
上文述及杜德桥《前身考》质疑当时孙悟空原型的推测,他后来的文章《<西游记>的猴子与最近十年的成果》(以下简称《成果》)又继续质疑了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后期学界对此问题作出的新推测,主要是日本学者矶部彰及其赞同者提出的孙悟空形象源于福建神猴信仰的说法。[14](264−265)与《前身考》不同的是,在《成果》中,杜氏不再将质疑统归为口头材料的缺乏,而是作出了更为缜密的思考,他思考这些推测基于证据所运用的学术方法。他认为《西游记》原型研究里存在两种证据:本证(primary evidence)和旁证(circumstantial evidence)。“本证缓慢并少量地积累;旁证迅速并大量地积累。本证安上了一条不灵活、不舒坦、不自在的规则;旁证则创造出热情、朦胧而愉快的光辉。本证牢牢并永久地保持在讨论的中心;旁证随着个人观点和偏好的闪现而来去自由。最终,对于我们问题的解答只能依靠本证;而直到那时,我们还将十年又十年继续用我们头脑里新生出来的旁证去填充新的著作。”[14](255)他指出唐僧原型研究依据的是本证:玄奘前去印度学习取经的史实,所有研究者都是围绕它展开论述,这就是所谓的“规则”,这样的研究虽然单调,但最终有明确的定论。孙悟空的原型研究则不同,因为缺乏一个公认的证据,学者各自提出自己的旁证:从《西游记》以外文献中找出一个或几个猴子形象,利用外证与孙悟空对比,发挥联想,论证原型,这样的研究方法虽然兴致勃勃,新见迭出,但难得定论。
杜德桥试图以新方法对孙悟空原型问题作出解释。在《前身考》里,他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在《西游记》里“为什么一个民间流行的宗教偶像(指玄奘)要有奇怪的动物随从,并且为什么猴子在中间特别杰出。”当时他自己对这一问题并不能深入解答,只是笼统地归为“喜剧元素”。[9](166)在《成果》里,他参考了有关台湾、香港、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地方传统社区里宗教风俗的实地考察材料,发现在这些社区里的葬礼仪式中,当灵柩被抬去墓地时,人们往往扮作各种动物为其开道,此俗自古就有。人们相信逝者的脆弱的灵魂在西去极乐世界的道路上是凶险多难的,途中需要动物神保护驱魔——这是以上仪式的主题。而《西游记》里易被伤害的玄奘西去求取正果的路上正是由动物随从相伴,与以上仪式主题完美对应,杜氏认为这一主题很可能就是小说的隐喻意义。那么为什么猴子在其中特别杰出?他的解释是《西游记》中有孙悟空偷盗仙桃的情节,仙桃在中国文化中是长生的象征,它也是逝者前往极乐世界的护身符,逝者如想通过一个动物神得到它,那么猴子无疑是最有用的。这就是杜德桥给出的孙悟空原型分析,当然这也非定论,杜氏亦承认自己也运用了旁证:宗教风俗现象的考察。但与以前研究者思路不同,他已不再寻找《西游记》以外文献中的猴子形象来与孙悟空作类比,而是挖掘故事内部所隐寓的意义,并论述猴子对于此意义的重要性,按他自己话就是“故事内部的鉴定”。[14](271−274)
杜德桥有关孙悟空原型研究的反思与新解具有学术史眼光,我们不妨将之与余英时名文《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所论的大观园原型研究相比较。余氏认为红学考据派在“自传说”典范的影响下,利用小说以外文献材料考证大观园在现实中的地点问题,但是始终难以避免“南北混杂的严重矛盾现象”,这是该派学术上的危机。要超越这一危机,必须建立新典范,其方法是将“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造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从文学的构思考虑大观园的产生。[15](150−153)这种新典范的方法与杜氏的观点相通,杜氏同样认为从外证的考据永远无法获得孙悟空最终确凿的原型,应该另谋出路,试图通过分析文本内容结构探索小说隐寓意义,进而再证明猴子对这一意义的重要性。从欧美学界来看,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杜德桥的此种主张有一定相契之处。例如余国藩致力于探讨《西游记》宗教哲学寓意,认为小说中蕴含着儒释道三教的“修心”观念,而孙悟空形象的设定和中国习语“心猿”一词有相当的关联。[7](272−274)余氏的具体观点虽和杜德桥相差颇大,但他们二人从小说内部的寓意来探索人物原型的研究思路却是相同的。
[1]竺洪波.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2]柳存仁.〈四游记〉的明刻本[J].新亚学报, 1963, (2): 323−375.
[3]LIU Ts’un-yan.The prototypes of “Monkey (Hsi Yu Chi)” [J].T’oung Pao, 1964, (51): 55−71.
[4]杜德桥.〈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J].新亚学报, 1964(2):497−519.
[5]杜德桥, 苏正隆, 译.百回本〈西游记〉及其早期版本[C]//中国文学论著译丛.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85.
[6]柳存仁.〈西游记〉简本阳本, 朱本之先后及简繁本之先后[C]//和风堂新文集.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7.
[7]余国藩.李奭学译.〈西游记〉的叙事结构与第九回问题[C]//〈红楼梦〉, 〈西游记〉与其他: 余国藩论学文选.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8]ALSACE Y.A technique of Chinese fiction: Adaptation in the“Hsi-yu chi” with focus on Chapter Nine [J].Chinese Literature: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79, (1): 206−212.
[9]GLEN D.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0]阿尔伯特·贝茨·洛得.尹虎彬, 译.故事的歌手[M].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1]HSIA C T.Book review: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1, (30): 887−888.
[12]ANTHONY C Y.Hsi-yu Chi and the tradition [J].History of Religious, 1972, (12): 90−94.
[13]GLEN D.Communications [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72, (31): 351.
[14]GLEN D.The Hsi-yu Chi Monkey and the Fruits of the Last Ten Years [C]// Books, Tales and Vernacular Culture: Selected Papers on China.Leiden·Boston: Brill, 2005.
[15]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C]//余英时文集·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新一代江格尔奇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