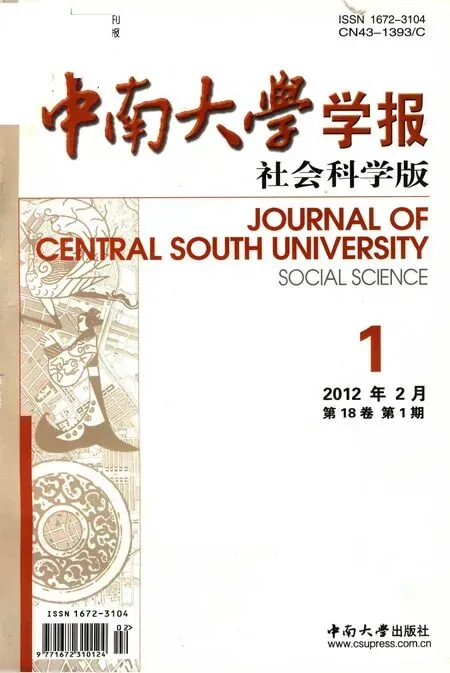唐代客籍文人涉蛮诗研究
肖献军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
唐及唐前对周边少数民族称夷、羌和蛮。夷分布在东部或东北部,称之为东夷;羌分布在北部或西北部,称之为西羌;蛮分布在南部和西南部,称之为南蛮,所以《后汉书》中有《东夷列传》《西羌列传》和《南蛮列传》。据《后汉书》载,南蛮包括武陵蛮、长沙蛮、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夷等。这种称呼也不是绝对的,《后汉书》中又有《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包括夜郎、滇、哀牢、邛都、莋都、冉駹、白马氐等。但《后汉书》中的西南夷在《旧唐书》称西南蛮,在《新唐书》中则并入了《南蛮列传》中。因而本文中的“涉蛮诗”中的“蛮”相当于《后汉书》中的南蛮和西南夷,也即《旧唐书》中的南蛮、西南蛮或《新唐书》中的南蛮。《旧唐书》中有《南蛮西南蛮列传》,蛮包括“林邑、婆利、盘盘、真腊、陀洹、诃陵、堕和罗、堕婆登、东谢蛮、西赵蛮、牱蛮、南平獠、东女国、南诏蛮、骠国”等,[1](5269)《新唐书》中有《南蛮列传》,蛮包括“南诏、环王、盘盘、扶南、真腊、诃陵、投和、瞻博、室利佛逝、名蔑、单单、骠、两爨蛮、南平獠、西原蛮”等,[2](6297)其实这只是势力较大的蛮族,唐代还有许多较小的蛮族部落。据新、旧《唐书》载,唐代大大小小的蛮族部落不下百种,唐诗中“百蛮饮泽”[3]“百蛮朝骑日骎骎”“流歌彻百蛮”中的“百蛮”绝不是夸大之数。
唐代“百蛮”分布很广,据《新唐书》载,剑南道诸蛮州有九十二,江南道诸蛮州有五十一,岭南道诸蛮州有九十二,共计有235个州。[2](卷四三)这里所指的“蛮州”是指刺史或都督为蛮族首领且得世袭的州。这些州集中分布在戎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府、泸州都督府、黔州都督府、桂州都督府、邕州都督府、安南都护府、峰州都督府内,这还只是仅指蛮族的集中分布区,事实上更多的蛮族散落在其它各州,只不过这些蛮族与汉族杂居在一起,他们较少反叛,故《唐书》蛮传中没把他们列入,但在诗人眼中,他们居住地仍然是蛮区。这个蛮区包括江南西道的西部和南部,剑南道的南部,黔中道南部、岭南道的全部及南诏地区。有的诗人甚至把山南西道部分地区也称为蛮,但这只是沿袭前人的说法。事实上荆州地区在唐代基本上被汉化了,蛮风、蛮俗都已消失,荆州蛮已不复存在,荆州也算不上蛮区。因此这里所说的涉蛮诗主要是指文人在江南西道、剑南道、岭南道、黔中道及南诏等蛮区创作的诗歌。
由于蛮族大部分居于高山深壑中,语言、风俗都迥异于中原地区,经济条件极端落后,甚至还有裸蛮的存在,因此遭到汉族统治者极端诋毁。蛮,亦虫也,把他们与动物等同,甚至还写入正史之中。《后汉书》载:“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其后滋蔓,号曰蛮夷。……今长沙武陵蛮是也。”[4](2929−2830)蛮族不可能是人畜杂交的产物,这无疑是史家在刻意贬低。诸葛亮在征南蛮后,在凤迦异筑柘东城,并刻石曰:“碑即仆,蛮为汉奴。”[2](671)根本就没有把他们与汉民族同等看待。这种状况在唐时稍有改观,如武陵蛮、澧州蛮、长沙蛮虽然还存在,但正史中已经没有记载了。但对于蛮族集中的235个州,唐王朝依然以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
正因如此,蛮区在唐王朝的政治地位被边缘化了。对蛮族集中地区,唐王朝基本上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甚至有些蛮族在朝贡时狂妄无礼,皇帝也不去计较,各州刺史也由蛮族人担任,而且可以世袭,总之只要他们不添乱就行。而那些唐王朝保持了较强控制力的蛮族居住地区,则成了贬谪文人和下层低级文人的安置之地,刘禹锡在贬谪朗州期间所作的《武陵书怀五十韵》中写道:“邻里皆迁客,儿童习左言。”朗州正是武陵蛮的聚集地,可见蛮区在唐王朝中的政治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政治极度边缘化时,朝廷对该地的控制力也就会越弱,在蛮族集中的235个州和南诏地区,蛮族与唐王朝有很长时间都是敌对关系,因此唐王朝的用人制度和贬谪制度在这些地方很难行得通,到达这些地方的游宦文人和贬谪文人也就很少。唐代诗人“涉蛮”多数集中在唐王朝控制力较强的江南西道和岭南道蛮族居住区。如宋之问流钦州,沈佺期流驩州,张说贬岳州、李白流夜郎、王昌龄迁龙标、刘长卿贬南巴、刘禹锡贬朗州刺连州、柳宗元贬永州刺柳州、韩愈贬阳山和潮州、李德裕贬潮州和崖州等都是这样,这些唐代著名诗人并没有进入蛮族集中地区,他们进入的是唐王朝控制力较强的蛮区。
二
蛮区毕竟是未开发的地方,经济落后,民风剽悍,风俗与中原地区迥异,因而文人对蛮区存在畏惧心理。文人涉蛮大多是被动的,是外力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干预的结果,朝代更替、权奸擅政、朋党之争、宦者作祟、武人为祸等,是导致唐代涉蛮诗人增加的主要原因。还有部分文人涉蛮虽非受政治因素干扰,如文人从军、游历幕府等,但这些文人大多政治失意或生活困顿,涉足蛮区也非心甘情愿,可以说文人涉蛮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在心理层面上文人涉蛮诗有许多共同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涉蛮诗中普遍存在畏蛮心理。畏蛮心理主要来源于政权的威力。许多涉蛮诗人不仅要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还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特别是遭受贬谪的诗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他们再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对前途充满畏惧。如永贞革新失败后,元和元年(806)宪宗下诏:“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1](418)王叔文也在本年赐死于渝州贬所。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写道:“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5](762)如他在永州所作的《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等诗就表现了这种惴慄心理。
沿途的艰辛和危险、贬地环境的恶劣是文人畏蛮心理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蛮地荒远,沿途多高山险岭、激流深壑,且文人涉蛮多提家携口,许多文人还未至贬所就饱受病痛和亲人死别的凄苦,当他们到达贬所时,“炎荒万里,毒瘴充塞”的环境使得他们身心备受摧残,他们的诗歌也因此充满了对生命的忧虑感。如沈佺期神龙元年(705)年贬驩州途中所作的《入鬼门关》:“夕宿含沙里,晨行冈路间。马危千仞谷,舟险万重湾。”写出了涉蛮途中的艰辛及随时都面临的死亡威胁。项斯《寄流人》:“雾开蛮市合,船散海城孤。象迹频藏齿,龙涎远蔽珠。”则重点突出了流人对蛮地生活的不适而产生的畏蛮心理。另外,蛮地民风彪悍、动乱反叛较多、许多地方盗贼纵横,也增加了他们的畏蛮感。如岑参《阻戎泸间群盗》中写道:“南州林莽深,亡命聚其间。杀人无昏晓,尸积填江湾。饿虎衔髑髅,饥乌啄心肝。腥裛滩草死,血流江水殷。夜雨风萧萧,鬼哭连楚山。”面对这种环境,即使心理素质再好的文人只怕对蛮区也会充满恐惧感。
其次,涉蛮诗中还存在较强的骚怨心理。唐代诗人经历蛮区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走蜀道,这是一条陆上交通路线,包括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傥骆道、金牛道、米仓道等,一路多崇山峻岭,交通不太方便,唐代涉蛮诗人经历此道的不多,大多是本地作家由此而出川。另一条是从洞庭湖南下,沿湘江而至岭南地区,或者沿沅水南下而至黔中地区,这是一条繁忙的水上交通线,大多数涉蛮诗人都是走这条路线。屈原晚年正好流寓在这一带,因而这里受屈骚文化影响很深。文人在经历这一地区时,无疑会由屈原的身世命运联想自身,从而与之产生共鸣,由此在诗中表现出较强的骚怨心理。如景云二年(711)宋之问在贬钦州时作《过蛮洞》:“谁怜在荒外,孤赏足云霞。”表现出了诗人对抛弃蛮荒的怨恨和惆怅。长庆四年(824)李端由户部侍郎贬端州司马,途中作下了《涉沅潇》,诗人更是借屈原之事直指当朝小人,表现出了对自己无辜被害的愤恨:“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何不驱雷击电除奸邪,可怜空作沉泉骨。”柳宗元也是如此,《新唐书·柳宗元传》载:“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2](5132)元和三年(808)年,他在永州司马任上写下了《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也对自己无辜被贬表现了强烈愤恨。涉蛮诗中的骚怨精神是对屈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诗人报国无门的忧愤心理的集中体现,也是涉蛮诗中最具思想价值的部分。
再次,漂泊心理对于涉蛮诗人而言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中国是农业社会,诗人的乡土情结很重,“从社会心理的深层上说,乡土社会是拒绝迁徙的”。[6](84)文人常年在外内心总有不踏实的感觉,好像自己是随风的柳絮,不知飘向何方。对于涉蛮诗人而言,这种漂泊心理更强烈,这些诗人长时间流寓在外地,饱受人世艰辛和世态炎凉,而且前途无望,感觉自己如飘蓬一样。特别是在刘长卿、杜甫、戎昱、张祜、李咸用、杜荀鹤、黄滔、刘昭禹等中下层文人的涉蛮诗歌中,表现更为明显。如张祜“早工篇什,研几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7](169)但一生以处士终,有较长时期流寓于蛮区,他的《湘中行》:“南去长沙又几程,二妃来死我来行。人归五岭暮天碧,日下三湘寒水清。远地毒蛇冬不蛰,深山古木夜为精。伤心灵迹在何处,斑竹庙前风雨声。”(《全唐诗补编上》)就充满着漂泊感。除了上述原因外,涉蛮诗中的漂泊感也与蛮区自然、经济条件恶劣相关,诗人到达蛮区后很难适应蛮区生活,时时把自己视为异乡人,这也增加了他们诗中的漂泊感。如“三湘漂寓若流萍,万里湘乡隔洞庭”(戎昱《湖南春日二首》、“年华蒲柳凋衰鬓,身迹萍蓬滞别乡”(李咸用《和人湘中作》)、“万里飘零十二秋,不堪今倚夕阳楼”(殷尧藩《九日》)等涉蛮诗漂泊感都很强。
当文人在蛮地漂泊时间较久时,他们心中会升起回归家乡和帝都的愿望。对于诗人而言,家乡是他们自幼生长的地方,这里有他们的亲人、朋友,家乡的山山水水都深深印入了他们的脑海中。屈原《哀郢》:“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8](330)汉无名氏《古诗十九首》:“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都是思乡情结的体现。同时,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功名和家同等重要,而要实现自己的功名又往往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帝乡”一词在唐诗中出现频率非常高,恐怕诗人不仅仅视之为“帝王之乡”,而大有把帝都当作第二故乡的想法。因而在涉蛮诗中,思家和恋阙经常交织在一起,如李德裕《谪岭南道中作》:“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与普通诗相比,由于涉蛮生活极度痛苦,诗人的思归感也就更强烈,往往和血泪交织在一起,如“岭头无限相思泪,泣向寒梅近北枝”(李德裕《到恶溪夜泊芦岛》)、“生还倘非远,誓拟酬恩德”(宋之问《早发大庾岭》)。甚至有时候他们的思家恋阙之情,与其说是希望在事业上再次有所作为,不如说他们只是想尽快摆脱漂泊蛮区的痛苦,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
三
虽然涉蛮诗在整体上呈现出许多共同特征,但由于时代环境、个体情感特质及贬谪之地条件的不同,故不同诗人创作的涉蛮诗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下面就唐代创作涉蛮诗较多的几位诗人作简要评述。
(一)王昌龄与龙标诗
龙标属叙州潭阳郡,地处黔中道,其地与夜郎相接,有巫州獠、辰州蛮、五溪蛮和叙州蛮杂居于此。《新唐书》载王昌龄贬龙标尉是由于“不护细行”,[2](5780)《唐才子传》载同。但其友人常建说:“谪居未为叹,谗枉何由分。”他自己也说:“谁识马将军,忠贞抱生死。”则其被贬或为冤屈,因而诗中也有骚怨心理,如《为张僓赠阎使臣》:“哀哀献玉人,楚国同悲辛,泣尽继以血,何由辨其真。赖承琢磨惠,复使光辉新。犹畏谗口疾,弃之如埃尘。”虽是在写友人,但诗中也寄寓了个人身世之悲。
王昌龄虽有怨恨,但并没有陷入无穷的痛苦中。他的涉蛮诗充满着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来源于诗人对自己才能的充分肯定和大唐盛世培养出的高蹈扬厉的人生态度。虽然面临仕途坎坷、远谪蛮荒的现实,但残酷的现实并没有使他沉沦,相反却激起了他的斗志,在他的诗中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和执着的追求,如“明祠灵响期昭应,天泽俱从此路还”(《别皇甫五》)、“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龙标野宴》)、“远谪谁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乡”(《送吴十九往沅陵》)、“谴谪离心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送崔参军往龙溪》)等。在涉蛮诗人中,能像王昌龄一样保持如此乐观人生态度的实在不多。
(二)刘禹锡与朗州诗
永贞元年,顺宗继承皇位后,果断任用王叔文等人实行变法。由于革新派在朝中无甚根基,顺宗又染瘖疾,加上革新幅度大,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变法持续了几个月就失败了,刘禹锡就是在这次政治事变中被贬谪于朗州的。朗州是武陵蛮的集中地,在唐代属于江南西道,从《后汉书》看,诸蛮皆是由武陵蛮繁衍而来,东汉时期武陵蛮叛乱频繁,但从三国时起叛乱逐渐减少,唐时史书不再载有武陵蛮叛乱事例,但武陵蛮依然散落在朗州一带。
与其他涉蛮诗人相比,刘禹锡的朗州诗呈现出两个新的特征。一是不屈的革新精神,这种精神来源于革新的进步性和他刚直的人格。革新失败后刘禹锡生命遭受了威胁,但他依然对朝中新贵进行冷嘲热讽,写下了《鶗鴂吟》《萋兮吟》《聚蚊谣》《百舌吟》《飞鸢操》《秋萤引》《白鹰》等诗,在《酬元九院长自江陵见寄》中写道:“无事寻花至仙境,等闲载树比封君。金门通籍真多士,黄纸除书每日闻。”诗中用充满激愤的语言对那些破坏革新的新贵进行了强烈讽刺,讽刺了他们投机钻营的卑鄙行径。二是与蛮同乐的思想。刘禹锡初到朗州时,也有畏蛮心理,但他性格达观豪爽,故不像柳宗元等人那样充满“惴慄”之感。加上他在朗州时间长达十年,对蛮族的生活开始逐渐适应,对蛮风蛮俗由排斥转变为欣赏接受,表现出了与民同乐的思想。据《旧唐书》载:“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1](4210)《莫徭歌》《蛮子歌》《踏歌词四首》《龙阳县歌》《竞渡曲》《堤上行三首》《采菱行并引》《秋风引》《清湘词二首》等就是刘禹锡所作新辞。从这些新辞中可以看出刘禹锡与当地蛮族忧乐与共、关系融洽。这些新辞语言通俗、幽默,随物感兴,往往调笑而成,充满生活气息。
(三)柳宗元与柳州诗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出为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卒于任上,前后在柳州有四年,柳州属于岭南道,是个蛮族杂居的地方,主要有峒氓、林邑蛮和牂牁蛮等。用柳宗元的话说这里是“百越纹身地”,不仅语言难通,而且蓄奴、劫掠贩卖人口之风盛行。他在《寄韦珩》中写道他刚到任时的情形:“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因此柳宗元不是一般的畏蛮,而且还对蛮族有敌视态度,他在《柳州峒氓》中说:“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寄韦珩》:“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描画出了当时官、蛮之间紧张的关系。
但柳宗元在认为蛮“不可亲”的同时却尽力化蛮、惠蛮,他在任柳州刺史期间废除买卖奴隶的陋习,重修孔庙,种柳树、植柑橘、凿深井,最终使柳州“皇风不异于遐迩,圣泽无间于华夷”(《谢除柳州刺史表》),[5](1001)他在《种柳戏题》中写道:“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柳宗元的化蛮、惠蛮思想是与永贞革新思想相一致的,是永贞革新思想在局部地区得以实行的体现。正因为柳宗元的到来,使得柳州地区开始由野蛮走向文明,在他死后三年,柳州人捐资修建了罗池庙,并立碑以纪其功绩,碑曰:“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髙无干。秔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9](494−495)
(四)雍陶与益州诗
雍陶是成都人,成都在唐时属剑南道之益州,益州本是个蛮族居住地,《后汉书》中的益州蛮就散居于此,但经过西蜀政权后,就如同荆州蛮一样,益州蛮被汉化了,在唐代这里已经算不上是蛮区了。但雍陶在年轻时,却“被涉蛮”了一次。据《唐诗纪事》载:“杜元颖为西川节度使,治无状。文宗大和三年,南诏蛮嵯巅乃悉众掩邛、戎、嶲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掠子女工技数万而南。”[10](1530)雍陶在文宗大和三年(829)和大和四年(830)先后作下了《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蜀中战后感事》《答蜀中经蛮后友人马艾见寄》等数诗,其中《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写得尤为感人。如《别巂州一时恸哭,云日为之变色》:“越巂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便为蛮。冤声一恸悲风起,云暗青天日下山。”《入蛮界不许有悲泣之声》则写道:“云南路出陷河西,毒草长青瘴色低。渐近蛮城谁敢哭,一时收泪羡猿啼。”这些诗歌深刻反映了唐王朝和南诏之间的战事给边地百姓带来的痛苦,具有史诗意义。在唐代诗歌中反映唐王朝与南诏之间战争的诗篇有许多,如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这些诗有很强的政治讽喻功能,但由于诗人没有亲历战事,对边地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灾难感受不深,故诗歌的感人深度反不如雍陶诗。
四
唐代蛮族诗人较少,创作诗歌更少,他们长期居于蛮区,往往对家乡风物“熟视无睹”,因而他们的诗基本上不能反映蛮区生活的实际情形。而大量的涉蛮诗不仅抒写了诗人在蛮区生活的痛苦,而且从多方位全面反映了蛮区的民情风俗,从而使得涉蛮诗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同时,诗人的涉蛮经历对于创造弱势地区的强势文化及提升蛮区的文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涉蛮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唐代蛮区特别是蛮族集中的地区,文化相当落后,许多蛮族都没有文字,没有能力保存自己的文化,而汉民族对这些蛮族往往采取歧视的态度,他们在正史中对这些民族的文化记载十分简略,这给我们今天全面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带来较大的困难。而唐代文人的涉蛮诗由于数量较大,反映面较广,因而保存了相当多的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这些地方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资料包括蛮区的政治资料、蛮族与汉民族关系资料、蛮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资料、蛮区的民俗风情资料等。如韩愈《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就较详细记载了岭南蛮区的饮食情况:“鲎实如惠文,骨眼相负行。蠔相粘为山,百十各自生。蒲鱼尾如蛇,口眼不相营。蛤即是蝦蟆,同实浪异名。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惊。”想要了解唐代岭南蛮区的饮食习惯,通过韩愈这首诗可以找到,而这些资料在正史中是很少有记载的。
涉蛮诗也具有不同于一般诗歌的审美价值。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1](576)韩愈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揭示出了自然环境和人际遭遇与诗歌的创作关系。[9](262)涉蛮诗人大多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他们用诗歌记录下了涉蛮期间的心路历程,创作出了极具感染力的诗篇。如李德裕的《到恶溪夜泊芦岛》:“甘露花香不再持,远公应怪负前期。青蝇岂独悲虞氏,黄犬应闻笑李斯。风雨瘴昏蛮日月,烟波魂断恶溪时。岭头无限相思泪,泣向寒梅近北枝。”这是用血和泪写出来的诗,它的艺术感染力不是那些宫廷诗所能比的,也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抒情言志诗,如果不是诗人亲历蛮区,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强的感染力的诗篇的。不只李德裕的诗是如此,宋之问贬钦州的诗、张说贬岳州的诗、刘长卿贬南巴的诗、刘禹锡贬朗州和刺连州的诗、柳宗元贬永州和刺柳州的诗莫不是如此,这些诗代表了他们诗歌的最高成就,即使放在整个唐诗中也毫不逊色,并且至今依然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
唐代涉蛮诗还有很强的功利价值。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类现代文明不断吞噬着原始文明,刚开始时人类还为这一点沾沾自喜,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人类文明需要多样化,单一的文明不能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因而复原蛮族地区原始文明,开展原生态旅游越来越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如,2011年5月23日,湖南省旅游局召开《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发展规划大纲》征求意见会,就体现了对原生态旅游的重视。大纲指出,要建设好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就必须抓住大湘西生态、文化两大特色,特别是文化方面要受到重视。湘西地区在古代是武陵蛮、澧州蛮、溆州蛮、辰州蛮居住的地方,要开展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就要恢复这里居民的一些原生态生活。正史对他们的生活虽有记载,但十分有限,要详细了解当时生活情况,还需要加强对涉蛮诗的研究。如李商隐在《射鱼曲》中写道:“思牢弩箭磨青石,绣额蛮渠三虎力。寻潮背日伺泅鳞,贝阙夜移黥失色。”记载了湘西蛮区用弓箭猎鱼的生活,而且当地人还有绣额的习俗,这些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它极具观赏性,如果能够开发出来,必将成为当地生态文化旅游的一大亮色。唐代涉蛮诗的功利价值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不少涉蛮诗中还写到了地域性极强的民俗,如竞渡、赛神、驯象等,这些对于丰富和发展地方民俗活动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这些功利价值的挖掘还有待于对涉蛮诗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除了多样性价值外,涉蛮诗人和涉蛮诗的大量出现对于提高蛮区的文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首先,创造出了弱势文化地区的强势文学。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南蛮地区不重视,导致了蛮区文化极端落后,许多蛮族居住地区文学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在较长时间里出现停滞状态。以洞庭湖地区为例,据现存资料统计,唐前没有一个本地作家,文学的发展处于空白状态。即使到了唐代,本地作家也远不如关中、山东、吴越地区多,属于文化弱势地区。但在唐代由于许多文人贬谪于该地,无论是诗歌的数量还是艺术感染力,洞庭湖地区的文学都不弱于上述文化底蕴深厚的三大区域,从而创造出了文化弱势地区的强势文学。虽然岭南地区、剑南地区和南诏地区涉蛮诗不及江南西道地区多,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文人涉足于蛮区,改善了该地区本土文学发展落后的状况,提升了蛮区文化发展水平。
不仅如此,面对蛮区文化落后的状态,涉蛮诗人还试图努力改变它。如韩愈之任潮州刺史、柳宗元之任柳州刺史、刘禹锡之任连州刺史期间,在任所办乡校、兴教育、除陋习、修水利,对于提高当地经济文化水平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甚至亲为人师,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9](512)韩愈本人也以好为人师著称,他贬阳山令及潮州刺史时,多和当地年轻文学之士有交往,对他们提携更是不遗余力。中唐以后,江南西道、岭南道、剑南道及黔中道地区本地文人增多,与这一时期涉蛮诗人的大量到来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此以后蛮区的本土文学才真正发展起来。
王世禛在《艺苑卮言》卷八中说:“古人云:‘诗能穷人。’究其质情,诚有合者。今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不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佳。”[12](389)对诗人而言涉蛮生活是一段痛苦的人生历程,但也正是经历了情感的痛苦才成就了他们诗歌创作的高峰,同时,他们的涉蛮经历及涉蛮诗作部分改变了蛮区文学落后的状况,促进了蛮区本土文学的发展,对于提升蛮区整体文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5.
[2](北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5.
[3](清)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 中华书局,1960.(本文所引诗歌,除特别注明外,所出皆与此同)
[4](宋)范晔撰.《后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65.
[5](唐)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 中华书局,1979.
[6]李浩.《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J].《文学评论》,2005:2.
[7]傅璇宗等校笺.《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M].北京: 中华书局,1990.
[8]蒋天枢校释.《楚辞校释》[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宋)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下册[M].成都:巴蜀书社,1989.
[11](南朝)刘勰撰,杨明照校注.《订增文心雕龙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明)王世贞撰,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M].济南: 齐鲁书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