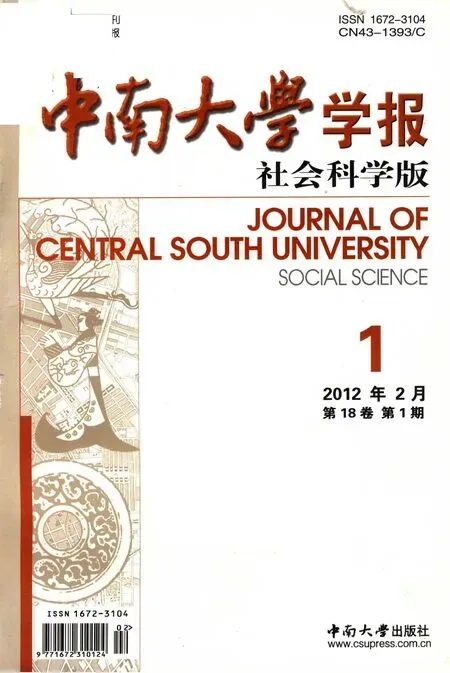“Bildung”和“教化”概念辨析
张颖慧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250100)
“Bildung”在伽达默尔的理论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作为人文主义四概念之首出现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称之为“18世纪最伟大的概念”,并且认为“正是这一概念表现了19世纪精神科学赖以存在的要素”。美国学者Nicholas Davey在研究伽达默尔的著作《Unquite Understanding》一书中指出:“Bildung这个概念在哲学诠释学中起着核心的作用。”[1](37)有学者将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称之为“教化(Bildung)解释学”[2](44),虽说这一称呼有待商榷,但是“Bildung”之于伽达默尔理论的重要性确实毋庸置疑。
然而这一德语词汇,却使汉语以及英语世界都遇到了解释的困难。英语词汇中没有单词可以诠释Bildung的涵义,因此《真理与方法》的两个英译本均不翻译,采取直接引用的方法。不可否认,德语和英语有一定的相通性,而且英语中有和 Bildung相近的词汇,如Bildungsroman(教化小说),因此,这种翻译方法并不会给读者造成理解的困难。然而,对于和德语有着巨大差异的汉语来说,这种翻译方法则很牵强。鉴于该词具有教育、培养、文化、修养等方面的涵义,商务印书馆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真理与方法》均将“Bildung”翻译成“教化”,并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但是,“Bildung”并不等同于“教化”,如果完全忽略两者的相异之处,就会造成理解的困难,甚至学术对话的障碍。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中文的“教化”和伽达默尔 Bildung的意义差别,以推进专业领域内更好的理解和对话。
一
“教”与“化”在荀子之前都是分开使用的。《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3](127)《尚书·皋陶谟》:“无教逸欲。”蔡沈谓“教”:“上行而下效也。”《说文解字》:“化,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3](384)由此看出,中文的“教化”是一种从上到下的行为。
“教化”作为一个词汇首次出现在《荀子》中,如:
“养六畜,闲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荀子·王制》)
“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辟公之事也”(《荀子·王制》)
“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是圣臣者也。”(《荀子·臣道》)
“尧舜者,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荀子·性恶》)
“教化”作为乡师之事、辟公之事,有专员专司其责,是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后世之“教化”大体沿用了这一层面上的意思,如汉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陆贾:“教化不行,而政令不从。”(《新语·怀虑》)并明确指出:“要以上化下,下从上为准。”董仲舒称:“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色……”(《汉书·董仲舒传》)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某将灭人种也,则必上之于议院,下之于报章,日日言其种族之犷悍,教化之废坠。”当前流行的辞书也强调“教化”的政治含义,《辞源》《辞海》《教育大辞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对“教化”的首要释义便是“政教风化”,《教育大辞典》简编本更是明确将“教化”解释为:“中国古代政治和道德教育有机结合的一种统治术。”因此,中文的“教化”是一种上行下效的政府行为。
但伽达默尔的 Bildung则是无关政治的,它是主体主动性的行为。Bildung起源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后为巴洛克神秘教派所继承,通过克洛普施克那部的史诗《弥赛亚》得到其宗教性的神秘意蕴。按照这种神秘主义传统,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的灵魂里带有上帝的形象,而且必须在自身中造就这种形象。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把 Bildung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他指出要“达到人性的崇高教化”。在此基础上,黑格尔提出Bildung就是脱离人的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从而舍弃特殊性向普遍性提升。
在黑格尔的基础上,伽达默尔从解释学的角度丰富了Bildung的内涵。他指出Bildung包括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理论性的教化(Bildung)在于学会容忍异己的东西,并去寻求普遍的观点,以便不带有个人私利地去把握事物”。[4](25)个体在与外在的交往中接触到陌生的东西,形成对自身的否定,然而个体不是逃避这种否定,而是积极地反思自身,从而舍弃掉自身的特殊性,完成向普遍性的提升。因此,否定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是有意识地自我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要付出艰苦的努力,通过学会容忍异己的东西,在他物中重新发现自身,返回到自身。对于实践性的教化(Bildung),在评述黑格尔“劳动的本质”的观点时,伽达默尔指出:“劳动着的意识的自我感包含着组成实践性教化(Bildung)的全部要素。”[5](13)劳动是对物品的塑造,然而劳动的过程也体现了人自身的能力和技能,因此,劳动者可以在劳动中获得一种自我成就感,并找寻到自身的意义,从这个方面说,劳动也是对劳动者的塑造。实践性的教化(Bildung)就在于获得这种自我感。因此,总体来讲,Bildung是主体主动地认识自己、塑造自己的过程。
而且,这一过程是通过与他者的平等对话获得的。伽达默尔指出,教化(Bildung)的特征就在于为他者、为其它更普遍的观点敞开自身,只有通过他者才能实现对自身的否定和提升。因此,主体和他者的关系,不是简单地效仿或顺从,对话也不在于以一个人的意见去反对或补充对方的意见,“真正的对话改变的是双方的观点。一场对话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人们不会再回到谈话之前的不一致状态”。[6](96)自身与普遍性是有距离的,而 Bildung就在于超越自身向普遍性提升,这种提升只有通过个体与他者的对话才能实现。
因此,从实施者的角度讲,中文的教化是不同于伽达默尔的Bildung的。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行为,它是从上到下的,而后者则是主体自身积极主动的自我塑造,并且这一行为是在与他者平等的对话中实现的。
二
中文的“教化”是以礼乐制度和伦理规范为内容的道德教育。中国向来很重视“教化”的德育功能。《左传·文公十八年》在谈到舜治国时说:“舜臣尧……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对于此处的“文”,朱熹《论语集注》:“道之贤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汉代的教化也以德为主,贾谊就认为:“四德: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德不张,国乃灭也。”汉武帝时,董仲舒则以六艺,即《诗》《书》《礼》《乐》《义》《春秋》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三纲》《五常》的行为原则。这些道德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培养人们的礼义廉耻,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和个人修养。《北史·苏绰传》对教化的描述很好地表明了教化的这一作用,“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日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之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为化也。然后教之以孝悌,使人慈爱;教之以仁顺,使人和睦;教之以礼仪,使人敬让,此之谓教也”。
而这种德育功能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在一定程度上讲,教化和刑罚一样,是统治者统治的政治手段。孔子就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西汉的贾谊也强调:“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新书·大政下》)西汉的董仲舒也主张:“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以不相顺,故君子重之也。”(《春秋繁露·精华》)“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以后的历代王朝也都以法制和德治相结合为治国方略。德治相比于纯粹的法制来讲,是以民为本的,但是其最终目的依然是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统治者的统治。而且统治者的教化既有启发民智、提升个人修养的作用,也有愚民,培养顺民、淳民的倾向,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韩愈也主张培养顺从统治者的淳民,“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示德,民以示淳”。[7](132)从这种角度讲,中文的“教化”有提升个体自身修养的功用,但其更重要的目的则是政治统治和社会的稳定。
伽达默尔的 Bildung则不以政治统治的社会功能为旨归,它首先着眼于个体,以个体的提升为目的,进而获得人类整体素质的提高。人的教化(Bildung)虽然要经历异化,但其最终目的是向自身的返回。伽达默尔指出:“构成教化(Bildung)本质的并不是单纯的异化,而是理所当然的以异化为前提的返回自身。”[4](26)这就是精神的基本运动,即“在异己的东西里认识自身,在异己的东西里感到是在自己的家”。[4](25)在异化和回归的过程中,我们重新发现自身,在自我成形过程中,我们所吸收和同化的文化传统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构成我们新的家园。在教化(Bildung)过程中重要的不是我们学到了新的东西,而是将这种新的东西整合到自身的生活实践中去。在一定程度上讲,中文的教化就是统治者实施统治的工具,而 Bildung则不具有这种外在的工具性,伽达默尔说:“在教化(Bildung)中,某人于此并通过此而得到教化(Bildung)的东西,完全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4](22)而且教化(Bildung)的过程是没有终点的。黑格尔认为这种异化和回归的辩证过程将在绝对的知识中达到完满的实现,伽达默尔指出:“黑格尔的答复将不会使我们满意。”[4](26)在他看来,终点虽是原来起点的终点,但它本身又是一个新的起点。Bildung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上升的过程,人们就在Bildung中不断提升自身。而且这种提升不仅限于道德的提升,而是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
由此看出,教化和Bildung具有不同的实施目的。教化更多着眼于政治统治和社会群体,它本身是统治者实施统治的工具,Bildung则首先立足于个体的自我提高,不具有外在的工具性。
三
就实现方式来讲,中文的“教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旨在通过外在环境的影响提升人的道德情操,现代辞书《辞海》和《四角号码词典》对“教化”的第二个释义便是“比喻环境影响”。
中国文化向来很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墨子在《所染》中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环境影响的过程就是“化”的过程。《说文》曰:“化,教行也。”《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因此,“教化”作为一个上行下效的行为,最终是通过“化”来实现的, 而“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改变人于无形之中,《管子·七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荀子在讲到“化”的特点时说:“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天论》)《礼记·经解》也说:“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8](479)所以,“教化”即统治者将各种政治思想和伦理规范在社会中推行,通过学校教育、家教家训、官府训导和宣扬礼教等形式构建一个社会环境,人们置身于此环境中,便会自然而然地受它的影响。因此,普通群众在被教化的过程中虽也有自己理解消化的过程,但在接受这些行为规范时,更主要的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对于受教化者来讲,中文的教化更多地是一种外在的影响。
而对于伽达默尔的Bildung,虽然要通过和他者的平等对话来实现,但主要是主体个人内在的精神活动。伽达默尔非常赞同威廉·冯·洪堡对Bildung和修养所作的区分,即“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语言来讲教化(Bildung),那么我们以此意指某种更高级和更内在的东西,即一种由知识以及整个精神和道德所追求的情感而来,并和谐地贯彻到感觉和个性之中的情操”。[4](20)Bildung作为异化和回归的过程,要舍弃特殊性,“即对欲望的控制,以及由此摆脱欲望对象和驾驭欲望对象的客观性”。[4](23)要“学会容忍异己的东西,并去寻求普遍的观点,以便不带有个人私利地去把握事物,把握‘独立自在的客体’”。[4](25)这就意味着主体要走出自身,超越自身,接触外在世界,但又不能在外在世界中丧失自身,而要返回自身,获得自我意识,达到普遍性。这整个的过程都是在主体的内在精神中进行的,Bildung是一种深刻的精神转变。
因此,伽达默尔的 Bildung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而是个体积极主动地通过与外在环境的交往舍弃特殊性、同化陌生性,然后返回自身,最终达到“超出自身而进入普遍性的提升”。而且这种提升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教化(Bildung)的结果总是处于经常不断的继续和进一步教化(Bildung)之中”。[4](21)
综上所述,中文的教化和伽达默尔的 Bildung虽有着很多共同点,如都是对个体修养的提升,都要通过与外在环境的接触来实现。但是其涵义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只有明晰这些差异,才不至于将两个概念混同,也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两个概念。
[1]Nicholas Davey,Unquite Understanding: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2]何卫平.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论纲[J].武汉: 武汉大学学报,2011,64(2):44-54.
[3][汉]许慎.说文解字注[M].[清]段玉裁,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5]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 [M].Translation Revised by Joe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Marshall.New York:Continuum,1995.
[6]Hans-Georg Gadamer.The Gadamer reader: a bouquet of the later writings [M].Edited by Richard E.Palmer,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7.
[7]韩愈.韩愈全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周礼·礼仪·礼记[M].陈戍国,点校.长沙: 岳麓书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