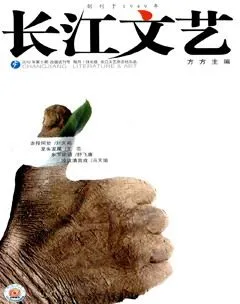我会很失望
梁晓声:知识分子不郁闷了,我会很失望
作家不老。
因为他们总是站在文字背后。任铅华尽洗,字字珠玑的思想力度,仍让读者觉得,那个写下这段段文字的人,还是乌鬓青丝、翩然年少、光芒四射,多少年过去,容颜不改、脾性不改,风范也不改。
在梁晓声的字里行间,岁月似乎就不曾留下痕迹。当年写《今夜有暴风雪》的那个人,今天依然将生命投射到平凡生命之中;当年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那个人,今天依然将目光叠加在现实目光之上。
许久不曾带来著作的作家梁晓声,今年3月推出了随笔集新作《郁闷的中国人》。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始终都是梁晓声作品的一大主题。哪怕已然鬓发斑白,他也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温情脉脉。在与他的对话中,他回避了柔软的一面,继续以一种愤青式的强硬,抗争着那些无法忽视的尖锐话题。
“我一直都非常郁闷。”在北京的一家酒店里,理应万事顺遂压力全无的梁晓声,并没有舒展眉头,露出多少闲逸的表情,反而满脸写着“忧国忧民”几个字,几乎以一种“一个都不原谅”的决然,谈论他所观察到的社会心态,以及他个人的生命经验。
一切的一切,都叫做“郁闷”。
一
采访约在六点半,但六点钟时候,梁晓声接到过去一个学生打来的电话。
学生在一家公司上班,加班,困,累,没法和老师说,于是发来一条短信,抱怨说“如果能够一觉睡过去,不再醒来,该有多好”。梁晓声问,既然这么累这么困,能不能请假?回答是不能。于是作家感慨:“即使这样的劳作,这些年轻人攒下的钱,别说买房,连养老都不够,怎能不郁闷呢?”
郁闷,不是梁晓声的发现,但是他鞭辟入里地阐释了这个词的内涵。郁闷是一种先天存在的心理基因,更是一种社会现实失衡的表征。自我意识的崛起,让郁闷浮出水面,这是近年来中国人越来越郁闷的原因。
梁晓声并不打算回到过去那个所谓的“理想国”,因为他深知,贫穷而平均主义的年代,郁闷并没有消失。他把目光投射到年轻人身上,投射到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智识者,并寄望于他们——如果这些人都只是囿于自身的小郁闷,而不去思考属于社会和时代的大郁闷,那么梁晓声真的该失望了。
范宁(以下简称“范”):新书为什么会定名为《郁闷的中国人》?
梁晓声(以下简称“梁”):我有一些朋友,不常聚,但是聚在一起,绝不是单纯地为了吃饭喝酒叙友谊,因为大家都很忙,聚在一起绝对是为了交流思想。哪怕只是喝喝茶、抽支烟,一定要有思想的碰撞。
大家都有困惑,不能自己判断,所以请有思想的朋友们来评判。和朋友的交流中,我忽然发现了“郁闷”这个词,慢慢就形成了书里的文章。
“郁闷的中国人”,这几乎是一个脱口而出、漫不经心得到的书名。如果我没有记错,“郁闷”这个词挂在中国人嘴边上已经很多年了吧?大家很早就在谈郁闷,我把它定为书名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觉得,它是一个有新意的名字。
范: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常常会把郁闷挂在嘴边,但如果时间回溯三四十年,这个词似乎没有今天如此“高频”。为什么当年不会有这种郁闷感?
梁:像我们这一代人,生下来所处的环境,大部分人都处在一个贫穷的状态。我们很多人会认为,这就是日常的生活。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上山下乡。其中有不少人盼着返城,哪怕是回来扫大街、扫厕所,他们也希望能回来。有朝一日,忽然就接到了返城的通知,而且下乡的那几年还能算工龄。没有想到的大命运就这样实现了。
而返城之后,大家面临的环境都是差不多的,所有人的工作差不多、工厂的工作环境差不多、收入也差不多,收入都很低,全中国大部分工人的工资都是三十几块钱。
当你身处一个庞大的群体中,他们的生活状态都跟你一样,你作为个体不会感到特别的失落。这就像长征,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爬雪山过草地,连首长也不过是多骑一匹马,彼此之间没有可比性,所以既没有特别的幸福感,也没有特别的不幸福感。
这种状态下人的心性,有点像非洲大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它们集体穿越河流,集体寻找食物,集体被天敌追逐,大家都是如此,没有谁会有不同的感觉。只有差别出现的时候,那种异样的感觉才会特别明显。
范:所以很多人都在怀念那个年代那种状态,觉得其实安贫的日子也可以过得挺舒心。
梁:那仅仅是一个表面,有很多现实并没有在回忆中呈现出来。你要知道,在从前,只要工资差上7元,有些人可以发疯、可以跳楼、可以自杀。为了这几元钱,可以走后门,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姿色。八十年代初,一些女孩子为了一双丝袜或者一副蛤蟆镜,就能够委身老外。不要以为穷就一定能愉快着。
范:郁闷是来自不公平的感觉吗?
梁:我们原来认为,公平意识是后天养成的。孩子长大后,才会对公平与否产生反应。但是根据外国社会学家的研究,人类长期繁衍而来,公平感其实是先天存在的。哪怕是两三岁的孩子,比如给他们糖果,有的孩子有很多糖果,而其他人则明显少很多,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明显的不公平的时候,孩子们的脑波和反应显示,他们也是不愉快的。所以追求公平对人类而言,可以说是一种本能。
平均主义也不是一种公平。因为平均主义简单到了极点,形成了另一种不公平。
范:您过去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现在您写《郁闷的中国人》,两部作品都与国民性有关系。那么郁闷仅仅存在于某一个阶层当中,还是在不同的阶层里,人们普遍郁闷着?
梁:一些影视明星,拍一部影视剧的片酬动辄八十万上百万;一个画家的画作可以卖出天价,这些人的郁闷相比别人,可能要少一些。但是在影视圈里,在绘画圈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个水平,许多人无法出头,许多人怀才不遇,机会落不到他们头上,你说他们不郁闷吗?
范:但是我想,您写作《郁闷的中国人》,应该不只是想去描述一下国人今天的郁闷状态。尽管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存在于各阶层,但是它似乎也分成一种个人的郁闷,还有一种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状态的郁闷。个人的不愉快,可能与生活的艰难甚至是欲望有关,而属于社会和时代的郁闷,似乎是您这本书中并没有点明的隐含之意。
梁:我们很多人有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好了的时候,他看这个世界,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美好,而且他希望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要再改变了。他不理解别人对这个世界不好的感觉。我接触的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持有这样的观点,我就忽然觉得一种悲哀,感觉到太没有希望了。
谈个人郁闷是没有意思的,世界上所有个人都是有郁闷感的。法国的富豪到了沙漠国家,看到连沙发扶手都是纯金的,会觉得自己是个穷光蛋;两个失恋的姑娘相遇,如果不是都因为男友负心,也是没法引起共鸣的。
郁闷是伴随着自我意识的产生和提高而产生的情绪。当你需要孝敬老人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没有这个能力,这时候你感到郁闷,不仅仅为你自己,而且在反思你周围的环境,这时候郁闷有了更深的含义。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看世界的视角,一定不再是以个人的感觉,而是心怀整个世界和社会。你的郁闷感,不是从你个人发出的,而是要为现实问题所郁闷。
范:今天的网络是一个愤青聚集的地方,这里郁闷的氛围也非常浓郁。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的人很平静,但是他在网上就会发表非常激烈的言论,以致人们会惊讶,这个人怎么会这样?
梁:网络中国和现实中国是不完全一样的两个中国。从网上,时常看到的是郁闷或愤懑的中国,但也正因为有这么多情绪都集中消解在网络中,发泄情绪后,人们回归现实又自觉纳入秩序、规则甚至包括潜规则中。
网络上表达出来的大众郁闷,就像是一团“积雨云”一样。若天上乌云密布,积雨云和积雨云互相碰撞在一起,就会产生闪电和雷鸣,其实,积雨云本身并不可怕,因为积雨云并不必然产生闪电和雷鸣,有时候清风就可以把它吹开,而这个“风”除了人文精神,不可能是其他。
二
采访中,梁晓声说了一句话:“我一直在郁闷着。”
这位已经霜上发梢的作家,脸庞瘦削,颧骨高耸,气场与周遭空气都有些格格不入。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作品开始,梁晓声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有评论认为他是平民阶层的代言人,慷慨陈词式的写作,激情外露,即便在今天的文坛,也并不容易看到。
所以当问他,已经花甲之年,是不是变得温和一点,文字是不是已经柔软起来的时候,他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依然用文字鼓呼奔走,为心目中理想的道义与公平。
拍照环节,梁晓声把手放在膝盖上,端坐于沙发,面无表情,那情形,让人想起鲁迅的那句话——“我一个都不原谅”。但他也会调侃,眼睛认真地看着镜头,目不斜视地对摄影师说:“这次被你们当明星来拍了!”
一个始终和社会现实保持距离的作家,在他一路走来的岁月中,见识过怎样的风景呢?依旧围绕郁闷的话题,梁晓声谈到了自己当年面临的贫困和窘迫。
范:您的小说有一大主题——知青,知青返城,其实有一种人性的东西被您捕捉到了,那就是尴尬。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境况,因为归来既是一件喜事,但也有烦恼。
梁:知青回来要面临一个房屋的问题。有些知青就很忧愁,回城还是不回城呢?回家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对于家人而言,一方面手足回来是快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排斥,因为生存空间被挤占了。这也会引起争执。如果说郁闷,这也是其中一种。
范:您也面临过这样的郁闷?
梁:我下乡回来,跟你们的年纪差不多。当时我到北影厂做编辑。回到城里的家,越靠近家门,心情越沉重,我所处的空间使我不快乐。
我这一代和你们还是有区别。我们那时候是多子女的,我们在家里可能是兄长,看着弟弟妹妹,不能独善其身。
我是最早的复旦大学工农民学员之一,1982年就获奖,1984年连续获奖,所以我选择对象的话,简直有一系列的候选人。但我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家里的负担很重,所以我会把婚期一拖再拖,把钱尽量供给家庭。
我在选择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什么样的伴侣会接受我的家庭。社会名流、高干子弟、影视明星,都有,但是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把她们带回去面见公婆,除非她是一个天使。这是我跟年轻一代最大的不同。
如果我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可能就不会这样。
范:生活经历中一定会有一些关于艰难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梁:你见过城市的贫民区吗?就是那种一排排低矮的房子,有的甚至是茅草搭建,破败,外面是泥土地,屋里也是泥土地,都没有水泥。
那时候城里人要抹锅台,想尽了各种办法,用烧煤的炉灰,然后到什么地方去挖一点黄泥,还有理发店里的碎头发,把草也剪碎,甚至到铁厂去搜集一些铁末子来,和在一起,就是为了让锅台更坚固一点。但锅台仍然粘不拢。
我父亲是建筑工人,我小时候始终想用水泥把锅台抹一下。但我没有水泥,找不到水泥。我曾经偷过水泥。家里要装修,想把墙刷一刷,我都要提前几天看哪里要盖房子,去找白灰,这样把自己的房子刷起来。
如果说,那个年代因为大家都穷,所以就不郁闷,我不是这个意思。
范:那个年代因为贫穷而痛苦,那么现在呢?
梁:做文化的时候,这种感觉并没有消除。一直到现在我都是郁闷的。做编辑的时候郁闷,自己创作的时候也还是郁闷,做到今天,发现自己的思维空间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比过去还狭窄。
范:某种程度上,当今的创作也非常媚俗。
梁:编剧是否只能去写韩剧那样的作品?假如一个作家自觉地提高自己娱乐大众的能力,那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吗?你们感觉这种文化的糟糕了吗?我接触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并没有这种感觉,我的心情会沮丧到极点,一切都懒得说了。我突然觉得,说什么呢?为谁说?我跟谁说呢?
范: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那么严肃的人文教育是否还那么需要呢?
梁:娱乐本身没有错,但那一定要建立在人文价值观普及落实的基础上,展示想象力的娱乐主要表现于两个层面:一个是想象力向外的激发,《阿凡达》就是超前、超一流的一个想象力的激发,包括高科技介入,也是属于想象力的一种呈现;一个是向内的激发,如心理现实主义、精神分析现实主义等。
我们的文化任务完成了没有?答案显然不容乐观。因此,价值的意义一定要大于娱乐的喜感。
三
作家的灵魂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说,在于作品,比如营造出一个完美的艺术世界;你也可以说,在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当然其中包括版税或名望;你还可以说,他完全可以退回到自我的空间里,丰富自我的内心。
而这些,仅仅只是灵魂的出口。
灵魂附着于对于社会现实以及人本身的关注上,它演化成一种守望的姿态,这应该是作家最为动人的姿态之一。
沉思者、凝望者、言说者、批判者。在梁晓声的旧作新书里,他始终保持这样一种姿态,提供给现实丰富的思考成果,并启发解决方案的路向。他的声音已经苍老了许多,但依旧十分尖锐。
“难道你们都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美好到没有什么可以郁闷了吗?”他这样问采访现场向他提问的记者,语气里多少有一种怀疑。
或许这就是梁晓声。
范:新作《郁闷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有何关系?
梁:《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毕竟是13年前的思考,那时各阶层的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心态写真和今天相比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譬如,那时代的草根阶层的社会意见就很难在书中得到展示,而13年后,博客、微博等“短、平、快”的意见表达迅速登陆,主流传媒对某事件的报道甚至都要引述网络上的公众态度。
范:今年是雷锋去世50周年,淡出人们视野多年的雷锋又回来了,而且引发了一些争议。您怎么看待人们对于雷锋这个曾经积极向上的形象的质疑?
梁:雷锋至少是一个比较好的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心地善良的人是应该得到尊敬的。
范:您的书中在进行青年阶层分析,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现在的青年形成了许多个阶层。像人们俗称的“富二代”,也有草根阶层的后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阶层分化,是通过不同人的命运的分歧而造成的,那么现在青年阶层分化的出现,更多的可能还是与上一代人有关?有关寒门学子上升通道越来越狭窄的问题,有关大学生求职难的尴尬,我想您也许有话要说?
梁:青年阶层分析,本来是别人出的题目。原来我可能关注,也有感受,但没有那么深入地思考。别人找来了,我就会吸一支烟,慢慢去思考。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一些重点大学中底层子弟的人数会慢慢少起来。这就和运动员一样,有的运动员每天吃牛肉,有教练训练;但有的连营养都满足不了,这就是输在起跑线上。
范:最近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活熊取胆,看到这样的事件,我们不由得会去思考,今天的文学,究竟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了什么?文学为什么没有能安抚和改善我们的灵魂?
梁:我一直奉行“文学要使社会进步,使人的心性提升”。人类是地球上的高级动物,与普通动物相比,如果心性不得到提升,人类甚至可能是地球上最不好、最凶恶的动物。其他的动物,哪怕是肉食类的猛兽,也只不过为了饱腹,为了后代的抚育、生存,不会在折磨中获得快感,老虎也不可能看到一群角羊然后一只一只咬死他们,囤积起来。比如狮子和老虎,无论是亚洲的,还是非洲的,它的领域范围内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人如果没有经过文化孵化的话非常凶恶,非常残暴,报复心很毒,贪婪心很大。最近讨论的活熊取胆实在残忍万分,之前还有活蒸娃娃鱼,泥鳅穿豆腐,这些都是坏掉的心性。文学的终极意义,就在于使我们心性变得更豁达、更开朗,更善于自我化解忧愁、化解烦闷。
范:您如何看待韩寒与方舟子之间的争论?
梁:我很奇怪,关于“代笔”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广泛的讨论?
最初的时候,我是比较欣赏韩寒的,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韩寒刚呈现在文坛。我觉得在八零后中有这么一个青年,他开始体现出不只局限于个人经历,而是对于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各种关注和意见表达,这是我欣赏他的一个前提。
第二,这样的一个青年一旦产生,那么他作为一个青年个体也要生存,将来也要结婚、养育子女,需要有房、有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有一些商业性的色彩介入到他的各种意见表达中来。这就使我们非常困惑了,不能厘清他的哪一种意见是较为纯粹的社会意见表达,而哪一种意见是要形成一个商业概念,或者形成一个商业的热身。
只要一个人一旦成为了社会公众形象,意味着他同时具有了商业代言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有人能把持住自己,有人就不能。
也曾经有人找过我拍广告,但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去做广告实在是怪怪的。我也曾经动心过,如果我哪一天真去拍广告,这笔收入是一定要用于公益。我现在没做,只不过由于我对自己的形象感到沮丧,不佳的形象弄得满街都有,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方韩事件,我毕竟不是十分清楚,然而这件事本身,在国外应是不需要那么多人卷入讨论的,很难说这些恩怨是非能够在主流媒体上持续如此长的时间。
范:您怎么看待微博这种传播形式?
梁:一些人沉迷于当公共知识分子,为了增加粉丝和引起社会关注,经常弄些没常识、耸人听闻的东西。每天无数次地想,下一个140字以内的话该说什么,说什么大家喜欢听的,传播什么能让大家传来传去。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是非常可笑的,变成这样他还是知识分子吗?
许多微博都有意思,而有意思恰恰是危险的,是陷阱。你有意思,我比你更有意思,都比着怎么有意思。表达应该是严肃、郑重的,考虑明白、表述清楚、直指要害地发表问题,不能把严肃性抹平。
说到底是我们在玩,不但在玩微博,还在玩意见表达。
在人人都有“自话筒”的情况下,每天碎嘴子一样,什么事都发表个态度,什么事都参与讨论。除了说明你在玩话筒,痴迷于话筒,变成了话筒依赖症,还能说明别的吗?恰恰是因为有了一个话筒,更该珍重自己的话筒,拿着话筒更不能轻易说,有时候甚至不说。
没有必要不参与,参与一定是真诚的表达,而且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表达。
责任编辑 鄢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