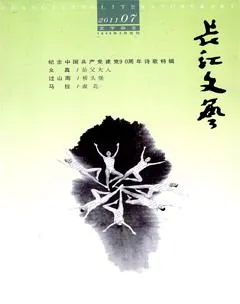月照中堂
月堂,是我隔壁家的一个女孩。
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她自己肯定说不出所以然,她也绝不会为这点小事去寻根问底。要弄明白这个名字的来历,完全只能凭借我的想象。
那天夜晚应该是一个满月之夜。月堂的母亲经受了十月怀胎之苦,终于“发动”了。十月怀胎对于女人来说,如果仅仅是一种折磨,那么一朝分娩简直就是一道鬼门关,尤其是在乡下连赤脚医生都没有的年月。接生婆早早地来了,是湾子里年长的一个老妇人。湾子里的接生婆都是无师自通,生的孩子多,见的事多,加上湾子里老老少少从她手上接生的人也多,接生婆的知名度自然就高了。接生婆的所有工具就是一把剪刀,能剪断脐带就行。当一把明晃晃的剪刀亮在堂屋里的时候,月亮还没出来。一家人屏气凝神地呆在堂屋里,听月亮出来的声音,听厢房里孕妇的呻吟,静静地等。只有等。
当一轮满月照在了堂屋正中的时候,月堂出生了。她惊世骇俗的一声啼哭,比堂屋里的月光还要明亮。但不管她的哭声多么动听,也只换来了一屋子人低声地喘了口气:是一个女娃啊,好在母子平安。月堂的爷爷还算识得几个字,幽幽地说:正是月光照在堂屋中间时生的,就叫月堂吧,还是个女孩的名字。至于明亮的月光将怎样照亮这个女孩的脸,又将如何照亮这个女孩的无数夜晚,那都与他们无关了。
月堂六七岁时,母亲就撒手西归了。就是为了要生出个男孩,结果死于难产。
“宁死当官的老子,不死叫花子娘”,这是一句乡下谚语。而这又是一个多么残忍的选择啊。月堂根本来不及选择,就不得不用她稚嫩的肩膀来撑起这个残缺的家。
残缺所产生的美,那是一种凄美。我一直以为,将残缺与美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是人类自制的一种残忍。人们从别人身上看到在与自身毫不相干的痛苦时,一种幸免于难的释然才有了叫着美的东西。
月堂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家人就这么残缺地让无情的日子开始拖着跑了。
月堂六七岁时,就得上灶台了。谁叫她是家中老大,又是个女孩呢。接近于零界限的生存环境,会激活人内在的巨大潜能。很短的时间内,月堂就熟知了基本的生存技能,这与她幼小的年龄形成莫大反差。乡下做饭并不像现在有电饭堡、电饭锅之类的这么简单。高高的灶台,一口大锅,以月堂矮小的身材不垫个矮脚凳在底下,根本看不到锅底。灶膛里也没有把好干柴,捡一点烧一点的,一顿半生不熟的饭,总是搞得身上脸上全是黑黑的锅毛烟子。好在她在做这些活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什么痛苦,一种本能的驱使,让她在不经意间扮演了一个本不该属于她的角色。两个妹妹只会拿着一只小碗跟在她屁股后面转。那种期望的眼神,让她有些恼怒,又有些满足,长哥长嫂代爷娘,她充当的是“长姐家中也是娘”的角色。
我小她两岁,因此也便和她有了共同语言。在她做饭时,经常去帮她往灶膛里添火。别人家的炊烟是从房顶缓缓升起的,在空中飘逸出好看的线条。月堂家的炊烟往往是从门里涌出来的,掺和着泪水和心酸。记得有一次,也许是柴草太湿或是什么的,灶膛里的火总是烧不起来。我以为是柴放的少,不停地往里加柴,结果是只冒烟,不出火。任凭我趴在地上用吹火筒猛吹,还是不见效。她只好急急忙忙将米下到锅里,然后从小板凳上下来帮我。别看她就大我那么两岁,的确比我有经验得多。她拿起烧火棍,在灶膛里一阵拨弄,灶膛中间就空出那么一点空来了,有了空间,自然就多了些空气,柴草也就燃起来了。正当我们摸着脸上的黑灰相互取笑时,突然闻到了一阵糊味。原来是因为柴放得过多,灶火太猛,一锅饭已烧糊了大半。
家中无米,月堂还暂时管不了。灶中无柴,那就是她所能想法的事了。每到秋收后,我们都要跟着她去田野里割谷蔸子。月堂割谷蔸子跟我们不一样,她把这件事纳入了她生活必要的程序之中。我们割多割少,也只不过是为家里增加点柴草,而她家所烧的柴大多则要靠她一个秋天割回来。秋天的田野,不热不冷,正适合于我们这些没人照管的孩子。几只叽叽喳喳闹着的喜鹊平添了一种喜悦的气氛,比之于青黄不接的日子,无论收成怎么样,都是让人高兴的事。稻谷收完后,稻田里一片浅浅的一截谷蔸子,割回家就成了最好的烧柴。高高低低的一群孩子,挑着恨不得比自身还要高的装谷蔸子的秧架,学着大人的步子,跟在她后面,也走出一道秋收后的风景。
月堂手巧,她的谷蔸子不但割得快,而且码得整齐。就像安放她心爱之物那样既得心应手又纹丝不乱。等到她已割好一担要装架了,我们往往才割了半个秧架。最让人着急的是装架,秧架本来是用来挑秧的,现在用来装短短的一截谷蔸子,怎么装都让人感到不踏实。月堂装架时,秧架总是伸开得不宽不窄,恰到好处。整齐的谷蔸子顺一排倒一排地装进秧架后,再将秧架上面的绳索绞紧,挑着无论怎么颠簸,谷蔸子都不会撒落出来。而我们不是因为秧架伸得过开,走着走着谷蔸子从中间“窝”下去了,就是因为伸得过窄,走着走着又从两边溜下去了。每当这时,大家也只能像她家里的两个小妹妹一样,眼巴巴地望着她,希望能搭把手。
乡下的冬天应该是被一棵一棵的小草,一蔸一蔸的青菜所拱走的。冬之将尽,去四野里剜猪菜,是我们最快乐的事了。每到傍晚,我们都将小竹篮,小菜铲子准备好,偷偷地盯着月堂的动静。只要她一出门,我们便像一群精灵,悄无声息地跟在她后面,然后在她指引的田野里四处散开,开始剜刚长出来的野菜,当然顺带也剜几蔸生产队里栽种的油菜。风很冷,拿着铁铲的手一会就冻僵了。把竹篮挂在胳膊上,将手伸进袖筒里,或者放在衣摆下捂一捂,就可以接着干了。我们巡游在田埂边,只要发现一点青绿色的东西,就会飞步向前,将其收在竹篮里。我们像冬日里饿慌的了一群麻雀,在田埂上跳跃着,寻觅着,欢乐着。瞄准机会,看到四下无人,便深入到油菜田中间,狠狠地剜它几蔸,然后飞奔上田埂。如果有谁在田中间呆得久了,月堂会生气的,下次我们出来的时候很可能就不会让他跟着了。这很像一场游戏,在紧张中期待,在期待中满足,在满足中快活,我们乐此不疲。
我每次看到月堂家的猪,总觉得就是比我们家的猪长得要大、要肥。这也难怪,每到年底,月堂和她两个妹妹的新衣服和过新年的一切开销,都是从她们家猪身上找回来的。因此,月堂对她们家的猪照料得精细、周全。而我想的没她那么深远。
时光过去了很久,又恍若隔昨。在离乡下很远的一个满月之夜,我在城市的一个小区,小区的一个石凳上,忽然想到了月堂这个名字。清冷的月光从高大的楼群缝隙中挤过来,被几棵原本并非生长于此的树木所阻,所剩无几地照在我脸上,我自然地想到了乡间在月光关照下的样子。月光无欺啊,它不但照看着今人古人,而且一如既往地照看着城市与乡下。此时应该是月照中堂的时候了,那个名叫月堂的女孩,踩着月光照亮的路,不知又在忙些什么了。
责任编辑 易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