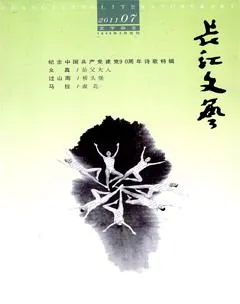地坪河人物
熊 医 生
熊医生原本不是乡村人物,二十多岁上就成了神医。在县城医院里当了几年医生,因医术高,被破格提拔为院长。这个小城里有不少曾被别的医生判过“死刑”的病人,只要转到他的手上,十有八九起死回生。由此,他的名字在小城里震天价响,不管是有身份的还是没有身份的,见了他的面,那腰板就矮了三分。
“熊院长。”人们恭敬地与他打着招呼。
“哦。”熊医生脸上堆着笑,老是回着这句话。走过几步他有时会回过头来说:“吃了?”
“吃了。”被问者赶忙回答。
熊医生很少再说第三句话,越是如此,小城人越发对他敬重有加。他们常在背后说:“只有有真本事的人才有那样的架子!”也由此,能得到他第二句话的人,总是带着莫名的兴奋离开,有喜欢炫耀的,常常要让人咂三天舌头。
熊医生很忙,只有三餐饭后才有上一二十分钟的时间上街走动。其实,他这一二十分钟也并不是闲逛,是饭后运动。熊医生常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县革委会的王主任见了熊医生不弓腰板。他的肚皮很大,就是肚皮不大,他也不会向熊医生献媚。因为他知道自己打个喷嚏,小城就会响三天,跺一跺脚小城准要晃动半月。你一个小小的医生,再神也神不出他的手掌。所以,他是唯一在熊医生面前挺着腰板的人。由此,熊医生也唯一不给他笑脸。有时候,两人打了照面,王主任仍然挺着大肚子,目不斜视地朝熊医生点点头。“哼。”鼻音很重的一声,算是打过招呼了。熊医生也板着面孔,“哼。”地回王主任一声。王主任开始很是惊讶,有些陌生地望了熊医生一眼,看熊医生再没有其他表示,就头也不回地朝前走。时间久了,小城里的人就知道了两个“权威”不大对光。
熊医生从不找王主任。院里有事需要请示的,他总是让副院长出面。而王主任也从不找熊医生,你医术再高,我就不得需你出面的病,小病小痛的自然有找上门的医生,鞍前马后服侍,看你神气个什么。
几年过去了,熊医生仍当他的院长。其实他不愿当院长,他不是当院长的材料。开会发言,人际应酬,没有哪一样是他喜欢的,但人们服他,无须他多说,无须他去八面玲珑,医院里哪一方面的工作都不差于别人,而且比别的单位强出许多。于是他的仕途看好,人们都说熊医生最起码也要到卫生局当个一把手。可是,在他手下工作的倒是一个个都上去了,就连他手下的年轻的副院长也被提拔当了卫生局的一把手,可他依旧干着老差事。他的材料报上去几次都被退回。王主任说:“他是技术权威,还是让他在专业上发展吧。”言之凿凿,无懈可击。
又是几年过去。很少染病的王主任忽然得了一种怪病,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睡。凸出的大肚皮就像打足了气的皮球,睡觉只能仰躺着不能动弹。不几日,人就磨得不成样子。县城的医生看遍了,仍摸不着症状。王主任就差人来请熊医生。熊医生见了来人,不假思索就拒绝了:“我又不是乡医,不上门看病。”来人再三恳求。熊医生说:“医院那么多的病人,我能丢下他们不管?”来人悻悻地走后不久,王主任就把电话打到了卫生局。曾是熊医生老部下的年轻局长又把电话打到了医院,他跟老领导说:“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医德,还是委屈求全吧。”熊医生半天无言,愣过一阵之后,熊医生被局长塞进了来接他的小车。
熊医生为王主任号脉,他的头始终扭向一边。号完脉,熊医生开了三副药方,尽是些医院里不常见的药。有经验的说那些是民间奇方。王主任见熊医生始终板着脸,也不便多问,纳了一阵子闷后,就差人到乡下去搜集。整整三个月后才将药方上的药配齐。三个月里,王主任受尽了磨难,人整整地瘦了一圈,过去高耸的肚皮差点贴上后背了。
吃了熊医生的药,不过三剂,那病就日见好转。十天以后,王主任就能下地了,王主任很是感激,第一次向熊医生弓了腰板。
“老熊药到病除,真神医也!”
“哈哈哈……”熊医生发出一阵高深莫测的大笑:“若非汝,病早除也。”王主任一愣,好久没有明白,及至明白了,才知道受了熊医生的愚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过不多久,熊医生被解除了院长职务,再过不多久,熊医生被遣回老家。原因是熊医生缺乏医德,不配作人民的医生。
熊医生成了乡村人物。乡下人们依旧把他看得很重,一个二个的在他面前恭谦得很。熊医生为乡下人看病极少收费,最多只是接受人们款待一顿,招待好坏从不计较,乡里人与他很谈得来。熊医生不再像在城里时一样言语很少,他谈性浓时说上半天可以不说原话。有人就很纳闷:像熊医生这样受过打击的人,应该是话越来越少的,怎么他倒越来越鲜活了呢?
后来,县里为熊医生平了反,并要他回原单位,官复原职。但熊医生却指着自己花白的头发,对县里的领导说:“你们看我这样子,还能干几年?让年轻人上吧!”县里请不回他,就补发了他的工资,很丰厚的一笔款子。熊医生常用这笔款子接济看病买不起药的乡下人。因此,乡人们更尊重他了。熊医生还带了几个徒弟,是县里送来跟他学医术的,目的是不让他的绝活失传。
熊医生成了乡村最有头面的人物。他的话比那些支书、村长还管用,因此,熊医生一直活得很滋润。
郑 文 书
郑文书在地坪河里算个人物。他高个子,一头银发。只是他的眼神游移不定,和人们说话也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但在地坪河里有他说话的地位。除了熊医生,就算他的话吃香了。
郑文书有两支土铳,一长一短。虽是土铳,但那做工却不同一般,精致得很。铳杆蓝幽幽的,铳托也油光光。郑文书就爱背这两杆铳在地坪河转悠。常常钻进竹林里打几只斑鸠或乌鸦吊在枪杆上,麻雀是不打的,太小,不够塞牙缝子,偶尔打几只,也是为了逗地坪河的孩子们取乐而已。因此,地坪河的早晨或黄昏,常有郑文书扛着土铳倒吊着几只猎鸟的影子在晃荡。
郑文书原是国民党县党部的秘书,写得一手漂亮的字儿,还有一肚子的经论。在县党部里还是个吃香的角儿。可忽地他不知中了什么邪,弃官不做,跑回地坪河里招兵买马,扯旗造反,还惩治了几位作恶乡绅。一时间,四乡富户居无宁日,纷纷到县党部告状,县自卫队闻风而动,倾巢而出攻打地坪河。郑文书的队伍刚刚扯拢,总共才百来号人丁,每人一杆土铳,根本不是自卫队的对手,才一支烟的工夫,一个个都成了自卫队的俘虏。郑文书耷拉着脑袋被押回县党部,审了一天一夜之后,被送上了法场。妈拉个巴子,掉下脑袋碗大个疤。郑文书手下的五个队长看着郑文书有些懊丧,便纷纷跟他打趣。郑文书咧了咧嘴,很想乐一乐,以告慰他的同伴,但他却怎么也乐不起来。五声枪响之后,郑文书身边绽开了五朵瑰丽夺目的鲜花。枪声还没静下来,郑文书“哇”地怪叫一声,在那广阔的河滩上没命地狂奔,嘴里不停地大喊:“造反,造反,哦嗬——”郑文书并不知道,县党部的那些旧僚保了他,只让他作了一次“陪杀”。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有人把他举荐出来。因有一笔好字和一肚子文章,再加上他扯旗造过国民党的反,被视为一段辉煌的历史,郑文书不费吹灰之力,就谋了个好缺。在政府里当了个带长的文书,地坪河的人羡慕得不得了,他们由此下县城也气壮了许多。碰上有相识的人问起,地坪河的人就说:“去哪?找郑文书呐!”言下之意别人不知道倒还是一件奇事。
地坪河的人炫耀时间不长,郑文书就出事了。那日,县里从部队上调来的一位新县长到任,县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一队队武装军士列队迎接。新县长一到,两百多条枪对天鸣放,“砰砰砰”枪声响成一片。郑文书当时也在欢迎的人群之中,两百多条枪栓拉起来时,他的身子本能地一颤,还未反应过来,枪声响了。于是,他便在广场上没命地飞奔,嘴里喊着当年河滩上一模一样的话语……
新县长的眉头紧皱着,看着他沿广场跑了三圈之后才问了一句:“这人怎么回事?”旁边的人便告诉他原委。新县长不再说什么了,吩咐两名战士把郑文书捉住,带回县府休息。过些日子,郑文书就被县里的车子送到了地坪河,县里与乡里作了交接,宣布他带病休息,并为他造了三间青砖瓦屋。郑文书的工资每月由专人送达,郑文书接过那摞钱时眼里溢满了兴奋。
郑文书把政府发给他的工资,拿到乡下的合作社里兑换成一角二角或五角的毛票子,放了整整两满箱,每到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就把家中晒粮的两口篾羌背到门前的稻场上放好,然后把箱子里的钱倒出来,让阳光暴晒。地坪河的人说:“郑先生,你做么事哟!”
郑文书说:“钱用不了哇,长毫哩,让它晒一晒。”顿一顿他又说:“新政府好哩,管吃管喝还管住的,只是我不能为政府做事……”说到这,他两眼露出茫然的光,又重复开头的话语。
虽然与郑文书交流不了几句,但地坪河的人们仍然尊重他。大家都知道他招兵买马,扯旗造过国民党的反,是个功臣。偶有一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说:“鸡巴功臣,上一次法场精神就失常了。”话还没说完,地坪河的人就像看怪物似地看着他们:“失常了又怎么样?换你去试试,不吓死才怪哩!”后生们知道自己对郑文书的不恭之词在地坪河里没有市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说过有损他形象的话。
郑文书每天背着他曾用来造反的两杆一长一短的土铳,在地坪河里悠哉游哉,那种闲情逸致真令人羡慕。郑文书就这么半人半仙地活着。
十 三 婶
十三婶被轿子抬到这个小山村的那年,十三叔在山外的小镇上谋了份教书的职业,两人在洞房才刚刚亲热三天,十三叔就被召回镇里去上课,谁知这一去竟是整整六十年!
十三婶清楚地记得,男人走后的第二天,地坪河里就开始过兵,先是穿黄衣服的“国军”,后是穿灰衣服、打绑腿的刘邓大军。“国军”仓皇而逃,刘邓大军则是浩浩荡荡挺进。那时谁输谁赢,十三婶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男人快些回来。可是男人竟如南去的大雁,杳无音讯。直到地坪河完全安静下来,十三婶迈着三寸金莲去小镇上寻男人,她才知道十三叔被“国军”拉去补员了。
十三婶痛不欲生。十三婶颠颠跛跛地回到家里,把自己关在房里哭了两天两夜。那哑了嗓子的干嚎,把小山村搅得好长一段时间宁静不下来。
岁月轮回。十三婶完全没有料到,在她人生历程即将走完的时候,一头白发的十三叔从“那边”回来了。十三婶捶打着男人,痛哭流涕:“你这死鬼,怎么不让我清净啊。”
十三叔无言以对。十三叔好久才说:“你怎么不嫁啊,我不值得你这么守啊。”
十三婶说:“不都过来了?这么些年……”
十三婶说着说着怎么也说不下去了,于是,只好抬起手来抹眼泪。
十三叔一边安慰她,一边为她抹去眼泪。十三叔还从包里拿出一捆钱来递给她,说:“我欠你的太多了,这20万元给你养老吧。”
十三婶惊觉起来:“你——又要走?”
十三叔低下了头。十三叔那边还有个家。十三叔惶惶地说:“我——以后还回来。”
十三婶不再做声。十三婶的那颗心彻底死了。
十三叔走后,十三婶家来往的人便多了起来。家族中人见了十三婶便说,随十三叔一同回乡的王顺如何为亲戚朋友花钱,说王氏家族每丁100元,说王顺的侄儿、侄女每人两万。那钱花的,少说也得二三十万,嘿,气派哩!
十三婶不理会这些。隔天,她打了个包袱,独自去了镇上。回来时,一垸人都把背对她。
十三婶家来往的人又稀落起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十三婶成了垸中有她不多,无她不少的人物。直到有一天,有人到她家去借东西时,才发觉十三婶已经倒在床上死去多时了。
十三婶下葬的那日,镇上的施工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山里。垸里人七嘴八舌一番打听,才知道十三婶先前到镇上去捐了20万元,要镇上尽快把早已计划兴建的山里小学建起来。
过不多久,在新校址奠基的同时,垸里人也自发地在十三婶的坟墓上立起了一块高大的墓碑。墓碑竖起时,一垸人无论年长年幼,一起对着那石碑跪了下去。
责任编辑 吴大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