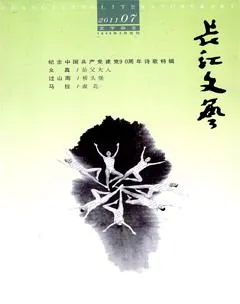学徒
太阳升起老高了,小满还没有起床。
其实他早已醒了,就是赖着不想起来。家里的被褥就是比城里睡的被褥舒服、暖和,不用皱鼻子就能闻到暖烘烘的棉花气息。哪像城里睡的那被子,气味难闻不说,还总潮乎乎的,要等把潮气焐透了,身子才能慢慢地暖和起来。他妈知道他昨天要回家,提前好多天就做了准备,在一个好晴天,把垫被盖被晒了个通透,床板上又铺上了厚厚的稻草。就在昨晚上床的那一刻,小满突然想起妈常说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一个晚上睡下来,他连梦的边都没有沾一下。
小满听见了窗外的鸟叫声,同时也听见了他爸和妈在灶屋里的说话声。
爸说,我去喊小满起来,学徒的人不能这样贪睡懒觉。
妈说,算了吧,在城里辛苦了一年,回家就让他睡个够,等饭弄好了再喊他起来。
爸说,吃过饭就让他把师礼送到檀畈去,告诉师傅正月初四请他到家里来吃年酒。
妈说,把小结子送给我家的那瓶酒让他带去,省得再买好酒了。
他爸嗯了一声。
吃过早饭,小满就上路了。小满拎着一只小竹篮子,里面放着一条黄山牌香烟、五斤腿子肉、两只猪蹄子,还有就是小结子送给他爸的那瓶酒。小结子三年前就被村里的红毛带到浙江湖州打工去了,前两年他都是跟着红毛二十八九才回村过年,今年却是自己一个人在过小年之前回来的。小结子喊小满爸表姑爷,回村的第二天他就拎着一瓶酒和一些湖州的糕点来看望他的表姑爷。听爸妈说,小结子在湖州混得不错,每个月能挣到一千出头,身上的穿着也变得像大人一样有头有脸了。这样一比,小满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小结子只比自己大两岁,就能挣到这样多的钱了。自己跟着建设哥学徒,拿不到一分钱不说,还要倒贴钱,要给建设哥送师礼,要请建设哥吃年酒。这样,小满就不愿意碰见小结子。
可不愿意归不愿意,小满还是在出门不久就遇上了小结子。
师傅家所在的檀畈距离小满家三里多路,中间隔着一条小河,要过河上的小桥就必须从小结子家门前经过。因为天气好,小结子邀一伙人在门前摊子上赌钱。现在都这样,一到年前年后,总能看到许多赌钱的场子。他们早已不打小扑克牌了,而是摇单双、推九点半、炸鸡,一场下来输赢千元左右。而且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有钱就能上场子。本来小结子是不会看见小满的,他正在做庄家,这个庄是个红庄,一个庄家做下来,小结子怀里赢了一大堆钱。小结子赢了这么多钱就不想再做下一轮庄家了,他把庄推给别人,别人不愿意接庄,说没有人像小结子这样做庄赢了这么多钱就不干的。小结子横得很,说不干就不干,从场子上硬撤了下来。正好看见小满,就过来和小满说话。
小结子像大人样的嘴里叼着一支烟问小满,什么时候回来的?
小满说,昨天天黑时到家的。
小结子看了一眼小满手里拎着的篮子说,去给师傅送师礼呀。
小满篮子里盖着一层布,但盖得不很严实。小满肯定小结子已经看见他送给他爸的那瓶酒了,就慌慌地嗯了一声,转身要往桥上走。刚踏上桥,就又听小结子说,小满,不要再和那个刘建设学徒弟了,干脆和我一起出去干算了,我包你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小满装着没听见,快速地通过了河上的木板桥。
小满学习不好,他爸早就放出话来,将来让他和建设哥学漆匠,说学门手艺,在城里打工容易找到事做。去年建设哥从城里打工回家过年,没想到师娘专门来到他家说让他学徒的事。他爸一开始还犹豫,说,小满还在读初一,等他念完初中再说吧。师娘说,我这也是为你家小满好,学手艺要趁早,早一天学徒早一天出师,也是说现在的伢都要读书,以前不都是十来岁就学徒了?他爸想了想,说,也好,反正小满学习不行,念完初中也没什么用,就答应了下来。正月里请拜师酒那天,师娘高高兴兴地抱着一岁多的小清华和建设哥一起来了。师娘在灶屋里看见小满,问他,喜欢学漆匠么?小满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但还是点了点头。师娘又说,你是头一回出远门到城里去,城里大得很也乱得很,你要跟着建设哥,不要乱跑,晓得么?小满又点头,说晓得了。
在动身来城里的头一天晚上,师娘又一个人来到小满家。在和小满爸妈寒暄一阵之后,她问小满出门的东西准备好了没有。小满说,差不多吧。师娘笑着说,让我来帮你看看,出门不像在家里,少一样都不方便的。说完就拉着小满的手进了小满的房间。师娘只是用手摸了摸小满放在桌子上准备带出门的行李,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认真细致地察看,接着她塞给小满二百块钱。小满不敢接,哪有师娘给徒弟钱的?虽说他家和建设哥家沾着一点远亲,但也不至于给钱呀,又不是到外面去读书,再说他爸妈也给了他一些钱。小满正要推辞,师娘说,我这钱不是给你的,是让你给我打电话的电话费。接下来师娘就把打电话的具体时间和小满说了。小满很疑惑,说干嘛不叫建设哥给你打电话而让我给你打呢?师娘笑笑说,等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从檀畈回到家,小满妈正在门口择菜。妈说,回来了,和师傅说了没有?小满知道妈问的是请师傅吃年酒的事,就说,师傅不在家,我和师娘说了。他妈抬起头来,看见小满两手空空,又说,篮子呢,篮子也没有带回来?小满说,哦,我忘了,下次去再带回来吧。
其实小满并没有忘记要把篮子带回来。小满进了师傅家,堂屋里没有人,静悄悄的,小满喊了一声建设哥,好一会儿师娘才抱着小清华从房间里走出来。看见师娘出了房间,小满就把篮子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师娘看上去情绪不太好,没有招呼小满坐下来的意思。她把小清华从怀里放下来,小清华就踩着凳子爬到八仙桌上去翻看篮子里的东西,看看没什么好吃的,就又下了凳子要她妈妈抱。师娘重新抱起小清华,才说,你师傅出去赌钱去了。小满有些疑惑,师娘以前在他面前都是说建设哥,包括在电话里也这么说,现在突然改口说师傅,这让他感觉师娘有些生分了,不再像原来那样把他当弟弟那么亲切。小满就把请师傅吃年酒的事和师娘说了,并把打电话剩下的钱还给了师娘。师娘也不客气,接过来揣在兜里。
小满向师娘告辞,看看八仙桌上的篮子,觉得不便把东西从篮子里拿出来,就空手回来了。走回到木板桥上,小满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他赶紧掏出口袋里的一叠钱数了数,发现自己真的把两叠钱搞错了。应该还给师娘的钱还在自己手上,这钱比已经给了师娘的那叠钱多二十多块。
小满非常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给师娘打电话是正月十七那天,这是他跟建设哥来到城里的第七天。小满本想把给师娘打电话的事告诉建设哥的,可那天建设哥的情绪很不好。建设哥就是这样,心情好的时候脸上笑得像一枝花,不好的时候脸黑得像焦炭,动不动就骂人。小满就自己去找打电话的地方,他走了足足两里多路才找到这个有公共电话的小店。他生硬地拿起话柄,连摁好多次号码都摁错了。终于通了,师娘问他,在外面还习惯不,想家不?小满的眼睛就一下子湿了,但他说,还好。师娘说了一些安慰小满的话,又问,你建设哥晚上都干些什么呢?小满说,没干什么,就在屋里打打牌。小满想起师娘曾说的,在电话里告诉他为什么要他给她打电话而不让建设哥给她打。师娘把这个问题绕开了,反而嘱咐他,给她打电话的事不要让建设哥知道。
放下电话,小满的眼睛红了,其实他是非常想家的,这出来的七天里他没事就想家。这个电话一打完他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唰唰地流了出来。收电话费的是个中年妇女,她等小满把眼泪擦干才把要找的零钱递到他的手上。
接连打了几次电话,收电话费的妇女对他说,你师娘让你这么做,肯定是想通过你监视你师傅。小满有些不明白,监视师傅什么呢?收电话费的妇女摸了摸他的头说,你真是个小木瓜蛋子,当然是监视你师傅不要在城里胡搞,比方说往美容院洗脚屋跑啊,比方说和哪个女人好上了。在回去的路上,小满认真地想了想收电话费妇女说的话,觉得有些道理。因为每次师娘都问到了建设哥晚上干些什么,不干活的时候有没有到城里去瞎逛,有没有把他甩开一个人出去的时候,而且一再嘱咐他,不管白天晚上都要和建设哥寸步不离。
从那以后,小满觉得,似乎应当为师娘做点什么,不然每次打电话说来说去还是那些原话,他觉得这样对不起师娘,把师娘打电话的钱白白糟蹋了。
还有三天就过年了,村子里真正地热闹了起来。这热闹不是大伙儿抢着办年货,抢着做豆腐蒸年糕,现在大伙过年好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这热闹是那些从城里打工回家过年的人带来的。王河村团脸的中巴车一天要往县城跑好多趟,每次从县城回来,路过村子的时候,就要吐出几个人来。这些人大包小包地拎着,笑嘻嘻地回家去,很快就把村子里的空气搅得骚动起来。
村子里的中饭向来吃得潦草,特别是在年前年后,有些人家甚至不吃中饭,只吃早晚两餐。但小满妈怕小满在城里吃惯了中饭,不吃不行,还是正儿八经地把中饭做好了。
吃饭的时候,小满妈显得很兴奋,她说,徐立本家的小懵子今天上午回来了,并且还带了个男朋友,衣服穿得花里胡哨地没有一点乡下人的影子。小满爸事不关己地说,她才多大,就谈男朋友了?小满妈掐着指头算了算,说,她比小满只大四岁,十七了。小满爸夹了一口菜到嘴里,边吃边呜噜着说,立本有这两个女儿,算翻身了。小满知道,他爸说的翻身是指徐立本家今年盖的那座两层小楼房。在大懵子小懵子未出去打工之前,徐立本一家在村里活得窝窝囊囊,没人瞧得起他们家。自从大懵子出去打工,又把小懵子带出去之后,不断地往家里汇钱,徐立本盖起了这座两层小楼,村里人才对他们家刮目相看。小满妈听小满爸说徐立本翻了身,很不以为然,也不顾小满在场,说,都是卖胯裆卖来的钱,算翻什么身。小满爸正了正身子,说你不要听村里人乱讲,看见人家盖了楼房,就说人家的钱来得不正经。小满妈不服气地说,这事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她姐妹俩才出去打几年工,就能挣出一座楼房来?小满爸不耐烦了,说好了好了,别人家的闲事少管。
小满妈不吱声了,过好一会才对小满说,你现在不是学生伢了,虽讲是在学徒,人也要放活辣一些,太老实了将来在社会上吃不开。小满爸也附和说,是咧,你看人家小结子多活辣,下午你去和小结子他们耍一耍。
说实话,小满在心里还是很羡慕小结子的。他觉得小结子比自己大了不止两岁,而是大了七八岁。本来跟建设哥学徒的应当是小结子,那年小结子爸妈已经和建设哥说好了,让建设哥带小结子出去。小结子死活不肯,硬要跟红毛去湖州打工。现在小结子不单说话老扎扎的,办事也很有主见,村里人已经把他当成大人看待了,正月里谁家请人喝酒,都要把小结子喊了去。似乎有了小结子在,这一桌酒才会喝得热闹,喝得有面子。去年他和红毛回家过年,从团脸的中巴车上下来,那派头比红毛冲多了,倒像是他领着红毛出去找事做似的。
小满并不想去小结子那里,他想在村子里随便逛逛就回家。离开村子整整一年,除了徐立本家竖起了一座两层小楼房,他觉得其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村子里不时传来小孩们的欢叫声,不时从某个角落里响起一两下炮仗的噼啪声,这些都预示着马上就要过年了。
河坡上有两个人在玩耍,小满认出那个女的就是小懵子,那男的应该就是她带回来的男朋友了。小懵子穿着一件加长的红色羽绒服,羽绒服的下摆把膝盖都遮住了,脚上是一双黑亮的高筒马靴,头发也染成了金黄色,并且高高地绾起,像个公鸡的大尾巴。小满觉得妈说得不错,小懵子已经没有一点乡下人的影子了。小懵子靠在一棵柳树上让她男朋友给她照相,照了很多张相后,他们在河坡上追逐起来。现在是枯水季节,河床的两边显得很宽阔,上面是干净的鹅卵石。他们从河坡追逐到河床上,在河床上找了几个光滑滑的石头又回到河坡上躺下了。河坡上有一大片一大片金黄色的草皮,他们很快抱在一起在草皮上打起了滚。小懵子咯咯咯的笑声银铃样地撒满了整个河坡。
就在小满看得失神的时候,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小满回过头来看见小结子站在他的身后。小结子嘴里叼着烟,脸上布着坏笑,说,看他们有什么看头,走,到我家去,我那有更好看的。小满还是不想跟小结子在一起,就搪塞说,你下午不赌钱了?小结子说,上午赌了一上午,下午不想再赌了,一天到晚赌钱也很累人的。看看小满没有和他走的意思,小结子又说,你猜我上午和谁在一起赌钱的?小满猜不出来,也不想猜。他勾着头看自己的脚尖,偶尔瞟一眼河坡上的小懵子和她的男朋友。这会儿他们没抱在一起了,而是坐在地上把头凑在一起翻看照相机里的相片。
经过收电话费妇女的提醒,小满就留意起师傅建设哥的行踪了。有一天晚上,建设哥他们先是喝酒,喝完酒接着打牌,就那么一直往下打着,没有停下来睡觉的意思。小满实在支持不住了,眼睛早已闭上了,耳朵跟着就要闭上,这时却听到门吱地一声轻响。小满很想睁开眼睛,但他实在太困了,很快进入了梦乡。等他睁开眼睛,屋里却是一片漆黑,一点声音也没有。这个出租屋里总共住了五个人,除了建设哥和小满,另外三个人两个是木匠师傅,还有一个是砖匠师傅。以前小满夜里醒来时,总能听到他们很粗重的呼噜声和床板吱吱嘎嘎的声音,有时还能听到一种很奇怪的哼哼声。现在这些声音都没有了,屋子里静得像一个巨大的黑洞,这让小满很害怕。他赶紧溜下床,把灯打开,果然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只听到白炽灯发出的咝咝的声音,几只飞虫围着白炽灯飞来撞去。小满开开门,带着哭腔对漆黑的夜里喊,建设哥你到哪里去了。喊声在空荡荡的夜里传得很远,撞到墙上又反弹回来,像被扯动的弹簧一样嘤嘤嗡嗡的。小满不敢再喊了,一头钻进被窝里把自己裹起来,浑身瑟缩着大气都不敢出,直到几个小时后建设哥他们回来上了床,他才重新睡着。
很快小满发现了建设哥他们的规律,大概半个月左右他们就晚上出去一趟。要出去的晚上他们会喝很多酒,然后打牌,直到他们认为小满睡着了为止。他们把电灯拉灭,悄悄地打开门,再从外面把门悄悄地带上。他们的脚步轻得像猫一样听不出任何声响。这时候小满反倒故意把呼噜声放得很大,似乎在提醒他们自己睡得很死,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出去。小满也不再感到害怕了,他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时把眼睛睁得老大,直到很困了才不自觉地把眼睛闭上。
小满打算把建设哥晚上瞒着他外出的事告诉师娘。
那次,他兴冲冲地拨通了师娘家的电话,师娘在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又问建设哥最近一段时间晚上干些什么,小满清了清嗓子,刚准备说,忽然发现收电话费的妇女正热切地望着自己。小满打了一个激灵,不知为什么,忽然改口说,还和以前一样,就在屋子里喝喝酒,喝完了酒就打打牌。挂了电话,小满晕了好一会才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在把钱交给收电话费妇女的时候,他看见收电话费的妇女向他做了个小鬼脸。
小满决定跟踪一次建设哥,看看他晚上出去到底做什么,干嘛要瞒着他。只有把建设哥的行踪搞清楚了,才好向师娘交代,也不枉师娘对自己的信任。这天晚上几个师傅又喝了很多酒,然后打牌。小满有意比平时早一点上床,装作睡着了,故意打起了很重的呼噜。果然不一会建设哥他们就出门了,小满计算着时间,估计差不多了就迅速地跟了出去。
他们所租居的出租屋是在接近郊区的一条偏僻的巷道里,巷道里没有路灯,只有两边房子里透出来的微弱的灯光。这给小满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他既可以随时把自己藏在暗处,又可以借着灯光不会被建设哥他们甩掉。出了七扭八拐的几个巷道,建设哥他们往南边拐去,穿过一片荒地,他们来到了一条河的河堤上。小满知道这条河,有一天建设哥干完了一家活计,下一家的活计还要再等上一天,建设哥和小满就在出租屋里休息。建设哥让小满出去逛一逛,小满想到师娘说的寸步不离建设哥的话,心里不愿意出去,但又不好违背师傅的意愿,只好出来逛一下,就逛到了这条河边。
小满不知道这条河是死水河还是活水河,河水很深,根本看不出流动的迹象。水面上漂浮着各式各样的垃圾,有沤得发绿的泡沫饭盒,有各种颜色的塑料袋,有腐烂了的果核果皮,偶尔还能看见死了的鱼虾。河上面还有一座桥,已经很老了,那天小满无聊地从桥上走了一个来回,看见没在水里的桥墩爬满了青苔,桥身上到处缠绕着枯死或半枯死的藤蔓。桥的下面及两侧倒有一片开阔地,像是经常有人来到这个地方,小草被践踏得歪歪斜斜的。现在,桥和河流都隐没在朦胧的月光下,桥的周围有一些人或站着或坐着或缓慢地走动。小满不明白建设哥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是到这里来散心么?散心为何要把自己撇开,搞得这样神秘兮兮的呢?
时间正值初夏,夜风吹在身上有些暖暖的感觉,很舒服。风也把河里的臭气带到了岸上,但小满连鼻子都没有皱一下,和天天闻到的刺鼻的油漆味相比,这些臭气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人多,小满觉得应该向建设哥他们靠近一些,不然这些人一混杂,就认不出哪个是建设哥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建设哥他们很快分散了开来,建设哥向大桥旁边走了过去,迅速混杂在一堆人影里。
小满只好在一处僻静的河堤上坐下来,他不敢和别人离得太近,他能隐约地感受到空气里一股躁动的气息。
不知过了多久,小满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香气,猛一回头他吓了一大跳,一个女人站在身后向他笑着。女人嘴唇猩红,头发遮住了半边脸,她衣服穿得很少,许多地方都露着皮肤,喷香的气味就是从她皮肤上发出来的。小满不知道她要干什么,也不敢多看她一眼,站起身来就跑,边跑边隐约听到女人在后面说,原来是只仔公鸡。
小满惊惶失措跑回到出租里,钻进被窝把自己蒙起来。他使劲抽动鼻子,那女人的香气似乎还能闻得到。
可是,小满仍然没有把这天晚上发生的事用电话告诉师娘。
虽然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但二十九这天晚上和以往没有任何的不同。小满吃过夜饭,看了一会电视,就早早地上床了。在回家的这几天里,小满特别恋床,晚上早早地上床,早上很迟才起,就是大白天,没事也喜欢在床上躺着。他爸也不再说学徒的人不能这样贪睡懒觉了。
小满迷迷糊糊眼睛刚要闭上,忽然听见村子里的狗叫声,这声音听上去有些阴森恐怖。接着他听见自家的大门打开了,他爸和妈都出去了。这一定是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穿好衣服也出了门。
小满跟着人群跑起来,很快来到了小结子家的门前,一辆警车停在这里,大伙围在警车的周围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从他们的议论中,小满知道了大致的情况:警察是来抓小结子的,小结子和红毛在湖州不仅参与了几起诈骗,还到处贩卖黄色碟子。据说红毛已经在湖州被抓了才没有回村过年,是红毛供出了小结子,警察才追到这里来了。小满很想知道小结子有没有被抓到,恰巧小懵子和她的男朋友就站在旁边,她男朋友从后面把小懵子搂在怀里,下巴磕在她的肩膀上,双手环在她的腰间。小懵子说,小结子听见狗叫,出门看了一眼,发现一辆车子打着雪亮的灯向他家这边开过来,他就立即从后门跑到后山上去了。小懵子还说,小结子在城里混了几年,已经变成精怪了。
不一会儿,两个警察从小结子家里出来了,果然没有抓到小结子。一个警察的怀里搂着一大摞碟片,有一张掉到了地上,他没有弯腰捡起来,而是一脚踏在上面,碟片被踏成了两瓣。小结子的爸妈从屋子里跟了出来,警察回过头对他们说,要是小结子回来了,立即把他送到乡派出所去听到没?小结子妈边哭边说,晓得晓得,他一回来我就送他去乡派出所。
警车进村的时候没有拉警笛,开走的时候却把警笛拉得呼呼响,大伙很快就散掉了,夜晚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小满回到家,看见爸妈早已回来,正坐在火塘房里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关于农民工的节目,这些农民工都是不准备回家过年的,他们正享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关怀。有人给他们送来吃的,有人给他们送来了电视机,只要你愿意,还可以免费看演出。小满看了一会就打起了呵欠,这时却听见了噼哩啪啦烟花的爆响声。他爸妈赶紧站到门前观看,并且喊小满出来一道欣赏。
烟花是徐立本家放的,也只有他家的小懵子和她的男朋友才会在年前的晚上放烟花,其余人家过年也放烟花,但无论如何要等到大年三十吃了年夜饭以后才放。
村子里有七不出八不归的说法,所以绝大多数外出打工的人都选在正月初五初六这两天出门,剩下的少数初九初十才出去。小满去年就是初十这天和建设哥一道离家进城的。今年什么时候出去,还要等建设哥来吃了年酒再决定。
但正月初四这天小满家请师傅吃年酒没能请成,头一天师娘就托人捎口信过来,说她和建设哥初四这天有事,不能过来吃年酒了。捎口信的人也没说师娘把吃年酒的日子往后推到哪一天,小满爸就让小满到檀畈师傅家去一趟,把吃年酒的日子重新定下来,让建设哥尽快决定哪一天带他进城,家里好有个准备。
小满走到檀畈身上出了很多细汗。建设哥家堂屋里又是没有人,小满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正准备喊建设哥,忽然听见有啜泣声从师娘房间里细细地传出来。师娘的房门是虚掩的,房门上面师傅和师娘结婚时写的对联还没有褪色,大红的喜字还端端正正地贴在中央。小满犹豫着,轻轻推开了师娘的房门。
一股呛人的酒味扑鼻而来,小满看见房间里乱糟糟的,有两只凳子被打翻了,地上有一只碎了的酒瓶子,洒了的酒把地上弄湿了好大一块。酒瓶子的旁边还有一只底朝天的塑料碟子和一些散落的瓜子。
师傅建设哥不在房间里,师娘坐在床沿上轻声地啜泣,像是不知道有人来了,连看也不看小满一眼。小清华坐在师娘的屁股后面,用小手一下一下扯着她的衣服。
小满立即明白,师傅建设哥和师娘吵架了,而且吵得挺凶,到了摔东西的程度。小满不知如何是好,干巴巴地站了一会儿,才想起应该把师娘的房间整理一下。他把打翻了的凳子扶起来,又找来扫把打扫,在扫酒瓶的碎屑时,他看到了酒瓶上的标签,这酒正是小结子送给他爸,又被他拿来送师礼的那瓶酒。
地上打扫干净了,小满喊了一声师娘。
师娘停止了啜泣,好半天才说,小满,我没想到你不老实,师娘把你当弟弟看待,你打电话却不告诉师娘实话。
小满自知理亏,勾着头不敢看师娘。
师娘站起来,把小清华抱在怀里,走到小满的面前说,你看这是什么?
小满抬起头来,看见师娘手里拿着一个火柴盒那么长,两根手指那么宽的小塑料袋子,袋子粉红色的,两边有锯齿。小满只看到袋子上面有一个“避”字,另外的字被师娘的手指遮住了。
师娘说,你晓得这是什么不?
小满摇了摇头,他确实不知道。
师娘接着说,这是从你师傅的包里搜出来的,有好多个呢……
小满不知道师娘后面还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家的。
……
家里冷冷清清,静得没有一点声音,爸妈都不在家,也许是到隔壁人家串门去了吧。小满觉得脑袋昏昏沉沉,不知不觉进了自己的房间,和衣在床上躺了下来。
也许是家里的床太舒服了,每次他躺到床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这次也是一样。和以前不一样的是,以前很少做梦,这次他一闭上眼睛就做了一连串的梦。
首先进入他梦乡的是一只孤零零的小鸟,小鸟站在柳树光秃秃的枝桠上。他明明看见小鸟的嘴在动,却听不见它的叫声。不知过了多久,小鸟展开翅膀飞了起来,它穿过金色的麦田朝一个未知的地方飞去,直到成为一个青色的小不点……天空忽然暗淡了下来,旷野里冒出了一朵奇异的鲜花,鲜艳欲滴。他慌忙用手去采,那花却缩成一团,从他眼前魔术般地消失了……天空又晴朗了,炽热的太阳弄得他浑身躁热。他感到口干舌燥,匆忙跑向一条河流。可是河水很脏,水面上漂浮着各式各样的垃圾,有沤得发绿的泡沫饭盒,有各种颜色的塑料袋,有腐烂了的果核果皮……河上面有一座老桥,没在水里的桥墩爬满了青苔,桥身上到处缠绕着枯死或半枯死的藤蔓……他无奈地在老桥旁边的草地上坐下来,无聊地数着天上的小星星。奇怪,天空中明明有太阳,怎么会有小星星呢……数着数着,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香气,他回头看了一下,发现徐立本家的小懵子站在身后向他微笑着。小懵子顶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衣服穿得很少,许多地方露着皮肤……小懵子在他身边坐下来,轻轻将他揽入怀里……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山崩地裂,身体猛地痉挛了一下……
第二天小满妈在洗小满衣服的时候,发现了内裤上地图一样的污渍。小满妈愣了一下,接着用鼻子嗅了嗅那团污渍,然后捂起嘴偷偷地笑了。水面上的阳光折射到她的脸上,就像是一朵灿烂的太阳花。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