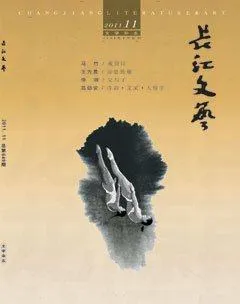大智大义刘湛恩
在中国现代史里,曾经有这样一个人来过——
他是辛亥革命以来,一位自强不息、拥有国际声誉的的人文学者,出身贫寒的他,曾获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学位,但却在乱世中放弃清雅的书斋,终生以社会为杏坛讲堂,以民众为启蒙对象,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但他逝世之后竟未给子女留下任何物质财富。
他还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曾出任知名教会大学上海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但他却矢志不移地保持着一个中国人的骨气与尊严。抗战爆发后,当大量学者纷纷出洋或转移至大后方时,他却成为了“孤岛上海”为数不多“守土抗日”的知名人士,最终遭日寇暗杀。
他牺牲后,国民政府曾赐予他“国葬”资格,上海一度万人空巷为其公祭;1949年之后的中央政府又追认其为“革命烈士”,上海理工大学至今仍有“湛恩纪念图书馆”以资纪念。
这样一位民族英雄,由于年少颠沛流离,他的籍贯竟一直被后人所误记。有学者说他是“湖北汉阳人”、“湖北咸宁市人”,也有学者认为他“出生于江西九江”,甚至还有书中称其“上海市南汇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大家只晓得——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响当当的中国人。
但是,作为他的后学同乡,我必须要知道,他叫刘湛恩,来自湖北黄石。在辛亥百年的特殊时刻,这个快被忘记的名字重新被提起并被铭记,很有必要。
一
在元曲《琵琶记》中,曾有一句话,是歌颂男主角蔡伯喈的,叫“全忠全孝蔡伯喈”。
“全忠全孝”曾一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评价一个人的最高标尺。但随着“五四”以降,孔家店被打倒,忠孝不再具备之前那闪耀的光环。因此对于一些英杰的评价,也开始“与时俱进”了。
那么,用什么词来形容刘湛恩呢?
“大智大勇”是我此时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个词,这个词曾是中国话本小说中对于乱世英雄的最好定义,譬如曹操、岳飞等人,且这个定义是不过时的。刘湛恩虽逢乱世,但却是一介书生,虽有大智但却无“匹夫之勇”,因此,笔者在这里稍微更换一下,“大智大义”,这个词仿佛更贴切。
对,大智大义,这个词再合适不过了。
最早知道刘湛恩这个名字,是在章诒和先生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书里顺带着提了一句他的遗孀刘王立明。刘湛恩的名字于是就出现在了刘王立明的“脚注”中。头衔只有一个:沪江大学校长。
沪江大学的创立,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这所由“南浸华中差会”与“北浸华东差会”在1906年合作建立的大学,一开始就充满了内部矛盾。因为在建校章程中就规定“这所学校的土地、建筑和设备费用由两会平均分担,产业归其共同所有”。矛盾重重之下,最终导致了1911年沪江大学校史上最大的一次学潮。
辛亥革命之后数十年,随着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曾爆发了著名的“非基督教运动”——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与一批有见识、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一道,喊出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口号,这个运动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收回教育权”。
这便是刘湛恩主政沪江大学的历史背景。很难想象,在这样一股伟大的历史洪流下,作为一个刚刚留学归来的年轻博士,刘湛恩是如何受命于危难之际,踏上这条道路的?
我们还必须要记住的是,刘湛恩接管沪江大学时,刚刚31岁。
二
31岁,是一个怎样的年龄啊!
31岁的比尔•盖茨,刚刚完成微软的上市,还是硅谷IT界一个初露头角的新贵;31岁的毛泽东,刚刚当选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组织秘书;31岁的鲁迅,刚刚就任教育部的“佥事”,并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对于当下许多“八零后”而言,31岁的他们正在因为裸婚、蜗居这些“不给力”的生活而“鸭梨山大”着。
从这个角度看,刘湛恩是早慧的,更是幸运的。
在军阀混战、外寇入侵的乱世,将一所大学扭亏为盈,“沪江模式”成为当时上海甚至国内教育界的样板。这不得不说是刘湛恩的“大智”,而这一切,皆是由他爱国情怀使之然,这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大义”,着实令人钦佩。
当然,最重要的、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刘湛恩在沪江大学实现了他的“职业教育”伟大实践。
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自于清末的“戊戌变法”所设立的“自强学堂”、“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等“官办学堂”,从培养人才的本质上看,依然是传统科举制度的延续。但在西方看来,大学教育不是神圣的,而是世俗的、必须要满足的是人类生存需要的。简而言之,本质必须是职业教育。
刘湛恩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便是职业教育。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乃是“学而优则仕”的“学堂”都变成了“官员培训学院”,而大量国计民生的职业却只是老百姓口里的“行当”——没有职业医生,靠的是江湖郎中;没有职业会计,靠的是账房先生;没有职业工程师,靠的是木工铁匠,一个庞大的社会,若是各行各业都不是受到正规职业教育的人,规矩何在?国家发展的前途又何在?
那么,将职业教育纳入到大学教育,该怎么做呢?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有过多年海外考察经验的刘湛恩,通过修改課时、更新授課与学分计划来实现他在沪江大学前所未有的创举。但当时国难深重,经费紧张,刘湛恩“带着镣铐跳舞”,实行“五年规划制度”,相继在沪江大学开设了“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新闻”与“化工”等社会迫切需要的职业专业,完成了“职业教育进沪江”的教学革命。“学以致用”立刻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化工系的几位学生甚至曾在业余时间兴办了一家味精工厂。
但是,沪江大学高昂的学费使得一批贫困学生不得不退学谋生。刘湛恩为了尽可能地实现“全民教育”的梦想,在全国首创“勤工俭学”的模式,在学生中组织“互助社”,为贫困生介绍兼职工作,填补学费,并开设“城中区商学院”,为社会各职业提供免费或低廉学费的职业培训。
一个动乱的世界,先驱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精英,刘湛恩的影响与意义,尤是如此。
四
当然,沪江大学校史上最壮美,最华丽的一笔,是在抗战爆发后。沪江大学成为“孤岛”上海知识分子的抗战大本营,而这个大本营的“总司令”就是手无寸铁的刘湛恩。刘湛恩历史生命的大幕,在沪江大学而徐徐开启,因沪江大学而巍巍落幕。
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往往决定了他的一生。刘湛恩之所以有这样的情怀,这与他少年的经历有关。出生于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的刘湛恩,从小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家族威逼其母改嫁,母亲不得不带着刘湛恩逃到离家一百公里的汉阳县浸会医院做护工,生于乱世、长于贫家的小刘湛恩,从小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是受到教会、好心人等社会各界的资助长大成才的——这导致了他对于苦难深重的民族、生活贫穷的民众有了别样的同情。
“九•一八”事变之后,刘湛恩主政的沪江大学自发组织了学生抗日救国会,甚至还一度成为“孤岛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湛恩遂被选为“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主席,他临危受命,在难民中兴办“难民学校”,传授谋生手艺。
刘湛恩的举动遭到了“吉斯菲尔路76号”日伪特工的忌恨,日伪曾让汉奸梁鸿志来拉拢刘湛恩,称他若肯下水便可担任伪政权的“教育部长”——此时日军已经将上海著名作家、“第三党”中央宣传委员张资平拉下水。但刘湛恩不是张资平,梁鸿志的威逼利诱换来的却是刘湛恩的严词拒绝,甚至刘湛恩还规劝他“从良”——“不要做这丧尽天良的无耻行为。”
日军对刘湛恩的仇恨,变成了刘湛恩家里时常收到的子弹、毒水果甚至飞入院墙的手榴弹、匕首,这些伎俩,对于一个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大智大义的基督徒、教育家与爱国者来说,是根本无济于事的。也许,他早已料到会有那一天——
1938年4月7日,一颗来自汉奸的子弹,射入了刘湛恩的胸口。
四月,春天的气息刚刚蔓延到安静的黄浦江上,只是没有人去欣赏,据天气预报记载,那天上海是阴天,没有风。
五
曾经有个电影,叫《黄石的孩子》,讲的就是抗战时期一群小孩从黄石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乱世,小城,战争,这些元素结合到一起,注定就是宿命般的居无定所。想想刘湛恩,也是如此。
记得在前些时日一个交流会议上,我向一位阳新县委的领导提及刘湛恩,他说:刘湛恩的主要事业是在上海完成的。
这话不错。
但是,英雄是时势造就的。作为中国的“抗战孤岛”,刘湛恩选择上海,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若一直生活在阳新,刘湛恩也好,沪江大学也罢,都要一切重写。危机四伏的上海,最终可成就他的“大智大义”。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位乡贤,自从五岁离开黄石之后,便再未曾回到自己的家乡。
但现在,他来了,就在不远处。
责任编辑 胡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