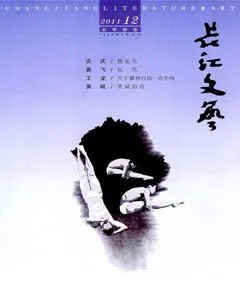另一视角中展现的辛亥首义叙事
有关辛亥革命历史的种种艺术化阐释很多,在以往的文学叙事中,“宏大叙事”成为了表达辛亥事件的基本思路和起点。的确,作为现代中国开端的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王朝对中国长达260多年的封建皇权的专制统治,对中国的现当代历史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这注定了在小说的营构上,先天地赋予了这类叙事所惯有的叙事方式,即以一种宏大的建制来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似乎只有那种全景式、总体性地展现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描绘风卷残云的起义斗争的历史画卷,展现出史诗品格的作品,才符合人们对表现这一历史事件所抱有的热情和期待。因着这种缘由,大多表现辛亥叙事的小说主旨都比较趋同趋近,大都是把叙事的重点放在表现和还原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过程中,尤其是那些参与铁血首义的重要人物的所作所为,更成为文学作品的核心体现。
不过,这种多少有些先入为主的预设的叙事模式,总让人觉得有些固型化,如果想要对辛亥首义做新颖、独特的文学表现,就需要有新的思路和观照视角。尽管这一题材的历史特定性会影响和决定作家叙事的立场和叙事的方式,但在强调尊重、不回避和解构历史的本质与主流的前提下,文学也需要对辛亥革命做更加多样化的艺术传达,不仅是还原或重建这段历史,而且也要充分地去表现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牛维佳的《武汉首义家》就做了这样一次有益的尝试,以另一种观照视角完成了自己对辛亥革命的个人化叙事。
一
遥想百年前的这场革命,今天该去做怎样的表达,从什么角度去写,都是可以好好去深入进行思考的问题。在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中,新知识分子、学生和新军,是这一事件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理当成为文学叙事的主体。不过令人感到有所缺憾的是,在有关辛亥革命的叙事里面,读者看到的只是占据人群少数的精英群体的革命行动,由革命党和新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启蒙和鼓动活动,以及由学生和新军等组成的起义军在1911年10月10日进行首义的英雄壮举,成为革命思潮和起义行动的主要载体,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总体形象。许多有关这场革命的各种话语,诸如武昌起义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而走向共和;还有这纯属一场偶然发生的起义,一场不彻底的革命,一场被篡夺乃至失败的革命等等;都围绕着他们的行动来进行印证和辩驳。而各种文本却多少有些忽略了那些隐身其后的芸芸众生,尤其是那些主动或是被动地被卷进了这场起义的普通劳工和广大的市民,尽管上述话题看似与这些小人物不大搭界,革命却仍然是以不同的传通渠道关联着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只是很少会有人把那些生活在石板深巷中的底层市民群落当作主要的观照对象,去想象这些普通人在被后人认为是惊天动地的辛亥年间经历了什么,这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带给他们精神和生活上怎样的变化。也不会有更多的人去深想,如果缺少了对这些尽管普通但却是革命和时代的当事人的关注,那么又怎么可以说对辛亥革命历史有了完整的认知和表现。
辛亥首义,对武汉这座城市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华中重镇,武汉经历了从历史名镇到商埠、城市,再到大都市的发展过程,这既是一个城市自身发展的生态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和文化生态的发展过程。辛亥革命对封建和皇权专制的政治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改变了中国的政权性质和整个社会政治的格局;同时也改变着城市的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武汉历来被人认为是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市民群落结构多元而复杂,生存情态多种多样,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必然会对具有历史相沿性的生活传统和社会习俗造成巨大的冲击,影响到城市文化和习俗的历史传承。牛维佳的《武汉首义家》在表现城市政治生态变化的同时,重点表现了城市经济和文化生态的变化,将观照的视角投注于革命首义的背景下呈现出的世情民俗的沿革与流变上,试图以一种新的历史图式来完成对辛亥革命的个人言说,从这一点来看,《武汉首义家》的叙事角度非常特别,体现出一种特殊的叙事意蕴。
在《武汉首义家》中,牛维佳将叙事的重心移到了这座城市中的普通民众那里,围绕服装衣着这种最日常化的物件展开叙事,以此去观照一个世纪前发生的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辛亥革命,重现了百年之前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普通百姓服饰和风俗的影响,表现了发生在服装上的“首义”革命,同时也艺术化地展现了最关切百姓民生的服装产业化的发展过程。小说通过谦泰鞋帽庄的二掌柜洪山恩这一凡常角色,还有像吴买办、宋先生、张二、刘勇等各类散发着武汉市民气息的小人物,描摹了凡俗的市民阶层求生存求发展的过程,将平民百姓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多姿多面显示了出来,以此构筑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叙述空间。
这种透视历史的视角,与日常世俗存在和生存表象关联,表达着世俗的欲望和利益,看似有些化重为轻,却并没有回避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相反,服装对武汉市民日常生活的广泛介入性,使得服装上的“首义”革命对普通市民的冲击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政治生态变化对百姓的冲击。从小说中可以看到,市民们在对衣装的更换上,情感复杂,既想如弃敝屣般地割断与满清的联系,又有些不知如何续上中断几百年的汉装传统,在变换服装上表现出的人情百态和世俗心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民心民意,也成为决定和影响日后生存的民生的取向。因此,从这点去审视,《武汉首义家》体现出自己的创意,这种以另类的视角完成的对辛亥革命的叙事,表现了宏阔历史背景下的世情民俗的沿革与流变,从创作的整体走向上反映出城市服饰生产发展的历史延续性。
二
《武汉首义家》的题旨有着双重的寓意,辛亥革命发生在武汉,这场首义引发了多省响应,改变了由满清贵族统治国家的现实,终结了早已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在革命首义的背景下,小说表现了发生在服装上的“首义”革命。
从历史来看,“改正朔,易服色”已成为时代的普遍规律,朝代更替,服饰衣色也必然会发生变化。在《武汉首义家》中,谦泰鞋帽庄制衣和经营的转型,辛亥革命是催化剂。武昌起义的枪声,使延续了几百年的满清王朝轰然崩塌,时代之激变几乎是发生在一夜之间,民众生活方式亦随之激变。时代的更替对普通百姓带来的剧烈冲击,除了男人剪辫子外,主要就表现在衣饰这样一种外在表征物的变化上。最庸常的市井人物剃头匠张二,只半天工夫就敏锐地洞察其变,他对这一时代变迁的直觉反应就是剪掉了辫子,然后急不可耐地拿着银子到谦泰鞋帽庄来,赶着要将自己从上到下的衣褂换成地道的汉人的服装。剃头匠张二的行为不是个别的,众多市民纷纷剪掉辫子换掉满族人的衣袍大褂成为了一种社会趋势,普通百姓在革命后本能的心态是想通过服装的更换,表达长久以来被压抑着的“反清复汉”的情绪,通过换装,割断与过去的一种联系,也借此发泄在外族的统治下积蓄了多年的无法言说的痛苦。但汉装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只有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戏服算是与汉装沾边。于是谦泰鞋帽庄为剧团制作的古老的戏装,就被民众认为多少接近于他们认为的“汉装”,纷纷购置上身,结果弄得一街人就像戏中之人,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作为谦泰鞋帽庄的二掌柜,洪山恩以商人的敏锐发现了商机,顺应和迎合了这一时代潮流和民众的需求,不仅做戏装,而且大胆尝试设计缝制新装,一时顾客盈门,市民们都想穿上此前所没有的新装,使得武昌街头各种新奇的服装充斥市面,谦泰鞋帽庄也赚得盆满钵满,借势积累了资本。
服装上的“首义”,使谦泰鞋帽庄的二掌柜洪山恩出了名,发了财。起义失败后,侥幸余生的洪山恩重整旗鼓,使服装生意不断地扩大,因此他将谦泰鞋帽庄改名为“首义家”服装厂,从作坊式经济迅速提升为大机器规模化生产。由此,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小说的基本主线就显露了出来,由谦泰鞋帽庄到首义家服装厂,再到首义家服装有限公司,这是一个开放的叙事走向。也由此,我们可以把握到牛维佳创作的整体规划,即以辛亥革命为起点,展开“首义家”的创业成长故事,这个动态的过程还可以后续延伸,在《武汉首义家》之后,还可以将首义家服装生产的转型故事继续下去,去充分伸展“首义家”最后成为武汉三镇知名、甚至在全国服装行业占有重要地位的服装工厂的故事。看得出,牛维佳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小说题材所拥有的巨大的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承载量,他会从服饰民俗的沿革与流变中,去书写历史的风云变幻,去继续这一类的小说叙事,所以《武汉首义家》本身已显露出一种大制作的思路。
牛维佳对主人公洪山恩进行了多方面的刻画。借助于这个人物的生存轨迹,小说展示了从辛亥起义到袁世凯称帝后退位这五年时间的背景下,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急剧动荡和变革,而洪山恩作为特殊时代和辛亥革命的当事人,经历了一系列由社会政治、习俗观念等激变所带来的冲击。有意无意之中,他个人命运的起伏,以及他所经营的服饰生产的起起落落,都与革命和社会情势密切相关,起义后改换新装成就了他的事业,袁世凯登基,首义家被查封,倒袁后又再度兴盛。洪山恩身世坎坷,经历丰富,他一出场是以商人的身份出现的,出于正义感洪山恩做了保安社社长,又以自己对革命的认知和拥趸,带领大家加入了义军,参与了辛亥起义的战斗,主动去增援汉口的民军,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既是商人又是半个革命者,遭受失败后心灰意懒险些出家。作为谦泰衣帽庄的经营者,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困难,洪山恩无疑是个成功者。但他并不唯利是图,而是一个敢承担、有情有意的人。他开办服装厂,所雇请的工人和雇员,大多是参加了首义的士兵和家眷,对革命党徐世华两人相识时日不多却成为生死之交,拿出金条资助徐世华去搞暴动,当徐世华被处决后,是洪山恩不顾杀身之祸,冒着危险安葬了他。在洪山恩身上“义”的分量要远远大于商人的“利”的成分,这与牛维佳有着很大的关系,他是在按自我的喜好和心理需求去想象性地再造人物,赋予洪山恩侠义正直、谦让温良、重义扶危、善良多情,有责任感、道义感等多种向善向美的人格品行,而不是“在商言商”地写人。因此,洪山恩显得有些理想化,不大像个不满三岁就到谦泰衣帽庄的人,这么多年的耳濡目染,又做了数年的二掌柜,这样的人似乎应该更多些圆滑的商人气的。
三
《武汉首义家》将宏大的历史变革主题置于一种市井化、日常化的叙写之中,由此聚合起市井社会的人情百态和世俗心相,在小说中,牛维佳将平民百姓在辛亥革命中的多姿多面显示了出来。他塑造的市井社会中的各类市民形象,如满族平民金小安和女儿金穗,教书的宋先生、剃头匠张二、花姐孙筠秋、码头帮刘勇等,平时都是些名不出闾巷,难以进入史册的小商人或市井人物,却在大革命的舞台上张扬了一把,接受着历史的文学记载。
牛维佳力求使自己的叙事更接近民间市民社会最本真生存的状态,在一种历史化的语境中,去完成对人物的塑造。在小说中重构和再塑的历史人物中,最为突出的是两类人物,一是“女性类型”,另一是“市民类型”。
“女性类型”有金穗、孙筠秋、姜全芳等,金穗和孙筠秋在洪山恩的生命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表面看三人爱恨纠葛的的男女关系构成了传统言情小说的架构模式,但实际上这并未成为小说叙事的重心,小说中着重表现的是这两人在洪山恩的服装经营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金穗有着特殊的身份背景,作为满人的后裔,清王朝的垮台对她和家人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为了避免成为杀戮的对象,以求自保,父亲金小安匆忙把金穗许配给洪山恩,尽管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但金穗却感到悲愤与委屈。正是这个几乎成为革命对象的人,却对革命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她认为革命不应有满汉之分,所谓共和就是所有人都和平相处。正是这种认识使她不刻意去复制“汉装”而是设计出“新装”,谦泰衣帽庄的新服装样式都是出自金穗之手,“新装”广为人们所接受,洪山恩抓住了这个商机并由此而发达,使谦泰鞋帽庄实现了向首义家服装厂的转型。
另外一个身份较为特殊的女性是孙筠秋,洪山恩发现青楼女子往往引领着都市服饰的新潮和时髦,常常别出心裁地做出各色服装,这使他看到了第二个商机,尽管受人非议,但他决定和孙筠秋通力合作,推出时尚的衣装。结果孙筠秋设计的又大胆又开放的女装样式,虽招来人骂,穿的人却很多,再次让首义家成为行内的佼佼者。对首义家的掌柜洪山恩而言,孙筠秋显得更为重要性,这不仅因为孙筠秋是他的第一个女人,在少女时候就生下洪山恩的女儿,更重要的是与金穗相比,孙筠秋可说是洪山恩的红颜知己,能替他排忧解难,不管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生意上的危急时刻,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洪山恩陷入危难的时刻,孙筠秋独立经营的服装厂成为首义家再次崛起的关键,她不惜牺牲自己,甘愿嫁给黑帮许白面去帮洪山恩借高利贷筹措资金。她的鼎力相助使首义家服装厂完成了第二次转型,由一家变成四家工厂,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工艺和规模的首义家服装有限公司。孙筠秋的形象比金穗显得要饱满丰富些,她对洪山恩既爱却又无法抛开身份的自尊与纠结,以及表现出来的经营智慧和牺牲精神都描摹得很细致真实。
“市民类型”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的人物,以洪山恩为代表的本地商人,以吴买办为代表的买办群体,和作为帮派文化的代表的刘勇、猫伢等,还有像剃头匠张二之辈的市井人物,这各色人等都在作品中得到了最细致、最丰富的还原。从这些小市民的生存状态和心态特质中可以显现出市井世相和民风遗俗,也最能传达出城市的世俗气息和市民趣味,尤其是那些市民的方言俗语的运用,既成为武汉这座城市鲜明的市井文化的标记,而且也成为不同阶层人物身份和个性人格的最直接的显示。对这些人物的叙写,牛维佳融进了源于城市人自身生活的体验,源于对市民生存本相和毛茸茸细节的感知和悟性,武汉的风物风情早已悄然融入他的人生经验和寻常印象之中,这也是这类人物写得比较生动的原因。
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些个性张扬、经历奇特的人物,如洪山恩的生父善于逃遁的江洋大盗吴飞,还有来无善缘、去无慧根,野性难驯的小莉云,留着八字胡须的侯将军等,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生命质地的繁复性、生动性,直观而生动地把已经远去的历史人物鲜活地还原在读者面前,这些人物,随便站在哪里,都“汉味”十足。
在《武汉首义家》中,牛维佳以写实的方式诠释着武汉的市民文化和商贾文化,在对市民日常琐细生活存在的本体形态的显露中,也对武汉的民俗做了充分的描摹。小说中还引入了湖北大鼓这种民间的艺术,这些都提升了小说的地域性的特点。
责任编辑 易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