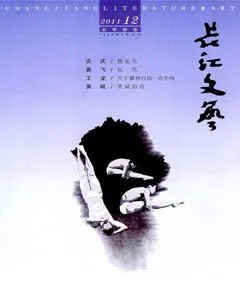写出革命的复杂性来
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望见蓉的长篇历史小说《铁血首义路》出版了,可喜可贺!读过以后,觉得她对于辛亥革命那一页历史的回眸,有独到之处。
在历史学家眼中,辛亥革命爆发于武汉,有许多历史的机缘。而在作家望见蓉的笔下,那场革命是有民风作为依托的。小说中有一段文字,写“武汉的气候和人一样,不喜暧昧,是爱走偏锋的。夏天热成火炉,冬天冷若冰窖。在这样的城市生活,人也要随时接受大起大落的命运。”小说对于那些革命党人的激进言行(例如关于曹新生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意志而断指、并且大声喝问“还有谁不相信我曹新生的?我把头割下来悬梁示众!”的情节)的描写,就令人震撼。武汉人容易冲动,而冲动不正是革命者的基本素质之一吗?然而另一方面,作家显然无意美化那一页历史。民风永远呈现出复杂的效应,即使在革命年代也不例外。我甚至觉得这部小说在突出武汉人的另一面上颇具慧眼:“他们又精得像水里的鱼”。这“精”指的是“精明”,是武汉人在码头上求生存、求发展练出的心机。这心机使武汉人善于经商,又常常因为“太精”而坐失良机。小说写革命箭在弦上之际“湖北革命者辛苦拉扯起来的队伍,只因互不买账,甘愿大权旁落,真是自己栽树,别人摘果子”那一段描写就相当深刻揭示出了武汉人的软肋。是的,革命不仅需要热血、需要冲动,还需要胸怀、需要谋略。此外,在小说中的刘银根身上,也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武汉人粗鄙的一面:他口口声声“谁让我姑娘不痛快,我就要让他不痛快!什么狗鸡巴革命,谁惹老子不高兴,老子就革谁的命。”“个斑马儿的,是革命重要,还是过日子重要?”“革命,也不能先革到自己头上啊!”话虽这么说,他仍然对未来的女婿、革命党人曹新生欣赏有加,并最终把自己的性命献给了革命。这几笔,作家也写得细致入微,曲尽其妙。甚至,小说在革命后来受到挫折以后让灰心的曹新义发出了“革命是为了什么”的叹息,感慨“革命,它让我匪夷所思”,并最终遁入空门,也写得相当有深度:革命有高潮也有低潮,革命常常不似许多参与者想象得那么浪漫、富于诗意。而那些经历过革命又终于看破了红尘的人们,也未必都是懦夫。
《铁血首义路》因此而写出了革命与武汉、与武汉市民的历史因缘,同时也寄寓了作家对于革命的复杂的独到思考。在我们纪念辛亥革命时,当然应该记得那一代革命者的英雄业绩,同时也不能忘记革命的复杂、历史的玄妙。革命,既然是千百万人参与的壮举,就自然免不了形形色色的人性表演、命运浮沉。
围绕着这样的思考,作家努力还原了老武汉的历史场景:从胭脂巷的脂粉气到英租界的洋场气,从昙华林的书香气到花园山的英雄气……在一幕幕场景的变化中,就写出了浓浓的“武汉味”。小说有不少情节是在胭脂巷的脂粉气中展开的,而那脂粉气时而成了儿女情长的氛围,时而又成为革命党人开展秘密活动的掩护,也写得颇为别致。武汉是个大码头。码头上的三教九流各有自己的人生追求,这些追求之间的碰撞、交织,使得这里的革命也打上了特别的烙印:张之洞在这里推行“新政”,本欲挽救清朝的命运,却不想也阴差阳错为革命打下了基础(小说中关于“现在湖北的学堂多着哩。武高等学堂、文高等学堂、文普通学堂、武普通中学、方言学堂、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军医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等等,不下百所哩”的一笔就写出了湖北的新气象。辛亥革命由张之洞一手训练出的新军发动,也相当有讽刺意义);还有关于“我们湖北有哥老会、洪江会、三点会、江湖会、红灯会。他们都骁捷善斗,十分凶悍。他们的目标就是‘排满’、‘兴汉’、‘灭洋’”的描写也写出了民间结社与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作为辛亥革命前奏的四川“保路运动”中,哥老会等民间组织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说起武汉文化的基本特质,一般都认同“码头文化”的说法。只是,人们对“码头文化”中好勇斗狠的一面批评较多,却常常忽略了“码头文化”中行侠仗义那一面的积极意义。事实上,在革命中,行侠仗义的品格常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铁血首义路》对革命党人秘密结社、慷慨就义的描写可以说是对“码头文化”中行侠仗义品格的一次成功讴歌吧!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了。那场革命的硝烟早已消散得没有一丝痕迹了。然而,历史仍然以这样的方式提醒了我们的记忆:那场革命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当我们在了解武汉的历史时,当我们在读到《铁血首义路》这样的历史小说时……
责任编辑 易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