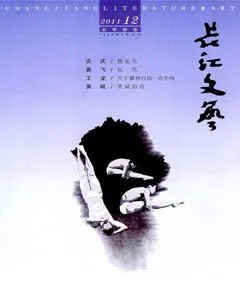关于瞿秋白的一点争鸣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各种纪念庆祝的文章层出不穷。不过我更对一个人物感兴趣,那就是瞿秋白。从关于他的一些争论中,可以看出我们很多宣传思路十分有趣。
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近年来最集中的争论,是关于长征开始前他是否被博古“扔包袱”留在苏区,才导致被捕牺牲的问题。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严重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决定高层干部“走留”问题,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学者们各执一端,争议甚多。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都担当着艰巨的任务。因而林伯渠在告别留下来的老战友时,在其诗《别梅坑》中也不由自主地发出“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有“走”的机会,都愿意跟随主力红军杀出重围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那么,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是否非其所愿?他是以被抛弃者的身份为革命殉道的吗?2007年,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一文中坚持认为,瞿秋白被害原因是博古趁机要“把瞿秋白扔掉”,以达到其“根本解决”、即“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的目的,于是“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学者认为,把瞿秋白被捕牺牲的矛头不是指向国民党蒋介石,而是指向革命先烈博古,这既是对博古的肆意伤害与扭曲,更玷污了瞿秋白坚定的革命意志。归结起来理由有几点: 一是博古中央将瞿秋白留在苏区是出于公心,因为其间决策理由正确,组织程序正当;二是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瞿秋白当时主管宣传,还主编《红色中华》,而掩护红军秘密撤离需要正常出版报纸以迷惑敌人,瞿秋白一旦辙离,他的工作别人很难替代;三是瞿秋白被留下,还因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
双方的观点似乎都不无道理,但我觉得争论的焦点主要还是混淆了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这几个问题上。这样全方位兼顾分析瞿秋白的主观愿望、当时的客观实际以及博古中央的真实意图,才有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首先,看瞿秋白“应不应走”。
瞿秋白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瞿秋白。就是说,一旦留下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
瞿秋白当时确实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常咯血,热不止且风难禁——让这样一位重病缠身、难以自理的病人留在大兵压境的严酷环境打游击,显然凶多吉少。王彬彬所说让瞿秋白留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苏区,“无异如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生还可能性十分渺茫”,并不为过。
要说患病,毛泽东当时也刚刚身患疟疾,憔悴不堪,以致于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可还是照样随军行动。贺子珍当时已经有几个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还是上路了。至于是否因为瞿秋白身患重病无法随军长征,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后来有这样的说法:
“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像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
另一方面的例子是,1933年4月,王稼祥遇敌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长征开始时,王稼祥腹部插着管子,坐着担架开始了行军。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全程坐着担架走完了长征,坚持到达了陕北。可见,连王稼祥拖着这么严重的病躯,坐着担架也走完了长征全程,瞿秋白也不见得就经受不住长征之苦。
其次看瞿本人“愿不愿走”。
2009年3月,党史研究者曹春荣撰写文章《历史岂容任意涂抹》中,根据瞿秋白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忠实积极、奋不顾身地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表现,从侧面否定了王彬彬教授关于瞿秋白“不得不留”的说法,斩钉截铁地认为瞿秋白“出自他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完全是自觉自愿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他认为瞿秋白这样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怎么可能跟“不得不死”这样被动、消极的心态和遭际相提并论呢?
仔细琢磨,曹文在细节上都对,整个看起来就错了。曹先生的论据看似逻辑严密,冠冕堂皇,却首先无法解释他自己文章中的一句话:
“……面对吴亮平为瞿秋白留下说情,张闻天也说过,瞿秋白被留下,‘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吴黎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它》)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瞿秋白自己主动愿意留下来,还用得着这么多人为他要不要留下来“说情”吗?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张闻天1943年12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同志(即上文之吴黎平)回忆说,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
“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出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回忆张闻天》)
会后,毛泽东确实找过博古,结局是毛自己所说:“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也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王树增:《长征》,第67页)那一瞬间,瞿秋白明白了,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任其自生自灭。
瞿秋白能不能走是一回事,本人愿不愿走却是另一回事。如果其本人坚持走而最终只能“留”,那就要问一问其中到底是何原因?
反驳王彬彬观点的几位学者都指出,瞿秋白留下来是由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决定的,而不是由博古一人操控的。博古不管任何人说项,都不再违背组织的决定,正好表明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和原则性都很强的领导人。但从上文所引的资料看,同意瞿秋白走并为他说情的有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吴亮平等人,而现有资料表明反对的只有博古一人。但长征开始前,有人主张将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留下,因为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坚持,他们也参加了长征。我们姑且相信博古确实如其老部下黎辛如言“是一个很讲组织原则的人”,可这个原则为什么到了瞿秋白这里就一点变通的余地也没有呢?何况后来延安整风的时候,博古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干部以后(有)遭受牺牲,这是我(应)负责的。”
可以想见,此时“左”倾领导者把他们任何一位不喜欢的干部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都可以说是“革命事业”的需要,都是有着堂而皇之理由的。因此我赞同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观点:“他(瞿秋白)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让他听任命运的摆布,实际是听任国民党的围剿大军的摆布,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反观整个苏区内,此时瞿秋白作为刚刚才在上海犯过错误的“待罪之身”,留下来“戴罪立功”,理所当然。在残酷的政治游戏中,瞿秋白虽然已经出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对角逐者的抛弃过程就已经结束了。
吴黎平回忆,走留名单公布后,他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瞿秋白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满腔悲愤地说: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学习与研究》,1981年创刊号)
当瞿秋白站在萧瑟的风雨中目送红军出发长征时,他把自己身边一位身强力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再三叮嘱他保重身体,同时还将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他已经预感到,留下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了。
瞿秋白此时的心境无疑是相当复杂的。在那时的共产党人中,瞿秋白是一个较为“儿女情长”的人。自己过去屡经挫折,饱受打击,不为身边的同志所信任,在此关键时刻仍然如离群的孤雁,被抛下单飞;现在目睹革命遭遇严重失败,和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就要远走他方,今后是否得见完全无法预料;将来还要拖着沉重的病躯,在十面埋伏的苏区和数倍于己的敌人艰难战斗,胜负难料,生死难料。这一切,能不让他身心煎熬、意绪难平吗?瞿秋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尽管服从组织安排,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但他也是肉体凡人,而且是一位有着丰富情感的文化人。在如此悲伤苍凉的生离死别之际,还能不允许有一点自己的情绪波动吗?
那些一心想让革命人物变得“高大全”的先生们真是多此一举。真正的革命者不需要包装,更不需要粉饰。战士也有一腔柔情,但当冲锋号吹响,他们照样奋不顾身、一往无前。
送别了战友,瞿秋白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时刻忧心红军撤离的安危,如同坚守战壕的战士,不顾咳血疲惫,夜以继日地工作,坚持《红色中华》正常编辑出版,形成红军主力仍在苏区活动的假象,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方醒,急急忙忙闯入早已空空如也的中央苏区。
由此可见,瞿秋白愿意走,并不代表他不愿意留。但作为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他履行组织赋予的使命时毫不动摇,直到最后一刻,依然如同一头负重羸弱的老牛,拉着深深勒进皮肉的革命之车奋力前行。
瞿秋白是一位智商非常高的人,再加之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经验,使他内心深处并非不明白自己一旦留下来的悲剧命运。但对于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投身了“革命”,就意味着皈依自己永生的信仰。尽管“同一营垒”的人对他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真诚,他自己所经历的许多事,也确实使他对这种残酷斗争“政治”情感上的疏远和背离,但在行动上他必须与“革命”保持一致,他已经没有为自己重新选择道路的“权利”。既然总得有一批高干留下,那么让身患重病的自己留下来帮助中央实现预设的战略目标,尚可以避免其他同志的牺牲。
虽然作为一位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屡次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但中国传统士人的良知道义,和一个革命者坚定不移的个人操守,使他尽管怀着复杂伤感的情绪,依然以归于平静的心态走向苍凉的命运之路,把自己孱弱的身躯献上革命的祭坛。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的身体,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捕获,后被杀害。在他最后的遗言《多余的话》结尾处,瞿秋白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时,仿佛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豆腐是软弱易碎的,但瞿秋白终于没有被外力压扁,而是保持了洁白完整的外形。
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大仁者,虽九死犹未折。在人生定格的最后一刻,他将生命价值又推上了一层。
从这段党史可以看出,那些站在神坛之下,一心想维护革命人物的“圣洁”,把革命者打扮得光鲜亮丽、一尘不染的人,大可不必。在他们的观念里,革命不能沾染半点余念杂质,而只有大义凛然,光荣正确;革命者更不能多愁善感,而只能视死如归,无情如铁。但诚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言:“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表面上气壮山河,客观公允,实则其崇高的行文语气和革命的出场范式却颠果为因,大而无当。“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以偏概全、曲解历史固然不对,故意穿靴戴帽、站在自以为正统的立场“正解”历史更是功利主义的表现。
责任编辑 易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