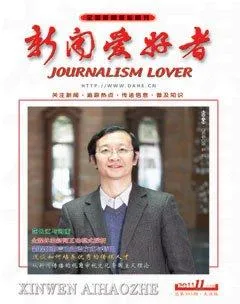杂坛从此少容颜:怀念刘思同志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已经去世的大嫂。她生前多病,面目黧黑,没有生机。可是在梦中,她的身体还是那个孱弱的老妇,面色却与身子形成极大的反差,红润得倒像仅有三四十岁,令我惊异。
早晨,我好想忘记了那个梦。电话铃声一响,继兴同志告诉我:昨夜刘思走了。
刘思同志走了,我想写点什么,可又不知从哪儿说起。
随即继兴同志用手机短信发来他自己以及杨诚勇先生、陈鲁民先生、宋子牛先生等文友悼念刘思先生的诗句。于是在我的心头慢慢地涌出这样的句子:
诗入摩罗笔如椽,文追屈子剑指天。
尔时,我正在攻读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是在为纪念王大海先生逝世十周年做功课。
大海先生生前极为推崇鲁迅的这篇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论述了英国、波兰、匈牙利、俄国的摩罗派诗人如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微支、斯洛伐斯基以及裴多菲等,称赞他们用诗歌作武器,是“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因而他们都是“精神界之战士”。“摩罗”是印度梵语,意思为“魔鬼”。“魔鬼”的对应面当然是“上帝”,是当权者,是正统的意识形态。所以,鲁迅在论述拜伦时就说,拜伦是借他诗中主人公该隐的口说出了“恶魔是真理的传播者”这样的话。大海先生早年参加革命,深受摩罗诗人的影响;刘思先生由诗歌转向杂文,常常嘲讽荒谬,解剖谰言,鄙视权贵,具有摩罗诗人的风骨。因此,我把他比做摩罗诗人,比做敢于剑指苍天的屈子。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文章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人的忧国忧民以至于忧党的责任感。但鲁迅这篇文章于1907年用文言写成,十分难懂。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今天读这篇文章,不借助专家的注释翻译,困难很多。所以,我是读读放放,久不能入其堂奥。当然,这是题外之言。我写的第二句是:“人生六十耳不顺,咳玉喷珠多佳篇。”那是想到了他的《耳不顺集》是他六十岁时出版的。但他此后继续写作,仍然有“耳不顺”的问题。所以,后来听了子牛先生所言,我琢磨:改为“听风观雨”庶几能够差强人意:
听风观雨耳不顺,咳玉喷珠多佳篇。
刘思同志身高、脸红,说“面如重枣”也不为过。因此,我们见面我常学着侯宝林大师的那句话打趣:“那个红脸的他是谁耶?”刘思笑笑算是应答了。听继兴先生言,刘思这次走得极坦然、极潇洒,不吊唁,不告别,不让惊动朋友们,几乎是和老伴开着玩笑就走了。想到大海去世的时候,他满含泪水,跑前跑后,却坚持要放《欢乐颂》的情景,想到昨夜梦到的那个“红脸”,我虽然不信鬼神,却不能不想到“心理感应”的说法:是刘思来向朋友们道别了。于是顺口流出:
昨夜红脸入梦来,今晨忽报汝登仙。
大海十年,搞个活动,是我的倡议;大海十年的活动尚未举行,刘思又先行一步,未免使人伤感。于是就有了结句:
大海十年刘思又,杂坛从此少容颜。
我们这帮人,平时在一起畅所欲言,口无遮拦;打趣玩笑,家常便饭。“红脸入梦,刘思道别”,并非虚妄。当年,朋友们和刘思开涮,有时也会开到文字里。1992年,我主政《新闻爱好者》的编务后,开始约请刘思先生写文章;刘思的文章是每到必发,前后发表了十八九篇的样子。有时来得勤一些,有时得编辑催。刘思后来来信了,一本正经地写道:
孔副主编:
阁下索稿,我曾在数月前奉上一则之后,又开始写其二,但写了大半因种种原因又搁下了(种种原因有贵刊稿酬甚至低于郑州晚报的原因在;但“市场经济”也不能没有友情为重,何况允诺在先?)今日检出补完奉上。
刘思
8月7日
刘思说的要“补完”的这篇稿子,即发在《新闻爱好者》杂志1992年12月的《饮食之道通诗文——读袁札记》一文。他从袁枚的饮食之道,悟到诗文;从诗文的求新求奇,又说回来要求“旧”;从袁枚又说到钱钟书:
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八中又这样说:“诗虽新,似旧才佳。尹似村云‘得句浑疑是旧诗’;陈古渔云‘得句浑疑先辈语’……”钱钟书先生阐释:“按此境即济慈与友人论诗第一要义所谓‘好诗当道人心中事,一若旧而得者’。”这是大手笔之大境界,简言之:人人心中所有——旧,人人笔下所无——新,“诗虽新,似旧才佳”;《红楼梦》尽写儿女情家务事,却贵在没人那样写过。鸡鸭鱼豚寻常事,名厨烹制饕餮惊,方见名厨技艺,并不“标新立异”到把人不可食之物端上桌来,此或可为求“新鲜”者一戒。
这就是刘思的思维,旁征博引不离主题,放得开又收得拢;反复说此,而意在道彼;云天雾罩、山重水复之后,又会让你豁然开朗。
我记着刘思的情谊,到1998年6月,在《新闻爱好者》出版150期的时候,我以《短简情深 尺幅万里》为题,发表了诸多前辈名家等作者给编辑部或者直接给我的来信。我说:我利用两个“大礼拜”的时间,“重新翻检、阅读”,“上千短简,使我又一次次地感受到师友、同仁间的友情是多么的珍贵”。这发表出来的“短简”就包括上述刘思那封来信。刘思看到后,稍有责怪的口吻,说:“你还把我要稿费的话也发表出来?”我说:“你是杂文家,还在乎这个?”
刘思博学、健谈、思想敏锐,每每叨到问题的要害,但并不是直来直去,而是上下翻飞,左右铺陈,旁征博引,贯通古今,在听者入迷的时候,突然甩出一句要害的话或发人深思的话,戛然而止。因此,朋友们聚会都爱听刘思发言;听刘思,是一种享受。而在许多的所谓敏感时期,刘思的文章也往往不同于流俗,他不做官样文章、应景文章,更不讲官话套话拍马溜须的话,他的话往往是话中有话,耐人寻味。刘思同志讲话如此,行文也如此。1994年12月,他把刚出版的《耳不顺集》送我;我在读过之后,随手于目录页记下这样几句话:
1995.5.27读完第一集,第二集及第三集前三篇,其余,作品发表时多已读过。
刘文恣肆汪洋,广征博引,曲而有致,岂能一遍而过?!
刘思的辩才令我折服,我愿意阅读他的作品,也愿意发表他的作品。我曾经是他的一些作品的“第一读者”;我从他的文章中获益良多。
他走了,让我感到杂坛黯然失色。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读读他的杂文。
(写于2011年7月26日上午、中午)
(作者为本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