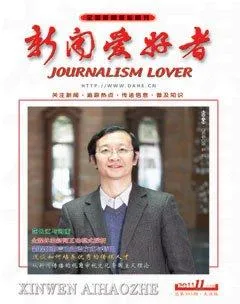论申艳诗歌的悲情意识
在申艳的诗歌之中有着对时间、生命、本真生活状态的体悟与诗化阐释。这种生命不仅仅是当下的生命,更有人类的历史,历史是人类生命的积淀。在以诗化语言表达的生命体悟之中浸润着一种深厚的悲情意味。我们以之为视角来对申艳的诗歌进行分析。
何谓“悲情”
悲情是一种美学范畴。这种在审美意义上的悲情不同于生活中因苦难而呼天抢地之悲,也不同于悲剧之悲。它们有相似之处,但各不相同。现实生活中的悲,因有着直接的现实性而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如生活中悲惨的事件等。悲剧的外在形式可以概括为由冲突而抗争,由抗争而走向毁灭。悲剧的主人是具有正面价值的人物。悲剧之悲,超越了现实的功利性,是艺术化的具有审美品格的悲。悲情不同于前两者,首先悲情不是由现实生活的直接的悲伤之事引起的情绪波动,也不是美好事物遭到毁灭而产生的悲剧激情。悲剧与悲情有着相似之处,但二者又有不同。一是形成的原因不同,对于悲剧而言,造成悲剧的原因一般是明显的负面事物,如所谓社会悲剧等。致使悲情形成的事物,是无极限的东西,如时间等。二是存在范围不同,悲剧更多地存在于艺术之中,而悲情只存在于具有生命意识的社会个体之中。三是表现形态不同,悲剧激情猛烈而短暂,它产生于人们感受悲剧之时;悲情之悲绵长而持久,它存在于个体对生命以悲为基调的体悟之中,可能以生命为期限。①申艳诗歌之悲有着悲情之悲,而非其他之悲。
申艳诗歌悲情的具体展现
申艳诗歌中有着悲的因子,我们把它定义为悲情之悲。其具体展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从诗歌意象来分析申艳诗歌中的悲情意识。艺术要以形象来表情达意。艺术离不开形象,这种形象不是原始的纯粹的物象,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情以象显,象中含情的“情象”。②主体以含情之心去观照对象,对象也以自己特有的形象向主体“绽放”自身。因而,我们可以以此为切入,分析诗歌的情象进而把握诗歌的内在情感问题。艺术中的情感是艺术化的情感,具有超功利性。这种艺术化的情感往往借助着艺术形象来表达自身。读者可以通过感受艺术形象,接受其中的艺术情感,领悟其中的哲思,最终达到艺术的目的。
读申艳的诗,在其中的绝大部分审美意象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有着共同的审美倾向性:忧郁、沉静。这些审美意象是冷色调的,具有悠长绵绵的悲伤情愫。我们可以以时间类的审美意象为例加以说明,“长夜、寒夜、黄昏、清明、初春、夕阳”等,长夜难明,寒夜漫漫,初春的寒意浓浓,黄昏的光景迟暮,都让人为之唏嘘不已。这些意象具有冷与悲的色彩。我们分析一首申艳的小诗或许更能说明问题:月色如霰,寒夜封在水底/寂静抻平微澜。一粒沉睡的石子/梦见自己满身披绿/瞬间的惊恐又拉皱寂静/黑色漫延,泼醒水边居住的女人(《微澜》)。冷月与寒夜、寂静与惊恐、无边无际的黑夜与水边惊梦的女人等共同构成了有张力、有生发性的艺术之境,让人思绪万千,可以感觉到这首诗的基调是冷与悲。
其次,我们可以从申艳诗歌中显露的生命意识来分析其中的悲情。生命意识,是对人生与生命的认识与体悟。我们要在生命的过程中去体悟生命,但是仅仅是在“生”之中来体验生命是不够的。相对性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态,仅从一面是无法认清事物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这个命题的逆否命题同样成立。其实,要想真正地了解生,还要了解死的问题,因为生是与死相对的。海德格尔说,人是向死而生的。③某种意义上说,是死亡让人有了生命的感觉。具有生命形式的人是没有死亡的感觉经验的,我们对死亡的意识都是从现实中其他人或者其他生物的死亡现象中得到的。这种对死亡的思考是在没有任何感性经验基础上的纯粹的哲学思考。
生与死是人生之大限。追求自由与无限是人性的内在需求与倾向。当人有了自我生命意识,他们会对死亡问题进行思考。这其间有畏惧、有痛苦、有苦闷。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们在日常的功利生活之中会暂时地忘记死亡的问题。但是在其生命的过程之中生与死的问题总是长存的,是挥之不去的,它总会在某一时刻不期而至,成为困扰人的最大的最根本的问题。④有的人会用生活中具有欲望特征的事物来填充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想忘掉这个问题。在经过当初的畏惧与痛苦,苦闷与有意无意的回避,最后都是无助的,徒劳无功的。在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无奈。人类要以自己极其有限的生命时间以及有限的生命能力与无限的时空抗衡,最后的结果总是失败的。一旦从思想上明白了时空无限而人生短暂,而从心态上经过痛苦到痛定思痛,到最后的内心明了,心平气和,人们就会达到对生与死的超越。在申艳的诗歌中有着对生命的思考,有的是对生命之苦的表达,如《蚯蚓》;有的是对生命本身的思考,如《一只蚂蚁举着另一只蚂蚁》。
以悲情之心来思考人生与生命,人生是一场悲剧。因为生死相对,人是要死的,从有人类以来,这个用归纳法得到的命题还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个反证,它还是以无可争议的正确性来统治着人类。但是,以悲情之心来体验具体的人生与生命,这个人生与生命之中却没有一件让我们伤心的事。因为悲情超越了生死大限,以更高的视界来观照这个世界,以超越悲喜之心来应对功利世界。人们会以特有的平静之心去观照世间的万物。原本平淡无奇的事物也有了生命的厚重感。痛苦有可能变成可爱,瞬间可以成为永恒。我们来看作者的另一首诗《田垄上》:我弯下腰,才看清楚/一朵小花颤动着的,淡淡的蓝紫色/裸着柔弱的蕊。细微的香/在风中,和着雨后泥土的湿气/一只更小的蝶,藏不住/浅粉色的春心,绕着小花翻飞/想拍下它们若即若离的瞬间/我使用微距,再一次深深弯腰//因此我看清了由野菜、茅草、蝼蚁/以及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小生命/组成的春天/因此我憋红的一首小诗/啪地打开。
那不知名的柔弱的野花也可以有春天,那更小的不漂亮的蝶也可以有春心。这还不够,甚至是那野菜、茅草、蝼蚁等都可以有自己的春天与天地。它们是微弱的,甚至一生也不会被人发现。它们在无人知晓的时空之中,生长了又死去了。它们存在的时间很短,存在的空间极小,它们组成的风景更是微不足道。但这卑微的随时都可能被湮没的风景却同样可以是永恒的,只要它们曾经来过。这平常的景物在作者的眼里成为永远的风景。
最后,我们从申艳诗歌的历史感来体会其中的悲情意识。申艳的诗歌中有着很强的历史感。历史不仅仅是时间的积累,更是人类文明的积淀。对于艺术来说,这种积淀主要是人的情感,人对历史哲思的积累。历史感是扩大了的个人的情感与反思。无数的个人汇流成了社会性。把个人置于历史之中来思考,就会有无限大的视野,历史为个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背景。个人在历史面前感慨“渺沧海之一粟”的同时,也获得了无限的思考时空。历史感的宏大的视野让我们的思考具有了跨越时空的可能。个人的爱恨得失在历史感的大背景之下变得微不足道,个人消融于历史当中。如申艳的另一首诗歌《唐碑》,立于当今,回望历史也眺望未来,这样就有无尽的时间性,把人的存在渗透于时间长流之中。人的情感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变得细微而绵长,从有限走向了无限,现实存在的生命与有限的人生与此同步,也从有限走向了无限。
申艳诗歌悲情意识的启迪意义
诗歌是语言的精华,更是思想的精华。思想成为诗歌之骨,无骨而不能立,无骨而不能久远。而诗歌之思存在于诗歌的艺术形象之中,而不是概念的逻辑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申艳诗歌中蕴涵的悲情意识是一种情感因素。这种情感借艺术形象得以传达,这样的情感是一种渗透了对人生哲思的情感。我们在感受艺术形象的同时也体悟到其中的理性思考。人性的形而上追求倾向与人生的挫折经历成为读申艳诗歌而引起共鸣的两大心理基础。人们渴望自由,但是无法摆脱必然的限制,这就造成了人生的无奈。读申艳的诗歌可以让我们进行这种思考。在无奈、困惑之后,如果能以理性的方式,把问题给以解决,那么人的情感就会得到析释。正如冯友兰说的“以理化情”⑤,用理来化解情的困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让人无奈的事、让人困惑的事,也让人为之唏嘘不已、无法释怀。当我们以悲情之心去体悟这个世界的时候,从人生与历史的角度,通过哲理之思明白之后,就不会对这样的事耿耿于怀了。“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由无奈经苦思到明了之后的平和之情。申艳诗歌的悲情意识的启迪意义,就在于让强烈的情感经思考而变得平和,因明白人生事理而超越由人生必然带来的困惑与痛苦,最后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
注 释:
①王旭晓:《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7页。
②陈望衡:《当代美学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0~148页。
③④海德格尔[德]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1~276页,第293~298页。
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