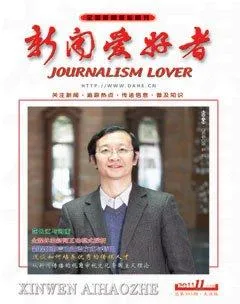《山楂树之恋》:男权社会中的商业制作
根据作家艾米的网络小说改编的电影《山楂树之恋》,是一部投资数千万元的国产大片,也是众多关心张艺谋导演的观众所期待的一部“文艺片”。凭当年《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系列文艺片登上大腕宝座的张艺谋,为了票房收入,拍出了《英雄》、《十面埋伏》、《三枪拍案惊奇》等票房大片,但也为此声名不再,昔日的艺术大腕沦落为了满身铜臭的片商,有人说推出《山楂树之恋》是他为了挽回自己声誉之举。但就笔者看来,这样的预期大概是没能实现,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谈艺术片《山楂树之恋》的商业媚俗带给观众的失望。
纯洁女性镜像的历史建构
电影宣传中再三强调,这是一个“史上最纯洁的爱情”故事。如果说是相对于当前的商品经济时代里,被无尽物欲搅腾得浮躁不安的社会风气而言,确乎也可以说是一股清新的风,以一种朦胧忧伤的调子,讲述一个过去发生的初恋故事,无论怎么说,都是独具匠心的。但仔细思考,又会有些困惑,“史上最纯洁的爱情”,顾名思义,应当是指电影中的爱情是历史上最纯洁的爱情,那么,何为“史上最纯洁的爱情”?笔者推测,导演所谓的“史上最纯洁的爱情”,大概是指影片中热恋的男女主人公曾经同床共枕一宿,但除了拥抱谈话外,并没有丝毫其他的关系。也许是由于太在意“最纯洁”的叫座率,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几次热吻在电影中都没有出现,两人的拥抱也是隔河相抱,甚至在小说中原本丰满性感、小资情调的女主人公静秋,变成了一个发育未全的“青涩”少女,这种“纯洁化”的结果,当然也使观众难以理解老三为什么要对静秋如此深情,只觉得这是一种畸恋。如此“最纯洁”的电影,为什么却单单要保留“让导演十分慎重”的“床上那场戏”?难道如此这般就是“史上最纯洁的爱情”了?这种缺乏生活逻辑,没有情感逻辑铺垫的“不及乱”情节安排,除了为叫座外,其深意实在是令人难以明白。再联系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制作与宣传,使人分明感到,导演对演员的选择标准是值得商榷的。两位演员都是新人,没有任何表演基础,但是导演却说:“这部电影的后半段他们的表演已经不输专业演员,而且有些东西还是专业演员演不了的。不是专业演员没有能力,而是他们无法再去复制一些本能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像初恋一样。”①但事实上,两人都自曝没有恋爱经历,拍完后又都承认:在表演中没有擦出火花。那么对导演的本能表演说应作如何理解呢?在影片宣传中倒是对挑选女演员的费心大肆渲染,说剧组是如何在两千多名候选人中,选择了一个高中学生,该女又是如何纯洁无瑕云云。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性仅是男性的欲望对象,一个女人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她是否“纯洁”,一个女演员的胜出不在于演技出众,而在于是否“纯洁”,甚至是“青涩”。编导通过故事情节与女演员身份的叠加,直接为观众建构了一个符合这一心理需求的“纯洁”女性镜像——为了商业利润,打着“不俗”的广告,做着迎合社会低俗心理的行为。因此,这所谓的“史上最纯洁的爱情”,若是被评选为2010年度“最成功也最纯粹的商业广告”,可能更准确些,若没有这样成功的广告,大概上座率就保证不了现在这么高。
男权话语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诱导
电影改编者取消了小说原本具有的较多文化思考的特质,在保留原小说主体故事线索的基础上,以“史上最纯洁的爱情”定位,将该片拍成了一部青春偶像剧,导演说,要使“每个女人都想嫁老三,每个男人都想娶静秋”②。电影中的静秋,导演认为要“清纯可爱”,观众才会喜欢她,因此消解了小说中其思考叛逆的性格特点,使她“青涩”又柔顺,说话总是燕语莺声、温婉平和,还略带忧伤。而老三这个人物形象,就是一个完美版的白马王子:不仅高大英俊,帅气阳光,对爱人用情极深极专,而且还有一个位高权重的父亲,因此,在一个吃饱穿暖普遍尚有困难的时代,他能拿出大白兔奶糖、冰糖、泳衣等赠送给生活在困境中的静秋,并且帮助静秋在别人都下乡当知青时,能“留城、参工、任教”一路畅通,让她为此感激不尽。但细细想来,这样一个中国版的王子与灰姑娘的故事,也并不是那么美好。静秋形象的改变,看似美化,实则是为了迎合男权主义的幻想,是媚俗化的结果。静秋的“好运”,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对女性社会角色规范的一种诱导:只是因为有了老三的爱情,她才有了命运的逆转,因此,她理当以他的意志为意志,以他的命运为命运,“他哪里走,我哪里跟”。③这一陈腐的观念,消解了女性在爱情婚姻中所应恪守的独立自主的人格尊严,也失去了面对生活创痛时冷静承受的克制与理性:“天呀地呀,你不要带走他,风呀雨呀,你不要伤害他,我要变做山楂花,随他化作泥土,在这里安家。”④尤其是,这“最纯洁”的爱情似乎还确证了一个潜结构:美丽的女人就是男权社会的紧缺资源,其配置方式要符合权力秩序,拥有更高权力(政治、经济或文化)的男人就可以有更大的优越权。因此编导很干脆地删去了农村青年老二长林与老三同时爱上了静秋的情节,这不禁使人想到:若是老三没有了位高权重的司令员爸爸,甚至还有一位正在挨批斗的走资派妈妈,编导又会让他们的故事怎样发展呢?塑造这样的“好女人”形象,并将其定义为“每个男人都想娶的”,使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在这种强大的话语压力下,行为自觉不自觉地都以成为一个被接纳的“他者”为目标,把人生希望寄托在偶遇一个好男人的拯救,从而放弃自己的主体意识,女性的主体性、人格自由等现代观念就被不知不觉地消除了。“每个人都想的”人物形象,就这样通过大导演大片的传播,将男权话语内化为女性的行为准则,重新将女性纳入到被看的角色地位上,借着浪漫爱情的名义,通过人们的无意识认同,使这一秩序结构拥有了秩序的合法性,进一步导致了女性在大众文化生活中主体地位的丧失,使爱情就这样成为女性致命的诱惑,成为一个权色交易的符码,成为男性争夺地位财富成功的战利品。
虚构的历史幻像迎合观众的审美趣味
电影《山楂树之恋》在宣传中,也非常强调这是一个“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⑤真实的故事,将那逝去的历史也进行了极充分的商业利用。电影的背景画面,给人印象很深的就是水彩画一样的淡淡的、朦胧的灰绿色调,使整个画面清新又朦胧,烘托了一种凄婉优美的风格,很美、很怀旧,因此也就很时尚。苏联歌曲《山楂树之恋》是与其青春记忆相伴随的,电影《山楂树之恋》的编导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电影虽是历史题材,却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历史真实,而是在与历史真实“似与不似”之间的选择虚构后,以迎合当下观众的文化娱乐趣味,满足他们的情感和心理欲望为手段,以此换取巨额的商业利润,也正因为如此,导演才将原本与情节不太相关的“文化大革命”舞蹈大段地植入。编导将这一历史年代中的人与事陌生化、奇异化地展示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电影《山楂树之恋》以三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叙事背景,这个物质极度贫乏、精神极其压抑的年代中的人和事,很好地满足了当下观众的幸福感需求。虽然总体上来讲今天的生活是比过去好了很多,但也并不是特别富裕,而消费主义文化又四处泛滥,在这种社会背景中,这部极其贫乏压抑的电影,不知不觉地使许多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在今昔对比中,倍感今日生活的富足,得到平等轻松的满足,比如静秋尚须以自虐的方式“挣表现”的情节,不知使多少观众在惊叹的同时,又潜滋默长出多少幸福感来。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今社会,在商业意识的主导下,电影《山楂树之恋》的编导,无疑是以历史的外壳包装当代社会的人物关系和情感表达,在这看似温情脉脉的爱情童话中,老三和静秋的故事模型,其实就是一个以男性中心的“英雄救美、以身相报、义辞不受、生死相随”老掉牙的模式,但经过编导用淡而远的时代为故事中的人和事上妆之后,与权力、财富相关的一切都不再赤裸裸的,一切都似乎变得让人赏心悦目了——历史的展示方式,只是方便了导演在时尚安全的怀旧外壳下,更为“艺术”地表达现实题材原本不宜直接表现的社会心理。
注 释:
①②⑤参见电影《山楂树之恋》专题网页。
③④电影《山楂树之恋》的主题曲《他哪里走,我哪里跟》。
参考文献:
1.艾米:《山楂树之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
4.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文秘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