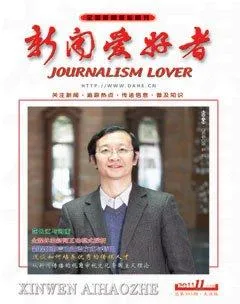从可接受性看喜剧小品的语用原则谢旭慧
现在的小品受众更多是通过电视(网络)而非剧场观赏小品的,相对于过去的剧场看戏,现在的受众具有分散性、个别性和随意性的特点。当代民众对喜剧小品的娱乐期待普遍较高,这种高期盼在其他形式的艺术门类中是不多见的。加之在南北地域、思想修养、文化水平、审美情趣、生活阅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决定了小品观众是难以应对的特殊受众。因此,小品创作要想获得比较满意的接受效果,只能努力去了解受众的接受需求,揣摩观者的接受心理,并不断获取受众的反馈,以调整改进创作的内容与形式。虽然受众千差万别,虽然小品艺术有其特殊的审美特点,但小品语用的一般标准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大众的可接受性”。所谓“大众”,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广大的老百姓,是与“小众”相对应的概念;所谓“可接受”,就是为大众所理解、所认可、所赏识。“可接受性”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是能听懂、可领会,这是对语言符号解读意义上的接受;二是不讨厌、不排斥,这是心理和情感上的接受;三是喜欢、钟爱、欣赏,这是精神和审美追求上的更高目标。喜剧小品要实现大众可接受性,我们认为必须遵循以下四个语用原则:
雅俗共赏
俗文化是指传统文化中来自民间的、大众的那部分文化。而“雅文化”向来有精英文化之称,是指以上层文化群体为主体、满足较高层次文化需要的文化内容,是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俗文化、外国文化中吸取的精华文化。喜剧小品是大众化的幽默艺术,属于俗文化的范畴。
作为俗文化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喜剧小品的“俗”应更多指向“通俗”。要实现大众可接受性这个标准,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小品语码解读意义上的接受。喜剧小品引起受众审美注意的首先是来自审美刺激较明显的幽默语言形式。由于对小品台词的解读更多依赖于语音听辨和语义理解,所以接受者的语音语义经验与舞台角色提供的声音表征、语义信息在多大程度上重合,决定了接受的质量。因此,台词编码过程中,语音、语调、词语等要素的运用一定要以清晰易懂、准确达意为基础,这是接受的前提。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见解独到:“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这种“俗”不等于庸俗、粗俗与低俗。20世纪末以来,伴随电子传媒和网络文化的普及,出现了一个俗文化大解放的时代。民间表达自由度的增大和感官欲望的嚣张,导致语言秩序的零散、语义所指的空洞、价值指向的混乱。喜剧小品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过分追求喜剧“笑果”,生编硬造、插科打诨、性暗示等种种庸俗化的倾向已成为当下小品语言的最大硬伤。当然,也不排除为求“雅”而过分强调“载道”功能,任意“拼凑”或随意“拔高”的现象,导致作品因缺乏戏剧性而难以吸引观众。
过雅,则曲高和寡;过俗,则难以致远。雅与俗之间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俗文化是雅文化的源泉,俗文化经过加工创作可以升格为雅文化。所以,我们在进行小品创作时,既要注意将雅文化因素与民间性融为一体,又要照顾到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尽力使作品既具教化功能,又不失却大众娱乐功能。
庄谐相融
幽默是“生活的不协调性的友善沉思及其艺术性的表达”。所谓“生活的不协调性的友善沉思”应该是幽默的理性特征,相当于美学概念的“庄”,是指作品的主题思想所体现的深刻的社会内容;而所谓“艺术性的表达”则更多体现为幽默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这种表现形式多半就是滑稽的、夸张的、荒诞的,相当于美学概念的“谐”。喜剧小品既需要积极的主题、深刻的立意这“庄”的一面,也离不开为反映主题、表现内容所运用的“谐”的“艺术性的表达”的一面。
幽默是喜剧小品语言的“生命”,是喜剧小品的质量标志,而幽默是需要适度的“庄严”来衬托的。所以,一定要注意把幽默与“油嘴滑舌”的“贫嘴”区别开来。鲁迅对“油嘴滑舌”就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