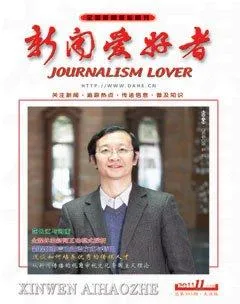《非诚勿扰》中的性别叙事探析
摘要: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里蕴涵着一个主角单一、层次明晰、戏剧冲突不断的故事,一个男人和24个女人的故事,主角是男生,配角是女生。在故事的演绎中,男生拥有最后的选择权与拒绝权,而女生则只拥有相对有限的拒绝权。看的主体永远是男性,而被看的客体永远是女性。
关键词:《非诚勿扰》性别叙事
江苏卫视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自2010年1月15日开播以来,影响日甚,长期雄踞周末收视冠军。据央视索福瑞71城市的收视率统计,《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一度达到4.53%,其他电视台的跟风效颦之作也层出不穷。分析其近两年以来风行不衰的原因,笔者认为这离不开制作团队所营造的音效、舞美氛围等,离不开主持人孟非的睿智博学、口才气场与现场调度能力以及乐嘉和黄菡的协助,也离不开男女生或业余或半专业的现场表现。笔者拟从性别意识形态的角度分主角与配角、选择与拒绝、看与被看等三方面来探析该节目中的性别叙事。
主角与配角
所谓叙事就是讲故事,人是唯一会讲故事的动物,叙事是人类一种获取生存意义甚至安身立命的本体性需要,故事因此也就成了人类“意义世界的基本成分之一”。①而所谓性别叙事就是从叙事中探究其中的性别意识形态,看其内里到底是男权思想还是女权思想。《非诚勿扰》表面上看是一档时髦的现代相亲节目,其实里边蕴涵着一个主角单一、层次明晰、戏剧冲突不断的故事,一个男人和24个女人的故事。与十年前的《玫瑰之约》《非常男女》等节目多对多的复杂混战风格迥然而异,男生是贯穿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和单一主角,而24位女生毫无悬念地沦为配角,在镜头时间的优势分配上再夺目的女生也无法望男生之项背。
《非诚勿扰》中故事演绎的几个阶段是:序曲是主持人和女生的亮相。叙事发生阶段是男生的上场,叙述契机就是男生上台自我介绍完后的心动女生选择。叙事发展阶段是随后人为设置各种矛盾与冲突的“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和“爱之终决选”等叙述环节。叙事高潮阶段是一个男生与三位(或两位)女生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并最后抉择,男生可能一往情深地“一根筋到底”,也可能审时度势地“移情别恋”。叙事结束是男性主角(或牵手或空手)离开时与众人的告别。尾声则是男性主角或一人或与牵手成功的女生两人一起(失败或幸福)的感言。
结局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是神奇还是平淡,都是围绕男嘉宾展开的。如果男生被女生中途全部熄灯而独自一人黯然退场,那就是一个中断了的故事,原因自然是男生实力不够或表现不佳。而最潇洒的结局是男生最后把三位(两位)女生请上场,经过交流对话后说全部不满意,鞠一个躬然后独自离开,把女生们尴尬地留在台上,如第114期的3号男生安田博士和第131期的3号男生郎波。观众则在或惊奇或扼腕的情绪状态中观看这么一个男性主角一上场就有多种发展可能性,然后不断现实化、具体化的故事。
在节目现场的空间布局上也可见出男女生的主次和中心边缘的区别来。现场的空间布局其实是一个扇形,24位女生均匀分布在扇沿上,而男生和主持人则站在扇轴轴心上,被24位女生和观众层层环绕,从而自然成为全场的聚焦点,他们在视线上也就能轻而易举控制全场。这种女生处在边缘(扇沿)男生站在中心(扇轴轴心)的布局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男主女次的角色分配与性别差异色彩来。
如果说心动女生环节与爱之初体验环节主要还是以貌取人的话,那随后的三段VCR其实是对男生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受教育程度、薪水财产和感情经历等社会实力的展示。最后有个环节是男生就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任选一项提问,这十项基本资料几乎全是男权社会对女性依附角色如贤妻良母、贤内助等的要求与规范,如三围、婚恋史、消费观、是否愿意和父母同住、是否愿意生孩子等。对男生的要求主要还是社会属性的物质保障为主,权责对等,这也符合几千年来男权社会的性别角色分配。
选择与拒绝
其实从故事一开始的男生出场及最后男生牵手一位女生离开就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男生应该主动选择、争取,女生应该被动等待、拒绝等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理念。比较一下男女嘉宾出场的背景音乐,《Can You Feel It》明显比《Girlfriend》要更具有雄性冲锋陷阵的征服色彩与阳刚意味。而在其后的故事演绎中,男生也是主动来表现与征服,而女生基本上就是安静地站在那里等待被审视与被挑选。
有人会说这其实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互动过程,再说女生还有特权呢!双向互动与选择当然没有错,但是在节目中选择的主动权始终在男生手中,女生只有被动拒绝的权利。如果一个女生对男生中意并留灯到最后,她有可能还没有上台就被男生灭灯,毫无主动争取之可能。而即使侥幸上台了,她还是只有1/3(或1/2)的机会。也就是说,女生要想与自己所中意的上场男生配对成功,自己只有“从一而终”,坚持留灯到最后才有1/24的可能性,如果自己开始不小心把灯灭了就不能再后悔了。而男生可以不“从一而终”,他可以在心动女生和其他亮灯的女生间随意选择,或者最后独自离开,当初的心动女生选择并不对他的最终牵手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而就拒绝的权利来说,男女生也是不对等的,特别表现在男生与心动女生的选择上。男生在权利反转后对女生拒绝的有效性是绝对的、一次性的,女生再不情愿也没有办法。但是,心动女生拒绝的有效性是成问题的,因为只要男生能够坚持闯过三关进入权利反转阶段,心动女生就会被再次请上台去,接受一个已经通过灭灯对其释放了拒绝信号的男生的最后纠缠,即回答男生问题与倾听最后表白。就已有节目的大致结果来说,90%以上的心动女生一般都是再次拒绝,但还是有百分之几的男生可能咸鱼翻生。也就是说,心动女生的拒绝要两次才生效,相比之下男生的拒绝权则是斩钉截铁的。总之,男生拥有最后的拒绝权、选择权与拍板权,而相对来说女生则没有主动选择权,而只拥有相对有限的拒绝权,这种选择权与拒绝权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与不平衡是非常明显的。
再说概率。24个女生之间其实是一种钩心斗角、争奇斗艳的竞争关系,而一个男生一上台就有24位女生在等他。就成功的概率而言,男女之间相差太悬殊,男生有24种可能,也就是24次机会,而女生呢,事实上一个女生一场就牵手成功的概率只有1/24。
1个男人和24个女人,表面上看是女生多,人多势众的样子。其实从文化符号学来看,文明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女性取代男性而标出”,男生是正项,是强势方、本色方,女生是异项,是弱势方、是妆饰方、标出方,女生的浓妆艳抹和伶牙俐齿都是一种“标出性”表现。正如拉康所言:“女性通过化妆,成为把‘无’的真实装饰在身上的存在。”②女生的刁钻古怪、尖酸刻薄甚至群起而攻之一般也不会破坏男强女弱的文化心理平衡。
看与被看
从精神分析学看来,影视文化正是利用了人类与生俱来的窥淫癖本能才在当代大众传媒中大行其道的。而电视因其是在更加私人化的空间中近距离地观看在特写比例上最接近真人的表演以及各种私密情感的暴露,故被誉为“所有大众传媒中最有窥淫癖的一种”。③但在一个由性别不平等和不平衡所安排的社会里,看的主体永远是男性,而被看的客体永远是女性,一如穆尔维所言:“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④男性把自己的欲望和幻想投射到女性身体上,女性则被迫客体化,不断指称男性的欲望,竭力迎合男人的视线。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性别是指文化性别和社会性别(gender),而非仅指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性别和生理性别(sex),那些没有性别意识和主体性的女性之看,其实是在已经内化与自然化了的男性思维主导下之男性观看。
这在《非诚勿扰》中也不可能例外。随着主持人孟非说:“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女生的“被看”就正式开始了。如果主办方让姐妹同台或让“高矮胖瘦”站一块儿还可以说是为环肥燕瘦的视觉效果而采取的差异化策略,那有段时间让母女齐上阵则纯粹是一个噱头了。反过来如果台上站着24位男士,那应该是一个女权色彩浓厚的节目,但其可看性就要大打折扣。因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生来是被看的,不管是从性别意识形态还是从其背后的理论支撑——精神结构来看,“男性人物不能承担性对象化的负荷”⑤,若要男性来替代女性成为被看的角色的话,我们只能说这种探索精神难能可贵,形式也新颖别致,但结局会以观众的逐渐流失和收视率的大幅滑坡而收场。
表面上看是24位女生同时观看与审视一位男生,其实她们在看的同时更是在被看。面向她们而站的男生、面向她们而坐的现场观众以及面向她们而设的替代电视观众观看的镜头等都是凝视她们的“眼睛”,而这些决定了整个节目的性质、形态与接受程度。同时24位女生的相对稳定也给了观众相对持久而愉悦地观看与窥视的机会。当初的叙述契机即男生“心动女生”的选择,其结果只有主持人、男生和电视观众知晓,24位女生则毫不知情,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大程度上已经无声无息地把电视观众置于一个双重窥视者的位置上了,这不但增强了观众与男性主角的角色认同感,而且无形中又增加了电视观众的心理优越感和窥视快感。
节目的奖励规定是男嘉宾在第一轮亮相获得22盏及以上的灯亮着,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都将获得一次夏威夷的浪漫之旅。这是节目对符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优秀男生的一种奖励,之所以不说是女生,是因为所奖励的女生对象具有非特指性,即不确定性甚至随意性。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女生处于一种无名的客体地位和被看状态。而从性别比例来说,台上孟非、乐嘉和男生共3男与24女,这也基本取得了性别比例的象征性平衡。一个男人对七、八个女人就是封建社会的性别比例平衡之要求,所以古代衡量成功男人的一项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拥有“三妻四妾”。而在中国数文化中,七往往是和女性联系在一起的命运之数,是“女性王国里的阳数”。⑥
至此,我们主要从主角与配角、选择与拒绝、看与被看等三方面就《非诚勿扰》的性别意识形态进行了具体而微的分析与探讨。该节目虽然表面上有着某种似是而非的女权色彩与女性话语权,但内里却有着相当浓厚且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其实只要我们运用相关的理论工具深入剖析,就能发现大众文化在娱乐化外衣下必然隐藏的意识形态内容,进而挑战和颠覆大众的常识,帮助人们弄清楚那些习以为常和天经地义的文化现象背后之权力真相与利益关联,使其明白“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⑦,最终为理性商谈意义上的公共文化空间之培育和建构提供某种理论上的方向性说明。
注 释:
①高小康:《人与故事》,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②赵毅衡:《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文艺理论研究》,2008(3)。
③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④⑤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载吴琼编《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第9页。
⑥吴慧颖:《中国数文化》,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76页。
⑦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作者为嘉应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