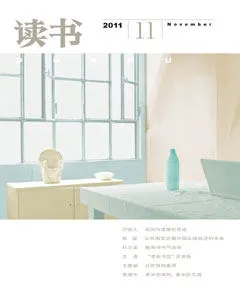理论的即物
怎样看待历史与政治?
迫使我追问这一问题的,是这些年艰难的写作实践。为了让自己的学术思考尽量避免生产伪问题,也为了在不脱离现实复杂性的前提下保持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张力,我尽量地写一些面对状况的分析性文字。与此同时,我要求自己尽可能不是仅仅做思想评论,而是在一时一地的具体分析中通过非直观的方式开放分析本身。这中间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效的分析要求理论能力,而这种理论能力却是大理论很难提供的。大理论正是因为它舍弃了具象问题的经验性,特别是舍弃了具象问题无法整合的内在矛盾与歧义,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逻辑一贯性,同时这也必然地使它所关心的问题集中于从各种不同经验中抽离出来的“一致性”或“同质性”。大理论之所以被认为是“普遍性的”,就与它的这种思维方式有关。
不能否认,大理论对于人类观念生活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它不仅追问那些最为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基于这种追问不断地为人类认知提供方向性启示。如果没有对大理论的理解力,任何形态的理论生产都会缺少自觉。但是,大理论的这种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它可以直接涵盖一切,特别是涵盖动态经验。在为人类的认知提供方向性启示的层面与对于具体经验进行理论判断的层面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它们不能相互取代。如何处理具体经验,我相信这是二十世纪语言学转向之后困扰着西方哲学家与思想家的根本问题,也是各种解构理论试图突破的困境。对于我们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人而言,还有一重更加棘手的困难,那就是如何生产切合自身历史经验的理论表述,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识传统。在此意义上,甚至什么是“经验”这个问题都显得有些可疑。为了有效地讨论这些问题,还必须清理一些相关的认识论误区,以期避免讨论走上歧途从而使得问题被消解掉。
第一个误区,我称之为“大理论帝国主义”。在第三世界的知识精英里面,它尤为明显。简言之,这一认识论误区因过分强调大理论的重要性并且贬低有质量的经验研究,已经造成了对大理论的膜拜。如果考虑到迄今为止的大理论生产基本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这种高度抽象后的理论又与普遍性画了等号,从而具有了不可动摇的权威性;那么可以进一步说,这样的思维定式暗含了某种“文化帝国主义”的特征。需要强调的是,指出这个认识论误区绝非意在否定大理论的功能,如上所述,大理论特有的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第三世界的知识精英把大理论抽象地定位为至高无上的标准,甚至把“反对文化本质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立场的时候,大理论的真实功能以及它的限度问题就被遮蔽了,这才是问题之所在。借用韩国思想家白乐晴的话说,它将导致的恶果是:第三世界的知识传统在不能得到第一世界知识界认可的情况下就无法形成。进一步,还有必要区别大理论与大叙事之间的差异。当今世界流行“宏大叙事”,这是使大理论具体化的一种实践。但并非所有的宏大叙事都成功,宏大叙事往往模仿了大理论的高度概括,却缺少大理论的内在紧张,因此它仅仅表现了尽可能涵盖多数事物的野心,却因为四平八稳而使得自己变得空洞无物。
第二个误区,是二元对立思维的绝对化。我称之为“对抗西方的误区”。由于理论生产特别是大理论的生产基本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导致了第三世界的一些知识分子以对抗的心态来处理本土的经验,生产完全与西方理论对抗的知识和理论。而在认识论领域,由于大理论帝国主义的负面效应,也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决定干脆放弃理论而用经验工作,以“实证”对抗“理论”。不仅如此,在知识生产领域内部,被通俗化了的二元对立感觉因为它的直观与简明易懂几乎构成一个无法被取代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远远超过了“东西方对立”这种具体的范畴,而成为一种知识习惯甚至前思考的条件反射。由于把“对立”理解为对抗和排斥,使人们在处理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时候易于使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进行反应,这一误区导致人们忽略历史过程中最为丰富的问题群,倾向于从两极出发去认识问题。
第三个误区,是对于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对立想象。它建立在前两个误区的基础上,即把理论设定为普适的和高层次的,把具体的个别性设定为理论的对立面,也就是无法具有普遍性的低层次表象,这就使得研究者往往急于寻找个别性状况中那些可以被抽象出来的要素,并且通过这种抽象建立与西方主流理论相对立或者相对应的第三世界知识立场。于是,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具体存在形式,抑或普遍性经历什么样的思维过程才能与个别性相区分等等问题,很难成为理论讨论的正面对象,它只是在似是而非的“共识”中被一笔带过。
必须承认,上述三个误区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误区,它们在特定历史阶段中曾经为认识论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营养,发挥过积极的功能。尤其对于第三世界知识精英而言,它们同时也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训练,使得人们相对顺利地与西方世界“接轨”和对话。但是,当历史不断运动、世界越来越一体化从而反倒使得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地域化的时候,人们开始发现,不仅后发达国家的知识是地域性的,发达国家的知识随着霸权意识的松动也越来越地域化了:当世界尚未一体化的时候,人们满足于了解相互之间那些类似性的地方,并借以进行沟通;更何况在西方霸权的扩展中,只有确认了与西方社会文化中关键环节(例如现代性)的一致性,才能为后发达地区带来知识的合法性。但是当世界一体化(哪怕是借助于资本的力量进行的)进程深入之后,人们就不再满足于从抽象的层面进行这种同质性的理解了,因为他们开始有能力发现,即使是在那些借助于霸权把自己的历史要素解释为人类共通性的“发达地区”,其知识与思想传统也受制于自己的历史,因此是地域性的。而经过了鹦鹉学舌阶段之后,所谓“后发达地区”的知识精英也开始不满足于用修正各种“进口理论”的方式工作,他们试图用更尊重自己历史的形式寻求有效的理解和解释。可以说,与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中充满矛盾对抗的一体化进程互为表里,认识层面的地域化趋势已同时在东西方的知识领域里悄然生长。于是,重新思考普遍性的含义,跨越直观的求同或存异趋势以期建立真正的相互理解,成为越来越现实的课题。用已经用烂了的话说就是,到了今天,“多元化”的问题才开始变得真实了。而多元化的需求,也必然暗含一个知识的进路,那就是从抽象的形而上论述转向历史。
可以说,当历史走到今天,当我们不再满足于把自己的历史分析套进西方的理论模式中去,以求获得第一世界认可的时候,上述三个曾经有效的思考维度才开始变成了误区。我之所以这样判断,是由于我们不能再满足于使用“同质性”的视野去处理异质性问题,这种肤浅的“普遍性”认知已经不再是有效的沟通手段,而所谓“反对文化本质主义”作为一种知识立场,它也仅仅能够对应那些粗浅直观的“本质主义”,基本上没有什么理论建设性。于是,麻烦也就来了。在今天这个霸权虽然存在却无法再维持一元格局的世界里,那些富有理论前景的个别性经验,只有在它拒绝一元性统合的时刻才可能具有原理性的价值。因此,仅仅依靠同质性的抽象无法创造多元化的原理,这才使得下面这个问题成为问题:以异质性为原理的理论必然拒绝同质性的抽象,它最可能的形态将是被特殊处理的经验本身。那么,“经验性理论”是否是可能的?如果是可能的,这将意味着它在超越一时一地具体经验的同时,并不舍弃经验特有的歧义性与个别性,它要以个别的方式成为“普适的”,也就是说,它不以追求同质性,而是以追求多样性乃至异质性的方式,完成它的普适化过程。
理论是否能够以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方式存在?理论是否可以“即物”?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设定理论只能体现为高度抽象的不即物形态,那么它就必须舍弃自身的歧义而最终走向趋同。因为只有具备趋同的特征,抽象才是有意义的。反之,如果试图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个难题从而使理论思考不再满足于从具有理论意义的个别性经验中抽取抽象命题,并且如果承认这种个别性经验的理论价值只能通过它的个别状态加以呈现,那么,理论与经验、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关系,就必须重新加以设定。显然,这不是一个通过发明几个新概念就可以解决的简单问题,它需要重新进行理论思考方向的调整。
促使我进行这样思考的契机,是我对沟口雄三先生的阅读。沟口通过对李卓吾的个案研究,触及到一个非常尖锐的理论问题:建立“形而下的理”,如何才是可能的?如果改成现代用语来表述,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种理论(特别是关于道德的和政治的)叙述,却又不使它失掉经验性与个别性?
借助于李卓吾有关“不容已”、“真空”、“童心”的特定论辩,尤其是他在这些论辩中体现的“不立论”的立场,沟口提出了这样的分析:
对他来说,本于形而下性质的存在的、人人普遍的客观实在之理,与其说是理,不如说是真空,它的确实性几乎同时就直接暴露着不确实性。
李卓吾的自然是人的自然,也就是所谓的“不能空”,是说不能以形而上的观念思辨来造型。他认为,把人的自然本性特定为不容已的孝悌,不外是观念的造型。换句话说,这是因“我”的观念才得以存在的被塑造的我,等于以“亡牛存人”的人使牛成为无的牛。他认为,以不被“我”所观念化的我,经过因“我”在而始在的我,达到非因“我”在之故而在的我,才是我的自然。它时而是欲望,时而是私。
沟口这些分析背后隐藏着的那个理论关怀,一直是困扰着我的基本课题意识。这个课题在沟口那里的表层含义是:从阳明学的“无”到李卓吾的“真空”,发生了一个对于“理”的阐释的结构性转换,“存人欲的理”突破了既成理概念的束缚,获得了方法论的确立,它意味着理(秩序)不再是先在的对人的规定性,相反,它只能是从个体的社会生活(按照李卓吾的说法就是“穿衣吃饭”)那里产生的结果。如果再结合十六世纪以来儒教向民间渗透这一历史过程加以理解的话,那么上述引文中李卓吾关于形而下性质的理、关于无法用形而上观念造型的自然的思考,就获得了思想史的具体意义:它意味着个体的欲望和“私”作为形而下之自然,具有了社会价值。
对于没有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训练的我而言,这个课题的表层含义是可望不可及的,但是它吸引我的理由却不在于它的内容本身。对我而言,沟口推进了一个关键的理论环节,那就是他借助于李卓吾特有的“穿衣吃饭作为人伦物理”的思想轨迹,建立了一个“不能空”的论述空间。
沟口这样论述李卓吾“穿衣吃饭”这一个别性视野的普遍性:
定理之所以成为“定”,是由于这个理被视为具有“一”的普遍性。……李卓吾则要从正面破除这个观念,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成佛者,成无佛可成之佛”,人人各自是本来佛,在这一点上,人人是普遍的,而在作为应成之佛的意义上,不是普遍的。……人本具有佛性(即理),在这一点上是普遍的,然而其发显则是个别多样的。所谓个别多样,换言之,是说人是各自作为人而活着的,各自作为人而活着是人的普遍性。
沟口在此颠覆了对普遍性的通俗理解。作为“应然”的“一”,亦即作为先在规定性的抽象定理,并不是普适的。对定理的普遍性进行颠覆,是因为它自上而下地规定了单一的秩序体系。对于李卓吾而言,对这套单一秩序体系的否定意味着自然法与治政观在原理上的转换,对于沟口雄三而言,对通俗的普适观念的颠覆则意味着打破直观的一元世界感觉或者二元对立观念,建立一个真正多样的思维空间。
我注意到沟口表述多元多样的“人人”所具有的普遍性格时,打破了追求同质性的惯性思维。首先,他否定了“应成之佛”具有普遍性的假定,这是易于理解的:今天,用“应该”去讨论历史将导致非历史的结果,在学界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特别是当“应该”的假设具有了某种“自上而下”性格的时候,它遭到历史的报复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已不必解释。但是沟口并不在这一层面止步。他进一步指出,“各自作为人而活着”,这才是人的普遍性。即使人人具有佛性是普遍的,这一普遍性也仅仅是相对于“应成之佛”而言才能成立,亦即人人具有佛性只有在否定单一的应成之佛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上,才是普遍的;但是指出人人具有佛性却不是重点,它仅仅提供一个讨论的起点。李卓吾说“发愿者,发佛佛各所欲为之愿,此千佛万佛之所不能同也。有佛而后有愿,佛同而愿各异”,这导致了沟口对于普遍性的讨论。他揭示了两个不同的普遍性维度:一个是人人具有佛性的那个同质的普遍性,一个是千佛万佛不能同的差异的普遍性。借助于李卓吾,沟口在这两个普遍性论述中建立了潜在的关联:同质性的普遍性,其自身不具有形态,是“真空”,换言之,它无法表述,因为当它被赋予形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成为应然,成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秩序;差异的普遍性才是普遍性的真实形态,它不但是千差万别的,而且“不能空”,具有实在的形而下内涵。因此,关于普遍性的论述,不应该建立在真空的同质性层面,而应该建立在“不能空”的异质性层面。
我就此联想到竹内好在《作为方法的亚洲》结尾的讨论。他提供了一个更容易理解的解释:人在类型上是等质的,文化的价值也是等质的。但是文化价值并非是浮在空中的,它通过渗透到人的内部才能获得现实性。显然,这个关于“等质”的论述就是李卓吾“人人具有佛性”论述的现代版本,它也同样体现了对立于“自上而下”(准确地说是“自西向东”)强制性秩序的平等意识,而强调文化价值渗透到人内部才具有现实性,也是在说文化需要通过个体的人加以个别性的体现,以个别的形态自我实现,否则它将无法直接呈现自身。竹内好关注的是近代西方通过武力把它的文化价值渗透到东方之后,东方如何处理这个外来价值内化的难题。他的态度是,东方必须以自己独特的主体性重新打造来自西方的价值,而不是直接把它视为普遍性。
沟口显然在更精致的认识论层面上推进了竹内好的问题。他揭示了普遍性只有在无法言说(即“空”)的意义上才是同质性的这一关键环节,换言之,任何一种可以言说(不能空)的理论都不能够以同质性的方式寻求普遍性;而可以言说的普遍性,却一定是多样的、异质的。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普遍性的感觉方式必须调整到体认异质性本身的层面上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立场的实现。
如果继续推进沟口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将遇到的理论困境是,以个别形态呈现的普遍性如何不被个别性局限,并且也不被形而上的同质性回收,它如何以个别的方式成为普遍的?
沟口并未直接讨论这个问题,他只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揭示了与竹内好在方向上一致的认识论:把中国作为方法,把世界作为目的。亦即对中国的研究不以中国本身为目的,而仅仅把它作为方法。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对于“方法”的解释,是强调它并非是实体的,说它是一个主体形成的过程。显然,如果把中国思想的历史视为一种个别性的话,它的普遍性只能体现为在非实体的意义上与世界相关,也就是说,它通过超越自身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这当然对所谓文化本质主义和直观的反本质主义同时构成了批判。沟口进一步说,把世界作为目的,是与把世界作为方法相对的。后者是把某种既定的“世界史”方法作为标准,以此衡量中国的历史,而长期以来,所谓世界史的方法,就是欧美的方法。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表面上似乎是“反本质主义”的,但为何受到沟口的强烈质疑?原因就在于它为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而以既定的西方标准衡量中国的相似性或者差异性,这实际上是一种被伪装了的一元论认识论,在现实中是与霸权关系共谋的。
从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和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中,我受到了一个启示:个别性以个别的方式成为普遍的,并不意味着它被抽象后转用于其他的个别性之中,也不意味着它超越自身去涵盖其他的个别性。事实上,如果把个别性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为普遍性的话,那么它并非借助于有形的同质性,亦即并非借助于内容或结构要素的类似性,能否沟通取决于个别性之间是否具有竹内好所说的“价值上的等质”。在充满了不平等与歧视的现代世界,真正造成沟通困难的并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的诚意。只要想一想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如何缺乏好奇心,而第三世界如何努力理解第一世界,今天通行的所谓“普遍性”的深层含义在于它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且往往是不平等的价值判断,这一点就不需要论证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论状况,沟口的李卓吾研究才具有了理论意义。他对于个别性本身的普遍性认知,特点在于拒绝把个别性抽象到那个无法具有形状的“价值上的等质”中去,而是固守着个别性本身,同时以价值上的等质这一平等的立场来开放这一固守。用沟口的话说,这个价值上的等质就是“作为目的的世界”,它本身不构成方法,亦即不构成衡量的直接标准。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认识论的倒转。这个倒转重新确认了普遍性的存在方式以及它与个别性的关系,使我们可以通过对个别性的深度阐释获得普遍性,而不是通过对个别性的舍弃抽象出普遍性。
对于普遍性与个别性的讨论,也同样适用于对理论和经验的讨论。理论在今天所以具有潜在的霸权,与它被语焉不详地赋予了普遍性价值有关。理论在追求同质性的过程中表现了使自己成为“方法”的意图,亦即使自己尽可能地涵盖经验的多样性,并通过对同质性的追求完成对单一体系性解释的建构。这造成了“大理论”的流行。似乎后结构主义理论扭转这一局面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今天的理论生产,表现了更强的实体性和直观性特征,对于经验的歧义性与多样性缺少必要的敏感和对应能力,更缺少理论生产者必备的对于经验的爱惜之情。
经验是个别的,当个别经验具备了超越它自身的要素时,它就具有了理论性格。但是,不通过抽象出同质性的方式把握这种要素,需要建立一个必要的认识论程序,这个程序必须打破直观的惰性,使个别经验的理论性转换为间接的认识论,而不是直接的抽象叙述。认识论是无法套用的,它只能通过个人的体悟转换为观察现实的能力与发现问题的能力。当沟口通过李卓吾强调“各自作为人而活着是人的497ac6697719c6e61577f96c7063c159普遍性”的时候,他并非在说个体的多样性与活着这一形而下事实本身是普遍的,而是在说当人们有能力在这一形而下事实的层面固守并拒绝通过抽象来赋予其意义的时候,他就将获得一种认识论,帮助他克服直观的以可视的事实为事实的论述,从而在形而下的经验中发现个别问题之间不可视的关联。我认为,揭示这种关联性应该视为即物性理论的重要工作之一,它在某些情况下是结构性的(例如沟口雄三的研究),在某些情况下则未必具有结构性(例如丸山真男的研究),本书在不同章节中分别讨论了这两种工作方式,并试图深化同一个问题60ee363495a1f6b8584732bd60a7ba57意识:个别性开放自身的重要标志,就是它与其他的个别性发生深度关联,并在这种关联中保持自身的个别性。在沟口雄三那里,这种深度关联的个别性通过完整的结构意识获得开放性,而在丸山真男那里,这种深度关联的个别性则通过非实体的动态分析环节获得开放性。
政治思想史作为经验研究,需要对于各种个别要素之间的关联进行理论想象。或许这种研究迫切需要即物性的理论,就是因为它必须对经验的丰富性不断提供新的解释,为经验打造新的形状,同时个别性经验之间的关联往往不是通过类似性而是通过差异性完成的,它们的关联也并非仅仅依靠逻辑就能够推导。这些工作绝非直观的方式可以胜任,因此这种经验研究不能仅仅凭借经验感觉来完成。同时由于经验研究特有的面对史料的性质,政治思想史的解释绝对不可能是自由随意的,它们必须经历“史料的反抗”,亦即充分尊重史料本身的逻辑(在此姑且不讨论史料本身的逻辑应该如何判断的问题,这涉及另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并不断在史料的冲击下对解释本身进行质疑与完善。正是在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过程中,理论的想象力才有可能真正“即物”,它呈现出的事物之间的关联性才不会被史料本身所推翻。
沟口对李卓吾的研究涉及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那就是李卓吾“不立论”的知识立场。这不是说李卓吾不使用概念、结论,或者说概念没有价值;而是说概念与结论对李卓吾而言并非是第一义的,他随时可以抛弃这些东西,绝不会以此安身立命。“以不依靠概念的方式使用概念”,并不是提倡概念的随意性,事实上,沟口在他的研究中也体现了这种不立论的知识态度,这并不妨碍他为了找到准确的概念一直摸索到晚年。这种知识态度强调的是,概念不可以成为“方法”,更不可以成为标准,它充其量不过是“得鱼忘筌”的那个“筌”,不能自我目的化。因此,仅仅在概念层面乃至仅仅就结论进行讨论,就政治思想史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所谓理论需要即物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与这个“不立论”的知识态度相关。这就是说,即物的理论一定要有自我相对化的能力,它只能不断通过概念方式把握事物的动态结构,并且不断对自己“挂一漏万”的宿命有清醒的自觉。因此,即物的理论一定要通过不断的调整甚至是自我否定来面对经验的“个别性”,在个别性中寻找开放个别性的契机,这也就导致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物的理论不一定具有理论的形态,但是同时它也不是经验的;因此,即物的理论是否可以独立地存在,就成为一个问题。显然,它很难作为一个自足的知识范畴自我确立,这也是导致它无法被正面讨论的原因,但是假如我们不愿意用粗浅的态度把知识分成理论的和经验的两种,并且不愿意在种种关于理论的误区中就范,那么显而易见,这个“不立论”的理论,可能提供意想不到的思考契机。
(《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历史与政治》,孙歌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