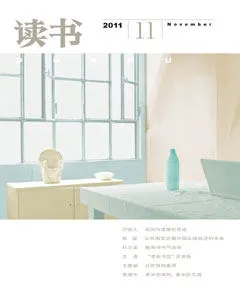千岁忧
一
生命中有一些特殊的情境,很难理解,但存在。
焚一炷香,决定开笔写文章是在夏日雨后。天净心也净,想着开笔,居然好半天就凝神看那炷香烧下去。袅袅香烟翻卷中,想到川端康成。记得川端写过,在修行僧的“冰一般透明的”世界里,燃烧线香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房子着了火;落下灰烬的响动,听起来如同电击雷鸣。这样的感觉,在我们平常人通常只看成是文学式的夸张描述,但川端康成认为,在禅僧的世界,这“恐怕是真实的”。
川端在这里使用了“冰一般透明的”这个说法。这说法来源于芥川龙之介的遗书《给一个旧友的手记》。说来正是这份手记,给了川端理解这“冰一般透明的”世界一个契机:
所谓生活能力,其实不过是动物本能的异名罢了。我这个人也是一个动物。看来对食欲色都感到腻味,这是丧失动物的本能的反映。现今我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像冰一般透明的、又像病态一般神经质的世界。
也是在这份手记中,芥川提到了有名的“临终的眼”。他写道:
我什么时候能够毅然自杀呢?这是个疑问。唯有大自然比持有这种看法的我更美。也许你会笑我,既然热爱自然的美而又想要自杀,这样自相矛盾。然而,所谓自然的美,是在我“临终的眼”里映现出来的。
这些话很深。在生命的第四十五个秋天,我才真正理解这“冰一般透明的世界”的存在,才第一次感觉到人生“临终的眼”,直到此时,我才认识到芥川这里是在说,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美丽是连在一起的。二○○七年十一月初,在清华大学教师惯例的年度体检中,我被查出肺部出现五厘米大小的肿块,医生怀疑可能是肺癌,十一月十二日,在北京肿瘤医院做了肺局部切除手术,幸运的是肿块呈良性。从发现病状到手术到恢复身体,感觉就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又回到人世间。记得刚被诊断出肿块的时候,想到过很多可能性。比如最坏的可能是这块不到一年就长到五厘米的肿块是恶性的、并且已经扩散,那么我的生命大概只还有半年或者一年。如果那样,多年积累的“学问”哪怕成千上万,那时都会被归零,仿佛一棵想要成材的树,耐过许多风霜雨雪的磨炼,却突然将在雷电之中拦腰摧折。那一刻我深切意识到,生死之间只隔一层纸。死亡其实从来离我们都不远,它像影子,一直就跟着我们,并终有一天会吞噬我们每一个人。然而奇怪的是,想到这一切时,眼前的世界却变得非常美好。记得病中老友杨笑天到清华看我,我们坐在清华学堂前的长椅上说话,忽然就有几只麻雀飞落在脚前啄食。草木鸦雀,平时常见。但这蹦蹦跳跳的生命,和那绿茸茸的青草,在我眼中忽然闪出空前无法言说的美丽亮色。
多少个春秋在我们身边流过。世界如此美妙,但我们太匆忙,居然经常见却看不到。也许,只有直面死亡、直面生命脆弱的一面时,生命才有这种美丽的展现。
在直面死亡的瞬间,一个问题骤然升腾而起——我们脆弱而美丽的生命,如何才能获得永恒?时间与永恒,这与人类历史同样永久的问题,其实是生命自身携带的一份焦灼。
二
志贺旧都尽荒芜,
唯有山樱开若初。
最初接触这首和歌,是一九九一年的秋天。教我这首和歌的大学院先辈渡边指着后面“よみ人知らず”问我,中国是否也有这种署名?我回答说有。因为这署名直译就是“读者不详”,一部古老的歌集中出现这样的署名,我想当然就直接把它转换为“无名氏作”。当时我更在意的是日本人把和歌的作者称为“读者”,我想这反映了早期的和歌更多是先发乎吟咏,然后才记录为文字,中国古代《诗经》中的很多作品也是如此。然而那位大学院的先辈渡边却又反复说,这并不是真的无名氏的作品。那中间的缘故,是几年后读书才弄清楚的。
有生皆有死。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写道,四季循环尚有固定之序,死却毫无定规可循,死往往非自前来,而是由后逼至。尽管人皆知有死,不过总以为死是以后的事,不知死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悄然掩袭至前,一如远隔浅滩千里,潮水涨来,瞬间却已淹至脚边沙石。一句话,不期而至是死亡的特权。但是,命运也常常做出特殊的安排,让有些人预先知晓自己终期不远。那么,如果一个人,当他从属的集团彻底失败行将覆灭,他已经直面兵败如山倒的局面,觉悟到自己的生命也行将结束,剩下的只是不远的将来,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走完最后的过程。当他觉悟到自己命当如此,一切业已无法改变,此刻直面自己的死亡,他会想到什么?他会做些什么?他为什么想?为什么做?他最后的执著一念是什么?
有关这最后的执著一念,有一段难忘的故事。十二世纪末,在日本有过一场武士集团间的生死搏斗——源平之战。平氏本是殿前武士,曾满门公卿权倾朝野以至于视“非平氏者皆非人”。但当年战事发展到平氏从京都出逃的时节,平氏一族的将来已经山穷水尽,败相尽显。就在源氏家武士们身影已经出现在京城街头巷尾的时候,平氏军团中几个黑色影子竟然逆着溃军的人流而上,回到京都,来到歌人藤原俊成家的门前。
“我是平忠度”,来人喊着。藤原家的大门紧闭,兵荒马乱,谁家都怕乱兵趁火打劫。但平忠度毕竟是写短歌有名的歌人,所以听到来人报出名号,家主藤原俊成的心放下了一大半,叫家人打开关得死死的大门。门外站着的,果然是大将军平忠度。冒死回到京都的忠度,对着藤原俊成深深一礼说道:主上蒙尘,平家败走逃出京都,此后已经断无胜机,平家武士团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一样都在走向终结,只是自己还不知道这终结点在哪里而已。这一切都是命运决定的,自己有觉悟坦然接受。此番悄然潜回京都,只为了找到藤原俊成。他要把自己一生所撰写的诗作托付给他。因为忠度知道,俊成奉天皇敕命是新的和歌集的编撰者,只是因为战乱他尚未着手编撰工作。他期望俊成有朝一日编写歌集时,能收入自己的一首作品。那他今后不论永沉海底还是曝尸山野,今生今世都再无遗恨。说话间他从铠甲下取出自己的一百余首和歌,递给了俊成,然后上马紧了紧头盔的纽带,向西方骤驰而去,身后留下的,只是俊成凝望的身影。
《平家物语》描写这一段后写道:“此景不胜哀愁。”
让自己的作品能传诸久远,就是忠度临死前的最后一念。
几年后时局安定下来,藤原俊成开始编撰《千载集》。他既哀于已逝的忠度的一片诗心,又因忠度名在钦案,没有办法直接披露他的姓名,所以只好在忠度作品中选了一首和歌,并把作者标为“佚名”。这就是我当年学到的“志贺旧都尽荒芜”。知道忠度的故事后,我曾反复吟诵俊成所选的这首和歌。歌中选择了废都与樱花两个核心意象,把人世兴废与自然四季无情的循环放到一起,构成的鲜明对比很像是《诗经·黍稷》的境界,读来让人感慨人世荣华易逝,无常迅速。不枉忠度去冒死相会,俊成所选,的是佳作。
重要的在于忠度的选择,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选择。在我《日本民族研究》的课堂上,有一次一位同学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提问说:“为什么日本人死前都要写一首诗明志?这是从什么时代开始的?”当时我一下被问住了。我也很想知道那些临死的人,那些直面死亡的人,为什么要写下诗句来?后来再去日本,在书店特地买了中西进的《辞世之辞》。阅读这本书后我才知道,日本人死前写诗明志的传统,并不为古代日本所专美,因为这种方式原本自中国的文化。中西进举了很多中国古代的绝命诗做例说明之,并谈到朝鲜半岛也有很多这样的诗作。读了那本书我才了解,期望在自己生命的终结点上,借诗作让自己的信念超越死亡传诸久远,这种发想,正是东亚地区共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三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往今来人们一直面对的,是怎样超越死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东亚地区有着自己的思考。
所谓“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我们身边的世界,在古代中国人眼中,是一个“运转无息,天地密移”的世界,一个刚柔相推,阴阳相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生则必有死,一如万事万物无不在变换迁流。而能够依靠来超越死亡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文化与精神的不朽。
佛教文化传入之前,传统的中国人基本沿着两条路径试图超越生命的时间界限。一条是超越现实的升仙之路,成为神仙后就可以完全超越时间的束缚。历史上走这条路的人多得很。秦始皇遣方士入海觅仙药,魏晋的竹林之下也多有服食药石以求神仙者。惜乎“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尽管人们耳朵里听到过很多白日飞升的佳话,但仙人异界,毕竟成仙之事在现实中很难证明。另一条则是立足于现实世界,追求不朽的声名。一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叔孙豹所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依靠立德、立功、立言,人就可以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获得“虽久不废”永恒的精神生命而不朽。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超越生死的名声足以让人死而不亡。明白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孔子会说君子惧没世而名不称。
在古代中国,文章一直被看成是可以超越死亡的存在。与升仙相比,很明显这条路径更有可操作性。有了“虽久不废”的三种不朽,就有了超越生命局限性的可能。三不朽之中,与立德立功相比,立言所需要的条件最低。所以,文章之道,在古代的地位高得很。曹丕《典论》论之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操、曹植、曹丕这“三曹”是非常特殊的,他们执著文章之道,并均自有建树,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文字。这在历朝历代高官贵戚帝胄之门是少见的。我想期求声名不朽,或者正是他们热心进行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一个主观动因。而对于活在今天语境中多数的知识人,文章可能只是饭碗,是考勤表上的业绩,在他们的知识框架中,文章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已经很难建立起直接联系。
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尽管可能“虽久不朽”,但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这就是历史。尤其是德行事功,要传诸久远,都必须借助文字的力量。换句话说,是史学家的一支笔,决定一个人最终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历史的写作,因此在古代中国获得了非常特殊的位置。中国古代史学的高度发达,正可以从这一角度获得一种深层解读。王国维曾论及古代史家地位之尊崇,以为:“殷周以前史之尊卑虽不可考,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可见重视史学的传统由来已久。古代中国史学文化也极为发达,历史写作上有以董狐、南史为代表的不畏强御的史官直笔传统,思想方法上有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终极文化关怀,具体到历史编撰,著史者更秉承着“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傍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阴,校计毫厘”(司马光:《进书表》)的写作态度。在古代经史子集的知识体系中,史学仅次于经学,良有以也。
饶有意味的是,这份文化传统还扩而及于东亚全域。八世纪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刚刚略有小成,马上就编撰了《日本书纪》。此后陆续出现《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记》、《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等正史。进入幕府时代后,先要提到的是《吾妻镜》,写的是立脚于东日本的镰仓幕府的历史,书名“吾妻”,是古日语“东”的表音字,而《镜》则直接取于中国古代的“以史为镜”。这样的镜子还有《大镜》、《今镜》、《水镜》、《增镜》等很多面。再向后到德川历代将军的实录,日本的古代的历史可以说一直代不绝书。在朝鲜半岛,则先后出现了《三国史纪》以及《高丽史》和《李朝实录》。明代开始琉球王国在东亚舞台上崭露头角,也先后编撰了《中山世鉴》、《中山世谱》、《球阳》等历史著作。在越南则有《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这些历史著作的写作,很多是直接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参照的,甚至撰作的目的就来自于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追随。金富轼《进三国史记表》云:
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