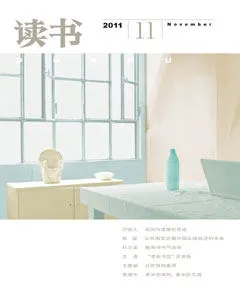哲
《说理》序言起首说:“这本书的主线是道理与说理的关系,道与言的关系。”其实,看似不酷的书名“说理”已暗自应和了这一主线,“说”和“理”合为说理,题目自己点题。序言末尾则引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篇幅极短的序言,引而不发,却已透出立意深远,立言无虚的心意。
并非很多年以前,中国曾有一个“全民哲学”的时期。身为哲学家,陈嘉映先生视之为不正常的时期。并非因为那时的“哲学”是错误或空洞的。在《梦想的中国》一文中他说:
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濯足的,容得下什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
与此相通,《说理》1.2节说“有多种方式达乎道”,“我们画画、下围棋、解牛、办实业、从政,也可能‘所好者道也’”。哲学的特异之处,是“哲学通过说理达乎道”。哲学和足球不大一样,哲学从头到尾都在言说,哲学和小说也不大一样,哲学从头到尾都在说理。可是,道理岂非人人都在说,那么人人都在做哲学了?也许人人都有一点做哲学的倾向,这一倾向却不止是说理,而是穷理。“什么道理初说起来都像是可以成个道理,稍加追究,却难免生出疑问,需要进一步澄清。这样从一个道理追向另一个道理,谓之穷理。所谓哲学,大致就是穷理。”(4页)
然而穷理求道的道却不是高高在上。“道甚至根本不在上,而就在我们的层面上,在各界之间融会贯通。”(15页)系统说理(穷理)的系统性不是建筑式的层级结构,仿佛各原理按其基本的程度层层搭建起来,而是网络式的相互交织。“网络没有开端。我相信,穷理必定是循环式的,而非线性的发展。”(38页)论理系统依托于生活世界的支撑。这种网络不是凌空而下的天网,而是大地的道路之网,地面的起伏、地层的结构、走于其上的人,都影响着道路的断续。
哲学与语言学
本文的目的是指出《说理》二至四章中的一条线索。《说理》本身是一个系统说理的网络,其中的线索是繁复且相互交织的,乃至作者曾考虑不分章只分节。即便是某一部分的主要线索,也无法“概括”其义旨。所谓线索,无非是提供一个看待的角度,一幅换步移行的景貌。
《说理》第二章的题目是《哲学为什么关注语言?》这问题是在语言转向的背景下提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一个重要的“转身”是区分事质研究和概念研究(语言研究)。这一区分又是在科学与哲学分野的大背景下做出的。“philosophia曾为一切知识的总称⋯⋯今天,哲学与科学各司其职。”(50页)粗略地说,科学是事质研究,哲学是概念研究。过去的形而上学往往把概念问题误会为事质问题,成了一种幻造的科学。
然而,语言转向也带来了一个疑问:“既然所谓哲学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语义问题,那么,哲学岂不是应当划归于语言学了?”(53页)今天的哲学只是做点语言分析(语法分析)?哲学如何区别于语言学?“语言转向引导我们更明确地把哲学与物理学区分开来,然而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怎么把哲学与语言学区分开来?”(54页)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非哲学家的问题——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曾对此做过揶揄——也是哲学家自己的问题,是语言转向后的哲学中始终在那儿的问题。
这个基本疑问是《说理》全书反复触及的一个核心之点。在我看来,尤其在二至四章(或许还可加上第五章),是一个主要的主题;当然,这个主题时而在高音区,时而在中音区,时而在低音区,与其他主题交织呼应。澄清这个疑问不是此书唯一的主题,也不是此书澄清“哲学是什么”时的唯一指向;欲把第五章《感觉与语言分析》归于这条线索时,我们觉得犹豫——这种犹豫刚好体现了此书自己指出的一点:“理解理解本身从来不是单独的目的,我们始终与理解世界联系在一起来理解理解。”这话反过来说也同样重要:理解世界始终牵扯到理解理解。(104页)“哲学是什么”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但绝非唯一的哲学问题,也绝非此书的唯一要旨。
穷理与达道
在这条线索中,第二章的地位是统领式的。此章直面哲学和语言之间关系的种种困惑,指明语言转向的一个根本之点在于“对象化之知”和“有我之知”的分野。这当然是从另一个角度解说“事质研究”和“概念研究”之分。语言转向突出了哲学并非对象化之知,但是若把哲学混同于语言学,从前门赶出的对象化之知就又从后门溜了回来。语言转向后的哲学重视语言,与语言学之研究语言,虽然颇有相似之处,也不乏重叠之处,但根本的取向不同——语言学恰是以对象化的方式研究语言。
哲学为何与语言纠缠不清?“有多种方式达乎道”,哲学通过穷理达乎道,但“通过穷理达乎道并非与其他种种达乎道的方式平行的一种方式,而是达乎道的高标特立的方式。因为道与言说紧密交织”(29页)。一方面,语言中凝结着人类对世界的根本理解,凝结着根本的道理;另一方面,哲学在说理时采用了论证的方式,而唯有语言能论证(54页)。陈先生接着说,“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但如何紧密相连?在这里我愿对此给出一点自己的解读。
在引人入胜的第七章《看法与论证》中,首先讨论了柏拉图《泰阿泰德篇》中提出的Episteme定义,英语一般将其译为“science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s”,即“知识是经过辩护的真看法、真定义”。这里的“justified”译的是“λóγο”,即Logos。陈先生指出,整句的更恰当译法是“哲学—科学是由说理—论证展示为真的深厚信念”。
或可说,真知是带有Logos的真看法。怎么叫“带有Logos”?把此句中的Logos译作“说理—论证”极富启发性。但若把这里的Logos理解为论证,那么自然的追问是:什么样的论证?当然,这是一个此书从各角度反复讨论的问题——厘清说理、论证、证据、事实、科学、哲学等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
哲学寻求并给出论证,但这论证却不是“证据—结论”模式,而是意在把网络连通。这连通不只是“自圆其说”,这网络不是自圆其说的任意网络。这连通是连回到我们的自然理解,或不如说,我们的自然理解本就是用以连通的道路。“语言中凝结着人类对世界的根本理解,凝结着根本的道理”,所谓“根本的道理”,并非就抽象程度而言。“在一个基本意义上,原理不是先于事物的源头,原理之为原理,在于事物通过原理互相联系。原理不是作为在上的概括提供统一性,而是作为居间的中介提供了统一性。”(29页)
这样,一方面语言中凝结了根本道理,即凝结了论证的道路,另一方面哲学以论证的方式说理。不妨说,哲学凭借语言中凝结的道理追索语言中凝结的道理。哲学的这种反身性特点意味着哲学关乎的总是有我之知,而非对象化之知。
哲学不只是语义分析
就我所知,“论理词”这一极富启发性的提法是陈先生的独创。《说理》的第四章首次集中讨论这一概念名下的诸问题。
所谓论理词,乃是用来论理的词。“仁、礼、道、物质、心灵、分析、综合、平等、自由、经验、体验、感觉、实在、真、符号、形式、本质、原因、理由,这些是典型的论理词。”(111页)一听到这些词,我们就知道现在是要说理了。少数论理词专为论理而设,如“先验”、“语言游戏”、“此在”等等;大多数论理词是从日常语词转化而来,如“平等”、“我”等等。就后一类论理词而言,谈论语词的“论理用法”更为恰当。
针对两类论理词,各有一个核心疑问。对于专门造出的论理词,我们要问:哲学家有没有权力发明新词?对于从日常语词转化而来的论理词,我们要问:语词的日常用法与其论理用法是不是同一个用法?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里有一句著名的话:“只要‘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个用法,它们的用法一定像‘桌子’、‘灯’、‘门’这些词一样卑微。”(PU,§97)的确,维特根斯坦在论理时竭力避免自造术语,而在谈及“语言”、“经验”、“世界”这些日常语言已有的词时,他亦竭力只去“描述”其用法,并说若描述得当,哲学中将不会有争论。他的这些说法和做法确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真的做到了吗?不这么做的哲学家真的就是在“speaking nonsense”吗?我们不也在比如海德格尔笔下领悟到不少道理吗?
维特根斯坦也发明了“语言游戏”、“生活形式”这样的概念,虽然这不是新造的词,只是新造的词组,但无疑是新造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只“描述”其用法呢?新造的概念还谈不上可供描述的稳定用法。另一方面,如本文已谈及的,维特根斯坦的“语法”与寻常意义上的“语法”不是一回事,他谈“语法”概念时,并非只在“描述”其用法。
通过具体考察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提法,陈先生颇令人信服地厘清了语词的日常用法和论理用法之间的关系。王阳明说“知行合一⋯⋯知行本体原来如此”,即“知行合一”是“知”的真义。这似乎应和了“哲学只是作语义分析”的断言。王阳明在论证时确实依赖“知行”的实际用法,但“知行”的实际用法却不只支持“知行合一”,也支持“知行不合一”,为何“知行合一”就是真义呢?但与其说这里关乎的是真义,不如说关乎的是道理,“这里出现的事情只是: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字的用法引申出不同的道理,有人引申出平俗的道理,有人引申出深刻的道理”(131页)。
哲学不只是作语义分析,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哲学中用的大多是论理词。论理词往往并无稳定的用法,在论理中往往是怎么说都不见得荒谬,端看你接着说的是什么,有没有说出什么洞见或道理;既无稳定的用法,又何谈“只是作语义分析”?若说某些论理词在某个哲学传统里有相对稳定的用法,那么回答是,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因为对论理词的“使用”多半是和对之的“考察”同时进行的。
在多年求索之后,在《说理》一书中,陈先生首次和盘托出自己的说理系统。这本书在他的著述中无疑是里程碑式的,里面包含了大量艰苦的思考。此前我曾在他的课上、文章里目睹许许多多闪光的瞬间,下意识地张开懒散的眼睛;此刻,这些闪光的东西汇拢到一起,我才渐渐辨认出他描绘的图景,仿佛第一次辨认出星座。
此刻我渐渐意识到,为什么他要去想这个或那个我不感兴趣的问题,背后的用意和难处是什么,而我感兴趣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叶公好龙。
这个说理系统当然不是什么独创的哲学理论(这件事现在已不可能),而是一个系统说理的网络。网络没有开端,也没有尽头,仍有许多我颇受启发的想法并未编织其中。对此我极为期待。至于这个时代还在多大程度上期待这样的系统说理,对我来说仍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