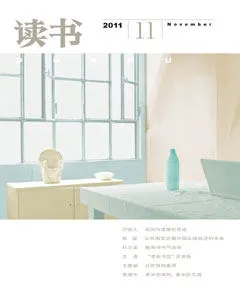用汉语写作好的哲学
陈嘉映在《说理》中把语言称作“一种最典型的实践”。单拎出这句话,听上去或许挺古怪的。首先,我们的直觉可能会被某些熟语说法吸引到相反的方向:比如一个人可以“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可以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事情“说来容易做来难”等等。这些说法似乎支持同一种直觉:说与做——更“理论”点说,“语言”与“实践”——直是两码事,而且,似乎说总比做来得省事。
这个简单的直觉背后布满了疑点。说与做总是两码事吗?说出了承诺,可不就是做出了承诺?说总比做来得轻易?承诺的履行的确难过一句轻飘飘的誓言;但要把我们在行止日用中默会的道理讲说明白,同样要求特别的能力。实际上,“说”与“做”会在若干不同的维度上形成错综交织的对照与联系。说出承诺与履行承诺,可以视作说与做的关系,但也不妨视作做与做的关系,两种具有内在关联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可能他 嗦嗦解释了半天,却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的解释。但我们不也说“他说了半天,什么也没说出来”吗?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一个要点就在于破除说与做的简单二分。八哥学话,却不会说话。要说得有内容、有意义,就要使说话具备行事的力量。
笼统地谈论“说”与“做”,难免空泛。以言行事与其他行事方式相比较,有何独特之处?明理与说理,道理与言说,为什么具有特别内在的联系?在何种意义上,对语言的反思有助于系统论理,乃至为后者所必需?在这些问题的若干紧要的关节点上,陈嘉映的《说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指示的路标。
在我看来,《说理》对实践与语言之辨的直接论述虽然不多,却构成了问题索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根据陈嘉映的洞察,实践与其他行事方式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实践的自治性上。“我们的各种实践活动,都含有自治的维度。”为了种树,我们挖个土坑,这不是实践。因为在挖坑这类事情上,没有什么既定的实践准则可供参照,坑要挖成什么样子,全由种什么树规定。把坑挖好,涉及技术,但不涉及规则。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诉诸词句来表达感情、讲故事、说道理,但这些词句本身从属于一个大的语言系统。抛开一门语言的既定语法,我们无从判断一个说法是否合用。种树要求挖坑,但挖坑不要求种树。语言却可以“造就自身的目的”。只有会说话的人才可能产生讲说一番道理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艺术、行医、政治都更类似于语言,应共同归属于“实践”的范畴。
从自治性理解实践、理解语言,这条思路并不新鲜。希腊语的praxis(实践)源于动词prassein(做),广义上可以指一切有目的的活动。但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已有了更为限定的意指。依照主流的解读,狭义的praxis特指目的内置于活动自身的人类活动,与只具有外在目的的poiesis(制作)相区别。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的任意性与自治性,维氏研究学界对这一论题的讨论可说汗牛充栋。但《说理》语法章对自治性的考察仍然新意迭出。陈嘉映的核心洞见体现在这一问题上:语言——广而言之,实践——是不是完全自治的?换言之,语言与实践的目的是否只由其内部的规则、规范决定?答案是否定的。实践活动的重要特性在于,其目的既不全在实践之外,也不全在实践之中。
游戏是完全自治的活动。“他游戏,因为他游戏。”(海德格尔语)我们下象棋,可以说是为了赢棋,但赢棋这个目的完全内置在象棋规则中。尽管可以为游戏附加上一些外部目的,比如为了赢钱而下棋,但这些目的与游戏的关系是纯然外在的,恰恰要把这类外部目的排除到下棋之外,我们才能充分体味下棋的意趣。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的自治,麦金太尔强调实践的自治,都喜欢举象棋为例,道理也就在这里。不过,陈嘉映指出,正因为游戏没有外部目的,以游戏范型来理解语言与实践,极有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门具有深厚传统的实践活动不单单从外置于这类活动的目的中汲取标准与意义,这是事情的一面;这类活动却也并非悠然飘游于我们的生活日用之外,这是事情的另一面。我们在行事中说话,以说话来行事,语言必须在最广阔的范围对现实做出应对,因此,语法不可能只是一套游戏规则。
维特根斯坦也常用工具比喻来讨论语言的自治性。陈嘉映注意到,在象棋范型与工具范型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张力。游戏排除了一切外部目的,让人“乐在其中”。相反,工具必须有用。“不管工具的构成有多复杂,它总受到其功用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更像一门复杂工具,而不像象棋。“合用使语法受到约束。”人类辨别颜色的能力大体相当,但各门语言的颜色词有很大差别。这个例子鲜明体现了语言的自治性,但不表明颜色词的设置是全然“任意”的。颜色词的设置仍要“为现实负责”:不是在与颜色的自然事实一一对应的意义上,而是在合用的意义上,即:适合于我们在生活日用中言说颜色,言说现实。“我们不能在符合意义上谈论语法的对错;我们谈论语法是否合宜。”
“语言是一种工具。”对这个命题已广有批评,不过在陈嘉映看来,很多情况下错不在这个命题,而是人们对工具理解得不够。“我们不仅制造工具,我们也被自己的工具塑造着。”在年深日久的实践传统中,工具逐渐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治性,不再是用以达成目的的纯粹外在手段。维特根斯坦认为形而上学错把“概念问题”当成了“事实问题”,而这个错误很大程度上源于忽视了语言的自治性。“物体是有广延的”,这曾经被视作对世界本质结构的描述,而维特根斯坦称之为语法命题,取决于我们对现象的陈述方式。为了凸显这层差别,维氏甚至把哲学直接定义为“语法性的考察”。
陈嘉映敏锐地指出,维特根斯坦的一系列重要表述中,语言的自治性被过分夸大了。为扭转形而上学的思考模式,这种夸大情有可原,不过也留下了诸多问题。语言的自治集中体现在语法规则上:一个说法是否合乎语法,完全由这门语言本身说了算。但哲学论理要求的不是说得合乎语法,而是说得合乎道理——尽管说理从不可撇开特定语言的语法。语言中蕴藏着广泛深厚的道理,但这些道理更主要地体现在语词的用法上,而非一般的语法规则上;正如棋理体现在怎么行棋上,而非象棋规则上。说话必须遵行语法,但远不止于遵行语法。在陈嘉映看来,与其把语言理解为遵行规则的活动,不如理解为“规则辖制的活动”。
语言并不是完全自治的。与下象棋时“盲目地”遵从象棋规则不同,我们对某种实践规范的遵行从来不是盲目的。一方面,行事的道理受到既有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行事方式的转变,理解的转变,也会促使我们修订既有的规则、约定。这样循环反复的结果,愈是在一门传统深厚的实践活动中,“道理与约定”就愈是难解难分地“交缠在一起”。陈嘉映指出,在人类的诸种精神建制中,语言实践的传统最为稳定,所涉范围最为广阔,正因为如此,语言中要这样说而不那样说,常常凝结着根本的道理。对道理的探索本身就要求我们不断地转向语言。
实践规范形成于各自分殊的文化传统中,但实践的人要应对的现实处境具有更为一般的共通性。哲学中的概念考察工作致力于从特定的语言规范中发掘一般的、普遍的道理,所要依赖的不仅是语言的自治性,而且更多是语言的互通性。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是对“哲学语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概念系统随语言而异”,但不同语言之间仍可以翻译沟通。“这是因为,语言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语言之外,有着一个共同的世界。”(陈嘉映:《分殊文化,共同世界》)或者,若干个可以共通的世界。陈嘉映提议,应一般地从“可翻译性”上来理解“普遍性”。没有一套普适语法,不过,我们仍可以借助特定的语言洞见一般的道理,说出一般的道理。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论理实践中,陈嘉映是一个先行者。如何用汉语写作好的哲学,《说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传统、规范的形成需要的是典范的力量,这一点陈嘉映多有强调;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也许有一天,哲学将以会说中国话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