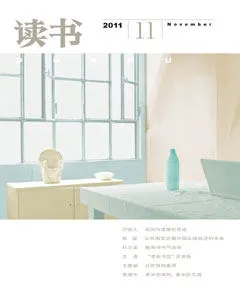赫德书信的流转
五十多年前,革命语境下的史学研究将近代来华西方人——除了极个别之外——做了公式化和脸谱化的处理,他们统统被打上“侵略者”或“殖民者”的印记,赫德(Sir Robert Hart)也不例外。近年来,“现代化理论”对“出身决定论”发起了挑战,有学者试图以更加超然的态度肯定近代西方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为其中一些人翻案,然而赫德不在其列。这个掌控近代中国海关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英国人,最终被认定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代理人”,这个历史结论甚至写进了中学课本。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视角与柯文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不谋而合,他们都试图剔除外国影响因素,在中国发现历史。近代来华西方人面临着一场新的末日审判,而决定其判决结果的正是他们在中国所作所为的客观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理论抑或“中国中心观”在跳出脸谱化窠臼的同时,也斩断了近代海关和西方列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似乎仍难以廓清海关史的全貌。
换一种维度来思考问题总是有利于接近历史真相。一直以来,我们很少问这样的问题——“帝国主义”是否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把赫德和他的海关当做自己的代理人?按照逻辑推理,西方史学视角下的赫德和中国海关将是一个与东方完全相反、积极而正面的形象。就像在中国所遭受的批评和指责一样,在英国,赫德和他的海关获得怎样的褒奖和赞誉都不足为怪。然而,近代中外关系以及英国政体内部的复杂性总是让这些简单的推论显得幼稚和可笑。
在近代中国,由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的中国海关始终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在大英帝国看来,海关并不是它的代理机构,驻在香港的殖民地总督、北京的驻华公使以及各地领事馆的外交官们才是维多利亚女王在大清帝国的合法代理人。海关,作为清政府、北洋政府乃至国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并不隶属于英帝国的任何政治机构,它被完全排斥在英国的政体之外。
让中国人感到耿耿于怀的,是外国人担任了中国政府机构的行政长官,这件事有伤中国国体。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人似乎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认为,一个英国人屈从清政府的法律和制度为中国政府服务,作为英国子民的他在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的同时是否还效忠于女王陛下,这是尤为值得怀疑的。中国人强调海关行政长官的外国背景,而英国人更看重海关行政机构的中国属性,这是造成近代中国海关处于两难境地的根本原因。
赫德的北爱尔兰身份是英国政界对他心存芥蒂的另一个因素。十九世纪,爱尔兰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在与英格兰势同水火般的斗争中,北爱尔兰人更是以不屈和英勇而著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生在北爱尔兰的赫德自然不可能得到以不列颠为核心的大英帝国的完全信任。
一九一一年,赫德和他曾生活了五十余年的大清帝国同时寿终正寝,西方媒体立刻开始品评赫德的是非功过。由在华西方人编辑出版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认为赫德最值得肯定之处在于:“他是中国政府最忠诚和忠实的奴仆,但与此同时,他也从来没有违背作为一个英国臣民对国家的忠诚!”这看似褒奖却又暗含讥讽的话语使中国海关的尴尬地位显露无遗。不过,这样的评论还算厚道,来自英国本土的声音则更加尖刻。《泰晤士报》批评说,“赫德在向清政府屈从方面变得过于熟练”,他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太长以至于看问题的视角已经完全中国化。曾在海关服务了十三年并担任过赫德私人秘书的布兰德(J.O.P.Bland)在回忆录中肯定了《泰晤士报》的评论,他承认赫德的工作作风是中国式的,独裁、专制并且任人唯亲,“中国是赫德觉得越来越舒适的精神家园,他对待中国人远没有对欧洲人那么严厉”。
赫德和他的海关游离在英国政体之外。在情感上,他们归属于大英帝国,但母国却并不接纳他们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在法律上,他们是中国政府的组成部分,但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无论清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在努力削弱或消除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赫德和他的海关既得不到中国人的认可,也得不到英国人的接受,他们只能在中外两种力量的对比中求平衡。在赫德的外甥梅乐和(Sir Frederick Maze)担任总税务司的时代(一九二九——一九四三),海关所面临的来自中外两个方向的张力达到了极点。
一九二九年,围绕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的竞争异常激烈。英国人易纨士(A. H. F. Edwards)是这个职位的热门人选,他得到了以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为代表的英国政府的支持,另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是日本政府极力推荐的岸本广吉,英日之间由此展开了争夺中国海关的角逐。此时的梅乐和已经年届六十,虽然具有多年的海关工作经验,不过由于他和赫德的亲属关系以及相同的北爱尔兰背景,梅乐和的形象和呼声都难与易纨士匹敌,英国政府甚至把他的出现看做是赫德大搞裙带关系的恶果。英国远东事务部的维克多·威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曾回忆说,英国使馆在反对梅乐和的过程中甚至使用了“很不得体的侮辱性语言”(Atkins,Informal Empire in C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