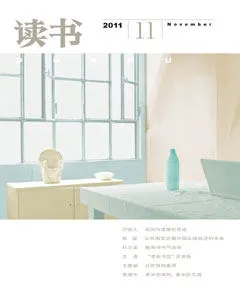杨公骥的学术风范
在中国学术界,杨公骥先生以其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卓越成就而享誉学林,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文学》(一九五七)、《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一九六二)等书,都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对象,论述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内在规律以及相关问题的。同时,杨先生的学术研究,又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文学史研究的范围,而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只要翻开《杨公骥文集》,就会发现,其中许多论题都深刻地涉及到哲学、史学、语言学、训诂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众多学科的广泛领域,并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科学精神、强烈的时代精神、深沉的使命意识,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今天,在杨先生九十周年诞辰之际,总结和弘扬其学术风范,对进一步推进学术事业的不断发展,显得具有特殊意义。
在先生晚年,我曾忝列门墙,在他指导下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得随诸位学长之后,亲聆先生教诲。耳提面命,春风化雨,使我略知门径,受益无穷。今天,纪念先生之业绩,缅怀先生之风范,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内心充满感恩之情。仅就管见所及,略述所知。
坚定的思想信念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家中,杨公骥学者的风范独树一帜。坚定的思想信念,使他的学术研究能够高屋建瓴、睿智透辟,显示出深刻的理论思辨性。他早年投身革命,即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困难,不管是在战争年代延安窑洞的油灯下,还是在动乱时期长白山区的火炕上,都从没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探索和思考。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是与他对民族命运、人类发展的深切思考紧紧联在一起的。他在一九五一年写出《中国文学》讲义第三稿,曾受到教育部的表扬,被认为“广泛地掌握资料”,“有创见,并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处理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通知》)。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里,杨公骥始终坚持从中国社会和人们的物质生活出发,以社会存在为基础,来分析研究由此而形成的精神生活,探讨民族精神生活的共性和个性,进而揭示不同文化形态(特别是文学艺术)的联系、过程和规律。
当一种思想学说跃居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达到指导性的精神地位,在其错综复杂的精神现象之下,在社会物质生活的深层基础中,一定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成功确立,及其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恰好印证了这一规律。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学说又必须时刻保持清醒,避免任何有意或无意、善意或恶意的教条化,以致脱离了物质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根本走向,变成一种不切实际的精神幻影。在这里,“实事求是”无疑是最能体现中国民族智慧的不可或缺的引导和启迪。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学贯中西的钱锺书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演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我只讲我认为最可注意的两点。”“第一点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否定事实和证据,反对‘考据癖’并非否定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第二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理论。”在过去,“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就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也无可讳言,偏重资料的搜讨,而把理论的分析和批判放在次要地位。应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就改变了解放前这种‘可怜的、缺乏思想的’状态”。钱锺书所指出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文学这两点特征,在杨公骥的学术研究中极为鲜明地体现出来。他始终注重全面系统的资料搜集、建立扎实可靠的理论依据,但反对为材料而材料、为考据而考据;他始终坚持在坚实广泛的资料基础上,融会贯通地认识历史,发掘规律,从而提炼出独特的思想,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杨公骥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解决中国文学、历史、文化的相关问题,但却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标签化、教条化的做法。他反复强调:“对于古代文学,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以分析与综合,经过科学推论得出理论性认识。但理论只能表现为研究的结果,并不可以作为研究的前提。今日的观念,只可用来分析古人,而不可赋予古人。因此,不可把今天的一些标签语超时间、超空间地加在古代作品上面。”“古云:‘金针度人’,我们主要是要学习马克思的‘针法’,从事新的创造,而不是把马克思制作的‘外衣’披在身上。这就是说,要做马克思主义式的生产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条文的消费者。”强调理论精髓的把握和科学方法的运用,反对皮毛式的作业,对教条主义保持清醒的警觉,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耐人寻味、富于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的。
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深层次把握,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从不同范围、不同门类、不同程度上,探究和揭示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深层特质和内在规律。空洞的理论是苍白的,失去了与现实世界紧密联系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是,人们对于空洞理论的排拒,不应该成为轻视基于千百年社会实践而形成的思想智慧和思辨能力、放弃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进行综合性、宏观性理论认识和把握的借口。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正是深刻的理论思维的水平和能力,成为杨公骥突出的学术个性。傅道彬先生指出:“在二十世纪最有成就的学者行列中,⋯⋯无不受到了新的学术思潮和理论的影响,无不具有学术方法的创新,比起新资料的发现,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更刺激了一个时代的学术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杨公骥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坚实厚重的文献考据,更有超乎常人的理论见识和思想洞察力。”在杨公骥的学术研究中,既显示出学者的丰厚底蕴,也呈现出思想家的睿智风采,他基于坚实的思想信念而展现出来的深邃的理论思辨性和思想洞察力,成为其学术风范的最鲜明的标志。
广阔的学术视野
杨公骥幼承祖训:“不博则不能通,不通则不能精”,“不通百经,不能专一经”。早在中学学习时,就曾阅读过有关天文、历史、经济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民俗学、考古、语言学的许多著作或译文,从而为毕生治学打下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及至投身革命事业,客观上所面临的环境,主观上所思考的问题,都远非某个单一的具体学科所能应对和解决。所以他涉猎和研究 都非常广泛,具有众多学科的渊博知识,并能够融会贯通,深入发掘,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系统理论。
虽然杨公骥以中国文学史家称誉学林,但他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中,都提出了独到见解,做出了重要建树。这当然是由其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志趣所致,但同时更是出于对时代使命的自觉担当。如在历史学方面,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性质的研究;在考古学方面,对东北地区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在语言学哲学方面,对汉语词根孳生及其所涉及的重要的认识论问题的梳理;在民俗学方面,对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及风俗的揭示;在民族学方面,对西藏古代历史发展的寻索等等,无不显示出广阔的学术视野,达到了融会贯通、博大精深的境界。一九四八年,他在艰苦条件下主持发掘吉林西团山史前文化遗址,并亲自撰写了《西团山史前文化遗址初步发掘报告》。其中为了说明族属,公布了西团山人的头骨示数;同时,将发掘出的与古代黄河流域陶器同形制的陶鼎支撑图版予以公布。这是在东北地区发掘或公布的第一个完整陶鼎,显示出高度的学术水平。对此,郭沫若先生曾予以高度评价。他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给《东北日报》的信中写道:“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性的文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