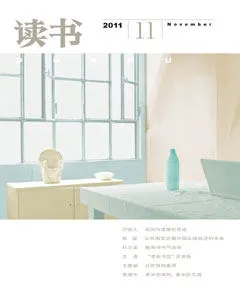从苏南变迁看中国区域经济的未来
三十年来,关于苏南的研究、宣传和讨论,有过四次高潮。
第一次是一九八五年前后,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费孝通先生将前店后厂、专业市场以及小城镇建设等特点归纳为苏南模式,引起理论界的极大兴趣;第二次是一九九五年十四届六中全会前后,全国都到苏南、张家港去取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时,江苏官方对苏南模式做了概括,叫“三为主两协调”,公有制为主、乡镇企业为主、加工业为主;物质精神协调发展、城市乡村协调发展。像现在的红色旅游一样,当时苏南各地都有一些参观学习的景点;第三次是一九九八年“十五大”之后,关于苏南模式的大讨论,这次讨论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之下进行的,理论界自然将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联系在了一起。那次讨论,笔者《苏南模式的终结》是一个焦点。最近的一次讨论是在二○○六年,有重庆官员评价苏州的发展是只长骨头不长肉,说苏州的发展,GDP数字很高,但是留给当地老百姓的收入不多,而且没有自己的品牌。这种说法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也引起讨论,新浪网曾有一组置顶文章——《贫困的苏州》。
苏南经济发展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域经济现象,对其进行关注是应该的。不过,关于苏南模式的争论,已经是一个过去时,我们可以不再去关注它。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苏南问题。我本人曾被称为苏南模式的终结者,但其实我只是一个苏南问题的观察者、研究者。我对各种各样的模式存有本能的警惕和抵触。如同有人热衷于“中国模式”一样,所有理想主义者们都是喜欢在现实世界里编织一个框,盛放自己的理想。但我认为,大而化之的抽象概括代替不了对现实问题的具体分析。多年来,我们始终有着极高级的“主义”和“模式”,但却面对着极低级的问题,一个模式一经提出便马上褪色,我不完全同意孙立平基于东北现实对社会断裂所做出的判断,也不完全同意李昌平基于中西部现实关于“三农”问题的观点,但我相信他们讲的是真问题,在他们的真问题面前,“模式”的灯笼一戳就破。我想,这也是我对苏南问题一偏之见的一点价值,而且,苏南是中国经济的先发地区,这里的问题更加带有趋势线、苗头性。
苏南有它独特的区位优势,这里原来就有浓厚的工商业传统。有些学者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写的文章把乡镇企业分析得玄而又玄,还用上了数学公式,真是没必要。实际上,乡镇企业只不过是近代苏南民族工商业的一个复活而已,它是近现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而且有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只不过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打断了这个进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恢复和延续而已。乡镇企业骨干人员的组成,很多都是近代民族工商业者的后人,他们精于算计,长于工副业。在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以一种“能人”的形式存在于“五小三就地”(小钢铁厂、小水泥厂、小农机厂、小化肥厂、小煤矿,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之中,改革的春风一刮来,他们就成了乡镇企业家。
那么,乡镇企业为什么后来戛然而止?“十五大”以后的改制是一个方面,因为改制后的乡镇企业已经不是《乡镇企业法》意义上的乡镇企业了,只能是一般意义的中小企业(现在虽然《乡镇企业法》仍然存在,但它是一部非常滞后的法)。但导致乡镇企业消失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乡镇企业是农村的工业化,或者说在农村里搞工业。就是农民们利用自己多余的土地,如生产队的场部、社队小型工副业的厂地,甚至是荒地、耕地发展起工业。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用地、征地由国家垄断,严格审批,原来比较宽松的农村集体土地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农民缺乏了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自由,农村工业化进程可以说已经结束了,乡镇企业也就自然消失了。那么这些企业到哪里去了呢?九十年代之后,它们与外资企业一道集中起来了,进入了各类开发区、高新区。所以,苏南现在是园区经济为主,园区经济在苏南经济当中占了很大位置。在这一点上苏南和浙江也可以做点比较。浙江曾有十分普遍和发达的各类专业市场,但除了义乌小商品市场之外,像永嘉桥头堡纽扣市场等等,多数专业市场已经消失。这些市场都到了互联网上。阿里巴巴就是浙江现代版的集大成式的专业市场。有人曾经发问:阿里巴巴为什么没有产生于上海?其实,这个道理就如同义乌小商品市场只能产生于义乌一样。它们的共同基础是浙江十分发达的中小企业。
从制度上分析,园区经济与乡镇企业一样,它也是由政府来推动的。一些学者在分析乡镇企业的时候,用了一个概念,叫“社区政府公司主义”。这个概念是美国华裔学者戴慕珍研究中国乡镇企业的时候所用的一个概念,是从美国的“城市政府公司主义”那儿借用来的。美国的城市管理中有一种叫经理制的方式。城市的市长是选出来的,但叫经理,不叫市长,就像职业经理人。戴慕珍在研究乡镇企业及其社区关系的时候,借鉴了这样一种体制。这个词在解释中小企业的社区背景时的确有某种解释力。
但戴慕珍所不了解的是,“社区政府公司主义”到了中国,到了苏南,就变成了“干部资本主义”。南橘北枳,叶徒相似,味大不同。“政府公司主义”的叶下,结出了“干部资本主义”的果实。可惜,我们的一些学者,看不到这一层,至今还在生搬硬套。其实,仔细分析,“社区政府公司主义”根本不是把社区当公司来经营,而是以干部为主体来搞市场经济。当然,进一步分析,“干部资本主义”在苏南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苏南的民间工副业基础较好,经济重心历来较低,发展主体主要在乡村这个层级。近代以来,苏南保留了比较完善的乡绅精英自治传统,虽然乡村这一级把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功能始终混合在一起,但自治和共治的色彩十分明显,超越于民间自治的外来权力并不是一个经常性的存在。但人民公社之后,情势有了彻底的改变,干部得到自上而下的授权,所谓“社会管理”,变成了一些人管理,另一些人被管理;所谓“经济发展”,变成了一些人发展,另一些人被发展。这种独特的治理和发展结构,其结果就形成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干部资本主义”。源自苏南的“吴文化”又是一个特别强调秩序的文化,这种干群二元关系越来越深深地固化,且历久弥新,当碰到市场经济的时候,这样的社会结构始终无法形成平等的市场主体,只能是干部配置资源、干部发财优先的“干部资本主义”。
只有成为干部才能攫取更多的收入,这就是“干部资本主义”的危险所在。不正常正在变成正常。这个“道理”和“规则”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意识形态,老百姓认为干部就应该多拿。当官就是发财,老百姓绝对相信这个。全国的公务员考试是趋之若鹜,而在苏南尤甚。这就导致体制性腐败的更加蔓延和世俗化。所以,如果说要从制度上判断“苏南模式”内部的所谓核心机制的话,需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要轻易地拿“社区政府公司主义”这些所谓“学术概念”敷衍了事。这也就是我对苏南——中国市场经济发达地区所出现的趋势线、苗头性问题的担忧。
除了制度变革中出现的“干部资本主义”问题之外,苏南目前还面临着都市化问题、人口结构问题、生态问题。
都市化问题 “十二五”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像苏南和整个“长三角”这样的“熟地”,区域优势十分明显,搞小城镇建设和城镇化实在是严重的浪费。应当纠正以往过于分散的满天星的发展,进行区域优化和集中。发展大都市、都市圈、城市群应当是这一地区未来城市化的新的战略选择。步行和人力船交通的时代是小集镇,自行车时代是小城镇,汽车时代是大中城市,随着汽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迅猛发展便出现了都市圈。以现在的交通网络而言,一个以上海为核心的都市圈已经瓜熟蒂落,挡也挡不住。至于这个都市圈叫“长三角经济区”也罢,叫“大上海经济区”也罢,叫“泛长三角经济区”也罢,其实质就是以现代交通支撑起来的大市场。一九八三年,费孝通先生在江苏写下了著名的文章——《小城镇大问题》,自此,“长三角”尤其苏南地区掀起了近二十年的小城镇建设热潮。今天回过头来看,小城镇建设是和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相适应的,但事实上这是城市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农村工业的最终出路还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并进。也许在乡村工业发展的早期,小城镇的出现有其合理性,但后来,长时间内广泛铺开的具有浓重政府行为的小城镇建设,不仅耽搁了“长三角”这块熟地的城市化和都市圈化的进程,而且也造成大量的土地浪费和基础设施浪费。
人口结构问题苏南和“长三角”人口承载压力大,人地矛盾突出,但可以通过都市化来解决,现在更重要的是人口的结构性矛盾。现有的社会管理制度下,当地人口和外地人口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形成了有别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当地人与外地人的“新二元结构”。苏南和“长三角”的都市化需要移民,也理应吸收更多外来人口。社会保障、户籍制度等制度改革跟不上,当地人和外来人口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形成一股子怨气。尤其到了打工者第二代,这些小孩一出生就受到种种歧视,对社会产生仇恨心理。苏南乡镇企业里曾有明显的干群关系,而干部后来都通过企业纳税贡献换来的户籍指标转成了城市户口,所以,乡镇企业内部的干群二元实际是城乡二元的延伸,二○○○年前后乡镇企业改制,干群关系又变成了劳资关系,干部成资方,群众成了劳方。如今社区内部的城乡、干群、劳资等矛盾统统居于次要矛盾,而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生态问题苏南的优化开发,绝不是无序开发,而是严格生态保护下的开发。苏南传统的理念是先发展、后治理,但已带来不可逆的严重后果。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那种分散发展的方式带来了生态灾难。江南水乡普遍的水质性缺水。水很多,但都是臭水、受污染的水。二○○八年前后的太湖蓝藻现象令全世界震惊。什么原因?一、苏南至今都有强制性种粮指标,但经济效益十分低下,尤为糟糕的是,大量的化肥农药通过农田灌溉系统注入太湖,水质变坏;二、太湖平原大大小小的河流如同太湖的毛细血管,形成了太湖与西侧荆溪、北面长江、东面大海的交换,太湖原本是一个会呼吸的湖,但后来这些毛细血管通过小城镇建设和大办乡镇企业多数都填埋了,太湖变成了一个死湖。现在,苏南的很多产业又向苏北转移,苏北的很多河流包括淮河、泗水河等也开始污染。南水北调的东线,就是要通过苏北的这几条河,到时候调到北京来的水能不能用,也是问题。
应当说,上述三个问题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都带有前沿性、趋势性。苏南现在面临的问题或许是未来中国其他区域即将要面临的问题。